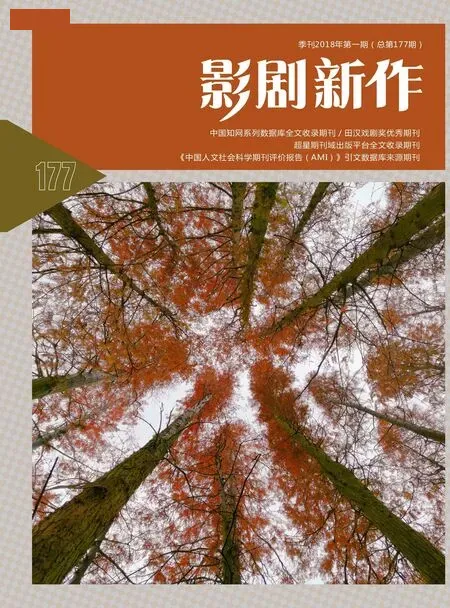《汤学探胜》前言
2018-01-24沈达人
沈达人
龚重谟从海南郑重地寄来他的大作《汤学探胜》打印稿,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我参加过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的编写与修订。由于工作需要,阅读了汤显祖的剧作和诗文,但是不等于读懂了汤显祖。重谟惠赐的《汤学探胜》,激起了我极大兴趣,希望读后能更加接近汤显祖。读了全书,果然大有收获,使我对汤显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有了为《汤学探胜》写前言的依据。
首先,重谟的大作犹如“汤学”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为关注“汤学”者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情况。汤氏的家世、生平、著作,尤其是他的“临川四梦”,都可从书中得到较多的了解。这也显示了作者研修汤氏诸作的扎实功底。
沈达人
其二,作者在论述作为政治家的汤显祖的一些篇章中,涉及文艺、戏剧创作的一个非偶然性现象,即《作为政治家的汤显祖》一文中所说“官场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在剧场演绎着百态人生”。政治的失落,成全了其戏曲的伟业。汤显祖“本来是务政”的,志在“做贤臣良吏,拯救世风”。没想到在官场“沉浮了28年”,终未能实现“变化天下”的宏愿,最后只能“弃官归隐”,把“胸中块垒”“发而为辞曲”。
其实,不仅明代的汤显祖有这样的遭遇,往前看,元代的杂剧作家同样有这样的遭遇,其中以元杂剧的奠基人关汉卿最有代表性。钟嗣成的《录鬼簿》说:“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户。号已斋叟。”朱经的《青楼集·序》说:“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钟嗣成、朱经都是元代人,他们说关汉卿是“金之遗民”,入元后“不屑仕进”,只是个“太医院户”,转而从事杂剧创作,可信度应该是很大的。可知关汉卿在金末元初北杂剧形成期间开始杂剧创作,到元朝大德年间,总共编成了60多个杂剧剧本(天一阁本《录鬼簿》收录62种)。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达到极高成就。他把自己胸中的强烈爱憎化为奔腾的激情,歌颂了一些代表着正义力量的被压迫者、被戕害者,鞭挞了蒙古贵族、皇亲国戚、贪官污吏、衙内恶少、地痞流氓等元代社会的恶势力。而且以正义力量终于取得胜利,宣告了传统的社会理想、道德文明的不可湮灭。
往后看,明末清初的“苏州派”传奇作家也不例外。以他们的代表人物李玉来说,于明末崇祯年间考中副榜举人,在明朝覆亡后“绝意仕进”,致力于戏剧创作。其作剧约40种,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驰名,《万民安》《清忠谱》歌颂了明代后期的市民运动。他的传奇作品在当时剧坛传唱极盛,作者也因此颇负盛名。李玉的生平与创作再一次印证“政治上的失意,成全了戏曲的伟业”,确是大多数古代戏曲作者生平遭遇的现实性问题。
其三,《汤学探胜》对汤显祖的交游也作了有意义的探讨。比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贽是否来临川与汤显祖会见。重谟认真研究后,在《汤显祖和李贽未曾在临川相会》一文中认定,李贽来临川与汤显祖会见一事“诚为子虚乌有”。根据是:一,2005年问世的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叙述,万历二十七年全年,李贽寓居南京永庆寺,“每月都有可考的活动踪迹”。此外,1957年出版的容肇祖《李贽年谱》也明确记载,万历二十七年,李贽住在南京的“永庆禅室”。是年冬,山东河漕总督刘东星召李贽赴济宁。当时李贽已是73岁的古稀老人,故而复信其子刘用相(字肖川)说,“此时尚大寒,老人安敢出门”“自十月到今,与弱侯(焦竑)刻夜读《易》”。李贽整整一年未离开南京。二,如果万历二十七年李贽与汤显祖在临川会见,李贽是汤显祖“心目中所崇拜的一‘杰’,不能两人都没有诗文记述”。所以“李贽与汤显祖只是神交,始终没有见过面”。这样的探讨不仅有意义,而且有必要,以免引起误读。
再如汤显祖与邓渼的“忘年至交”。1992年出版的黄芝冈先生的《汤显祖编年评传》,提及邓渼两次到临川拜访汤显祖。指出邓渼是“新城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除浦江县知县”;万历二十七年“调秀水县知县”;万历二十九年,秀水县令邓渼赴京“上计”,“便道访汤”,两人“畅谈文学”。不久,“诏拜河南道御史”。万历四十年(1612),邓渼第二次到临川“访汤”,从当年的“闰八月”到次年的“立夏节后”,住在“沙井新居”的“芙蓉西馆”。所述较简略。
重谟的《汤显祖与新城邓渼》有充分论述。对第一次“访汤”,强调了两人见面后“上下古今,无话不谈”,“论文说政,推心置腹”;对第二次“访汤”,说明是在邓渼调任云南巡按以前,回新城老家探亲时。至于汤显祖对邓渼的影响,不仅在文学主张方面,而且在为官施政方面,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忘年至交”。又在对邓渼的两次“访汤”记述中,交待了邓渼的生平。邓渼生于隆庆三年(1569),逝于崇祯元年(1628),建昌府新城人;中进士后历任知县、道御史、巡按副御史、巡按御史、监察御史等。特别记述了邓渼任监察御史后,为巡城御史林汝翥“疏辩”,被阉官魏忠贤陷害,流放贵州。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召复原职时,不幸病死。这些资料都表明邓渼一生为官都是以“纯吏”来要求自己的。这就使读者对邓渼及邓渼与汤显祖的交往有了全面的了解。
其四,全书开掘、阐明了汤显祖的编剧理论。周育德《汤显祖论稿·前言》统计“汤显祖的文章有108篇”,涵盖了序、题词、记、碑、文、说、颂、哀辞、志铭、墓表、解、疏等门类。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汤显祖集》,收录的汤显祖尺牍更有449封之多。重谟从如此大量散见的篇章中开掘、审订有关素材,为疏理、阐明汤显祖的编剧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汤显祖的编剧理论,在《汤显祖的作剧理论》中,重谟有自己的解读。一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二曰“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三曰“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四曰“以若有若无为美”。从戏曲艺术产生的“底因”这个“根本问题”,到戏曲创作应当遵守的“原则”,再到戏曲“作剧主张”,终结于戏曲创作如何“反映生活”——如他在结语中所说,是“自成体系”的。仅以“作剧的主张”一项来看,重谟认为包含的内容主要有四方面:“重神似”“尚真新”“主灵感”“信天才”。比如“重神似”,是针对“后七子”的“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以及沈璟、臧懋循的“曲必宋元”的口号,反对戏曲创作的“步趋形似”,主张戏曲创作要有“灵性”,从而富有“实践性”,没有“空泛之论”,是从“本人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重谟的结论是:汤显祖虽然没有王骥德、李渔那样的曲论专著,但他的“散见”剧论深刻地论述了作剧的肯綮。王骥德的《曲律》“重在论‘律’”,李渔的《闲情偶寄》“重在论‘技’,汤显祖的剧论“重在论‘意’”。三家理论“各成体系”,都有“重大价值”。故此,汤显祖、王骥德、李渔的作剧理论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鼎立而峙的三座高峰”,三家作剧理论的“总体面貌”,才可以称为“全面、完备的戏曲理论体系”。
总之,《汤学探胜》是一部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具有新锐观点的著作,值得向“汤学”爱好者、乃至戏曲理论界推荐。当然,这并非说这部著作完善无缺憾。如果书中的某一见解引起讨论,促使对问题的认识深化,于学术研究来说总是好事。我对《汤学探胜》的这些看法只是一家之言,仅供识者参考。
2017年仲春,北京草桥欣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