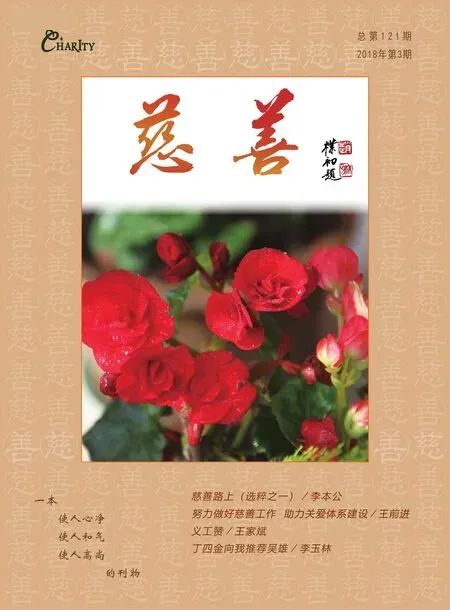怀念母亲
2018-01-24赵浩义
文/赵浩义
清明时节回家祭祖。祖坟坐落在秦岭山脉一峰下面的林子里,松柏挺拔,桃花盛开,犹如仙山琼阁。在曾祖父、祖父、父辈的墓碑前一一上香、烧纸后,在母亲坟前坐了下来,回想母亲的历历往事。
1921年的10月,母亲出生在南秦河畔的一个杏林之家。外公是有名望的老中医,在县城开间很大的药铺,由于身高体胖,晚年走不动路的时候,四台大轿出诊行医悬壶济世。优越的家境,母亲可谓是大家闺秀。不仅女红做得好,而且断文识字,能读报纸上的文章。
母亲20岁时嫁到槐荫堂赵家。槐荫堂是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弟兄二人、祖父辈弟兄六个都没有分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家有几十亩地,在县城开有商铺数间。母亲和几个婶娘就成为家里的炊事班,天不亮就下床为一家60多口人做饭,晚上还熬夜为城里的蜡烛铺制作蜡烛。到上床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腰酸背疼。
母亲生下大姐的时候,家道中落。先是两个曾祖父分家,接着祖父弟兄四个也分了家。分家时,爷爷已双目失明,父亲因患肺痨从于右任创办的三原中学退学回家。1950年祖父去世时,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父亲穿着孝服四处告借,最后砍了一棵桐树打了口棺材才将爷爷草草入葬。
爷爷去世后,父亲患病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几亩土地就全由母亲一人操持。好在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土地划归集体,先是合作社,后又人民公社,母亲就成为村上妇女中挣工分最多的社员,同男劳力一起下地干活。
父亲的肺痨全凭他从外公那里搬来的一堆医书,刻苦研读自学诊治,日渐好转终于康复。1955年我出生时,父亲已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中医进入乡联营卫生所挣工资了,每月38元,加上母亲挣的工分,勉强维持一个8口之家的生计。
1958年人民公社实行大食堂吃饭,家里的铁锅被收走“大炼钢铁了”,一顶石磨也划归集体被拉走了。当时家里每顿饭全靠母亲从食堂担回来的两大罐子稀饭。吃饭时,母亲总是先让奶奶和我们孩子吃饱,到自己饭碗里已经所剩无几,加之又要参加繁重的劳动,母亲常常饿晕在地头。记得有几次在担饭回家的路上,母亲突然晕倒,罐碎稀饭全洒在了地上。回到家中望着孩子们嗷嗷待哺的目光,母亲好一顿号啕大哭。有一次哭声惊动了好心的村干部,连忙安排食堂再做饭送到家里,全家人才免了一顿挨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遭遇了一场大饥馑,村上的人靠稻糠皮、野菜充饥,连榆树皮都被剥光了,饿死了几个人。母亲和奶奶整天上山挖野菜,挖来的野菜再拌上稻糠就是一顿饭,做好了先让奶奶和孩子们吃,到了母亲碗里就只有一点汤水了。母亲因为饿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幸亏父亲行医到深山里买回了一些喂牛的黑豆,才救了母亲一条命,全家人也逃过一劫。
“文革”到来,我家被补划为“地主”成分,家中的五间大瓦房和两亩地的大院子被村上没收改为村办小学,我们8口之家被赶到了二爷家的房子居住。狭小的空间,一家人都打地铺。二爷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小学教员,又在家搜出了一顶礼帽,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经常被拉出去批斗。
我家被补划“地主”的主要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前三年雇了“长工”。事实是一位叫“老李”的70岁老人讨饭时被大家族收养,1946年分家时老李已年逾八十丧失了劳动力,母亲同情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就将老李领回家像老人一样赡养,直到去世。母亲认为老李已丧失了劳动力,不能视为长工,就迈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步行数十里去公社、县革委会申诉。多次申诉后县上派人到村上调查,村上的老年人都站出来证明老李不是长工,这才去掉了我家地主成分重定为中农,一家人又搬回原来的房子住。
大姐嫁给了一名公安干部。每年要交给队上的粮款都是姐夫前来交钱,家庭经济开始好转。但村上还有许多贫困家庭,母亲时常接济,给这家端一盆米,给那家送一升面,和我同班的两个同学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她让我把钱送过去让同学复学。父亲回家后母亲总是给他说谁家的孩子病了、哪家老人头疼,把人家领到家里针灸。当时村里人都很穷,看完病买不起药,父亲就免费给药,时间长了父亲每月得为人垫付药费10元左右。因此父亲在南秦川道上博得“好先生”的美名,村上人也称母亲为“贤惠大嫂”。谁家做了好吃的,总是端一碗送来。有一天一个讨饭的老大娘饿得晕倒在我家门前,母亲把老人扶到家中细心调理,吃了几顿饱饭老人有了精神要走,母亲又挽留住下来,直到她的儿子来接才把老人送走。
“文革”高潮,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回村上当了“放牛娃”,每天扛着扁担到三十里以外的山上去砍柴。由于路途遥远,鸡叫就得出发,母亲总是半夜就起身做饭,饭做好摇醒我起床,吃完饭送给我一个用棉布包裹的饭盒,送我到村口和伙伴们一起出发。不等天亮就走到砍柴的目的地,太阳升起时柴就砍好,扛起七八十斤重的柴担就往家赶,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七八十斤重的担子越担越沉,走不动时想起母亲送我出村时那瘦削的身影,顿时浑身有了力量。记得有一次,山里人因我们到他家的自留山砍柴把我们柴担子夺了,我空着扁担往回走,泪流满面伤心至极,我不是心疼那一担柴,而是觉得对不起半夜就起来做饭,又把我送到村口的母亲。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母亲鼓励我复课考学,每天晚上陪我看书到深夜,天不亮又叫我起床读书,她总是念叨着要“头悬梁,锥刺骨”。家里有一张供桌,每天起床母亲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把书摆放得整整齐齐。高考前的三个月,她不让我下地劳动,总是做最好的食物让我吃。当我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她面前时,她笑着说了一句话:“我娃行,能吃公家饭了。”离家上学的那天早上,母亲把她缝好的崭新被褥递给我说:“你哥被村上推荐上了大学,要不是恢复高考,你这一辈子就只能当农民了,到了学校要好好念书,以后的路就靠自己走了。”我背起铺盖往前走,走了一里多回头看,母亲还是站在村口那棵大树下的一块石头上往前眺望。这使我想起了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
改革开放后,我们兄妹六个进城工作(只有老五因病在家里务农),相继结婚生子,母亲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劳役。先是给大哥管护两个孩子,接着又是为二姐、四弟、六妹、七弟看孩子,整整看了十五年,孙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上小学、上中学、读大学。这时母亲已年过花甲,本想能享几天清福了,不料父亲却突然中风,终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这就又苦了母亲,一伺候又是十年,直至1994年父亲病逝。此时,母亲已七十六岁了。终生辛劳,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但身体却还硬朗。
2000年,我调到省城工作想把母亲接来,无奈一直住着一间房子。2002年10月份单位分配我一套三居室住房,我第一天搬家,第二天起床就对妻子说:“我回去接妈。”妻子说:“东西摆了一地,等收拾好了再接吧!”我说:“不行,已经给妈说了,妈在村口等着。”驱车120公里赶回村子,老远就看见母亲提着一个包袱在村口的那棵大树下眺望,我上前握住母亲的手含泪说:“妈,您在家等嘛,外面风大。”接回西安,一位朋友为母亲接风在酒店设宴,母亲进门说:“茅子在哪里?”朋友不解问:“茅子是啥?”我说:“我妈想上洗手间。”惹得一桌人哄堂大笑。
妻子出身农村,通情达理,很是孝顺,为了照顾母亲主动联系借调到西安上班。每天早上起来把饭做好送到母亲面前,中午又步行数里赶回来为母亲做饭,每天还留下一些钱让她到街上吃零嘴。两个儿女也很懂事,争着在地板上打地铺把床让给奶奶睡。母亲在我这儿生活了一年多,体重增加了20斤。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妻子扶着母亲到钟楼看花灯,母亲后面跟了一群记者,镁光灯嚓嚓地闪。母亲问妻子:“咋这么多的人跟着我照相。”妻子笑着回答:“妈,人家在照您的三寸金莲,您同大熊猫一样,是国宝。”
大哥和我在单位都有职务,后来七弟也做了单位副职,母亲常对我们弟兄三个说:“妈不指望你们升官发财,但一辈子要积德行善,善事做多了,老天会庇护你们子孙平安。”2015年我退休后被一家民营企业聘去北京做一个公司经理,到任15天接到老领导刘维隆会长电话:“浩义,听说你退休了,来到省会做慈善。”开始我想:人家大老板在西安等了我七天,才来咋能提出辞职,但想起了母亲的话,就以老婆有病为由向老板请辞,老板见我去意已决,拿来一包钱送我,我说是我对不起你,分文未拿,连夜坐火车赶回西安到省慈善协会报到。朋友问我:“每月几万元的高薪你不拿,回来做慈善又不发工资。”我用徐山林老会长的话回答:“退休后一不干挣钱的忙事,二不干养花的闲事,就干扶贫的善事。”
2003年,七弟带母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照相馆将母亲照片放大展在大街的橱窗中,行人顿足:“这位老人好慈祥呀!”
2004年春节前,母亲突然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就请了一名保姆来照料,但母亲身高体胖,保姆扶不起来,大小便都在床上。只有我或妻子下班后携手才能帮母亲上洗手间。母亲的病经过诊治略有好转,大哥前来要将母亲接回家,走时母亲手抓着门框不放喊着:“我不想回、我不想回去……”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我也不让母亲走,大哥急了发脾气:“86岁的老人了,必须老在家中!”就这样,我流着眼泪送母亲出门。
2004年3月15日,我在北京参加CCBA会展,大哥发来短信:“母亲病危,速回!”我连夜乘飞机赶回西安,回到家中母亲已躺在灵床上了,面带微笑,安然慈祥。
母亲是一只蚕,为了儿女抽尽了身上最后一根丝。
母亲是一盏灯,淳朴善良的天性照明了儿女人生的路。
母亲,您太累啦,歇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