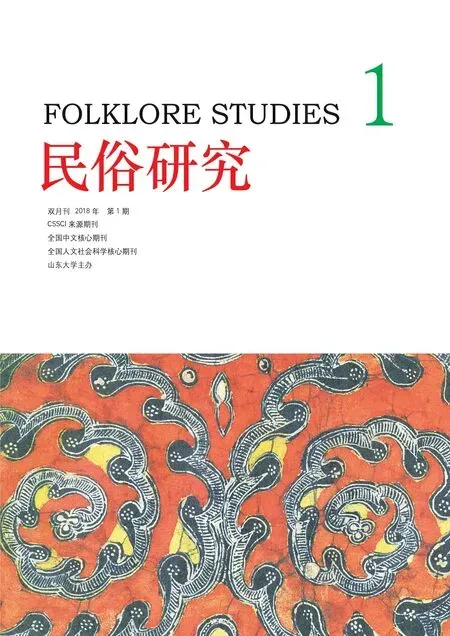彝族史诗“支嘎阿鲁”中次要人物的箭垛效应研究
2018-01-23王伟杰
王伟杰
一、“喧宾夺主”的次要人物的由来
胡适先生在《〈三侠五义〉·序》中指出了“箭垛式人物”的定义,并认为我国历史上的黄帝、周公、包龙图等等都是这些有福之人,成为较多无名的传说故事的归宿。如《宋史》中对包拯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元)脱脱等:《宋史》卷316至卷331,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15-10333页。,后来包待制就成为包公传说的根源,其“廉政爱民、断案如神”的核心特质成为核心箭垛。民间传说,愈传愈神奇,不但把许多奇案都送给他,而且造出“日断阳事,夜断阴事”的神话,后世佛道混合的宗教遂请他做了第五殿的阎王。*胡适:《〈三侠五义〉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六,亚东图书馆,1931年,第661页。胡适同时认为“大概包公断狱的种种故事,起于北宋,传于南宋;初盛于元人的杂剧,再盛于明清人的小说”,“由于后来民间传说,遂把他提出来代表民众理想中的清官,他却也有这种代表资格”*胡适:《〈三侠五义〉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六,亚东图书馆,1931年,第661页。,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然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包待制的传说并不随着包公成功神化为箭垛式人物而终止。胡适提出了另外一种演进方法,即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迁。胡适指出,明代《包公案》中《玉面猫》一条,“记五鼠闹东京的神话,五鼠先化两个施俊,又化两个王丞相,又化两个宋仁宗,又化两个太后,又化两个包公;后来包公奏明玉帝,向西方雷音寺借得玉面猫,方才收服了五鼠”,五鼠后来竟然成为了五个义士,玉猫后来成为御猫展昭,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与神话的人化了。同时在整个的文学题材中,“杂记体的《包公案》后来又演为章回体的《龙图公案》”,并又从中演化出来《三侠五义》。对比《龙图公案》与《三侠五义》后发现,前者仍是用包公为主体,而《三侠五义》却用几位侠士作主体,包公的故事不过做个线索,成为了一种陪衬。如此喧宾夺主的变迁在包公的传说中不止“五鼠闹东京的神话”一例,“李宸妃的传说”(夹杂“狸猫换太子”传说)也是次要人物转成主要人物的重要个案。刘锡诚先生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二章第九节“滚雪球与箭垛式”中论述胡适先生的箭垛式观点时提到,“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故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后世演变成一大传说,又渐而由传说演变为杂剧和小说,到清代,又把‘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情节也粘连进来,成为连台几十本的大戏”*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不管是“五鼠闹东京的神话”还是“狸猫换太子的传说”,都是包公传说的“粘连”和“堆积”效应的结果,进而在故事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迁,并成为各自语境的主角,从而将包待制降格为一种配角,“李宸妃”“三侠”“五鼠”等“喧宾夺主”,成为了各自传说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二、彝族史诗“吱嘎阿鲁”中的“次要人物”
支嘎阿鲁(以下统称为“阿鲁”)是彝族史诗“吱嘎阿鲁”*该处“支嘎阿鲁”指代的是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的总称,并不单指具体的《支嘎阿鲁》史诗,而包括《支嘎阿鲁王》《阿鲁举热》《支格阿龙》《直格阿鲁》《支嘎阿鲁传》等等多个版本的史诗,因此未用书名号,而用引号代替。中的箭垛式人物,围绕着其核心形象和事迹,产生了多种类型的箭垛式堆积效应,塑造了多个类型的次要人物,从而也产生了类似于“李宸妃”“三侠”“五鼠”等等多个反客为主的“配角”。从次要人物与阿鲁的关系与堆积的具体章节来看,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情形:阿鲁母亲是“不同身份、相同形象”的堆积;阿鲁妻妾是“不同身份,不同形象”的堆积;妖魔鬼怪是“相同身份,相同形象”的堆积。
阿鲁的母亲是“不同身份、相同形象”的堆积,以五个版本的史诗内容来看,作为阿鲁血缘关系最为密切的母亲,其形象基本都可以用“温柔善良,多灾多难”来概括。然而阿鲁母亲的名字却有多个,其身份也有“神”“人”之别,大多命运坎坷也有着不同的结局,但其核心形象基本相同。《阿鲁举热》中阿鲁的母亲是“从小失去爹妈的独姑娘卜莫乃日妮”,因被滴到老鹰的三滴水而受孕生下阿鲁;她将阿鲁交给老鹰抚养,但最终直至阿鲁坠海死亡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祁树森、李世忠、毛中祥记录整理:《阿鲁举热》,黑朝亮译,《山茶》1981年第9期。《直格阿鲁》中阿鲁的母亲是“地上最美的姑娘特扎喽”,她与天神恒咤铸私定终身并生下阿鲁,然而由于触犯天条,恒咤铸被天兵天将押回天宫并关入天牢,最终特扎喽寻夫未果,在将阿鲁交给马桑抚养之后纵身跳入侯戛海而死。*珠尼阿依(王富慧):《直格阿鲁》,载《彝族神话史诗选》,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354-384页。《支嘎阿鲁王》中阿鲁的母亲则是地上神女啻阿媚,从她与天郎恒扎祝相恋并“生了个巴若”,结果耗尽气力而亡,并“化作茂盛的马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支嘎阿鲁王》,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5-13页。。《支嘎阿鲁传》中阿鲁的母亲是天君策举祖的胞妹策戴姆,其丈夫直支嘎在结婚三天后就死去,遂成为寡妇并单独抚养阿鲁,后被纪家关进纪底牢并身染重病;阿鲁经过千辛万苦射掉六个太阳、六个月亮后救出母亲,并前往米褚山采得恒革治好了母亲。*传说中的不死药。《支格阿龙》中阿鲁的母亲是蒲家三女儿蒲莫妮依,雄鹰滴三滴血在其身上受孕而生阿鲁,但其母亲的命运在所有版本的史诗中最为坎坷:蒲莫妮依先是被食人魔王塔博阿莫捉拿,被阿鲁救出后其灵魂又被恶鬼欧惹乌基抓去,以嫁给天上魔头濮兹濮莫,在阿鲁历尽艰辛救出母亲魂魄并使母亲痊愈后,却又在阿鲁外出期间被吃人魔王首阿乎害死。*参见沙马打各、阿牛木支主编:《支格阿龙》,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页。
阿鲁妻妾则是“不同身份、不同形象”的堆积。阿鲁的妻妾同样有着典型的堆积效应,只是作为阿鲁的爱人们,核心形象千差万别。《阿鲁举热》中阿鲁原本没有老婆,在日姆被阿鲁杀死之后,日姆的太太和小老婆以及其他财产都被阿鲁继承,成为了自己的太太和小老婆。日姆的太太安于现状,接受了改换门庭的现实;日姆的小老婆却“心怀叵测、心肠歹毒”,总想着等待时机为日姆报仇,最后将阿鲁的飞马剪掉羽毛致使阿鲁坠海而死。《直格阿鲁》中阿鲁的妻子是天界有德有才有貌的四公主,她是天君筹举祖的女儿,不仅天生丽质,更聪慧过人,识破了天上人间的世态炎凉。《支嘎阿鲁王》中阿鲁没有明确的妻子,却在万难险阻中结识了两位恋人:鲁斯阿颖是大力山神鲁依岩的女儿,她为帮助阿鲁对抗父亲,结果为情殉命;吉娜依鲁是白海小龙王鲁依哲与鲁咪伦的女儿,她在虎王阻几纳的魔窟中解救了阿鲁。《支嘎阿鲁传》中忠厚老实未曾作恶的皮诺寿博散的幺女儿“溢居阿诺尼”(龙女),不仅聪明伶俐,又善良温柔,最后与阿鲁结为善缘。《支格阿龙》中阿鲁的妻子则是阿鲁在滇帕海底为母亲取九庹九尺长的头发时所救的红绿二位仙女,两人都为留住阿鲁而剪掉飞马羽毛,致使阿鲁坠马而死;阿鲁的情人吉娜依鲁与《支嘎阿鲁王》中的形象完全相同。
阿鲁惩治的妖魔则是“相同身份、相同形象”的堆砌。阿鲁在其降妖除魔的伟大功绩中,妖魔的角色也在不断堆积。《阿鲁举热》中的“妖魔”有七个太阳、六个月亮*在这里太阳和月亮并不是单纯意义的自然事物,而是有着人性化色彩(《阿鲁举热》中月亮是哥哥,太阳是妹妹)的“妖魔”,晒得万物枯焦,并且日夜不分,成为四害之二,具体见黑朝亮翻译,祁树森、李世忠、毛中祥记录整理:《阿鲁举热》,《山茶》1981年第9期。其他版本史诗中妖魔化的“太阳”“月亮”的形象大致如此。、蟒蛇(麻蛇)、石蚌,最终被阿鲁一一制服;《直格阿鲁》中只有穷凶极恶的措诅艾;《支嘎阿鲁王》中则有七个太阳、七个月亮、雕王大亥娜、虎王阻几纳、九大撮阻艾(专门吃人的妖怪巧必叔、谷洪劳、蜀阿余);《支嘎阿鲁传》中则较多,有三大海里的孽龙寿博兄弟、雕王弥立大、白骨之妖撮宇吐、魔鬼哼氏家族、洞中的杜瓦、纪底七兄弟(七个太阳)、洪家七姊妹(七个月亮);《支格阿龙》中的妖怪有食人魔王塔博阿莫、六个太阳、七个月亮、雷公阿普、巨蟒、恶鬼欧惹乌基、魔头濮兹濮莫、吃人魔王首阿乎、食人马、杀人牛、食人孔雀、雕王、虎王等等。虽然妖魔的数量和类别不统一,但有着共同的性质就是危害人民且生性残暴,其中的太阳、月亮、措诅艾、蛇、雕等等出现了多次,明显发生了堆积效应,且整个妖魔鬼怪作为一个“群体”本身也发生了堆积效应。
三、“支嘎阿鲁”中次要人物与阿鲁形象的深层次联系
从五个版本的史诗可以看出,阿鲁母亲、妻妾以及惩治的妖魔等多样化形象的堆积,是环绕在具有神性的英雄阿鲁周围的次要人物的形象的堆积,三个方面的堆积有着各自的核心人物形象偏好,对应着阿鲁不同的核心人物形象。
阿鲁的母亲在三个史诗中以“人”的身份出现,两个以“神”的身份出现。然而无论是“神”还是“人”,阿鲁母亲的遭遇都较为悲惨,面对生存的压力、抚养阿鲁的艰辛、妖魔的迫害等方面往往力不从心,其最后的结局也较为悲惨:三个版本的史诗中最终身死,一个失踪,只有在《支嘎阿鲁传》中达到了母子团聚的美满结局。在阿鲁母亲的个人形象塑造中,史诗的创造者似乎更多地以悲剧的色彩来描述,即使在一些史诗中阿鲁母亲具有神的身份,但却鲜有介绍并使用其神力的内容,史诗塑造的更多的是“美丽善良、不畏艰辛、多灾多难”的娇弱女子形象,借此达到反衬阿鲁英武孝顺等核心形象的效果:如美丽善良表明着阿鲁有着良好的基因,更有着帅气英俊的父亲,因此有着英武俊朗的外表;母亲的多灾多难更显示了阿鲁敬祖孝亲、能力非凡、决胜一切的英雄品德,每当母亲遇到困难之时,便能果断出击,不畏艰难地击败对手;母亲柔弱的一面则是阿鲁刚强一面的真实反映。
阿鲁的妻妾在不同的史诗中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不同,其“神”抑或“人”的具体身份也不同。然而在不同版本的史诗中,阿鲁妻妾有着一些共同点:一是有着美艳绝伦的外表;二是大多深爱着阿鲁,为阿鲁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或折服*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日姆小老婆怀恨在心,心念旧主,因此将阿鲁杀死。日姆小老婆并未深爱着阿鲁,但她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阿鲁的正统的妻妾,仅仅是阿鲁杀死日姆之后霸占的“财物”,是史诗中男权社会将女性“物化”的结果。;三是温柔善良,有奉献精神。这些共同点的存在,恰恰也从侧面反衬出了阿鲁的光辉形象。如众多妻妾美艳无比,正说明阿鲁有着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更有着令“女人”与“女神”甚至“龙女”等等倾心的外表和能力,才在周边环顾着如此之多的如花似玉的女子。阿鲁的妻妾大多深爱着阿鲁,朝思暮想乃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以致于红绿仙女二人由爱生恨,为挽留阿鲁而剪掉飞马翅膀,彰显了阿鲁在爱情方面的超凡的人格魅力。阿鲁妻妾的奉献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阿鲁遇到艰难险阻时,深受阿鲁“舍小家、顾大家”“心系苍生,救民于水火”的伟大精神所感染,而迸发出的舍身取义的精神追求。此时阿鲁的伟大不在于拯救了深处危难之中的百姓,而在于改变了一些高高在上的“神”的传统观念,和一些人“委曲求全”的旁观者心态,使他们真正地融入到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中去。*肖远平、王伟杰:《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正能量文化精神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4第5期。
史诗中妖魔的数目越来越多,魔性越来越强,危害越来越大,更显得阿鲁作为神话式的英雄人物出现的必要性,显得阿鲁作为一个神性英雄的形象愈发伟岸。在史诗的描述中,阿鲁面对的妖魔是多个邪恶集团,一些妖魔在不同版本史诗中反复出现,更在彝族传说故事、谱牒文本、历史文献等等中频有记载。如史诗中描述较多的措诅艾,其妖魔化的形象不亚于史诗中其他任何一个妖魔。《直格阿鲁》中措诅艾凶恶异常,“人间措诅艾/在吃人间女/在吃人间奴/四方各处打/四方各处杀”,同时又本领强大,“他的妖法多/千变又万化/……实在很厉害/口里一吹气/地下雾茫茫/狂风四处奔/四周看不明/四周看不清/千军和万马/难逃他手心/豺狼和虎豹/同样难逃生”,以致于“万物不能生/万物不能活/上天去告状”。天君筹举祖甚至许下了“谁平措诅艾/就将三公主/配他作为妻”的诺言,结果天兵天将拿措诅艾没有任何办法。阿鲁与措诅艾大战之后,措诅艾被打得打败,四处奔逃,每到一处就大肆害人,被阿鲁驱赶至天上,住在半空中仍不忘作恶,“黑云变冰雹/年年下冰雹/一年下一方/不忘害地人”,阿鲁返回天宫后措诅艾仍死不悔改,随即下界作恶,“大地被搅乱/大海被搅浑……到处去抓人/到处去吃人/到处玩女人”,阿鲁变为铁鹞将其封在葫芦口中,最终措诅艾被大火烧死。*珠尼阿依(王富慧):《直格阿鲁》,《彝族神话史诗选》,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407-443页。类似于如此凶狠残暴的妖魔很多,其堆积效应最为明显,措诅艾等妖魔在不同版本史诗中虽然名称相似,但其法力不同,被消灭方式也不同。然而,较为统一的是这些妖魔危害人间的本质特征是一样的,这些妖魔鬼怪“在天空,在地上,在林中,在洞里,无一不涂炭生灵,无一不吃人害人,无一不带来祸患”*田明才:《支嘎阿鲁传》,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7页。,其凶恶的程度越甚,阿鲁的贡献就越大,才能显示其勇敢与智慧异于常人,其神性英雄的光辉形象就愈发光芒万丈。
四、“支嘎阿鲁”中次要人物产生堆积效应的原因分析
阿鲁周边三类次要人物的堆积效应,塑造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产生堆积效应的“配角”形象,却间接反映着阿鲁自身的核心人物形象,且是在彝族社会历史进程中久经千年却依旧不变的核心人物形象,在这些次要人物身上进行故事的粘连与堆积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彝族英雄“吱嘎阿鲁”自身并不是单一性质的箭垛式人物,而是有着多重身份和功绩的复合式英雄;也是神人同体的神性与人性兼具的彝族君王;同时也是拥有完美与不完美两种形象的多面人物。*肖远平、王伟杰:《神人同体的彝族多面性箭垛式英雄人物支嘎阿鲁》,《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6期。除此之外,阿鲁的核心人物形象也是多元的,彝族的大量文学作品塑造的是一位英俊威武、善良智慧、神力无比、勇往直前、决胜一切的完美的神性英雄人物。*参见沙马打各、阿牛木支:《支格阿龙》,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1-2页。在阿鲁为主角的箭垛式堆积中,为了彰显主角某个典型的个性化特征,往往在相应的史诗中堆积更多的次要人物*祁树森、李世忠、毛中祥记录整理:《阿鲁举热》,黑朝亮翻译,《山茶》1981年第9期;珠尼阿依(王富慧):《直格阿鲁》,载《彝族神话史诗选》,民族出版社,2013年;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古籍办、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支嘎阿鲁王》,阿洛兴德整理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年;田明才主编:《支嘎阿鲁传》,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年;沙马打各、阿牛木支主编:《支格阿龙》,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随着史诗篇幅的增长和堆积故事的增多,次要人物在史诗的部分章节(或个别传说故事)中以一种“主角”的形式存在,并在其身边有更多的配角存在,渐渐地配角的配角不断堆积,配角也渐渐地形成了堆积效应,这是周边次要人物产生堆积效应的重要原因。
阿鲁的多重身份集于一身,造成了其周边人物(如部属和随从)发生着诸多变化,为不同形象和不同身份提供了堆砌和粘连的空间。不同于包龙图“断案如神”、关羽“忠勇可嘉”等等的较为单一的身份和单一的形象,阿鲁的身份是多重的,其核心人物形象是多元的。史诗“支嘎阿鲁”以及其他与阿鲁相关的传说故事中发生堆积效应的人物较多,如其父亲也是有着多重身份和多个名字的复合型人物。虽然在《阿鲁举热》中,阿鲁仅仅是一个由贫苦的孩子转变成为一方部落首领的英雄式人物,但在其他史诗中,阿鲁却是一个集合了多个身份的彝族君王,不但在历史上有典可查,更成为彝族各行各业的英雄,成为彝族各个行业堆砌的箭垛式人物,因此次要人物的堆积往往因为地域、行业、年代的不同而产生差异。阿鲁的身份有帝王、君长(部落首领)、臣子、布摩(毕摩)、摩史、将官带领人们战天斗地,治理洪水、劝勉农耕畜牧,乃至统一彝族文化,更是在天文学、地理学和历算学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因此,阿鲁成为了古代彝族社会中各个等级理想化的代表,被塑造成各个等级成员的完美形象。*田明才:《支嘎阿鲁传》,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5页。在史诗的章节中和传说故事中的次要人物也跟随着阿鲁身份的变化而变化,造成了其母亲、妻妾、部属等等形象发生了堆积效应。
不同版本史诗的流行,更为阿鲁周边次要人物的堆积做了铺垫。阿鲁不同妻妾的不同形象,恰恰是阿鲁神人同体的彝族君王形象的展现,作为首领或者部落君长,自然有着妻妾成群的特权,作为能与神接近的神性英雄,也能将仙女揽入怀中;作为有着凡人血统的阿鲁,自然有着身为凡人的男人的情感和缺憾。从日姆小老婆的歹毒心计到红绿二仙女的妒忌心肠,从四公主的聪明智慧乃至溢居阿诺尼的不离不弃,再到鲁斯阿颖的坚贞殉情,都看出了阿鲁作为神性英雄人性的一面;阿鲁没有女性天生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聪慧,但却有着常人对爱情矢志不渝、坦诚以待的胸怀,也有着普通男性在处理家务时考虑不周、麻痹大意等心态,以致后院失火、祸起萧墙。因此阿鲁周边次要人物的堆积效果与史诗有着多个不同版本有着莫大关系,其流传地域、族群和年代均不甚相同,其母亲、妻妾以及面对的妖魔鬼怪都因地域的不同而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差异,然而虽历经千年阿鲁的核心形象却不因地域的不同、文化的流变、民族的迁徙、族群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即使在一些民间故事等等中有一些“反面形象的箭垛”出现*关于支嘎阿鲁“反面形象的箭垛”的民间故事例证不多,“阿鲁诅咒彝族女人”的故事是其中一例,具体观点见肖远平、王伟杰:《神人同体的彝族多面性箭垛式英雄人物支嘎阿鲁》,《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6期;具体故事内容见杨正勇、何刚主编:《中国弈族支格阿龙故事精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但其核心人物形象始终不变,从而使阿鲁形象在时间、地域乃至族群等方面达到了惊人的统一。
阿鲁极强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斩妖除魔、为民除害的伟大业绩。从各个史诗版本看阿鲁所铲除的妖魔来看,有着鲜明的差别。首先是妖魔属性不同,他们有飞禽走兽,如弥立大雕、杜瓦大蛇、食人马、杀人牛、食人孔雀等;有天上日月,违背自然规律害人惹人;有以动物崇拜的残暴部族,如虎王、九大撮阻艾;以及其他妖魔鬼怪,如白骨之妖撮宇吐、魔头濮兹濮莫、恶鬼欧惹乌基、妖怪巧必叔、谷洪劳、蜀阿余等。其次是害人的方式也不相同:太阳是同时出来,晒得万物枯焦,月亮是照得大地昼夜不分,蟒蛇吞食人畜,石蚌踩踏并吃食庄稼,魔头濮兹濮莫觊觎阿鲁母亲的美色,措诅艾到处吃人、抓人、玩女人,是最为凶恶的妖魔。然而其核心形象都是穷凶极恶、危害苍生,最终的命运都是为阿鲁所制服或斩杀。这可能是彝族社会中在历史发展中遇到的各类危害的集合,太阳炎热、月亮光亮、动物吃人、令人恐惧的超自然现象、连年不断的部落战争等等,是萦绕在彝族民众头顶的噩梦,因此在彝族社会的民间文学中,阿鲁成为人们在心中的最大希望,民众通过口头文学的形式将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中的光辉业绩,转嫁到阿鲁身上,完成了对妖魔鬼怪的形象堆积,实则恰恰反映了阿鲁是彝族人民将其视为神话英雄的重要表征。阿鲁也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成功塑造的一位箭垛式英雄人物。
五、“支嘎阿鲁”中次要人物箭垛效应形成的启示
围绕在阿鲁周围的次要人物的故事和章节的堆积,是阿鲁形象的间接粘连和堆积,以其他形象为媒介来反映阿鲁的核心人物形象。经过粘连和堆积,史诗中的次要人物成为某个片段和故事中的主角,甚至逐步成为新的“箭垛式人物”。如同在一个中心人物“主箭垛”形成的同时,形成了多个副中心的“小箭垛”,形成了“众星捧月”的局面。例如阿鲁的母亲、阿鲁的妻妾(红绿二位仙女与日姆的大老婆与小老婆)、妖魔措诅艾、太阳和月亮、蟒蛇等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堆积效应,萦绕在其身边有着众多的版本故事和传说。在阿鲁自身发生箭垛式堆积的同时,阿鲁周边的“群星”也在发生着堆积,各种样式的传说将阿鲁的敌人说得更加丑恶。
箭垛式人物周边次要人物的堆积效应,在彰显了次要人物典型特征的同时,更展示了主要人物的核心形象,达到了更为良好的艺术渲染效果。不同于箭垛式人物的多面形象,主要人物(主箭垛堆积的人物形象)形象通过次要人物的形象将其更伟大光荣的形象刻画出来,达到了称赞其人而又不指名道姓的效果,远比直接称赞其本人核心形象的效果更佳。通过描写母亲生活的困苦,以及多灾多难的经历,以反映阿鲁困难的童年及成人后对待母亲的孝顺体贴,以及自身在艰苦环境中养成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突出阿鲁自身善良孝顺的品德;通过描述措诅艾等妖魔的“恶”,反衬阿鲁斩妖除魔的决心和神力无比的本领;通过描述妻妾的花容月貌,彰显阿鲁自身的英武俊朗。吱嘎阿鲁传说的发展与“李宸妃传说”的演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次要人物李宸妃,很容易成为包公传说中的章节中的重要人物,成为一个堆积的箭垛,久而久之成为“箭垛式人物”,因此阿鲁母亲或者其妻子(如其中吞神鞭而殉情的鲁斯阿颖)的善行有被演变为单独的传说的可能。妖魔形象的堆积类似于李宸妃的传说与包公的传说形成,通过李宸妃的传说来彰显包公传说的整体故事,借外来显赫的人的冤案来反衬包公断案如神的特征,同样史诗则是通过妖魔、父母、妻妾等等的传说故事来彰显阿鲁作为核心人物的多元的人物形象。
不同版本的史诗,因年代、地域乃至族群不同而表现出的阿鲁核心人物形象的统一,恰恰代表着彝族社会塑造阿鲁形象的神奇的统一。不同于其他类似机智人物的箭垛式堆积的情形,吱嘎阿鲁的人物性格是多元的,因此次要人物箭垛式的堆积也是多渠道的。由于史诗“支嘎阿鲁”不同版本的流行地域不同,年代远近不同,传播群体不同,其个性化特征自然是堆积的重要元素,然而历经千年彝族社会中人们心中的支嘎阿鲁的形象是统一。不同地域、年代和族群的人们对其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和宣扬,追求祖先在人们心中完美的神性英雄形象,以起到激励民众积极向上的效果,在每个深受阿鲁感染的心中,都满怀着“心系苍生、斩妖除魔”的决心,在阿鲁的感召下为民谋福利,因此人人都是阿鲁精神的传扬者,每个人都是一个“小阿鲁”,即使阿鲁不在了,阿鲁的光辉形象和追求和谐的精神,将会一步步传扬下去,这对于促进彝族人民和谐共生、团结互助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次要人物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为箭垛式人物,是连续性的过程,在其成为主要人物的同时,也存在着被自身周边次要人物“喧宾夺主”的威胁。由于彝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征战等重大事件,自身的生存空间发生了急剧变化,彝族民间文学发展的土壤一步步发生转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下,其具体的民间故事流传过程被弱化,次要人物单独成为传说故事,由于缺乏一定的文学土壤和类似于戏剧这样的表现形式,未形成类似于《狸猫换太子》《三侠五义》等等流传久远的大戏。这与彝族社会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其文化形态保存完好,不受外来因素影响,且由于长时间以来彝族人口有限、交通闭塞、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彝族民间文学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
六、结 语
阿鲁周边次要人物故事的堆砌,是阿鲁人格形象衍生的结果,是其多重身份和多元人物形象的解构,以此形成了另一种依附于箭垛式人物本身的堆积现象,它依附于主箭垛,是原有箭垛式人物形象的发展和延伸。李宸妃与刘皇后,是彰显包待制核心形象的次要人物,却能逐步发展成为章回体小说某个片段中的核心人物,乃至成为部分小说、故事的核心人物。如《三侠五义》中的有名侠士成为真正的英雄一样,包龙图成为了一种衬托,人们在关注冤假错案的悲悯、离奇大案的复杂的案情时,忘记了包拯在破案中彰显的巨大功劳,而只专注于大案要案本身,使“李宸妃”“三侠”“五义”等人物脱颖而出,更因为其身世富贵显赫却命运坎坷的经历,或者义薄云天侠肝义胆的精神俘获了下层民众,使包龙图在相关传说故事中变为了次要人物。
民间文学在成就了次要人物的同时,更发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响应,一是彰显了主要人物,借助于次要人物的极富个人魅力色彩的宣传,使主要人物的光芒尽显;二是成就了更多新创著作问世,“三侠五义”的传说故事,演绎为章回体小说等等,最后成为长篇武侠小说《三侠五义》乃至《七侠五义》,而著作本身则由一个简简单单的次要人物的主观行动,成为了千百年来百姓津津乐道的大义之举,民间文学对这些极富公平正义色彩的人物形象进一步扩大化的塑造,将围绕他的故事堆积成为了一部部宏篇巨著。然而,次要人物形象的堆积是一个长期的累积的过程,非一人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成,彝族史诗“支嘎阿鲁”中次要人物虽然形成了堆积效应,却未能形成属于次要人物自身的各类文学题材作品。这与历史发展进程中生存空间的缩小、族群的迁徙等等不无关系,尤其是在现代语境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逐步融合创新发展,彝族文化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因此,未来应该在重视民族文化发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生态,在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中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