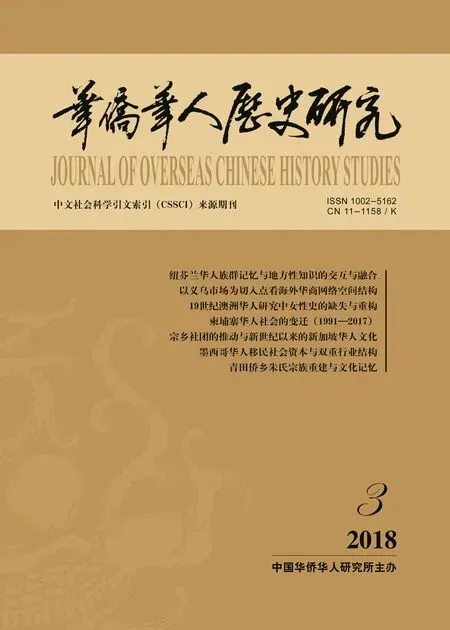青田侨乡朱氏宗族重建与文化记忆研究
2018-01-23张崇
张 崇
(浙江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传统村落与美丽乡村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3)
浙江青田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侨乡,“家家有华侨”是当地一大特色。朱氏宗族位于青田油竹镇下村。下村有900余户共计2300人,以朱姓、王姓、陈姓居多。早在清朝晚期,就有朱氏族人到欧洲谋生,一般靠做小生意赚钱,赚到钱后便返回家乡。由于青田“九山半水半分田”,从国外赚钱回来后人们通常会在温州一带买田,靠出租田地为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朱氏族人出国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又不断有族人到国外谋求发展,通过一带多、亲带亲等方式,通常从餐饮行业做起,并从餐饮行业发展到其他多种行业。这批人逐渐拿到所在国国籍后,积累了大量财富,从早期的“落叶归根”发展到现在的“落地生根”。不过,他们依然与家乡、祖籍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与侨乡宗族重建就是其一。
宗族是由共同祖先界定出来的父系群体,在几乎整个20世纪,宗族基本上被当作落后、消极的东西,[1]宗族似乎正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之中,如族产充公、祠堂挪作他用或拆除、族谱焚毁。[2]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乡村不断涌现(或曰再生、重建)的宗族组织,引发学者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如钱杭认为,汉人宗族之所以能够在波涛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生存下来,并且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取得相当大的发展,就因为它关注的主题,正是这个时代所失落的关于人类的本体意义之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3]在扬·阿斯曼(Jan Assmann)看来,这两个问题是归属感(或认同)问题,与文化记忆理论密切相关。所谓文化记忆,是指在某一社会或群体的互动框架下所有指向行为和经验知识的总和,人们可通过反复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动员,促使成员习得这些行为和经验知识,并一代代传承下去。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主体,超越个体记忆。因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公共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4]宗族作为传承和重构文化记忆的群体之一,如钱杭所言,体现了人们对于“本体性”,即归属感、责任感和道德感的文化和心理需求,“古代的汉人如此,现代的汉人如此;大陆的汉人如此,海外的汉人也如此。”[5]
冯尔康认为,判断宗族重建有两条标准:首先是否修谱或是否有谱,其次是否维修或重建了祠堂。[6]肖唐镖提出,宗族如果修谱和修宗祠,就会有牵头的人,而且需要资金组织开展活动。这两件事发生其一,就可说宗族在重建。[7]从这些角度看,青田朱氏宗族重建符合目前学者对宗族重建的研究结论。首先,朱氏宗族重修了族谱;其次,重修了祠堂。因此,可以说青田朱氏宗族重建具有一定代表性。目前国内学界对于海外华人参与侨乡宗族重建的研究,多是从宗族重建的描述和介绍出发,从文化认同、权力、地方建构等概念入手进行阐释和研究分析。①如刘朝晖从国家权力视角来看待海外华人参与的宗族复兴,认为当代的宗族复兴不可能像传统宗族那样成为国家权力格局的一极,而是主要起着文化与象征的社会意义(刘朝晖:《改革年代侨乡社区的宗族组织与政治过程》,《思想战线》2007年第3期)。麻国庆以福建樟湖镇的宗族重建为例,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下研究宗族复兴,认为宗族复兴是传统文化的复制和再生产(麻国庆:《宗族的复兴与人群结合——以闽北樟湖镇的田野调查为中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范可以福建南部宗族活动的复苏为案例,论证了宗族活动复兴及由此带来的认同建构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反应(范可:《旧有的关怀、新的课题:全球化时代里的宗族组织》,《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李思睿从侨乡空间和地方意义建构的视角,运用前美村的宗族重建为个案,研究作为侨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关系的空间时间下不同的文化意义和地方意象(李思睿:《跨国网络与粤东侨乡社会变迁:以梅州市大黄县百侯镇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周大鸣、潘争艳研究广东潭村的潘氏宗族复兴与村庙的关联,理解乡村宗教活动对于宗族的整合和认同作用(周大鸣、潘争艳:《宗族与村庙—粤西潭村石头庙与潘姓宗族》,《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宋平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以福建南部永春县的郑氏宗族为个案,提出海外华人参与侨乡宗族组织的跨国实践,既可以为一定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宋平:《传统宗族与跨国主义实践》,《文史哲》2005年第5期)。王敏等研究了跨国网络中的人口与资本流动,包括海外华人参与侨乡宗族重建,表明华侨“侨”的内涵发生变化,对于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也发生了变化(王敏、汪荣灏、朱竑:《跨国宗族网络与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7年第1期)。而且,关于海外华人参与侨乡宗族复兴重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广东和福建两地,对浙江省海外新移民参与侨乡宗族重建的研究较少。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研究侨乡宗族重建,是国内外学术界较少涉及的课题。本研究从经验层面提供浙江海外华人参与宗族重建的个案,运用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来解释宗族重建的细节。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宗族如何运用过去的历史对当下的宗族进行重新建构,并具有鲜明的当下与未来指向。本文运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将历史文献与当下社会调查结合,研究浙江青田朱氏宗族如何运用文化记忆进行宗族重建的微观过程,从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和阐释这一文化现象,丰富侨乡文化个案研究。为了能够获得朱氏宗族重建细节,2011—2017年间,笔者先后在下村进行了五次田野调查,主要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查阅宗谱及青田相关历史资料,获得大量一手资料。
一、朱氏大宗理事会与朱氏宗族集体记忆重构
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提出,互动式的群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以日常生活为基础,随着载体的消失而灭亡;比较之下,文化记忆以外在的符号载体和符号表征为基础,具有持久性。为了把暂时性的社会记忆变成长期的文化记忆,以便代代相传,需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细化和组织。[8]扬·啊斯曼认为,机构或群体(如公司、宗教、民族、国家等)运用集体记忆构建归属感(或认同)。然而,群体或机构并不像个人一样拥有记忆;不过,群体可以借助记忆符号,如符号、文本、形象、礼仪、纪念仪式、场所和纪念碑等,为自身制造集体记忆。运用这些记忆符号,构建记忆话语,发展相应价值体系,获得群体成员的认同和归属感。[9]
对于朱氏宗族来说,朱氏大宗理事会作为群体中的组织,在运用集体文化记忆重建宗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何需要这样的组织?笔者认为有四点原因。
第一,朱氏大宗理事会的成员仍然保有早期参加宗族活动的经历和记忆;而且,他们经历过“文革”,深谙宗族作为“封建的、落后的”事物被禁止和破除的原因。因此,在时间和空间许可的情况下,这一批人能够接续被“文革”砍断的宗族文化脉络,传承宗族文化中的精髓,并规避其糟粕。比如,在以前如果族裔成员家里没有生儿子,就相当于断了代际传承,因为女儿不写入族谱;但在新编撰的宗谱中,女儿及其后代也被写入宗谱;以前宗族祭祀活动只许男性参加,如今的宗族活动男女老少都可参加。在这批人的组织下,宗族构建既和历史上的宗族有相似之处,又能适应当下社会出现的新变化。
第二,理事会成员全部是60岁以上的男性,从个人角度说,他们大都属于“乡贤”,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并熟悉当地的传统风俗。如第一任理事会理事长是退休的中学校长,理事会其他成员还有中学老师。这些人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在经济上或独立,或有儿女孝顺,这为他们参与宗族事务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从文化心理上来说,单纯依赖血缘关系,无法维系紧密的代际关系,尤其海内外相隔遥远。下村朱氏宗族族裔有5000多人,其中约80%都在国外,且多已获得所在国国籍。族里的一位长者说,现在留在村子里的都是“老弱病残”:老年人不愿意出国;“弱”是指老人的孙子辈,在国外出生,被送回国内带大;其他的就是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出国。那些在国外的族裔,大都由于生活、工作原因,无法做到经常回国看望父母;父母也由于路途遥远,不适应国外生活方式,不愿出国与子女团聚。然而,族中老人希望能够密切与海外子女的关系。宗族基于血缘关系和人伦关系,能够成为密切海外子女与侨乡父辈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同时,海外的族裔大都保存有在侨乡生活的经历和记忆,他们的亲人、房产还在这里。因此,他们有能力,也愿意同家乡亲人保持这样的联系。
第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后出国谋生的朱氏族裔在海外逐渐站稳脚跟,这为朱氏宗族重建提供了物质条件。理事会成员ZJ①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所涉及的朱氏宗族成员的名字均为字母缩写。回忆,那时族人都还没有现在富裕,无论是人民币,还是美元等外币,海内外朱氏后裔几十元、几百元地把钱凑起来,为宗族重建提供物质保障。据族里老人介绍,1949年以前朱氏宗族还有一些田产,1949年后族产被充公,族里也就没有土地了。现在也没有土地,不过依靠族裔的捐款,以及平时出租祠堂空间举行活动,族里的族产已经达到了数十万元。
此外,从社会环境角度看,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从“文革”期间的禁止和打击宗族转为默许宗族重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使社会各界开始审视和认可宗族作为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10]朱氏宗族重建具备物质、人力、心理条件,顺应社会发展大势。朱氏大宗理事会作为宗族群体组织,通过募集族产、重修祠堂、重撰宗谱等,运用宗族集体文化记忆,重建宗族;并将宗族成员个体记忆上升为集体的文化记忆,与地方和国家历史勾连,成为地方和国家的集体记忆。下面就朱氏宗族重建过程进行详细分析。
二、认同的凝聚物和固定的点:朱氏宗族集体文化记忆的构建
扬·阿斯曼认为,群体根据在时间/空间架构所产生的社会意志及文化范式,处理集体记忆、地理空间、历史等材料,重新安排它们的意义。为了满足一定的目的,通过叙述方式,这些集体记忆被构建或设计出来。如果只是依靠血缘关系,这种原初的联系会使人忽略与历史脉络的联结,集体记忆的主要根基便失去意义。[11]可以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族群,如何在文化上自我定义和区分,就是通过和祖先、宗族和父母的关系来确立。这是中华民族获得意义和认同的基础,是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显著性认同。朱氏宗族不仅聚焦于当下侨乡父辈与海外子女之间的血脉联系,更重视这种血脉与朱氏宗族的历史联结,夯实海内外族裔成员的纽带联系。
群体借助文化记忆中特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构建集体记忆,被称为“认同的凝聚物”和“固定的点”,往往会被赋予超越自身价值的意义。如用语言、叙述、故事去塑造群体身份,即运用“客体化的文化”,这些客体可以是有形的(如建筑、博物馆、纪念碑),也可以是无形的(如仪式、纪念活动等),形成记忆的结构。[12]朱氏大宗理事会正是运用有形或者无形的客体化文化,重建朱氏宗族集体记忆,使成员获得归属感。具体如下。
(一)借助宗族文化记忆中特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构建宗族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始迁祖朱匡及其相关事件的集体记忆,包括朱匡的传说、朱匡的坟墓、纪念朱匡的怀远亭等,强化构建朱氏宗族的集体记忆。《青田县志》载:“青田自唐始县。”[13]朱匡是青田县设县第一任县令,亦是朱氏宗族青田始迁祖。在《青田县志》中这样记载朱匡:
朱匡,京兆人,光启间令,以勤吏事,卒于官,民不忍其丧去,留葬于旧县治,子孙遂居此守家。[14]
族谱又从朱匡追溯到更远的祖先:
朱氏起源于周代,为古帝颛顼之后,颛顼玄孙陆终第五子名安,赐姓曹,周武王时安之后挟封于邾国(今山东鄒县滕县一带),建都邾(今山东曲华南陬村),后邾国为楚所灭,其子孙去邑,以朱为姓。唐天宝元年(742)朱氏友年公以礼部尚书晋封京兆郡朱氏,郡曰京兆。[15]
有学者指出,许多宗族将祖先追溯到上古时期,难免牵强附会,甚至捏造事实。[16]然而,从文化意义上看,这可视作一种追寻自身文化之根的行为。根据这样的祖先追溯,所有中国大地上的宗族最终都会是炎黄子孙,这亦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据朱氏宗谱载,朱匡在光启年间(885—888)从陕西万年到青田做县令,其长子名彬,字存文,配郑氏,生子一,合厝一都大峙吴垅;次子名褒,授永嘉留守,遂居鹿城,为永嘉派;三子名儼,字存中,授九江通政,遂居家焉,九江之派。朱彬坚守父亲坟墓,是唯一没有做官的儿子,其子孙遍布青田各地,包括油竹、上京、坭岙、屏峰寨、横坑、湖口、小峙、山根、周岙、东源、西岸、大样下等地。1985年统计,青田县朱姓人口共有14351人,是县里第五大姓氏。
《青田县志》载朱匡的坟墓:“唐县令朱匡墓,县南五十步校场巷侧。”[17]据现已80多岁的朱氏后裔XL回忆,朱匡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都在青田县政府中,刚解放时他们还可以去县政府拜祭朱匡。“文革”时期,由于朱匡是“封建统治阶级”,其坟墓从县政府里移出。那时候本来是不准把墓移走的,但是朱氏的一个子孙偷偷地把坟墓移走了,还因此被关了一个星期。后来族里派人去找那个移出的坟墓,一直没找到。20世纪90年代,朱氏大宗理事会在下村公墓中为祖先做了衣冠冢,在村南的山上修建了怀远亭以缅怀祖先。[18]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修坟和丧葬是应有之礼。《论语·学而》记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9]意思是“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归于忠厚老实了”。朱氏后裔重视祖先坟墓,是追求归属感、历史感、道德感的行为模式,是民风德厚的体现。
(二)重修宗族祠堂作为朱氏宗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纪念场所
据朱氏族谱记载,朱氏大宗祠堂原在青田老城宝幢巷。12世祖源公迁居竹溪,建祠定祭,为竹溪房。清朝时,宝幢宗祠毁于火,后重建。重建后的祠堂与宝幢、小峙、西岸各为小宗,但共同撰写宗谱。油竹下村祠堂原为小宗祠堂,分自大宗。然而,历时数年,朱氏其他祠堂均已不在,唯有下村朱氏祠堂依然留存。据村里族人回忆,祠堂原有三进,有门楼。1958年大扒祠堂,门楼和正门遭毁。“文革”时期,朱氏宗族田产充公、祠堂分配给没有住房的村民居住和养牛之用。1993年冬,朱氏祠堂重修,理事会用族裔捐款将住在祠堂养牛的村民迁了出去。1994年,重修完成。XZ介绍,这个朱氏大宗原来叫“里祠堂”,和“外祠堂”相对。“外祠堂”是朱氏第二十一代子孙所造。这个子孙的父亲是过继到朱家的继子,但不被族里承认,于是他的儿子自己造了祠堂,被族人称为“外祠堂”。1958年,在外祠堂的位置建了华侨中学,祠堂大厅做饭厅。“文革”时期,村里把祠堂拆掉建加工厂。1993年“里祠堂”重修时,便把“外祠堂”的祖宗请了过来,合并成一个祠堂。作为“外祠堂”的后代,XZ说:“终究是同宗的。”[20]
(三)朱氏宗族运用多种语言和视觉符号承载宗族的文化记忆
如正厅中的一副对联:名宦开芝田第一留芳远,乡贤配太鹤先生吉庆长。这幅对联讲的是朱匡和青田城的传说(后文将详细叙述)。据XZ讲,祠堂建好后,在正堂挂祖先的画像,结果被人偷走;后来又重新绘制画像挂上,又被偷走。无奈之下只好把画像画在墙上。前文提到族裔成员向大宗理事会捐款,这些捐款人的名字和所捐数额、币种(人民币、美元或欧元)都刻在石碑上,摆在祠堂内。祠堂正门“树发千枝惟一本,水流万派总同源”的对联,从语言层面传达了无论宗族成员身居哪里,获得哪国国籍,这里永远是他们的根系所在。
(四)运用纪念场所空间内举行的活动呈现和激活宗族文化记忆,增强集体参与的归属感
如每年清明节、大年初一,都会召集族裔到祠堂聚餐。ZJ说,大家聚在一起时,互相寒暄,知道了对方在族里面的辈分,明确了亲疏远近关系;交谈之中,成员间增进了解,沟通感情。就像朱氏祠堂正厅中高高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叙伦”两个大字所传达的内涵。《说文解字》说叙:次第也。《释名》解释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说文解字》说伦:辈也。费孝通认为,伦重在分别,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是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如《礼记·祭统》中提到父子、亲疏、夫妇、长幼、上下等都是人伦,都是指有差等的人伦次序。[21]
在依靠外在符号的同时,集体记忆还需要一代代传下去,被不断重新表征和传递。通过各种仪式和纪念方式,个体成员内化并创造作为“朱氏宗族”成员的文化身份。集体的记忆和经历、仪式等都属于看不见的文化记忆,这些文化记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朱氏宗族成员做生日、举行婚礼或丧礼,都可利用祠堂的公共空间。特别是丧礼,送葬队伍要在祠堂中逗留,去世族人照片要放在祠堂,成为丧礼固定环节。
(五)族谱作为重要的语言符号,传承朱氏宗族的文化记忆
朱氏族谱在乾隆癸酉(1753)年编纂而成。按当时谱序中说,以前人数尚少时,族人的生卒年月坟墓坐落尚能记忆。然而,由于“近来荷休养垂裕之泽,生齒益繁”,“恐日后源益远,流益分,不但前此者莫可稽考,而骨肉且路人矣”,族谱因此而生。后来,族谱经过多次续撰。“文革”期间族谱遭到焚毁,幸有族人将民国时期编纂的族谱偷偷藏起来,这成为20世纪90年代重修宗谱的重要蓝本。
通过文字记录的宗谱在构建宗族文化记忆、密切成员关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ZJ说:“这个修宗谱是促进社会和谐,通过修谱知道我们都是同姓、同宗族,就不会争吵了。”同时,不管族裔在美国、比利时还是意大利获得当地国籍,都会被记载在族谱里。ZJ说:
关于祖先年轻人知道的很少,他们出国的人很多。造这个东西很有意义,不然的话,连祖宗都不知道了。特别是我们这个族谱上会记录这个人什么时候去世,墓在什么地方,什么坐向,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大家这个信息总要有的。现在条件好了,一年要祭拜两次,正月初二和清明节。这个大家都有的,总是爸爸给我生下来,孝顺这个意义,这个全国人民都一样的。[22]
所谓集体记忆,是集体通过协议自认为哪些记忆对于他们是重要的,什么样的故事他们需要特别突出记忆,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们想要分享。要成为集体性群体,就需要分享、学习、了解群体历史。这就超越了个体寿命的局限,是更长时间历史的传承。群体历史不仅要被“记住”,更需要成为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语义记忆和片段记忆的集合体,个体需要通过学习和参与仪式进行内化,创造“我们”的文化身份。[23]
三、宗族文化记忆上升为与地方和国家相连的集体记忆
提及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就不能不提到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可以说,哈布瓦赫是文化记忆理论的鼻祖,他提出的个体记忆(individual memory)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强调个体对于“记忆的社会结构(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①埃尔认为,从最基础的层面看,“记忆的社会机构”就是指我们周围的人们。如果没有和其他人的交流互动,个体不仅不能够借助语言和习俗去习得集体记忆,而且也不能够形成自己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借助他人的帮助和陪伴去不断重温有关这些集体互动的记忆和经历。通过与同伴的互动和交流,对于事件的日期、事实、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集体概念,以及思维方式、经历方式,才能成为我们的知识;通过共同参与这些集体性的符号,我们才可认知、阐释和记住过去的事件。家庭生活是最重要的场所,在这里社会文化机制得以习得。因此对于孩子来说,家就是那些构成过去的人物,是重要的“记忆的社会结构”。参见:Astri Erll, “Locating Family in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Vol.42, No.3, May/June 2011, pp.303-318。具有依赖性;集体记忆并不能脱离个体记忆而独立存在。相反,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互相依存;个体通过把自己放在集体/群体的视角保存记忆;同时,只有通过个体的记忆行为,集体记忆才可以被展演、感知和觉察。[24]哈布瓦赫的理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然而到了二战结束后便趋向式微;20世纪80年代,记忆研究又重新为学界重视,被称为“新记忆研究”(new memory studies),其核心集中在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建构与认同,[25]即记忆研究趋向于将个体记忆与民族命运、国家集体记忆联系起来。[26]集体记忆指向当下群体的需要和利益需求,因此,集体记忆的特点是具有选择性和建构性,其中“家族记忆”(family memory)①“Family memory”(家族记忆)是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研究中的焦点之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英语的“family”所对应的汉语释义。埃尔在研究文化记忆理论中的家族记忆时认为,“family”涵盖父辈、祖辈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可以跨越几代,甚至可延伸到久远的祖先。可以说,这里的“family”包含汉语中家庭、家族及宗族的含义。常建华提出,我国对于家族的界定主要分四种:以家族为家庭、家族是小家庭的扩大或组合、家族是家庭与宗族之间的组织、家族包括低层次家庭和高层次宗族。参见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因此,本文将“家族记忆”等同于宗族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类型之一,在个体记忆与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之间的互相转换、选择和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7]朱氏宗族在当下的重构取向之一就是把关于族裔成员的个体记忆建构成为整个宗族的集体记忆,进而与侨乡青田、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使宗族文化记忆上升为与侨乡和国家相关的集体记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朱匡的记忆。朱氏宗族把始迁祖朱匡和鹤城传说放在族谱开篇,把朱匡与青田县城起源联在一起,将宗族集体记忆提升为对青田侨乡的集体记忆。该传说大致内容为:
唐朝时青田县城没有城墙。每逢山洪暴发,瓯江水势汹涌,两岸老百姓就会遭灾。县令朱匡同情百姓疾苦,一心想围滩建城。他上奏朝廷请求拨款,却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开仓放粮以工代赈,发动民工围滩治江和建造城墙。结果连续三次城墙筑不到三尺高,就给山洪冲塌。朱匡一筹莫展。一天清晨,一对白鹤沿着瓯江北面绕后山连兜三圈,长鸣几声向东飞去,就这样重复三天。朱匡意识到白鹤是在给他提示,于是他令衙役跨上骏马追着白鹤跑,黄沙滩上留下一串清晰的马蹄印。朱匡照这些马蹄印划定城基,最终城墙建成。然而朱匡顶头上司因此事对他不满,上书朝廷说朱匡私造城池,笼络民心,图谋造反,皇帝大怒,降旨要将朱匡剥皮抽筋,朱匡含冤而死。后来皇帝知道错杀忠良,于是降旨追封他为鹤神,在县衙前立庙奉祀,人民为了纪念朱匡,把县城称为鹤城,城后的山为太鹤山。[28]
神话与归属感紧密相连,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所处何处提供答案。[29]然而,据《青田县志》引《永嘉记》载“青田”与“太鹤山”的来历:“青田有草,叶似竹染碧,名为竹青,此地所丰,故名青田。有只白鹤,年年生子,长便飞去,故又名太鹤山。”[30]看来太鹤山与朱匡并无联系。朱氏宗族有意将朱匡的形象与整个青田城的文化记忆相连,体现了更加宏大的文化关怀,不仅仅是一种低层面的“集合起来的记忆”。把地方历史与记忆联系起来,就是要保证这个宗族的连续性、合法化,建立比较荣耀的过去,而历史在这个阶段就要为满足当下需要进行适当调整。阿莱达·阿斯曼谈到历史与记忆时说,在文化记忆研究中,神话可指想法、事件、人或叙述,具有符号性价值,且在记忆中被着力刻画并传递。过去人们觉得,神话是假的——这是把神话看作是历史专业知识的对象。如果把神话看作是集体记忆的重大事件,而不是谎言的话,那么不仅仅是神话事件或创造神话那么简单,而是历史事件转型成集体的记忆。神话就是集体记忆的历史,不用真或假来区分,而是一种中性描述。[31]
有关家族的记忆经常是以浓缩的形象为载体,将长期的过程、重复性的行为、风俗和细节性的事件压缩成为人们可把握的家族思想。这种压缩通过单一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将过去含混不清的历史再现出来。不过,记忆很少是为记忆本身而建构,而是有未来行为的指向而进行的自我描述;宗族记忆需要被不断讲述,通过具体的交际和互动,强化成为这个群体的记忆。[32]青田县剧团把朱匡的传说编排成剧,朱氏宗族引以为豪。通过戏剧媒介的传播,朱氏宗族的集体记忆会逐渐成为更加广泛的公众共享的集体记忆,从而更加密切朱氏宗族与地方的联系。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所有的记忆都是个体记忆,无法再生,当个体死亡的时候记忆也就消失了。不过,记忆有两个重要维度:一是个体记忆可以与其他个体之间互动;二是个体与外部符号有互动。一旦用视觉形象表征或叙述出来形成言语,个体记忆就会成为一套符号系统,具有开放性,成为可以与大众共享的集体记忆。[33]朱氏族谱中,朱祥的事迹被特别标示出来。有关朱祥的记忆,原本局限于他自己的家庭范围内,但是当把关于朱祥在国外的这段个体记忆写到宗谱中,就演变成为整个宗族的集体记忆,也具有了非常鲜明的当下和未来指向。朱祥1938年旅居在捷克斯洛伐克,受“中国留德学生抗战后援会”之托,誊写油印《抗战报》,及时在侨胞中散发。[34]朱祥在法国巴黎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宣传委员,负责设计制作共产党报纸。1947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新中国的侨务工作建设。朱祥亦被列为青田侨乡最有代表性的华侨之一。在笔者的调查中,朱祥的二儿子XL讲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事情,并且把父亲的照片、墨宝、当年出国的护照等都摆放在一个专门的房间里。然而,在族谱建构朱氏宗族的集体记忆中,只是选择关于朱祥的这一小段记忆放在族谱里。一旦家族记忆把个人记忆通过比如族谱、报纸等媒介进行传播的时候,个人记忆也就变成集体记忆,家族记忆亦演变成为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形象。[35]有关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正是由于家族记忆的存在,使得这一段历史特别鲜活,长久地存在于朱祥的家人及朱氏宗族的记忆当中,这有助于强化那一段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因此,记住了朱祥的这段个体记忆,就是记住了整个民族那一段艰苦奋斗的革命奋斗史,记住了共产党及中华民族那段历史集体记忆。正如温特(Winter)所认为,家族记忆会使得民族国家关于过去历史记忆的公共纪念活动富有生命力,构成民族国家记忆的基础;如果失去了家族记忆,只保留单纯的民族国家的公共活动纪念仪式,则关于过去历史记忆的事件就会变得空洞。[36]
四、结语
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展现朱氏宗族运用有形或无形的“认同的凝聚物”和“固定的点”,包括纪念碑、仪式、纪念活动等符号重建宗族的具体过程。197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到欧洲,华人独特的文化认同使其在价值观、思维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不同于当地居民。华人认同研究成为欧洲学者研究的焦点。侨乡研究有助于移入国民众了解华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消除对华人的误解和偏见;亦有助于中国找到新的方式处理与海外华人的关系,以便更好适应全球化进程。[37]本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有以下三点。
首先,宗族重建在当下有其必然性,这正反映出历史和记忆的纠葛关系。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所谓历史,不是刻在花岗岩上永恒不变,而是刻在水里,会时刻发生变化,对于历史的解读会周期性出现,且会改变历史进程。[38]什么宗族记忆被保留或被抹去?这是人们在有意识构建宗族必然涉及到的。宗族重建不是墨守成规,有关宗族的记忆不断被选择和利用,成为新的群体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资源。
其次,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宗族重建,要有家乡亲人的召唤和指引。目前,大多朱氏成员虽身在国外,但一直维系着与侨乡的联结。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侨乡的成员,都有意愿保留他们的文化之根,心灵之故乡,精神之乡愁。[39]侨乡中他们的故居、祖先的古墓、祠堂等无疑是重要的物质性纽带。如今,他们的后代对父辈的中国乡村生活文化所知甚少。因此,有必要依靠记忆符号将华侨华人有关宗族、侨乡和祖国的集体记忆一代代传下去。
最后,国内学界对海外华侨华人参与宗族重建研究多集中在广东、福建传统侨乡,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浙江青田、温州新侨乡的宗族重建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用文化记忆理论研究青田宗族重建,将丰富侨乡宗族重建研究的视角与个案,增进国内外学者对青田侨乡宗族的认知,丰富群体构建与文化记忆和历史关系的微观研究。
[注释]
[1] 常建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二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3][5]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2期。
[4] [9][11]Jan Assmann,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Vol.65,No.65, Spring-Summer 1995, pp.125-166.
[6]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1页。
[7] 肖唐镖:《宗族在重建抑或瓦解——当前中国乡村地区的宗族重建状况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8] [12][23][26][31][33][38]Aleida Assmann,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Social Research,Vol.75, No.1, Spring 2008, pp. 49-72.
[10] 邓苗:《乡土传统与宗族重建》,《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夏循祥、李延睿:《宗族、宗族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3] [14][17][30](清光绪六年修)雷铣修,王棻纂:《青田县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55年,第41、371、250、46页。
[15][28]朱氏宗谱,1997年编纂。
[16]陆敏珍:《宁波家谱及其在区域史研究中的价值》,《浙江档案》2005年第10期。
[18]2012年4月29日,笔者于朱氏大宗祠堂访谈XL。
[19]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20]2012年5月1日,笔者与XZ去德清宫路上访谈。
[21]费孝通:《差序格局》,《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22]2012年4月29日,笔者于朱氏大宗祠堂参与式观察续修宗谱并访谈ZJ。
[24] Maurice Halbwachs,On Collective Memory, Lewis Coser (ed.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40.
[25] [27][32][35]Astri Erll, “Locating Family in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Vol.42, No.3, May/June 2011, pp.303-318.
[29] 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
[34]青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田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52页。
[36] Jay Winter, “Sites of Memory and the Shadow of War” , in A. Erll and A. Nunning,, (eds.), in collaboration with Sara B.Young,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2008, pp.61-76.
[37] MetteThuno, Frank N. Pieke, “Institutionalizing Recent Rural Emigration from China to Europe: New Transnational Villages in Fujia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39, No.2, Summer 2005, pp.485-514; Frank N. Pieke,Elena Barabantseva, “New and Old Divers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or’s Introduction” ,Modern China,Vol.38, No.1, January 2012, pp.3-9.
[39] Andrea Louie, “Re-territorializing Transnationalism: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Motherland”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27, No.3, August 2000, pp.645-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