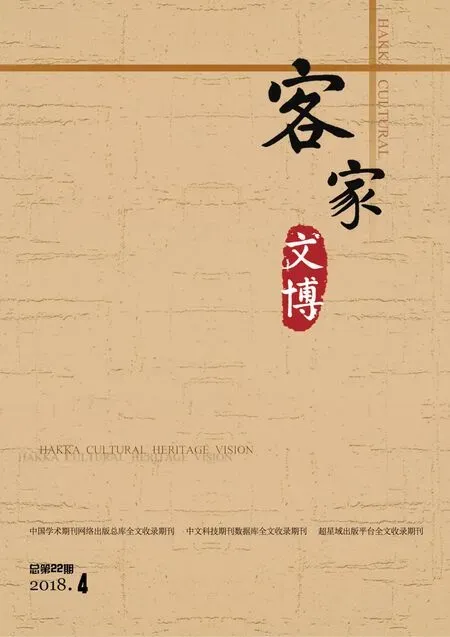牙璋研究综述
2018-01-23唐博豪
唐博豪
一、何为牙璋
牙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考工记》中,“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由于文献资料的言语不详,考古出土器物中又缺少相应的自命名资料,本文所述的牙璋主要特征为长条形扁平状、器身分为刃、身、柄三部分,刃部位于短边处,柄部与器身常见鉏牙,在柄部或器身上常见有圆形穿孔,常见的牙璋材质多为玉、石器,少数为骨、铜器。目前牙璋的发现与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但不可回避的是其中存在着某些研究缺陷。本文拟对2015年以前的牙璋研究文章进行相应梳理,资料多有阙如之处还请方家见谅。
二、牙璋研究历程
金石学在中国源远流长,然而牙璋在很长时间内鲜能进入金石学家的视野,直到晚清时期才被金石学界所关注,伴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为科学的认知牙璋提供了可能。以牙璋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来看,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金石学中的牙璋:从宋代至20世纪20年代末
这一阶段的牙璋发现多集中于古董收藏家和金石学家的著录之中,其研究从属于传统金石学框架之内,研究线索都围绕着《周礼》及其注释展开的,尤以汉儒郑玄、郑众的注释备受推崇。郑玄认为牙璋当是“鉏牙在琰侧”,郑众对牙璋的注释为“牙璋缘以为牙,牙齿象兵,故以牙璋发兵”。宋代聂崇义在《三礼图》中就有牙璋的记载,认为牙璋鉏牙在牙璋的一侧,用以发兵,功能类似于后世的虎符1,但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三礼图》中提及的牙璋乃是附会之图。龙大渊的《古玉图谱》中记载有3件牙璋,其中两件为“缘刻牙文”的器物,另一件在器身上有篆文“起军旅”字样2。然而《古玉图谱》本是托古之书,图谱中“牙璋”形制也并未有实物发现。
第一次真正将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的金石学家当属于晚清吴大澂,他在《古玉图考》中首次将“首似刀”“左右皆正直”“有旁出之牙”的器物考证为牙璋3,这在牙璋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吴大澂的学说在国内外的牙璋研究中都颇为流行,乐提在《中国玉器源流考》中直接将牙璋音译为“YA-CHANG”,认为是王权的象征4。萨尔摩尼、杰西卡·罗森等学者将这种玉器称为“scepter”5,“scepter”一词有王权、君权的意思,明显是牙璋“起军旅,治兵守”的意译。除了吴大澂外,我们在卢芹斋、黄濬、罗振玉6等人的藏品中看到牙璋的身影。关于牙璋年代的判断皆是通过《周礼》及其注释来完成的,多将年代定为商周至汉时期。
(二)“明暗双线”下的牙璋:20世纪20年代末至70年代末
这一阶段牙璋的发现主要由两条不同的路线构成,一条是来自于国内外收藏研究机构和收藏家的征集和收购活动,如萨尔摩尼、乐提、弗利尔、古特曼、劳费尔7等人在中国都直接或间接的收购有牙璋,国内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旅顺博物馆8也曾有过收藏牙璋的历史,这条线索下的牙璋往往缺乏时代背景和埋藏线索,但却是这一时期研究牙璋最为重要的一条“暗线”。另一条路线是科学考古出土的牙璋,自20世纪30年代前后,伴随着现代科学考古的引入,牙璋屡被发现,这构成了牙璋研究的“明线”。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的牙璋认知较为混乱,相关研究中出现了牙璋和琰圭的两种不同观点,在考古报告中更是有铲、戈形圭、玉立刀、戈形器、戈形端刃器等9不同的称谓,突显出独立于金石学之外命名方式的特点。就研究内容来讲已经处于科学考古研究范围之内,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制作工艺、时代关系和类型学演变等诸多方面,但由于考古材料缺乏导致形态演变研究、使用方法和功能等方面的深层次讨论不足,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更为丰富的“暗线”材料,并结合文献辅证,形成“明暗双线”的研究格局,由此亦可理解为何这一阶段的研究结论多囿于传统金石学观点的原因了。这一阶段的牙璋研究明显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全面的、具体的讨论还有待新资料的进一步丰富。
最早在考古活动中发现牙璋的当是美国学者葛维汉,他在《广汉发掘简报》中刊布了1931年广汉遗址发掘的详细过程,其中不乏有牙璋的出土,文中将其称为“玉刀”。葛维汉将广汉出土器物与安阳殷墟、奉天沙锅屯等遗址进行了细致比较,将广汉文化年代考订为公元前1400公元前1100年。值得一提的是,葛维汉还邀请了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戴谦和对广汉玉器的硬度和加工工艺进行了分析,戴谦和对广汉玉器做了如下结论:“器物上的有些刻纹是采用强压力制作使用拉紧的金属线制成的,其他纹线略呈弯形,器侧刻的纹线都很平直,这些匀称工具,均属实用工具,具有艺术纹路和良好的手柄,当时有这样的艺术品是令人叹服的”10。葛维汉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无疑具有现代考古学意义,尤其是对玉器工艺的观察,尽管这一观察尚不成熟,但可谓是高屋建瓴之举了。
郑德坤在《四川古代文化史》中梳理了四川广汉1929年(一说是1931年)的发现情况,援引郑司农、戴东原、吴大澂等相关文献资料,从器物形态上认为“狭长而薄,口端锋锐,向内凹进,作半圆形,左右成两棱角,柄端有圆孔,柄刃之间有不整齐之牙向两旁突出,间有平行直锯纹数道”的器物与《典瑞》中的琰圭相似,并将燕氏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玉刀”考证为琰圭,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700年之间,根据“琰圭”的出土背景推测该地是“祭山埋玉”之所,而这里的“琰圭”即是本文所说的牙璋了11。
凌纯声搜集了73件国内外的玉圭资料,按商周汉的年代进行分类描述,利用罗福颐《传世古尺录》、杨宽《中国古尺录》的著作对古圭进行了重新厘定,归为大圭、镇圭、命圭、琬圭、琰圭、榖圭六大类,并将本文所说的牙璋考订为琰圭,年代为商周时期12。然而,缺乏田野考古基础的类型学划分和年代判断并不准确,但却是牙璋类型学上的一次积极尝试。
1963年萨尔摩尼公布了他在北京征集到的牙璋资料,并对牙璋的柄部和刃部观察,臆断其来源于剥鱼的工具,年代判定为周代器物13。其后,林巳奈夫发文予以反驳,对萨尔摩尼牙璋来源推断进行了完全的否定,并通过河姆渡遗址、张家坡遗址出土的骨铲推测牙璋来源于骨铲14。
1979年冯汉骥、童恩正在《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中肯定这种器物是牙璋,但并不认为牙璋的牙来自于“鉏牙之饰”,而是牙璋之牙象征牙齿,有威胁攻击之义,取“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之意,其起源与玉戈、砺石有关15。
(三)新时期的牙璋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
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可以称得上是牙璋研究的高峰期。新的考古发掘材料遍布全国,在研究方法和认知上都有了更为深入的变化,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归结集中讨论、系统研究和问题复杂三个特点。集中讨论即为以牙璋为专题的大型会议多次召开,进行集中讨论牙璋问题;系统研究即为摆脱了金石学和文献学的束缚,以考古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阶段;问题复杂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细化出三个小的阶段,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21世纪初到现在。
1、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牙璋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考古活动发现了一大批牙璋资料,以石峁和二里头遗址牙璋的发现为契机将牙璋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林巳奈夫以石峁牙璋的发现为线索,通过扉牙的演变对牙璋进行了时代划分,认为其产生年代要比《周礼》记载的牙璋要久远得多,是否具有“起军旅,治兵守”功能是可疑的,牙璋的命名是不合适的,应当称为骨铲形器16。夏鼐则以安阳殷墟出土玉器为背景,结合石峁、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牙璋对其进行了考释,认为这种器物在殷墟中便已经罕见,不会是《周礼》中的礼玉或瑞玉,应当将其称为刀形端刃器,它的古名和用途还不清楚17。尽管这十年间的研究性文章相对偏少,但意义重大,林巳奈夫和夏鼐的研究将牙璋从金石学影响下彻底剥离出来,奠定了日后牙璋研究的基本格调,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以考古发掘品为基础,然后再去结合文献”的模式,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与以往研究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具有着分水岭般的作用。
2、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牙璋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牙璋及其相关遗址文化属性得以确定,“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会议”的召开更是将牙璋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此次会议收录的52篇论文中有20多篇专门讨论牙璋的,而撰写者多为直接发现和研究牙璋的学者,涉及到牙璋的命名、时代、源流、演变、功能等诸多议题。此外,海外流散牙璋相关资料也得到李学勤、邓淑苹、张长寿、王永波18等人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之上,这些发现和整理催生出一大批牙璋研究文章,林巳奈夫所提出的“骨铲形器”的假设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多的认可,郑光、张雪海、戴应新等学者先后发文予以肯定,认为牙璋来自于耒耜一类的农耕器物,是其形象化的体现19。夏鼐提出的“刀型端刃器”也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并演化出了“耜形端刃器”“歧锋端刃器”等多种称谓。当然,“牙璋”一词也保留下来,但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正如郑光所说的“可以沿用牙璋的名称,但必须要与文献中的‘起军旅,治兵守’的牙璋严格区分出来”20。
诸多学者在牙璋形态演变趋势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基本上确立了鉏牙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变简单,锋刃由斜弧刃变V型刃。从年代上基本肯定了牙璋在龙山时代开始出现,到商末在中原地区基本消失,部分地区沿用至西周战国阶段。对于牙璋的功能或用途,一些学者多认为是礼器或祭器,具有宗教意义;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牙璋是世俗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可能用于调兵的信节。总之,牙璋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人们物质、精神追求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然而学者间对类型划分和年代分期上存在着明显不同,代表性有郑光的“两期四段”、张雪海的“四种类型”、邓淑苹的“五种类型”、王克林的“三期说”、裴安平的“两型十式”以及陈德安对三星堆牙璋“三大型十一个亚型二十八式”等21,1996年王永波发表了《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一文,他收集了国内外牙璋共计248件,根据形态变化分为五型三十一式,是目前为止牙璋资料收集最为丰富的,较为全面的梳理了牙璋的发现和演变,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22。然而,受限于分析方法、观察手段和器物时空范围等诸多因素,这些研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牙璋的类型划分和年代分期的争论。
在牙璋起源地的探讨上形成了“南方起源”和“北方起源”两种不同观点,李学勤、牟永抗二人依据良渚出土的器物图案推测牙璋长期存在来于南方,并向北传播,山东所见的牙璋应当是受良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23。北方起源的北方特指黄河流域,饶宗颐认为牙璋起源于黄河流域,并不断向南传播,直到越南地区24。与此同时,由于北方地区所见牙璋多为采集而来,信息较为零散,缺乏较强的断代依据,形成“山东说”和“陕北说”不同的观点。张雪海、杨伯达、邓聪等人认为牙璋起源于山东地区,而郑光、张长寿、邓淑苹等人则认为牙璋来自陕北地区。
裴安平则对传播路线进行了细致的推测,认为牙璋的传播以长江流域为中介区,西线有湖北至湖南,入广西下越南;东线有长江下鄱阳湖经广东始兴、南雄入岭南25。林向提出了“中华牙璋”的概念,文中认为牙璋在三代中内涵各不相同,分别代表古蜀、鬼方、东夷、百越相互涵化的文化关系,牙璋南传闽粤,远布红河流域不仅限于文化交往的层次,而与民族迁徙有关26。
3、21世纪初至今的牙璋研究
进入21世纪后,牙璋研究者对以往观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一些新的观点也被提出。与此同时,牙璋研究中更加关注“人”的作用,结合文献资料和实验考古,开始了国家起源、文化传播等更深层次方面的探讨。
徐心希27、 彭长林28、谌小灵、李岩、王亮29等人分别就福建漳浦虎林山、越南北部、广东地区出土牙璋作为突破口对岭南(含越南北部)一带出土牙璋进行了相应讨论,涉及到文化传播路线、方式等诸多方面。江章华对牙璋传播路线进行了重新考量,认为东线从山东、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到香港、越南,传播时间从龙山晚期就已经开始了,西线从长江中游进入四川盆地,再到越南,传播时间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到商周时期结束,由于越南牙璋兼具早晚两期特征,应当是受东西两线影响下形成30。
邓淑苹、邓聪分别就“陕北起源说”和“山东起源说”不断的搜集证据,补充和完善各自的论点,邓淑苹将中国玉器分为华东和华西两大区域,华西玉器主要为牙璋、大刀、圭、壁、素琮等,玉料以深褐、灰青、墨绿为常见,与华东玉器的璧琮系统有着明显的区别31。并在《龙山时期四类玉礼器的检视与省思》中进一步指出山东地区零星出土的牙璋多为交易所得或前朝遗留,是华西玉器向东扩展的结果,而牙璋最终在中原地区的消失与属于华东系统的商族西进有关32。邓聪对山东龙山式早期牙璋进行了细致观察和分析后认为以罗圈峪YL:10、大范庄LD:211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出土牙璋从年代和各种技术特征的组合均反映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古老牙璋的特征33。同时,邓聪从形态特征和制作工艺两方面出发,将二里头VM3:4牙璋与南方地区出土牙璋进行对比后认为“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西南金沙所见影响是直接的,对东南地区大湾、虎林山则是间接的波及,南中国所显示二里头牙璋特征的传承关系十分明显。”在文章的结尾,邓聪认为二里头牙璋等实物资料的发现,足以论证夏王朝政治理念的时间,是东亚广域国家起源的关键34。
此外郭静云、孙庆伟和朱乃诚对牙璋起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静云认为屈家岭、石家河遗址出土的斜刃微弧璋是最早的牙璋雏形,向东影响下产生山东龙山牙璋、向北则是中原牙璋、向西则是四川类型牙璋,向南则传播至广东福建一带,越南出土牙璋则可能与四川三星堆牙璋有关,而石峁牙璋的来源则掠夺自南方35。孙庆伟、朱乃诚提出了牙璋起源地在河南的见解,孙庆伟在《<考工记·玉人>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认为牙璋中的牙饰不能作为玉器命名的主要依据,璋、戈为同类器的时代差异,牙饰退化,牙璋变成玉戈。并认为玉戈、玉圭、玉璋异名而同类器物。并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一步将这种器物考证为夏代的玄圭36,颇成一家之言。其后,孙庆伟刊发了《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和《再论“牙璋”为夏代的“玄圭”》两篇文章,并认为石峁牙璋不是普遍分布的且玉质选材和埋藏环境不同于玉铲、玉璜,当另有来源,而山东龙山高等级遗址和墓葬不见牙璋,且多为采集品,不支持牙璋起源和流行于山东龙山文化的观点,“牙璋”当起源于夏人活动的河南区域之内,是夏人的“玄圭”,并伴随着夏文化的扩展、迁徙或文化交流等原因大量流传到山东、陕北和成都平原等地,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高等级遗址和墓葬的考古缺失是“礼失求诸野”的典范37。朱乃诚根据牙璋的流传和分布特征认为牙璋起源于河南,是探寻夏代史迹和“汤作夏社”的线索,山东、陕西和四川发现的牙璋很有可能与夏部落在夏王朝之后或夏社被废之后四处流窜的史迹有关38。
三、研究前瞻
牙璋研究历程可以说是一部缩略版的金石学与考古学关系史。吴大澂等金石学家虽然将牙璋研究扩展到文献之外的实物上,但研究方式和方法依旧囿于传统史学早已建立的框架,是传统史学的衍生品,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些学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认为出土牙璋就是吴大澂所说的牙璋是文献中“起军旅、治兵守”的牙璋。其后,葛维汉、凌纯声、冯骥才等人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做是科学考古学的范围之内,但基于条件限制,牙璋研究不得不引用大量非考古出土材料,其结论依然是片段化、零散化的。自林巳奈夫、夏鼐之后,全国范围内出土牙璋的情况逐步清晰起来,新资料的出土和中国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进一步完善,极大的推进了牙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当然,牙璋具有存在时间长,器形变化慢的特点,属于考古学中的一种非典型器物,其形态演变并不单纯,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技术发展的物化形式,用传统的考古学方法进行阐释往往会有较大的认识偏差,这是牙璋研究的难点之一。另一方面,牙璋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即是中国文物的流散问题,即本文所提及的暗线,大量的牙璋流转至世界各地,多种因素汇杂在一起导致了数量非常大的牙璋缺失了原有的考古学埋藏背景,来源地已经不可考证,有来源地的出土背景也已经不可复原,这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极大的损失。事实上,也正是这也难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不断利用多学科、多视角的对牙璋进行研究。
从牙璋研究的历程来看,牙璋研究者逐步突破了“以文献论牙璋”“以牙璋论牙璋”的阶段,进一步的“透璋见人”,探索牙璋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必将是牙璋研究的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