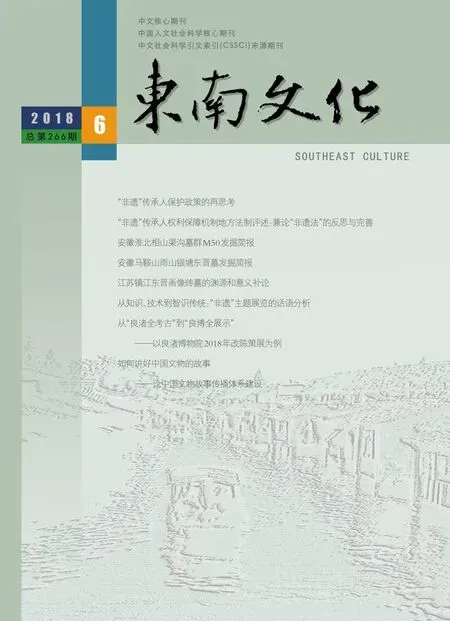北宋中期越窑瓷业技术传播及相关问题研究
——兼论核心区越窑瓷业衰落原因
2018-01-23谢西营
谢西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内容提要:北宋中期,以浙江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瓷业核心区窑址数量急剧减少,窑场规模缩小。与之相对,浙江其他地区却发现了大量这一时期的窑业遗存。研究显示,限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北宋中期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核心产区不再适宜大规模的瓷业生产,而这直接迫使制瓷工匠作出选择,或许其中一部分工匠开始另辟他地继续从事窑业生产,从而在浙江范围内出现了众多这一时期的窑址。此外,在瓷业技术的传入过程中,制瓷工匠也结合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创新。
传统观点认为,北宋中期是越窑制瓷史上的转折时期,是越窑瓷业生产由繁荣走向衰落的一个时间节点。支持此观点的一个重要证据便是越窑瓷业核心区窑址数量的急剧减少。然而据最新考古调查、试掘及发掘资料显示,在越窑瓷业核心区之外却存在大量这一时期的越窑(系)窑址,且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尤其是在一些原本没有任何窑业传统的地区突然出现这一时期的窑址,产品风格、瓷业技术与核心区保持同步。探索其中缘由,对于探索北宋中期越窑瓷业技术传播的动因、模式与面貌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北宋中期越窑瓷业生产年代及面貌界定
1998—1999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浙江省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实施的慈溪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考古发掘及整理过程中,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对考古发掘材料进行了整理,并结合纪年器物的排比,将北宋越窑制瓷业分为三期:北宋早期(960—1022年),即吴越国晚期至北宋真宗时期;北宋中期(1023—1077年),约为北宋仁宗至神宗熙宁年间;北宋晚期(1078—1127年),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至钦宗时期[1]。为了对北宋中期浙江地区越窑(系)窑址进行横向比较,本文拟采用寺龙口窑址的分期意见对北宋中期越窑瓷业生产年代进行界定。
寺龙口窑址发掘资料显示,越窑制瓷业生产面貌在北宋早中晚期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与北宋早期相比,北宋中期越窑器物种类明显减少,仍以饮食器具为大宗,而香具、文房用具等精品雅玩器物则不多见,器类主要有碗、盘、盒、钵、执壶、盏、碾臼、碾轮、熏炉、盏托、水盂、夹层碗、枕、多管灯、瓶、器盖、盖罐等[2]。器物总体质量明显下降,器物的制作一改晚唐五代及北宋早期的精工细作,而逐渐趋向粗放[3]。胎釉较之前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由于装烧方法的变化,釉色纯净度降低,釉色开始偏青灰色,多数缺少莹润光泽,品质下降。装饰方面,早期严谨规整的细线划花工艺趋于懈怠与简化。细线划花虽在本期得以继续沿用,但题材始终不及北宋早期多样,且了无新意;器物纹样种类较之前减少,图案趋于简化,莲蓬纹、龙纹、孔雀纹、飞雁纹、喜鹊花卉纹、对蝶纹、翔鹤纹等寓意丰富的纹样题材消失不见。需要注意的是,刻划花装饰的出现并盛行则成为该期最显著的特征[4]。装烧方法上,此期较早阶段少数质量较高的产品仍用匣钵单件装烧,坯件之间间隔垫圈,器物制作尚为精细。进入后期,为提高产量而大多采用明火叠烧或匣钵叠烧,且在碗、盘等器物的内底还留有支垫的泥圈,从而影响了器物的美感。
二、北宋中期浙江地区越窑(系)窑址的分布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暂且按照窑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北宋中期浙江地区越窑(系)窑址的分布情况划分为浙东、浙西和浙南三个大的区域。
(一)浙东地区
1.核心区域
作为唐宋时期越窑制瓷业的核心地区,慈溪上林湖窑址群包括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和古银锭湖四个片区。据统计,在这一区域内存在159处唐宋时期的越窑窑址,其中北宋时期窑址有83处,包括上林湖窑区51处、白洋湖窑区8处、里杜湖窑区8处和古银锭湖窑区16处。与北宋早期相比,北宋中期窑址数量明显减少,据统计仅(约)有18处,其中上林湖窑区8处、白洋湖窑区6处、里杜湖窑区3处和古银锭湖窑区1处[5]。
2.外围区域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上虞地区和鄞州东钱湖地区都被视为唐宋时期越窑制瓷业的三大中心之一。但据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区域内唐宋时期的窑址数量较少,其中前者约34处,后者约18处[6],均无法与上林湖窑址群相比,故而唐宋越窑三大中心说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两个区域内现已探明的北宋中期窑址有上虞窑寺前[7]、盘口湾、蒋家山、合助山和道士山窑址[8]等,鄞州东钱湖郭童岙[9]和上水岙窑址[10]。
再向外围扩展,诸如绍兴地区的上灶官山窑址[11],嵊州地区的缸窑背、下阳山、下郑山和下五岙窑址[12],奉化地区的于家山窑址[13]、宁海地区的岔路窑址[14],临海地区的凤凰山和后门山窑址[15],黄岩地区的凤凰山、金家岙堂、瓦瓷窑、下山头和左岙坑窑址[16]等都属于这一时期的越窑系窑址。
(二)浙西地区
这一区域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婺州窑窑址分布区,但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学界对于婺州窑的概念、产品面貌及瓷业技术传统等方面问题仍有很大盲区。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系统推进,在此区域发现了若干北宋中期的窑址——东阳地区的葛府窑址群[17]、歌山[18]和象塘窑址[19],浦江地区的前王山、白泥岭、徐家、徐家岭和东庄垆窑址[20],兰溪地区的嵩山窑址[21],武义地区的蜈蚣形山窑址[22]。限于已有观念与认识,在发现之初,很多学者都将其先入为主地判定为婺州窑窑址。但是随着认识的加深,特别是通过对浦江县前王山窑址的系统考古发掘并对比武义蜈蚣形山窑址早期发掘资料,其产品面貌、器形、装饰技法乃至装烧工艺都与同时期越窑核心区产品一致,故而应将其归入越窑系窑址。此外建德地区大慈岩脚窑址[23]和富阳缸窑山窑址[24]也有这一时期产品的生产。
(三)浙南地区
2013—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浙江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组队对龙泉地区的窑址(包括龙泉东区和南区的大窑、金村和石隆片区)进行了系统调查并选取个别地点进行了小范围试掘。调查显示,龙泉窑早期阶段的淡青釉产品仅在金村片区存在。在金村片区窑址调查发现34处窑址点中仅有4处有淡青釉产品存在,分布在溪东、下会、大窑犇及其对岸地区。在调查基础上,我们选取大窑犇窑址作为重点区域进行了小范围试掘,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地层堆积情况[25]。试掘资料显示,尽管胎釉有别,但是绝大多数淡青釉产品无论是从器形、装饰,还是从装烧工艺等方面来看,均与北宋中期越窑产品相同。此外调查采集的“甲申”款淡青釉器盖和英国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藏“天圣”纪年的淡青釉敞口碗也将该类器物的生产年代框定在北宋中期。
三、北宋中期越窑瓷业技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模式与面貌
(一)越窑瓷业技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兼论核心区越窑衰落原因
北宋中期开始,越窑核心区的窑址数量迅速减少,生产规模下降,呈现出衰落迹象,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原因。
1.内部原因
内部原因主要是基于越窑窑址本身。
首先,原料方面。越窑自唐代晚期创烧秘色瓷器以来,不惜工本,不仅瓷器产品使用优质瓷土,就连装烧用的匣钵也采用优质瓷土,且一匣一器、匣钵接口处用釉封口,并在烧成后只有打破匣钵才能取出产品。当然采用这种工艺确实提高了产品质量,但对瓷土资源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优质瓷土资源有限,且在短时间内不可再生,随着优质瓷土的日趋匮乏,越窑核心区基本丧失了能够保证大规模生产所需的优质原料供应条件[26],进而采用普通瓷土乃至更低档次的瓷土,使得胎料质量下降。就目前资料来看,自唐代晚期以后越窑瓷器胎料质量就已开始呈现出退步的迹象。
其次,燃料方面。整个南方地区瓷业产区包括上林湖越窑核心产区所使用的窑炉均为龙窑,以木柴作为燃料。唐宋时期龙窑的形制基本趋于稳定[27],长度大概在40~50米,每次烧窑所需要的木柴总量无疑是很大的,因而燃料的供应问题及其对环境的破坏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对此,庄绰《鸡肋编》的相关记载或可给我们些许启示:“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今驻跸吴、越,上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徧,芽蘖无复可生。”[28]
第三,工艺技术方面。化学测试显示,越窑瓷器在长时期内胎釉化学组成几无变化且烧制工艺墨守成规[29],缺乏创新。尽管从北宋中期开始越窑瓷器逐步将其生产重点转为刻划花青瓷,但是刻划花青瓷质量平平,使得其逐渐丧失了市场竞争力,丧失了生存的基础[30]。
2.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是基于越窑所处的国内外环境。
首先,国内环境因素。作为外部因素之一的土贡制度也与越窑的兴衰密切相关。历史文献对北宋中期的越窑贡瓷的记载,仅《宋会要辑稿》中有一条且数量较少,“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二月,尚书户部上诸道府土产贡物……越州……秘色甆器五十事”[31]。而在此之前的上一次进贡则要上溯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且贡瓷数量极大,“四月二日,俶进……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32]。从中便可见越窑贡御地位的逐渐丧失。在此之后仅《元丰九域志》中再次提到元丰三年(1080年)的越窑贡瓷,“土贡:越绫二十匹,茜绯花纱一十匹,轻容纱五匹,纸一十张,甆器五十事”,之后越窑贡瓷便再无相关记载。贡御地位的逐渐丧失,一方面源于越窑本身产品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与其他地区如北宋东西两京开封、洛阳周边地区以及定窑、耀州窑等地窑场制瓷业的逐步兴盛等有着密切关联[33]。另外王安石变法的推行也对越窑贡瓷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34]除此之外,国内普通市场也逐渐萎缩[35],甚至窑址周边地区市场也被其他窑口瓷器尤其是青白瓷大量挤压[36]。
其次,国外环境因素。唐宋越窑的对外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越窑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陶瓷通过海路的大规模外销始于8世纪中叶,在9—10世纪迅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时期[37]。在这一进程中,越窑瓷器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印度尼西亚地区发现的唐宝历二年(826年)黑石号沉船[38]、10世纪中叶的印坦沉船[39]和10世纪后半叶的井里汶沉船[40]出水的大量越窑瓷器即是明证。但是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11—13世纪中叶),尽管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持续进行,但从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虽然还有少量的发现,但规模很小,这些零星的资料甚至不能支持大规模海上贸易的水平[41]。这种现象很可能与占据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王国先后与爪哇岛的马打兰王国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国的战争有关,这些战争使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水道马六甲海峡处于交通不畅的状态,从而阻滞了当时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42],特别是阻滞了中国瓷器的输出。
总之,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越窑核心区制瓷业处于恶劣的境地。自入宋以来,两浙地区的经济获得巨大发展,至熙宁十年(1077年)“夏税两浙最多,二百七十九万七百六十七贯硕匹斤两”[43]。两浙地区范围内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无疑是农业经济高度发达之地。而制瓷业作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其生产需要占据较大的场地及大量的原料、燃料资源,且烧窑也具有一定的风险系数。北宋中期余姚县令谢景初曾对龙窑的烧成率低这一问题有相关记录:“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贾,斗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扑,争乞宁有厌?鄙事圣犹能,今予乃亲觇。”[44]此外,北宋以来人口大量南迁,使得南方地区劳动力十分充足,与制瓷业相比,农业生产成本较低而利润较高,加之宁绍一带经济繁荣导致工匠的雇值较高,使得这一地区不再适宜于制瓷业的大规模生产。而这也迫使拥有着制瓷手艺的工匠作出选择,是改行从事其他事业,还是另辟他地继续从事窑业生产?各地新出现的北宋中期的越窑系窑址或许可提供些许启示。
(二)越窑瓷业技术对外传播的模式
就目前考古调查资料,我们暂可将上述核心区以外的越窑(系)窑址所在地区以北宋中期为界,并结合当地的窑业生产传统分为两类:第一类,传统窑区。地处浙东的上虞、鄞州、绍兴、临海、黄岩和地处浙西的东阳、武义地区的瓷业生产都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地处浙西的兰溪地区的瓷业生产可追溯到唐代早期,地处浙东的奉化地区的瓷业生产可追溯到五代时期。当然传统窑区内的瓷业面貌比较复杂,个别地区本无窑业,到北宋中期开始出现,如兰溪嵩山窑址等;个别窑址在早期窑业基础上继续生产北宋时期产品,如上虞窑寺前窑址始于五代时期、绍兴上灶官山窑址始于唐代晚期、东阳歌山窑址始于唐代早期和武义蜈蚣形山窑址始于唐代晚期。第二类,新兴窑区。地处浙东的嵊州和宁海地区、地处浙西的浦江地区以及地处浙南的龙泉地区的窑业生产都开始于北宋中期,少数几个窑址后期有延烧。
关于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传播,有学者曾总结出三种模式:一是近距离的逐渐扩散,二是远距离的直接传播,三是制瓷技术中单一或几种因素被其他窑系吸收[45]。传统窑区内有一套固有的生产工艺流程,不太容易接受新技术,应该接近于第一种模式,属于越窑瓷业技术为其他地区窑业生产所接受的结果。而新兴窑区没有任何窑业生产基础,在具备一定窑业资源的情况下,随着新技术的传入只要接受便可立即投入生产,应接近于第二种模式,属于越窑瓷业技术向核心区以外地区的扩展。北宋中期浦江地区制瓷业的兴起为我们探讨该问题提供一个典型案例。
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县文保所对前王山窑址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并对周边地区的窑址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一区域的窑业生产始于北宋中期,面貌较为一致并形成一定的窑业集群。在窑址调查期间,我们还对周边的窑业资源及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了调查。首先,自然资源因素。第一,窑址周边地区瓷土矿丰富,白泥岭附近山体断面上可见瓷土矿裸露的迹象。第二,窑址区域地处仙霞岭龙门山脉支脉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较高,可为瓷器烧造提供充足的燃料。第三,周边水源充足,溪流纵横。其次,社会经济因素。第一,尽管地处群山峻岭之间,但窑址所在区域地处两浙路南北陆路交通干线的必经之地,其间古道相通如白泥岭、五路岭等,交通相对便利。五路岭古道古已有之,“一径高盘十里余,人心马足厌崎岖。只凭顽石专为险,不识青云自有衢。地气难通树多瘦,阳晖应近草先枯。我行方欲奋遐蹠,顾尔安能碍坦途。”[46]北宋中期浦江县令强至所作《五路岭》古诗即是明证。第二,地方官员为发展当地经济作出巨大努力。“浦阳在婺为穷山,商旅之过婺者,多道旁邑。”[47]针对这一现状,当地监征官钱宗哲为鼓励商贾前来,“凡商旅之过者,必裁减其数而征之。繇是皆愿出其途,而常岁之课愈登羡。”[48]第三,自宋以来,金衢地区由于交通和资源等因素的限制,以肩挑进行流动经营方式为主的各种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挑夫群体形成的“行担经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49]。这一经济模式正好与处于崇山峻岭之间的前王山窑址群相适应。
(三)越窑瓷业技术对外传播的面貌
北宋中期在越窑瓷业技术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被传入地区对于这一技术的接收程度如何?是全盘接受,还是有所创新?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对越窑核心区和核心区以外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进行整体比对,发现被传入地区在继承核心区主流技术之外还进行了部分创造。瓷业技术大致可以分为器形、胎、釉、装饰技法和装烧工艺等五个方面。首先,器形方面。被传入地区窑址的绝大多数产品类型都可在核心区窑址中找到相同类者,但部分地区如龙泉地区也适应当地葬俗需要生产出盘口瓶、多管瓶等特殊产品[50]。其次,胎釉方面。古代制瓷一般就地取材,因而胎釉成分受当地资源状况所限,无法与核心区完全一致,如龙泉金村地区在北宋中期的产品釉色呈现出淡青的色泽。当然具体的胎釉配方及成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还有待于科学检测。第三,装饰技法方面。绝大多数窑址在继承的基础上都有所创新与发现,如宁海岔路窑址新出现内底圆心下凹或刻有一圈弦纹的碗,此外作为碗盘类产品主要装饰纹样的龙头海水纹也不见于上林湖窑址[51]。第四,装烧工艺。浦江前王山窑址新出现了适应于执壶烧造的平底椭圆形匣钵,宁海岔路窑址中发现的元宝形支垫具也不见于其他窑址[52]。
四、结语
北宋中期是越窑制瓷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与早期相比,这一时期以上林湖窑址群为代表的越窑核心区呈现出窑址数量急剧减少、窑业生产规模缩小的态势。而与之相对,在核心区以外越窑瓷业生产则表现出窑址数量不断增加、空间分布不断扩展,在诸如浙东的上虞、鄞州、绍兴、嵊州、奉化、宁海、临海和黄岩,浙西的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建德乃至浙南的龙泉地区都出现了这一时期的越窑(系)窑址。分析其中原因,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越窑核心区基于多方面因素压力被迫减产而与之伴生的窑工向外迁移,以及核心区窑业技术向外传播存在着莫大关系,核心区以外新出现的这批窑址尤其是嵊州、宁海、浦江和龙泉等窑区的兴起即是重要证据。在越窑瓷业技术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对于上虞、鄞州等为代表的传统窑区和以浦江、宁海等为代表的新兴窑区在对新技术的接纳过程中所采用的模式可归纳为逐渐扩散和直接传播两种,当然,这也要基于当地具备烧造瓷器的资源条件。此外,在对被传入地区的窑业面貌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各地越窑(系)窑址在继承和吸收核心区主流技术的同时,还结合当地需求与环境进行了自我创造,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纹样装饰乃至装烧工艺技术。当然关于北宋中期越窑瓷业技术传播这一课题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瓷业技术传播的动态过程、瓷业技术传播过程中与其他行业的互动与竞争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的持续追踪。此外,限于材料,北宋中期浙江地区的窑业面貌还存在着很大盲区,还有赖于我们今后的持续考古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
[2]秦大树、谢西营:《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越窑的历史与成就》,《叠翠: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藏青瓷精品》,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44页。
[3]陈克伦:《宋代越窑编年的考古学观察——兼论寺龙口窑址的分期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2期。
[4]郑嘉励:《宋代越窑刻划花装饰工艺浅析——以碗、盘为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年。[5]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此外Y37为荷花芯窑址,经2014—2015年和2017年上半年的发掘显示,该窑址在北宋中期仍有烧造。
[6]任世龙、谢纯龙:《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越窑》,江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7]汪济英:《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文物》1963年第1期。
[8]201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资料。
[9]a.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郭童岙越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b.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编著:《发现——宁波地域重要考古成果图集(2001—2015)(下)》,宁波出版社2017年,第186—197页。
[10]罗鹏:《浙江宁波东钱湖上水岙窑址考古发掘概况》,《陶瓷考古通讯》2016年第1期;罗鹏:《宁波东钱湖上水岙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30日第8版。
[11]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上灶官山越窑调查》,《文物》1981年第10期;沈作霖:《绍兴上灶官山越窑》,《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
[12]嵊州市文物管理处编:《嵊州文明形迹》,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13]同[9]b,第178—185页。
[14]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海县文管会办公室:《浙江宁海县岔路宋代窑址》,《考古》2003年第9期。
[15]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题性调查资料。
[16]201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黄岩地区窑址进行过专题性调查。此外早期发表资料可查金祖明:《浙江黄岩古代青瓷窑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第8期;宋梁:《黄岩宋代青瓷窑址调查》,《东方博物》2012年第1期。
[17]赵一新、叶赏致、王卫明:《解读葛府窑》,载罗宏杰、郑欣淼编《’09古陶瓷科学技术7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18]贡昌:《记浙江东阳歌山唐宋窑址的发掘》,《婺州古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19]朱伯谦:《浙江东阳象塘窑址调查记》,《考古》1964年第4期。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浦江县前王山窑址考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8年第4期。
[21]贡昌:《记浙江兰溪嵩山北宋瓷窑》,《婺州古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周菊青、吴建新:《兰溪嵩山窑器物》,《东方博物》2014年第4期。
[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义陈大塘坑婺州窑址》,文物出版社2014年。
[23]建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建德古窑址》,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富阳太平村缸窑山越窑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十辑,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22—235页。
[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青瓷博物馆:《浙江龙泉金村青瓷窑址调查简报》,《文物》2018年第5期。
[26]徐定宝:《越窑青瓷衰落的主因》,《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7]沈岳明:《龙窑生产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9期。
[28]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77页。
[29]李家治等:《从工艺技术论越窑青釉瓷兴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
[30]权奎山:《试论越窑的衰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
[3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四〇、四一”,中华书局1957年,第5556、5557页。
[3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〇”,中华书局1957年,第7844页。其中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宋史》卷四百八十《世家三吴越钱氏》作“三月”。
[33]同[2]。
[34]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44页。
[35]谢西营:《唐宋境内越窑瓷器流布的阶段性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86页。
[36]对此权奎山先生曾有精辟论述。参权奎山:《试论越窑的衰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
[37]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
[38]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第13期。
[39]Flecker,Miehael.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Intan Shipwreck,Java Sea,Indonesia.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047,2002:101;杜希德、思鉴:《沉船遗宝: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2004年第十卷。
[40]秦大树:《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41]同[2]。
[42]王任叔著,周南京、丘立本整理:《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43]宋·方勺:《泊宅编》卷十,《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56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33页。
[44]宋·谢景初:《观上林埴器》,《<会稽掇英总集>》点校》,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45]李刚:《越窑综论》,载《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8—24页。
[46]宋·强至:《五路岭》,《全宋诗》卷五九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004页。
[47]宋·强至:《祠部集》卷三三《送监征钱宗哲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7页。此序作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至和乙未三月十一日,浦江令强某几圣题”。
[48]同[47]。
[49]王一胜:《宋代以来金衢地区经济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50]谢西营:《龙泉窑早期淡青釉瓷器初步研究》,载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古代瓷窑大系:中国龙泉窑》,华侨出版社2015年,第282—291页。
[51]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海县文管会办公室:《浙江宁海县岔路宋代窑址》,《考古》2003年第9期。
[52]同[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