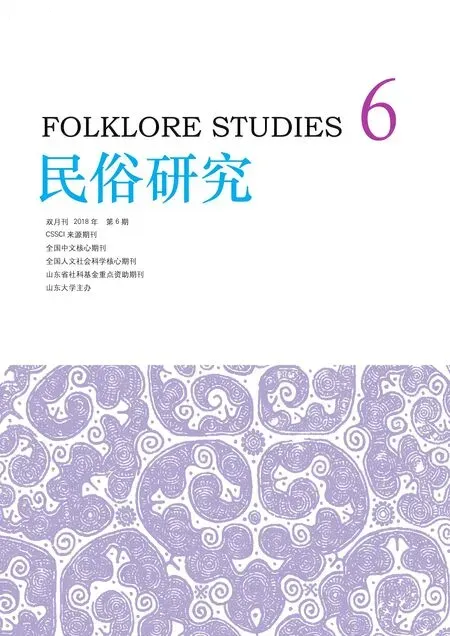中产阶层“不可统计”的生活经验
——民族志书写城市的新路径和可能性
2018-01-23马丹丹刘思汝
马丹丹 刘思汝
中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群体,指的是产业结构转型以来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出现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受雇佣阶层,又构成消费社会的主体。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的讨论进入到学术视野,它是第三产业兴起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包含了市场经济催生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与整合的社会内容。继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后,中产阶级以“新富阶层”的面貌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中。*David S. G. Goodman, “In search of China’s New Middle Classes: the Creation of Wealth and Diversity in Shanxi during the 1990s”,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1 (March 1998), pp.39-62.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印尼社会结构的异质性*Clifford Geertz, “Religious Belief and Economic Behavior in a Central Javanese Town: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 No. 2 (Jan. 1956), pp.134-158.,还是战后日本形成的工作与家庭泾渭分明的“工薪族”生活秩序*[美]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周晓虹、周海燕、吕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产阶级在四十余年的发展中,均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些中产阶级研究的先驱者们所揭示的社会结构转型现象和问题,与此同时,也在涌现它自身的本土化经验和特征。尽管中产阶级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境而言,再分配制度在社会转型中依然发挥着显著作用。*周晓虹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页。新中产阶层既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又依赖国家的建构,市场与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形塑中产阶级的社会形成。
由此,要理解中国中产阶级,不仅需要细致讨论工业社会的一般条件问题,还要深入考察中国其他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要素,人类学恰恰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出巨大优势。民族志实践在再现与辨认中产阶级的现实处境方面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这些田野调查对城市生活经验有浓厚的兴趣,多集中在物质、消费等方面。空间成了人类学者探索中产阶级群体的重要理论工具。费孝通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郊区化运动与市场联盟建构了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住在郊外新型住宅区的人们多多少少都是这些新型市场的债户”。[注]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七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34、339页。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孝通在访美途中对美国中产阶级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描述,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不过这一精辟的解析和理论兴趣却流露出了对中产阶级的研究端倪。1992年中国都市人类学学会成立。跟随阮西湖发起都市人类学的步伐,张继焦在追踪国际都市人类学的动态之后评述道:“人类学家很少‘向上研究’。他们太注重研究穷人和城市移民,而极少研究中产阶级、富人和政策制定者。”[注]阮西湖、张继焦:《都市人类学》,《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直到2000年伊始,本土学者才陆续加入到中国中产阶级的田野调查的行列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延迟”效应。
与社会学的社会问题导向不同的是,对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想办法开展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思考的是中产阶级这一抽象的概念如何在民族志中具体化。通过持续的深入接触,人类学者赋予定量的统计事实以更丰富、更复杂的生活面向。
欧美人类学早在实验民族志的思潮下就触及到了中产阶级。首先,以中产阶级为研究对象是乡民社会持续转型的结果使然。其次,方法论的创新性体现在对中产阶级、精英、职业者以及工业生产力重组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可能产生人类学、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马库斯等人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这样评价道:“因为它们关注的是超越隔离社区的阶级和族群,所以它们的确可能既具有清晰性和针对性的解释特性,又对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具有敏感性。”[注][美]马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5页。对主流的中产阶级生活进行实验性研究,成为欧美人类学“回归本土”的富有文化批评氛围的主要课题。
与之相较,中国人类学、民俗学在不断探索走出都市的边缘群体,例如由农民工、都市里的少数民族、都市现代化生活中依旧保存的民俗“遗留物”等研究对象构成的舒适地带的可能性,并付诸了不懈的努力。[注]约翰·吉利斯在为瑞典学者奥维·洛夫格伦等人的《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所撰的序言中说道:“近现代史学家们全心投入仪式或象征研究时,总是着眼于农民社会或边缘群体,如吉普赛人,而没有把精英阶层纳入思考范畴。”[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产阶级的实验动向作为都市人类学的突破之一,随着田野调查的实践和民族志成果的涌现,以崭新的方法论和理论表述给都市人类学带来了强劲的活力,同时也给社会分层研究注入了社会事实的微观透视和解释力度。可惜的是,研究内容的发散使得民族志成果呈现出弥散的效应,导致无法形成集中化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表述。笔者尝试从“定量之不能、田野调查之所长”的方面来对基于中国中产阶级田野调查的成果进行密集化梳理,换言之,找到定量与田野调查的联系点,从而展开民族志的论述。
一、产权、空间的私有化
相较于傅高义所言的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先富起来”的大量个体户[注][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凌可丰、丁安华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新中产阶级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产物。市场经济转型在中国并非一蹴而就,它从物质消费到住房改革,呈现出私有化的深化程度。社会分层致力于探索中产阶级经济基础与身份认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则捕捉到作为中产阶级的个体,在丰富的物质条件当中复杂的精神和情绪变化。
何伟在《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一书中细腻地描述了私家车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之间的联系。何伟见证了改革开放时期普遍拥有私家车的第一代中国中产阶级。因为交通规则的混乱、驾驶习惯的恶劣、速度的超前、驾驶学校的泛滥,他将“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称之为迷茫的一代。[注][美]何伟:《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张鹂提出全球化集合,以“灵活的后社会主义策略”来概括中国和越南的社会转型特点,新自由主义更多地作为策略来强化原有的统治体制。张鹂《寻找天堂》是一本有关私有空间的民族志著作。[注]Li Zhang,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该书抓住了住房改革推动下的私有空间在昆明的涌现,作者进入到中产阶级的社区生活当中,对空间建构、消费实践和私有产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出细致的观察与体验。围绕空间,即随着新住房运动涌现的私有空间,探讨私有空间开辟的物质化的阶级文化。
潘天舒探讨了“士绅化”运动在上海的际遇。[注]潘天舒:《田野视角中的地方归属感、集体记忆与“士绅化”进程:基于上海社区观察的思考与启示》,“中国中产阶级实证研究的对话与碰撞”会议论文,上海大学,2017年10月14日。虽然“新天地”等石库门往往是具有标志性“士绅化”的成功改造案例,然而他尤其关注上海的地方传统,那就是“上只角”和“下只角”根深蒂固的文化等级与心理歧视。湾桥案例充分说明了地方传统参与到了士绅化运动当中,而且,随着开发的加速,地方传统的选择又摆在人们面前,空间的重构不完全是地理的方位概念,而且触及到地理的心理屏障。
与湾桥的尴尬处境不同,地处上海城市中心的里弄空间在适应激烈的商业化改造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空间再造的能动性。Non Arkaraprasertkul作为租客,他在对静安区一幢里弄住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士绅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概念,相反,由于里弄的业主灵活地运用市场规则,通过app等软件寻找海外租客,对自己居住的里弄住宅进行积极的改造:保留旧式外观,内部装修则以现代化设施。其结果是该里弄从一个平民社区转化为新旧杂糅的中产阶级社区。Non Arkaraprasertkul认为士绅化的转变和业主的经营策略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在市场导向下“诉诸他们自己的方法和技术”,实践出来卓有成效的“文化资本”策略:将房地产租赁市场与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一媒介的存在,社区生活“更加多元化、富有而又充满活力”。[注]Non Arkaraprasertkul, “Gentrifying Heritage:How Historic Preservation Drives Gentrification in Urba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8,p.4,p.9,p.10.
汤芭对他在北京所居住的高档小区“希望城”的居民展开调查,他描述了由高收入和住房政策补贴实现的“业主”中产阶级。生活消费与生活方式这一匿名空间远离工作和劳动区域,提供了阶级形成的观察地带。高档小区横插入单位与住房捆绑起来的传统居住空间,宣告了单位统治关系的结束,引入了自我管理(self-government)的新型组织,例如业主委员会。[注]Luigi Tomba,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51 (Jan. 2004), pp.1-26.在2005年发表的《北京住房争议的居住空间与集体兴趣的形成》一文中,作者继续回应高档小区所带来的阶级形成以及社会组织的复杂性。[注]Luigi Tomba, “Residential Space and Collective Interest Formation in Beijing’s Housing Disput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4(Dec. 2005), pp.934-951.与分层研究强调住房的分层客观性不同[注]张文宏、刘琳:《住房问题与阶层认同研究》,《江海学刊》2013年第4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迅速转向社区转型带来的自我管理和自治的研究,社会自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新兴力量从空间私有化运动中涌现出来,中产阶级组织起来参与业主维权等集体行动,集结为“利益共同体”,从碎片化向组织化迈进了一步。
士绅化运动加速了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然而,变动更加激烈的是来自郊区的房地产运动对空间私有化的推波助澜。Yongshun Cai在《中国温和的中产阶级:业主抵抗的案例》当中,揭示了中产阶级在保护个人利益的维权过程中不同于工人、农民抵抗的方式与特征:1.依法维权;2.维权的原则是“温和而又坚定”;3.动用多种手段维权。尽管经济起到了支持作用,不过作者反复强调自己的核心观点:业主维权胜利并不取决于经济权力,相反,抵抗策略、领导人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在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推动斗争胜利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利益共同体的团结。[注]参考Yongshun Cai的业主维权研究。Yongshun Cai,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777-799.
张敦福对ML小区业主维权进行了案例研究,作者作为小区业主一分子,参与到小区维权运动当中。[注]张敦福:《Could Home-owners as Consumers Become Citizens?: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ML Xiaoqu》,“中国中产阶级实证研究的对话与碰撞”会议论文,上海大学,2017年10月14日。小区维权事件不过是物业公司更迭引发的连锁式反应。业主的自组织成立迅速,但伴随自组织的解散,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日常生活的抗争伦理引发了一个疑问:即使中产阶级拥有丰厚的社会资源,如果他们之间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那么自组织也无法享受到自主、自治、自立的快感。
菲舍(Fleischer Friederike)所著《郊区化北京》,专题研究北京的郊区——望京的崛起。[注]Fleischer, Friederike, Suburban Beijing: 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作者用了三种人群的分类来研究郊区的空间隔离、社会经济分层、消费分化这三个直接相关的生活状态:住在高档小区开私家车的中产阶级,有老单位福利房的退休的老人,以及住在郊区农家平房做生意的流动打工的外来人口。田野中有两个场景引起注意,一是作者在越野车酒吧与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会面,这群人常常光顾俱乐部(club),有着丰富的旅行经历和共同的习惯,充满了现代性的典范光环;另外一个场景是在郊区开店、租房带孩子的农民工妻子结成的友谊网络。作者与部分“底层”妇女断断续续的联系,表达了关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愿望,与中产阶级的空间运动范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自我管理与规训
素质话语作为新自由主义话语构建的重要部分,可以理解为“自我管理”(self-governance)。无论是素质话语,还是个体主义,均反映了分析单位的变化。前者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产阶级想要成为文明代理人衍生的语言、教育和市民身份的优越性,后者关注算计、理性和私有产权意识在个体层面的启蒙与觉醒。张鹂强调中产阶级信奉的这套价值观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突,指出了背负沉重的传统负担而不得不付出的个人代价。[注]Li Zhang,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85-186.话语和实践整合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崛起的社会图景正在形成。社会越分化,中产阶级的生活愿景越有感召力,这一生活悖论越真实。
尽管中产阶级奉行自我管理的铁律,不过根深蒂固的是国家政权在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占据的支配地位。An Chen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企业家阶级和民主》一文中挖掘了中产阶级与大众区分开来的精英意识以及精英意识渗透的心理障碍。[注]An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Autumn 2002), pp.401-422.联系韩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历程,他们在动员民众、抵制威权政府方面突破了An Chen所描述的中国中产阶级陷入的瓶颈,在民主体制改革运动中占据了主体性和主导性角色。其次,韩国高度强调国家在阶级形成中的角色。韩国中产阶级政治的性质和它与“工人阶级形成”的关系已被国家政治的性质所塑造。[注]Hagen Koo, “Middle Classes, Democratization, and Class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0, No. 4 (Aug. 1991), p.506.如果再联系和社会主义中国更相近的越南的经验,则惊奇地发现,中产阶级仍旧与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依附于国家。Martin Gainsborough于1996-1997年在越南调查,描述了越南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五大阶级的利益基础,展现了“政治变迁发生于国家之内”。作者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变迁称之为“尖锐棱角的渐渐软化”。[注]Martin Gainsborough, “Political Change in Vietnam: In Search of the Middle-Class Challenge to the State”, Asian Survey, Vol. 42,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2), pp.701-702, p.704, p.707.结合中、越、韩中产阶级所扮演的无法同质化的民主角色,印证了中产阶级在民主进程的角色复杂而多变。在笔者看来,中国中产阶级的民主道路不同于西方的本土化经历。这不仅仅是“不同的哲学和文化基础”的结果,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传统在社会转型的延续使然。中产阶级自我管理与政治的深刻关联,恰恰是中产阶级扮演民主角色的具体的现实条件。张鹂发现“间接统治”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变迁体现。[注]Aihwa Ong, Li Zhang, “Introduction: Privatizing China-Powers of the Self, Socialism from Afar”. in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原文的“from near and afar”意思是国家退出人们的私人领域,人们用市场竞争和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国家并不是说放任一切,而是在私人领域允许人们按照个体利益的原则自由的生活,但是超出生活领域之外,例如触及政治体制的统治,则被看做是越轨的。因此称之为“拉开距离统治”。
抛开自我管理与国家政治的联系,自我管理也形成了中产阶级管理自我、婚姻、家庭的生活政治。奥维·洛夫格伦等人揭示了中产阶级信奉的自律,也和新的时间观密切相关。[注][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页。丽萨·霍夫曼(Lisa Hoffman)对大连的人才交流市场进行田野调查,集中于大学生就业和中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她发现,人才市场、素质和专业能力相互交织,构成了文明的话语,渗透到大学生的自我表达当中。而中产阶级家庭在夫妻的职业取向上体现出了双轨制的特点。[注]Lisa M. Hoffman, Patriotic Professionalism in Urban China: Fostering Tal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0.田野研究结束后,她转向活跃在大连的NGO组织,关注中产阶级参与慈善公益的动向,触及到中产阶级的情感需求,涉及到情感与阶层、集体人格之间的微妙渗透。之后,她开始把中产阶级从事慈善组织的方式对象化,转变为治理的概念,治理对象针对“不稳定阶级”。参与慈善的中产阶级为了不让接受施舍的人感到屈辱,采取了种种有人情味的治理方式。Lisa将个体融入社会组织中,她发现中产阶级参与的非正式组织释放了巨大的情感空间和灵活的实践策略。[注]Lisa Hoffman, “Middle-classness in Urban China: Thinking About Responsibility and Affective Governmentality”, “中国中产阶级实证研究的对话与碰撞”会议论文,上海大学,2017年10月14日。有人情味的治理,作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的情感诉求与表达,正在填补政府治理的空缺,帮助政府排忧解难。她提醒我们,社会工作也有可能是这种情感治理的推动力量。
马丹丹在对中产阶级西餐厅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案例当中,发现了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隐匿的阶级关系。[注]马丹丹:《西餐厅与中产阶级的文化认同——上海某西餐馆田野调查》,《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Ma Dandan, Yangb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Diet for the Middle Class: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a Western Food Restaurant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hina Marketing, Vol. 6(2).之所以是隐匿的,是因为在中产阶级表演的背后存在的是真实的生产关系。相较于中产阶级以表演为核心的消费文明,工人阶级的形成是隐性的线索,工人阶级管理着后台的非正式活动、语言和特殊社会关系。
规训是一个微观权力与身体化实践相结合的概念,尽管越来越多的企业民族志揭示了白领的规训内化于身体的过程,不过尚且缺乏与其他劳工群体的差异比较,建立不同位置、不同“生活方式”的高端和低端劳动力之间的联系。由于白领的劳动是高度标准化的,其劳动性质又是“去技能化的”,不容许个体差异的注入和技艺的“不可控”等变化,因为这些不可控因素会威胁企业机能的统一运转和秩序。[注]德国学者艾约博(Jacob Eyferth)在《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一书中关注了夹江县这个以造纸为生的血缘村落的社会结构的解构过程,国家通过“去技能化”的策略,公开造纸技术,将造纸人从技术的掌握者变成普通工人,将历史上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夷为平地。参见[德]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韩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0页。与之一致的是,工人阶级高度协作的标准化劳动也在强化。个体溢出流水线的偶然性也是个体威胁生产机械化运转的来源。这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区别于体力劳动的知识、智识等精神活动特征乃至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批判角色怎样体现出来?这些问题均是自我管理视角需要深入思考的地方,其也还会在家庭教养模式中被继续探讨。
三、母职、照料与教育
如果说住房是塑造中产阶级的物理空间,教育则是中产阶级保证自己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手段。社会分层研究善于发现趋势和规律,但是无法进入到具体的实践路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则致力于回答文化资本如何影响社会地位获得,揭示文化资本作用于不同家庭教育和文化环境而展现的更多的教育处境的差异性。民族志更加细微地描述了家庭结构内部的女性角色和亲子关系,呈现了丰富多彩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母职和儿童叙事的研究视角初露锋芒。
Eileen Yuk-ha Tsang从生活机遇的角度论述了第一代中产阶级如何保证自己的子女拥有比自己更高的社会地位——教育消费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注]Eileen Yuk-ha Tsang, “The Quest for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Retrenching Social Mobility? ”, Higher Education, Vol. 66, No. 6 (December 2013), p.663.正是依靠单位、户口、关系积累的丰厚的经济资本,使得第一代中产阶级负担得起高昂的文化资本,将子女首先输送到国内私立大学,其次是海外留学。不过在雷开春基于2011年的上海白领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中,户籍对于白领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了显著影响,至少说明户籍在上海的白领移民群体中正在失去优势。[注]雷开春:《青年白领移民的中产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青年研究》2018年第3期。
连接家庭成员纽带的是女主人,“母职”的概念渗透到通过市场购买的家务劳动、购买和消费市场提供的教育服务,将母亲与孩子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母亲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家长角色。计迎春、苏熠慧等人对上海中产家庭的保姆开展调查,她们敏锐地发现了保姆拥有的代理母职的经验又会继续渗透于城乡二元分化的异质性空间之中。[注]计迎春、苏熠慧等:《遥远的乡愁咫尺的城市:中产上海人家的保姆》,“中国中产阶级实证研究的对话与碰撞”会议论文,上海大学,2017年10月14日。不仅仅是陈蒙观察的中产家庭的母亲“密集母职”的强化,与雇佣关系相关的是,那些离开孩子、到大城市照顾别人家的孩子的母亲同样成为“超级妈妈”。[注]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戴玛瑙(Norma Diamond)通过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家庭主妇发现,有工作的太太的社会化程度比全职太太高,后者逐渐与社会脱节。戴玛瑙认为1960-1970年发展的台湾经济,之所以会出现社会鼓励女人“结婚后回到家里去”,是因为男人害怕女人给自己抢工作,通过强化女性“母职”的舆论,进而强化男性在劳动市场和家庭占据的支配地位。[注]Norma Diamond, “The Middle Class Family Model in Taiwan: Woman’s Place is in the Home”, Asian Survey, Vol. 13, No. 9 (Sep. 1973), pp.853-872.与之相较,陈蒙所描述的密集母职赋予中产阶级女性在家庭更大的决策权,其代价是女性从社会职责和社会价值的撤退。[注]陈蒙:《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
Hale-Benson在论证黑人儿童的一般语言实践之余,号召对黑人儿童的表达风格和民俗进行民族志的研究,相对于语言的语法结构,她更强调语言的实用性和在互动中的应用。[注]Henson, J. E., Black Children: Their Roots, Culture, and Learning Styl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李一对儿童“谈资”的田野发现,拥有玩具、游玩等经历会成为儿童之间的“谈资”,甚至会构成交往或排斥的依据。[注]李一:《中产家庭教养实践的选择与困境——以参加“XES”辅导班为例》,《青年学报》2018年第2期。
中国中产阶级的本土化经验或许可以更进一步的延伸,将母职纳入亚洲、欧美中产阶级的家庭养育关系的比较框架中。例如儿童语言和社会化的议题可以被看作是母职议题的延伸,在不同国别的中产阶级家庭群体之中建立起比较的框架。Peggy J. Miller等人于1988-1991年分别在台北和芝加哥进行了中美中产阶级家庭教育比较的田野调查。他们从两到三岁幼童的个人叙事实践入手,通过共同叙事(co-narrative)这一概念,探索不同的亲子关系互动模式对于儿童自我建构的影响和塑造差异。[注]Peggy J. Miller, Heidi Fung and Judith Mintz, “Self-Construction Through Narrative Practices: A Chinese and American Comparison of Early Socialization”, Ethos, Vol. 24, No. 2 (Jun. 1996), p.257, p.267.在儿童犯错中,台北家庭的母亲强调儿童是越轨者,并且通过叙事让儿童感知到自己是越轨者。叙事彰显出权威的声音同样是叙事实践,从长木社区又衍生出来芝加哥达利园(Daly Park)与长木社区的比较,指向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家庭教育对两到三岁幼儿在培养自主性自我的差别,体现在反驳、矛盾和冲突性亲子对话类型中:在中产阶级孩子眼中是自然权利的所在,在工人阶级孩子那里却是要争取、捍卫的。[注]Angela R. Wiley, Amanda J. Rose, Lisa K. Burger and Peggy J. Miller, “Constructing Autonomous Selves Through Narrative Practi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king-Class and Middle-Class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Vol. 69, No. 3 (Jun. 1998), pp.833-847.工人阶级孩子被强化的反驳叙事类型与Peggy J. Miller在白人工人阶级社区调查发现的母子之间频繁进行的戏谑互动模式(teasing)有一致性。母亲通过戏弄的方式让孩子尽早了解生活的残忍,戏弄意味着语言的社会化。[注]Miller, P. J, “Teasing as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nd Verbal Play in a White, Working-class Community”, In B. B. Schieffelin & E. Ochs (Eds.),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cross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99-212.联系台北中产阶级家庭的权威声音和达利园社区的母亲介入的驳斥模式以及戏弄模式,依然能够辨认其欧美个体主义哲学和儒家文化影响的家庭差异所在。
Kimberly P. Williams在芝加哥某教堂社区黑人中产阶级单亲家庭(通常是单亲妈妈)进行4个月的儿童“讲故事”的田野调查。四到五岁的儿童“讲故事”这一实践在单亲妈妈那里得到鼓励并演变为日常家庭生活的常规“表演”。研究者发现,儿童“讲故事”作为一个导管,将价值、信仰转移到中产阶级黑人儿童个人经验的叙事。它辅助学校教育,创造黑人中产阶级儿童的“文化”认同,黑人儿童的身份构成是“有文化(literate)的人”。[注]Kimberly P. Williams, “Storytelling as a Bridge to Literacy: An Examination of Personal Storytelling Among Black Middle-Class Mothers and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Vol. 60, No. 3(Summer 1991), p.406, p.405.与之相较,国内对儿童世界的关注,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教养与成长的特殊经验,尚有待开掘。而设计开放的比较框架,无论是同类群体的跨国比较还是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对照比较,显然是中产阶级本土化经验的研究现状更进一步的努力。依靠田野调查的努力,丽萨·霍夫曼所言的拓扑效应才能够注入实在的学术活力。[注][美]Lisa M. Hoffman:《全球化与中产阶级:一个有关城市创新和社会区隔的拓扑学方法》,上海大学讲座,2015年6月9日。
在国内学者高度重视母职这一概念的学术热潮中,美国黑人单身(包括同居)的家户群体进入学术视野之中。这一群体被称之为黑人SALA(single and living alone),在1980年以来二十年间极大的增长,既是婚姻衰退的回应,又是反贫困策略使然。尽管研究者运用定量方法论证了自己的假设:SALA比已婚夫妻家庭更可能成为中产阶级,不过研究者还是主张对该群体加以进一步的民族志和其他定性方法,帮助学者理解美国黑人的家户类型、阶级地位和生活机遇之间的互动关系。[注]Kris Marsh, William A. Darity Jr., Philip N. Cohen, Lynne M. Casper and Danielle Salters, “The Emerging Black Middle Class: Single and Living Along”, Social Forces, Vol. 86, No. 2 (Dec. 2007), p.754.黑人单身群体的研究给国内学者带来诸多启发,以母职为中心的家庭单位有可能掩盖反向于家庭、婚姻的单身群体的存在。面对单人餐的餐桌设置在餐饮空间保留的一席之地,与其强化核心家庭的中产阶级刻板印象,不如从现实生活当中并存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出发,注意到群体内部的多元化构成。[注]杨波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描述了白领单身群体不仅是刚入职场年轻化的自然聚合,而且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年龄的增长,保持单身状态会成为白领群体的继续选择,他借用“走向单身”(going solo)来形容这种趋势。杨波:《青年白领群体的规训与自我管理——以C公司青年白领的劳动和消费为例》,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第64-65页。
四、中产阶级田野调查的方法论特色
民族志田野调查面临的中产阶级“可见度”问题,在抽样调查当中几乎被消解掉了,因为后者按照新白领定义的几个维度,就能够获得相对应的样本。而田野调查则首要突破“可见度”问题,接触到具体的中产阶级群体,进而与之建立稳定的田野关系。这一实践方式的不同,造成了研究贡献必然出现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发现了中产阶级不同于农民工等底层社会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该群体的职业为其提供了高收入、高消费的经济条件,包含了文化资本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其二是拥有相对丰富的资源,在利益受损时,可以动用多种资源、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中产阶级群体拥有的物质和象征系统,也给田野调查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走近这一群体,并被该群体接纳,首先需要研究者能够具备与其社交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其交往。例如,菲舍开着吉普车到酒吧与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会面。[注]Fleischer, Friederike, Suburban Beijing: Housing and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何伟在北京考驾照、租车上路旅行,才体会到第一代中产阶级“上路”表现出来的诸多恶劣习惯和“坏脾气”。[注][美]何伟:《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其次研究者应该进入被研究群体的朋友圈,与对方建立联系。例如Yongshun Cai采访到广州丽都花园小区维权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是研究者忠实的报导人。[注]Yongshun Cai,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 4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An Chen则是通过自己的私营企业家朋友引荐进入到深圳、温州的企业家圈子,访谈他们对政府、对民主的看法。[注]An Che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trepreneurial Clas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7, No. 3 (Autumn 2002).依托学生的熟人关系,马丹丹发现“白富美”个人的淘宝消费和她的微博“晒”之间的转化关系,进而关注“白富美”身份构建的表演性。[注]马丹丹:《看上去很美——“白富美”的个人秀研究》,2014年社会学年会“特大城市治理”分论坛,武汉。不仅如此,研究者甚至还需要具备某种专业身份,才能够被中产阶级群体接受,例如张鹂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开展田野调查。[注]张鹂:《中国全球化时代下的心理治疗的本土化》,北京大学讲座,2015年6月29日。继《寻找天堂》之后,张鹂即将出版她的下一本英文著作,从心理、情感和精神的角度,探索缠绕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焦虑等精神症候。来自笔者对张鹂的访谈,2019年9月7日,美国加州伯克利。第三,面对中产阶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不同阶层的差异,也要求研究者具备田野调查的弹性。例如面对纠纷和矛盾,研究者在台北受访家庭的“站队”是灵活的,或者偏向大人或者偏向儿童。在长木社区则是与母亲“共谋”,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参与观察从马林诺夫斯基建立现代人类学的初衷就明确指向“真实生活的不可测量方面”。采取田野调查方法介入中产阶级人群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其中一个瞩目的特点是,研究者不同程度地带入了自己的经历和角色。例如,陈蒙对母职的研究本身就包含了她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注]陈蒙:《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Lisa同样也是加入大连的一个慈善组织,作为其中一员,参与到伙伴们之间相互拥抱的“献爱心”集体行为。[注]Lisa M. Hoffman, Patriotic Professionalism in Urban China: Fostering Tal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0.研究者作为局内人,其身份资格的获得方式有以下几种:1.自己就是业主的一分子。这是大多数研究业主维权、中产阶级私人领域的研究者的做法。张鹂、汤芭、张敦福等人均采取这样的路径。[注]Li Zhang, 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Luigi Tomba,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51 (Jan. 2004), pp.1-26. 张敦福:《Could Home-owners as Consumers Become Citizen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ML Xiaoqu》,“中国中产阶级实证研究的对话与碰撞”会议论文,上海大学,2017年10月14日。Non Arkaraprasertkul则以租客的身份入住静安一幢里弄社区,他的关键报导人是“老虎”这样一位在里弄做茶室生意的租客。[注]Non Arkaraprasertkul, “Gentrifying Heritage:How Historic Preservation Drives Gentrification in Urba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8.傅高义夫妇入住M町期间,他们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们之间的社交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研究对象到成为田野告一段落之后不断互访的好朋友,足见友谊之深。[注][美]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周晓虹、周海燕、吕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2.进入公司成为一名白领。杨波以员工身份进入职场,深刻地体验到规训在自己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双重烙印,它发挥了自我管理的支配意识。[注]杨波:《企业青年白领的身体规训——基于上海C公司的调查》,《青年学报》2018年第2期。在习得纪律和规范的过程中,研究者还会进行中产阶级文化的自我教育。马丹丹就是利用服务员培训的机会,接触西餐厅鸡尾酒文化,并用员工价品尝不同种类的鸡尾酒味道,中产阶级的消费与感官建立接触地带。[注]马丹丹:《人类学者重新发现城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6日。3.进入中产阶级社交或者接受文化资本熏陶的文化机构,或者中产阶级把自己的孩子输送到私立学校等教育机构。Eileen Yuk-ha Tsang在深圳一家私立大学教授英语,利用工作之便,2011年她对学生的父母开展了15个深度访谈,15个入户访问。[注]Eileen Yuk-ha Tsang, “The Quest for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Retrenching Social Mobility? ”, Higher Education, Vol. 66, No. 6 (December 2013).李一在“学而思”机构做兼职老师,接触到一批中产阶级父母和他们的亲子关系。[注]李一:《中产家庭教养实践的选择与困境——以参加“XES”辅导班为例》,《青年学报》2018年第2期。Kimberly P. Williams通过长期参加周末“主日”教堂活动,认识了参加“主日”的黑人单亲妈妈和她们的孩子,熟悉之后有机会到她们的家庭拜访,得以在自然场景下观察到孩子“讲故事”事件的发生,而研究者本人也参与其中,成为母亲要求孩子“讲故事”的对象。[注]Kimberly P. Williams, “Storytelling as a Bridge to Literacy: An Examination of Personal Storytelling Among Black Middle-Class Mothers and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Vol. 60, No. 3(Summer 1991).徐赣丽的研究生在一家为中产阶级会员服务的文化沙龙工作,这些文化活动包括乐器培训、茶道、插花、瑜伽等。[注]徐赣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都市民俗学新课题》,“中国中产阶级实证研究的对话与碰撞”会议论文,上海大学,2017年10月14日。4.公共领域的社交。不少研究者是在公共领域与中产阶级的朋友接触并开展社交的,咖啡馆是“非正式”田野调查的瞩目场所。在这种空间里,William W. Kelly开始从咖啡馆里经常发生的一开始在他看来近似无聊的谈话中切入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日本中产阶级的双重情绪:现代化与怀旧并存、骄傲与焦虑集一身。而人们热衷的“无聊”谈话是Shonai地区流行的神道、神坛等“仙话”“鬼话”,依托20世纪60年代的农业绿色革命,从农民变身为“新中产阶级”的当地人不厌其烦地向游客讲述。[注]William W. Kelly, “Rationalization and Nostalgia: Cultural Dynamics of New Middle-Class Japan”,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3, No. 4 (Nov. 1986), pp.603-604, p.614.正是在咖啡馆泡出来的“共谋的默契”,使得他能够捕捉到现代化给予日本社会的两难处境。中产阶级的田野调查给予的启发是田野调查要在中产阶级生活和社交的真实空间里进行,从公共领域到注重隐私的家庭空间,伴随中产阶级群体丰富的娱乐、消费活动,散发着烟火气的民族志将以细腻的物质、感官体验,为近距离阅读(close reading)个人生活搭建桥梁,为感知城市特定人群的复杂情绪、社会氛围搭建桥梁。[注]笔者以为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渗透于同类人群的情绪、情愫,田野工作者因为深入田野情境反而能够捕捉到,解码它传递的关键信息。个人生活史同样在熟人关系建立起来后才有可能获悉。研究者与受访者的田野关系的建立并非易事,研究者需要寻找一个让受访者舒适的身份进入“飞地”,降低对其空间的侵犯感。“自然观察”是方法论强调的要点,调查者尽量减少干预、倾听、低调(lowkey)的行事方式,是话语、“讲故事”、谈话等多元化叙事实践作为重要的田野材料的来源。
用消费的方式购买文化艺术活动,较之不花钱的“自我调节”,文化消费又加深了中产阶级追求文化品位的需求当中,市场开发与消费群体的价值导向的联系。关于市场营销在创造中产阶级消费风潮和消费倾向的主导作用,Jing Wang对“波波一族”进行了细致的市场动向的观察。作者讲述了一款饮料充满痞子气的logo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又是如何成功投放到市场,吸引了一大批青少年接纳了这种不羁而又个性的卡通形象并自我标榜。[注]Jing Wang, “Bourgeois Bohemians in China? Neo-Tribes and the Urban Imaginar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3,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PRC (Sep., 2005), pp.532-548.杂志又进一步把男性魅力赋予中产阶级男性形象,身体的表征从工人“老大哥”的强壮体魄向中产男士的“士绅”形象转变,性感的概念被重新界定。[注]Geng Song and Tracy K. Lee, “Consumption, Class Formation And Sexuality: Reading Men’s Lifestyle Magazine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64 (July 2010), pp.159-177.这些例子不同程度说明,只有参与到研究对象群体涉入的活动和社会交往,依靠观察、亲身体验、交谈等多种方式,才能有可能发现中产阶级文化的经验构筑与符号发明。
五、结语:定量之不能、田野调查之所长
荷曼在“赋予中产阶级人类学的魅力”中强调,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理论化中产阶级的文化与历史,将劳动、消费和市民身份与实践、空间作为两个研究内容,探讨中产阶级的实践、意识形态和意义。扩大劳动的外延,与市民行动的新的形式,以及消费的重要意义,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将中产阶级经验理论化。[注]Rachel Heiman, Carla Freeman, Mark Liechty edited. The Global Middle Classes: Theorizing Through Ethnography. Santa Fe: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Press, 2012.这篇导言对于民族志贡献的经验和经验的理论化,给予极大的信心和鼓励。将劳动、空间、消费与行动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恰是中产阶级研究方法整合的尝试,也是理论化的真正诉求。
陈述了田野调查在接触研究群体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不同于乡村田野调查、都市边缘群体(例如农民工和少数民族)的方法论特征之后,笔者尝试概括定量之不能、田野调查之所长的若干基点。
1.生活方式。定量研究用抽样调查的统计方法可以呈现收入、学历和消费等综合指标构成的阶层状况,但是无法检测出生活方式,因而得出“生活方式模糊”、住房阶层化的结论。与之相反,与人群进行接触的田野调查和依赖深入访谈的质性研究则反复印证了中产阶层已经出现了某种生活方式的特征,瑜伽的身体感知、健身房的身体训练以及西餐厅食物唤起的感官愉悦,都在昭示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出现与扩张。这些无意识的行为惯习,是人类学的研究擅长,并对这一“无意识”行为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研究兴趣和富有洞见的民族志论述。[注]费孝通认为人的存在,物质是第一层次,制度是第二层次,情绪、情感、精神是第三层次,“见数不见事”“见物不见人”是社会学研究常见的弊病。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44页。研究发现,就中产阶级入住的高档小区(gated community)而言,局内人和局外人对道德的感知也是存在差异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身份看待空间的集体心理。局外人将“府邸”看作是飞地、孤岛,局内人则视“飞地”为私人属地,道德、素质话语在其中扮演了社会排斥作用。安全意识,如对外来者犯罪、偷盗的防范心理,也发挥了对“另类的他者”的排斥。[注]Choon-Piew Pow, “Securing the ‘Civilised’ Enclaves: Gated Communities and the Moral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in (Post-) socalist Shanghai”, Urban Studies, Vol. 44, No. 8, (July 2007), pp.1539-1558.可惜,人类学并没有有意识地将这些研究专长转化为现代生活的人类学旨趣,例如中产阶级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出民族志的参与和积累,无疑会有助于深化文化资本的分层研究。
2.亲属关系。中产阶级群体是高度碎片化的构成,由于中产阶级群体内部是如此多样化,不同的精英投射也就呈现出定量研究者界定研究对象的差异。亲属关系几乎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功。葛希芝在《中国马达》对明清时期的小资本主义以及妇女的商品化的精彩研究[注]Hill Gates, China’s Motor: The Petty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03-120.,依赖的分析工具就是亲属关系。随着人口迁徙、城市化进程加快,人类学者跟随着这些农民迁徙的脚步,继续追踪他们延伸到城市的亲属关系实践和财富积累的过程。张鹂的浙江村调查、张慧对开矿致富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的调查,展现出富裕农民享受到城市文明之后生活方式、观念和价值观发生的变化。研究者也要参与到这些“阔太太”的闲暇生活,例如打麻将、购物,才有可能从女人的“八卦”中了解到舆论包裹的道德和情感。[注][美]张鹂:《北京浙江村:空间与权力的暧昧冲突》,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贫富分化、“一夜暴富”让相对平等的邻里关系、亲属关系变得敏感、复杂,张慧对村民“羡慕忌妒恨”的情感与心理进行了民族志的细致刻画。[注]张慧:《羡慕嫉妒恨——一个关于财富观的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3.微观生活的观察。相较于参与、访谈而言,恰恰是观察,成为区别于统计方法构筑的可观察的行为科学的基石所在。往往是观察,能够发现不被统计的真实生活以及“大数据看不见”的生活经验。例如李一对儿童之间的“谈资”的论述,在抽样调查之中很难检测。[注]李一:《中产家庭教养实践的选择与困境——以参加“XES”辅导班为例》,《青年学报》2018年第2期。原因是这一儿童风俗依赖研究者对儿童群体的细致观察,才有可能挖掘出来。再如傅高义对M町的工薪族忌讳向亲戚朋友、邻居借钱,宁肯从银行贷款也避免向他人开口的矛盾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注][美]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周晓虹、周海燕、吕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他们用最体面的家庭外表接待客人,关起门来却是“吃糠咽菜”、节衣缩食。表演的前后台关系只有自由出入工薪族家庭门户,才有可能发现其家庭生活的常态。这部分信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很有可能在调查问卷中反映不出来。例如西餐厅田野调查,由于自我管理竭力以个体化方式来隐匿或阻碍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认同,问卷调查很难统计出来,原因之一是人们不大愿意如实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深入工人群体,才有可能观察到他们的异质性文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