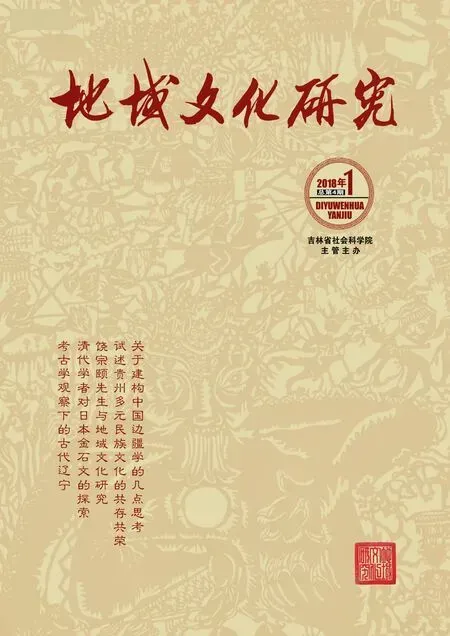试述贵州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
2018-01-23翁家烈
翁家烈
一、五大族系交汇于云贵高原
有关贵州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中国春秋时期《管子·小匡》所载齐桓公言:“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①(春秋)管仲撰,(唐)房玄龄注:《管子》卷8《小匡第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页。其所提及的邦国之一“牂柯”即为贵州,但其具体内容未见展开。关于贵州历史能确知的,最早当属“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全篇以“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开篇,以“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结尾,对战国至西汉时期地方民族政权夜郎国的地理位置、社会状况,在“西南夷”的影响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做出了精准的表述与记载。但对于建立夜郎的族属未作明示,仅以“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一语笼统带过。直到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方谓夜郎是传说中兴于遯水的“竹王”所建,故夜郎王亦称“竹王”。“竹王”被斩后,引发“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牂柯太守吴霸即“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②(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39页。明确指出夜郎国的君民及族属均为濮人。
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后,中央王朝在夜郎势力范围内相继设置犍为郡和牂柯郡,率先实现了对“西南夷”的最早开发。但犍为、牂柯二郡为“初郡”,不同于内地的“正郡”,即《汉书·食货志》所载:“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等,则取自“南阳、汉中以往各地比给”。地处云贵高原的牂柯郡,道路艰险,所需物资难于依时按量供应,朝廷遂以“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的政策应对,邻境巴蜀的豪强地主们便率佃户移居牂柯郡内垦殖,成为最早定居贵州的华夏后裔——汉人。西汉末期,夜郎部落联盟势力范围内的夜郎王、句町王、漏卧侯之间“举兵相攻”,还“刻木像汉吏,立道旁射之”,以藐视朝威,遂为牂柯太守陈立计杀,夜郎国灭。
雄踞“西南夷”的夜郎国灭,濮人势衰。氐羌族系的勿阿纳率部于东汉初年自今滇东北攻入黔西北;苗蛮族系的武陵蛮在抗缴增加的租税中累遭征剿,部分沿五溪散逃至今黔东北;百越族系的“西瓯”跨红水河进入今黔西南。四个古族系从不同方向进入云贵高原,与聚居其间的濮人族系长时期、大范围地接触和交往,出现融合和分化,于唐宋之际逐渐形成了仡佬、汉、彝、苗、瑶、布依、侗、水等诸多民族。元、明、清时期,随着国家军事、政局的改变,蒙古、回、白、羌等族亦相继进入贵州,一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群体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大量存在,被称为待识别民族,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大规模开展民族识别的工作中,其民族的族称问题方基本得到解决。贵州的世居民族确定为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瑶、白、壮、畲、毛南、蒙古、仫佬、满、羌共18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38%,在全国8个民族省区中,贵州是3个民族省之一。
二、从唐蒙通夜郎到贵州建省
建元六年(前135),番阳令唐蒙奉命“风晓南越”,“南越食蒙蜀蒟酱”。唐蒙问知这一特异的土产系蜀地商贾“持窃出市”据说拥有精兵十余万的夜郎,再经其境内之牂柯江(即北盘江)转输至番禺的信息后,遂上书汉武帝,建议借助夜郎的实力及其江道以攻击雄踞一方的南越。汉武帝遂以唐蒙为郎中将出使夜郎。“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①(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4页。“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②(汉)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4页。,也效法夜郎侯“且听蒙约”。汉廷在此基础上在夜郎境内西北部设置犍为郡。犍为郡虽属“初郡”,但意义重大,是中央王朝开发“西南夷”的开端及重要标志,此后,汉朝又在夜郎中心区设置牂柯郡。
夜郎国灭后,无政权依托的濮人势衰,招募来“田南夷”的“豪民稳定发展势力逐渐强大,成为东汉时期拥有部曲的豪强大姓。东汉初年,蜀郡太守公孙述于成都自立为天子,割据一方,牂柯“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5页。,得到汉光武帝的嘉奖。
三国时,“时南方诸侯不宾”④(晋)陈寿:《三国志》卷41《蜀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99页。,为维持蜀国后院的稳定,诸葛亮率师南征,得到雄踞云贵高原西北部氐羌族系首领济济火的积极支援,“积粮通道,以迎武侯。武侯大悦,封为罗甸国王”⑤明嘉靖《贵州图经志书》卷11周洪谟:《水西安氏家传序》。。平定南中后,诸葛亮由味县(今云南省曲靖市)经汉阳(今贵州省赫章县),取道僰道返回成都。《三国志·蜀志·费诗传》载,“建兴三年,随诸葛亮南行,归至汉阳,降人李鸿来诣亮”。
“五胡十六国”时期,建都于成都的成汉政权派大将军李寿攻降宁州各郡。唯牂柯“太守谢恕保城距守积日,不拔。会奕粮尽,引还”⑥(唐)房玄龄:《晋书》卷121《李寿》,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5页。。《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唯牂柯谢恕不为寿所用,遂保郡,独为晋,官至抚夷中郎将、宁州刺史、冠军”。①(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77页。牂柯郡城虽未攻下,李寿篡位后却“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为由,“从牂柯引獠入蜀郡……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橦,布在山谷,十余万家。獠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②(宋)郭云蹈:《蜀鉴》卷4《李寿从獠于蜀》,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12月,第52页。。十余万户“獠”人集团性地北移入蜀,牂柯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削弱,亦使夜郎遗裔更加式微。其社会身份由农奴,一下子变为“颇输租赋”的农民,后又常被军政权势者不断掠卖他乡为奴而融入汉族之中。
唐宋时期由南下的氐羌族系分解而成的“乌蛮”“白蛮”,先后建立“南诏”“大理”地方民族政权,紧邻的云贵高原则成为唐宋王朝与之缓冲的边缘地界,分别于乌江以北及武陵山一带设置黔中道,下辖黔、思、播、蛮、锦、叙等十经制州;于乌江以南置黔中都督府,辖牂、充、庄、蛮等羁縻州数十。宋代,其经制州大部属夔州路,羁縻州辖于绍庆府国。贵州的经制州,成为对官员进行流放贬谪之地。有唐一代,流放贵州者达三十余人。李白《流放夜郎赠卒判官》诗曰:“我悉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唐玄宗时,播州人海通法师于乐山凌云山上,见山前江水常于夏季猛涨覆舟,决心募凿弥勒大佛像以镇水势。佛像高71米,造型雄伟,仅其脚背即可坐百人,乃世界佛像之最。至道元年(993),西南牂柯诸蛮贡方物,宋太宗令其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良久,数十辈联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③(元)脱脱:《宋史》卷496《蛮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25页。,苗族芦笙歌舞因之进入史册。宋都南迁后,金、元雄峙北方,马道堵截,所需战马仰给于西南,朝廷特于邕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设置买马司。“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五经》《国语》……及医、释等书”亦随之传入西南民族地区。
元代在全国建立行中书省制(简称“行省”),作为全国最高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共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广东11个行省。贵州其时分辖于毗邻的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所设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领有顺元等路安抚司、思州军民安抚司、播州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管番民总管府等,实际上成为此三行省毗邻地的政治军事中心。元代在全国大修“站赤”(驿站),以大都为中心设站赤一千五百余处,通往全国各地。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的驿道相接于云贵高原,以贯穿黔东北、黔中、黔西南,其中由湖广通云南的驿道最长且尤为重要,并成为明太祖30万大军平定云南的主要通道,亦是明清两代官、商、民入黔的主干线。
明王朝建立后,元顺帝逃往塞北盘踞,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拥兵云南拒降。朱元璋平定云南后,置重兵控扼。明代于贵州设置24卫,超过西南地区邻省之四川(17卫)与云南(20卫)。其时的贵州土司林立,有的分属于卫管辖,如贵州卫即辖有安抚司1个及长官司25个,实行军政一统。永乐十一年(1413),思州、思南宣慰使为争夺“沙坑”(朱砂矿)导致连年争战,朝廷屡禁不止,遂将其革废,即其地设置8府。接着在此基础上设贵州布政使司,成为继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广、四川、陕西、河南、山东、山西、北平之后第13个布政使司,标志着贵州省的建立。卫所屯田制广布、府州县的广置,导致贵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等领域发生了空前巨变。主要表现为政治上土官制与流官制大范围并行,其趋势表现为前者不断削弱,后者日趋发展;随着卫所制的建立和府州县的涌现,汉族人口剧增,城镇兴起,以十二生肖命名的城乡集市贸易普遍建立;卫学、府州县学及书院应时建立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普遍发生,使长期被视为“苗蛮”或“蛮夷”之地的贵州,于有明一代发展为“苗汉”或“夷汉”杂居之区。康熙时贵州巡抚田雯《黔书·序》谓:“其人自军屯卫所官户戍卒来自他方者,虽曰黔人,而皆能道其故乡,无不自称为寓客;其真黔产者,皆苗、壮、仡佬之种。”①(清)田雯:《黔书·序》,清嘉庆刻本。卫所屯田制的官兵均须带眷属同往屯戍并编为军户世代承袭,而世居当地的少数民族则将这些新来的汉族官兵及其家眷视为客人被统称为“客家”。屯军及其眷属主要分布于城镇及交通沿线,故民间流传的“客家住街头,苗家住山头,夷家(指布依、侗、水族)住水头”,正是这一立体分布格局的形象概述。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明亡,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张献忠先后战殁,江南一批文武权臣拥立宗室藩王先后建立弘光、隆武、绍兴、永历等小朝廷组织抗清,史称“南明王朝”。“南明王朝”的前三者存在时间很短,唯永历朝廷在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支撑下存在长达15年之久,其间曾驻跸贵州安隆所(今贵州省安龙县城)四年。
清代,以雷公山为中心的苗语中部方言苗族聚居区,界于湖南与广西之间,“皆生苗地,广袤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②(清)方显:《平苗纪略》,贵州省图书馆藏本。,保有浓厚的原始社会遗存。“民自黔之滇、之楚、之粤,皆迂道远行,不得取道由苗地过。内地奸民犯法,捕之急,则窜入苗地,无敢过问。”③(清)方显:《平苗纪略》,贵州省图书馆藏本。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改土归流疏》中,历数土司的种种违法乱纪、残暴属民、当进行改土归流之后,引出“苗患大于土司”的结论,认为“苗性犬羊,何知信义。为长久计……必当相机进剿除”,采取铁血政策,对以雷公山山区为中心的“苗疆”发起大规模的武装进剿。在雍正六年至十一年(1728—1733)连续五年血腥镇压的基础上,先后于黔东南苗疆设置八寨、丹江、清江、古州、都江、台拱六厅,派官员管理,史称“新疆六厅”。继又置屯军8,930户、强占大量耕地作屯田,对当地苗族施行严密的军政管制,苗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村落及田土遭到空前的摧残、销毁与剥夺。清代初叶,贵州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数量上尚属“汉少苗多”;至清后期,黔北地区以及省会贵阳一带已是“汉多苗少”。贵州的少数民族人口种类多,其中以苗族人口数量最大、分布面最广、支系亦最为纷繁,又常与其他少数民族参错杂居,汉人对其难以区别,遂对贵州的少数民族通呼之为“苗”,如“仲家苗”“倮罗苗”“侗苗”“水家苗”“仡佬苗”等,以至民国年间许多人类学家来黔调研、发文,亦多相沿成习。清代后期,贵州全省建有12个府、3个直隶州、11个厅、33个县。民国年间,省会贵阳设市,全省共有1个市81个县。2014年,贵州共设6个地级市、77个县(区、市)及3个州11个自治县。
三、多元文化共存共荣
五大族系存在并进入云贵高原的时间和走向不同,导致其发展为后世民族后的分布格局各异。濮人后裔仡佬族原遍及各地,自夜郎国灭后,渐为各方进入的各族系挤压分解,加之李寿“引獠入蜀”,人口不断剧减,至新中国建立前仅两万人零星散布于省内县境;由氐羌族系发展而成的彝族主要聚居于黔西北、黔西南及黔中一带;苗蛮族系的苗族,其后裔分别于黔东北、黔西北、黔东南进入而后漫布全省各地;百越族系越红水河向北推进后,主要聚居于黔东南、黔西南、黔南及黔中地区;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是自“夜郎”始,借助于巴蜀二郡人力、物力,唐宋时期所设经制州亦在乌江以北,故汉族人口以黔北地区居多。明清两代“改土归流”后,周边省区入黔垦荒、逃荒、商贩、工匠者众而不绝。汉族人口以城镇、交通沿线为主逐渐漫布全省各地。各民族大范围杂居、小范围聚居成为贵州民族人口分布的历史态势,构成了贵州各族文化传承、传播与变化的客观环境。民族文化之张弛在于民族态势之强弱,入乡随俗往往成为社会历史运行的惯例,唐代蛮州刺使宋鼎及其后裔亦然。明清史籍所称“宋家苗”者,《贵州图经新志》卷一,“曰宋家者,其始亦中州裔。久居边徼,而衣冠俗尚少同华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其于亲长亦知孝友”。①(明)沈痒:《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宣慰司》,弘治刻本。近有学者考证其原籍为河北真定。又有称为“蔡家苗”者,“与宋家杂处,风俗亦少相类,故二氏为世婚”。②(明)沈痒:《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宣慰司·风俗》,弘治刻本。此两者系唐宋以来史籍所载有关汉族人口移居贵州后习染少数民族文化,而又保持本族文化基因的实例。
战国时期,濮人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夜郎”,成为贵州社会历史的开端。仡佬族是古夜郎创建者濮人留存至今的唯一族裔。最早并一直与之接触交往的彝族及其先民至今仍称仡佬族为“濮”,称仡佬族先民发祥地的牂柯江(即北盘江)为“濮吐诸衣”。旧时民间称仡佬族为“古族”或“古老户”,并有“蛮夷仡佬,开荒辟草”之说。仡佬族虽早已式微,但对其先民于贵州披荆斩棘的历史功绩却被各族人民世代铭记。仡佬族老人过世发丧时,不丢“买路钱”(撒纸钱)可穿行他族村寨;在农作物初熟的农历七八月间,贵州许多民族均过“吃新节”,唯独仡佬族“吃新节”时,其妇女提筐背箩结伴往数,十数里外无论何家、何族的田埂边摘取数株谷穗回来集体祭祖而不受任何阻拦或斥责。如若未有仡佬人届时去摘取,该田主甚至会产生今年收成可能不好的忧虑。
贵州人口最多、分布面最广、与境内各民族皆有交往的少数民族为苗族。其以蚩尤为首领之先民九黎,与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于“涿鹿”发生了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空前大战,蚩尤败后被杀,部众大部分渡河南迁。《拾遗记》载,“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后分为邹氏、屠氏”,成为后来华夏的始祖。秦始皇、汉高祖、梁武帝、宋太祖等帝王均以“兵主”视之予以祭祀。黔东南州之丹寨县境内龙氏苗族每年农历十月隆重祭祀蚩尤的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汉民进入苗区谋生,久而久之,习苗俗或与苗人通婚而成为苗族者众。清朝爱必达撰《黔南识略》卷十九载,“查汉民之黠者,多来自江右。抱布贸丝,游历苗寨……若夫与苗渐狎而诡为苗语、苗装,以通姻者,俗谓变苗”。③(清)爱必达:《黔南识略》,清乾隆十四年修刊本卷19,第7页。徐家干之《苗疆闻见录》载:“其地有汉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之人。懋迁熟习,渐结亲串,日久相沿,浸成异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④(清)徐家干:《苗疆闻见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苗族支系繁多,其中黔西北境内自称“蒙撒”者为“汉苗”,传说缘于“汉父苗母”;因散居鸭池河以西,亦名为“水西苗”;妇女头上歪插木梳一把,故又称“歪梳苗”。历代官府对苗族压迫剥削深重,苗民的反抗斗争亦频繁而强烈。雍正十三年(1735)六月二十四日,湖广总督迈柱在其率兵镇压新辟苗疆的反抗斗争时奏言,“窃查历来苗子滋事,不过抢劫民村、拒敌官兵而止。今则汉奸、熟苗,假装僧道、算命、打卦、师巫,乞丐等类,潜入各地方,探听虚实,指引路径,放火为号,从中指挥调度,攻陷城垣,抢劫食库、占据要路、阻塞驿站等事,无所不至”①《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充分反映出苗族人民在反抗官府压迫剥削的重大斗争中,得到了广大汉民的同情与支持。长期居于清水江两岸的苗族和侗族,不仅培植维系着“稻田养鱼”的生态农业,还开创了林业生产贸易。自明代输送“苗木”作为“皇木”运达北京建造宫殿,至清代内地客商组团携银至清水江口,由通汉语的苗民构成的“山客”从雷公山苗区采购杉木并扎排顺水划流至洞庭湖,然后转运大江南北销售。这种采买方式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数百年繁盛的林业生产和贸易,派生出留存至今的数十万份有关山林土地租佃、买卖契约文书,成为今天国内外学界研究苗汉文化交流发展独特、丰厚而珍贵的民间文献资料。
“夜郎”国灭后,进入贵州势力最为强大的少数民族为氐羌族系的后裔彝族。诸葛亮征“南中”时,其首领济济火,“通道积粮,以迎武侯。武侯大悦,封为罗甸国王”②明嘉靖《贵州图经》卷11。。宋王朝与辽、西夏、金、元长期对峙,南迁后军事烦仍,所需马匹被迫从北方转向南方。《宋史·兵志》载,绍兴三年(1133),“即邕州置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罗殿”“自杞”是贵州彝族所建地方民族政权,邕州在今广西南宁。周去非《岭外代答·邕州横山博易场》谓,“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人所赍麝香、胡羊、长鸣鸡、云南刀及诸物,吾商所赍锦、缯、豹皮、文书及奇巧之物”,③(宋)周去非:《岭处代答》卷五,《邕州横山寨博易场》。形成了以马匹为主兼及其他的内地汉民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明代贵州设有贵州宣慰司、播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四大土司,其中贵州宣慰司势力最大、辖区最广且最具特色,该司由元之水西宣慰司与水东宣慰司合并构成。水西土司为彝族任宣慰使,水东宣慰司由“夷化”之汉族任宣慰同知。司署设于贵阳城内,两者合署办公,由宣慰使执掌印信,遇事与同知共商处理。朝廷规定“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④(清)张廷玉:《明史》卷316《贵州土司》,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170页。,若有事需返水西,须经朝廷批准,印信则由宣慰同知代理。贵州宣慰使霭翠死后,其子年幼,由其妻奢香代袭。洪武四年(1371),“时都督马烨镇守贵州,以杀戮慑罗夷,罗夷畏之,号为马阎王。霭翠死,奢香代立。烨欲尽灭诸罗郡县之,会奢香有小罪当勘,烨械致奢香裸挞之,欲以激怒诸罗为兵衅。诸罗果勃勃欲反。时宋钦亦死,其妻刘氏多智,谓奢香部落曰:无晔,吾为汝诉之天子。天子不听反未晚也。诸罗乃已。刘氏遂飚驰见太祖白事”⑤(明)田汝成:《炎檄纪闻》卷3。。刘氏,名淑贞,汉族,以其远见卓识,不辞奔劳,既为奢香申冤雪耻,亦为贵州化解了一次行将爆发的民族冲突与动乱。奢香更是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要,忍辱负重,不为激变。当朱元璋知情同意处决马烨后,奢香不仅不计旧怨,还主动提出以开凿“龙场九驿”为报,此举深受朱元璋赏识。为示褒奖,朱元璋特赐夺得香之子为“安”姓。
布依族是贵州人口数量、分布面仅次于苗族的少数民族。人口300万,主要分布于黔南、黔西南两自治州及安顺、贵阳、毕节等市,旧称“仲家”。元、明、清时期,其土司制度在红水河北岸,主要表现为以甲统亭,以亭统寨,分兵驻守的军事统辖制度。其亭守称“亭目”,故曰亭目制。源于北宋狄青平侬智高起义后,分兵驻守广西左右江流域,其部属边官世袭而形成。以浙江岑氏为主,下辖王氏、黄氏、杨氏等部将。据《王氏族谱》载,“从武襄公狄青征安隆农智高……智高兵败广西……上表留仲叔,置部下将官住各处镇守……降诏委管长雹四甲、桑朗四甲”①《贵州省志·民族志》。。《杨氏族谱》载,“宋仁宗时上命八员将帅镇守广西,岑仲淑守古勘硐;杨廉贞守上林八甲;黄洪守红水江南北”②《贵州省志·民族志》。。这些奉命驻守红水两岸的军官后裔,日久变服从其俗,衍化为布依族,成为布依族中的大姓。
明代创建卫所屯田制,共约500个卫分设于全国各地。卫的建制为5,600人,下辖前后左中右5所,所下置屯、堡若干。卫所官军皆携眷属,列入军户于驻地世代屯驻,清代废卫所屯田制以绿营制代。屯军及其眷属均改为民,或散或聚,其习俗渐同于普通汉民。唯贵州安顺地区一带,屯军军户多来自江南,卫所屯堡密集而人多势众。军转为民后,生产、生活仍固守祖籍江南的习俗,而被特称之为“屯堡人”。其村落布局、民居格式、生产方式、婚丧节庆礼仪、民间信仰、语言文字、妇女装束等至今仍沿袭明代江南社会习俗。1903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至安平县(今贵州省平坝县)调研时,见屯堡妇女头饰奇特,又多不缠足,而误从当地官员介绍认为属于少数民族而称之为“凤头苗”。“屯堡人”的生产方式、民居格局、建材,年节、婚丧礼仪等,对当地各少数民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如“屯堡人”独创的地戏于周边布依族、仡佬族中均有所传播。
明清两代,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卫所、府、州、县建置的拓展、完成,和城乡汉族人口的激增,汉文化的影响面不断拓展,影响度日趋加深,贵州各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文化的濡染与涵化。汉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日渐为少数民族仿效和吸纳,以致民间渐出现“夷汉”联姻。
明弘治《贵州图经》载,思南府“夷僚渐被德化,俗效中华”,石阡府“郡夷多种”,曰“仡佬”“侗人”,“今则渐染中华之教。所变异者多也”。龙里卫之“东苗”“西苗”“仲家”“龙家”之习俗,“间有合于汉礼者”。安庄卫“环城百里之间,皆诸夷巢穴。风俗粗鄙,异言异服。然与卫人错居,近亦颇为汉俗”③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5《安庄志》,第2页。。嘉靖《贵州通志》卷之三载,中曹长官司仲家“男子戴汉人冠帽……通汉人文字”,思州府“郡内夷汉杂处……自入本朝,夷俗渐变”。思南府“蛮獠杂居,渐被华风……夷獠多效中华”,“朗溪司侗人……近来服饰亦颇近汉矣”。杨义司“其民皆苗、佬、仲家……近来知服役官府,衣服言语稍如华人矣”。普定卫“汉夷杂居,风俗各异……自立军卫以控制之,渐染中原之俗”。安庄卫“地杂百夷……异言异服,然与卫人错居,近亦稍变”。弘治、嘉靖为明代中期,据上两部史书所载,自明王朝于贵州广设卫所、建省、实施“改土归流”等一系列重大军政设施后,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进入和广泛分布,与各少数民族大范围错杂而居,汉文化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世居贵州的各少数民族产生影响,逐渐为少数民族所效仿、吸纳。清代,其影响则更广、更深。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后疏奏认为“改土归流”须以“开辟苗疆”为前提,时任镇远知府的方显于雍正五年(1727)在其《平苗事宜疏》中曰,“黔省故多苗,自黎平府以西,都匀府以东,镇远府以南皆生苗地,广袤二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内地奸民犯法,捕之急则窜入苗,无敢过问”④(清)方显:《平苗纪略》,贵州省图书馆藏本。。其时,官府权势未及的苗疆,成为贵州省一些为权势所迫的汉民的避难所。鄂尔泰以铁血政策开辟苗疆后,设“新疆六厅”,至此,贵州省全部纳入王朝管辖之内。盛产杉木的雷公山地区,明代因其盛产“苗木”成为修建宫殿的“皇木”征集地,清代则发展为全国重要的木材产出区。每年由安徽、江西、陕西大木商组成的“三帮客”及由湖南常德、德山、河佛、洪江、托口五地木商组成的“五勷”客均汇集于此,总数不下千人。他们从水路至锦屏的茅坪等地购买木材,被称为“水客”。木材商们不懂苗语,须由当地懂汉语、能识文断字的苗、侗农民深入山区为之寻找、联系货源,这些代为寻找货源的当地人被称为“山客”。成交之木材,扎成木排循沅江至洞庭湖后,散销大江南北。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贵州的大中土司均不复存在,散存的数十个小土司也已名存实亡,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交往更加直接、自然而顺畅,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日益加深。李宗昉《黔记》卷三载:“侬苗(布依族)在贞丰、罗斛、册亨等处……薙发、服饰俱如汉人,唯妇人束发、短衣长裙,仍苗装也”。“紫姜苗……在平越州者,多出入行伍,大力善战,及读书应试,见之多不识为苗者”。“洞苗(即侗族)在天柱、锦屏二属……男子衣与汉人同……通汉语”。“清江黑苗……种树木,与汉人通商往来,称曰同年”。“六洞夷人(指侗族)在黎平府属……男亦多读书识字者,丧葬礼悉与汉同”。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卷一载:定番州“州属苗多汉少。苗自仲家、青苗、白苗三种以外,又有谷蔺苗、八番老户,然皆薙发改装与汉俗同”。罗斛州判“其苗有名补侬者,有名青苗者……男服汉装,女仍苗制”。清代后期及民国年间,族际交往更加深化,汉民族的年节习俗及婚丧礼仪渐为一些少数民族不同程度地吸纳。男子着汉装者较普遍,能说汉语者增多,尤其是在城镇及道路沿线较为突出。但就民族文化而言,汉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化中仅是量的增加,而非质的取代,从而呈现出贵州民族文化共性突出而又个性鲜明的特征与特性。
贵州民族这一历史性、整体性的文化特性,是在“跬步皆山”的地理环境中,在大杂居、小聚居、立体分布及传统农业的经济基础上稳定发展而成的。历史上除了反抗官府残暴压迫和剥削外,基本上未出现过民族之间的对抗与战争。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长期大范围地接触交往,导致各族在生产、生活习俗上的交流、习染,在形式与内容上异彩纷呈。贵州民族文化最突出、最基本的发展变化态势为:既顽强、牢固地维系着各自固有的文化基因,又不断有选择地吸纳汉文化的某些成分。以前者为“源”,以后者为“流”。以前者为坚守,以后者为吸纳,历经岁月的整合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