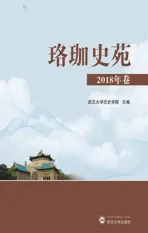“报名”:关于明代开中法程序的一个推测
2018-01-23胡剑波
胡剑波
一、关于“抢上之法”的考察
关于明代开中法程序问题,前人已有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徐泓的成果。徐泓在《明代前期的食盐运销制度》中对明代食盐运销程序进行了清楚的梳理,其中就涉及开中程序。徐泓将开中程序划分为三个部分:“订立则例,出榜召商”“编置勘合、引目与底簿”“商人入粟中盐”,并认为户部发布榜文后,“商人按照榜文的规定,前往各边镇报中盐引,运送粮草等至指定的仓场上纳”。①徐泓:《明代前期的食盐运销制度》,《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74年第23期,第241~243页。关于开中程序,也参考刘淼的相关研究(详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266页)。
可是存在一个疑问:在发布榜文之后上纳粮草之前,如何确定由哪些商人上纳粮草呢?王振忠的研究给人一些启发,他认为明代前期正常的开中情况下,商人上纳粮草实行“抢上之法”,即由于报中名额有限,“盐商谁先上纳粮料,谁就能得到相应的引盐报酬”①王振忠:《释“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41页。亦参考氏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一章第一节,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1页。。也就是说在明代前期,按照正常的开中程序,上纳粮草之前不需要决定由哪些商人上纳。抢上之法应该是一种解决办法,但是,明代开中法真的完全不用事先决定由哪些商人上纳粮草吗?
王振忠的依据是嘉庆《两淮盐法志》所载明代嘉靖户部尚书王杲的《议处盐法疏》:
其法每遇开中引盐,拟定斗头,分派城堡,尽数开出,明给榜文,揭之通衢,听有本商人抢先上纳,凡钱粮但以先入库为定,出给实收,先后填给勘合,则商人有资本者虽千、百引不限其多,何待于买窝?其无资本者虽一、二引亦不可得,何窝之可卖?商人上纳之多寡,在其资本之盈缩,郎中等官,虽欲高下其间,亦不可得。既不招怨于人,亦不取谤于己,一举而三益,法无便于此者。②单渠等:(嘉庆)《两淮盐法志》卷2《古今盐议录要上》,于浩辑:《稀见明清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第2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595~596页。值得说明的是,可能由于版本因素,笔者提供的版本与王振忠的引文相比,个别字有出入,本文引文尊重王氏引文,未改。
原文中,在王氏引文之前有“臣等查得先年各边行有抢上之法,始为尽善”数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抢上之法”应该曾实行于各边③此处的“各边”指明代北边的军镇。明朝政权为了防御北边的游牧民族,先后在北边设置了多个军镇,至万历时已达十四个,其中九个边镇(宣府、大同、辽东、延绥、甘肃、宁夏、蓟州、固原、山西)最为著名,“九边”之说也广为流传。,但是似乎不能据此否定别的可能性。另外,这种说法在明末汪珂玉的《古今鹾略》中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嘉庆《两淮盐法志》的记载可能来源于此)。①汪珂玉:《古今鹾略》卷6《利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5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637页。所以,在开中法中,“抢上之法”应该是存在的。但是它是唯一的办法吗?
其实,在《明世宗实录》中也有关于“抢上之法”的记载:
户部因开上预派各镇引盐额籍,且言:盐法之害,莫甚于买窝卖窝,累拟禁革而弊终不除者,以未得其术耳。闻之,前时边臣有为抢上之法者,似为良便。其法:遇开到引盐,定拟斗头,分派城堡,尽数开列,揭榜通衢,听各有本商人抢先上纳。凡银粮但以先入仓库为定,出给实收,按其先后填给勘合。不惟奸人不得虚报卖窝,高坐罔利,即司饷诸臣亦不得以意所憎喜,高下其间。比之验银准报,可以假借应点者,不可同日语矣。请着之令甲,下各镇从实举行,亦今日通商利国之一道也。诏俱如议。②《明世宗实录》卷278,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戊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5428~5429页。
在此记载中,此时的户部官员谈及“抢上之法”,只说“前时边臣有为抢上之法者”,也就是说以前九边各镇负责粮饷的官员有的实行“抢上之法”,那么也就可能有的官员未实行“抢上之法”,而使用的是别的办法。而且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九月之前,“抢上之法”应该已停止多时,直到此时才又重新推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古今鹾略》中提到的户部尚书王杲,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九月仍然在任,所以《明世宗实录》中关于“抢上之法”的描述大概也与王杲有关。③张廷玉等:《明史》卷 112《七卿年表二》,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3460~3462页。
通过以上考察,大概可以看出,在开中法中,“抢上之法”应该不是决定哪些商人纳粮上仓的唯一办法。也就是说,不能排除官府事先决定哪些商人纳粮上仓的可能。那么,官府有可能通过什么方式来决定呢?本文认为是“报名”。
二、关于“报名”的考察
就笔者所见,关于“报名”的材料较少,本文只能以可以确认的材料作为突破口进行考察。
成化四年(1468)三月初二日,宪宗发布一道圣旨:
近体得各边开中粮盐,内外官员之家,诡名开报,包占盐引数多,中间有令家人子弟,去买那不堪米麦上纳的;有自己不行上纳,转卖与人,徒手(的)[得]钱的;及转卖之人先用价钱过多,却称斗徒太重,具告官府,因而减数上纳的;那边镇守、总兵、巡抚等官,非但不能行禁革,中间也有曲徇人情,听令通同(通)攒官斗级,或将官军该支月粮,指廒作数,或将关出积年陈米,相沿进纳,虚出通关的;亦[有]自行包占盐引,转卖与人的;有先将本处米麦收积,临期增(偿)[价]、或插和糠秕,(籴)[粜]与客人上纳的。似此奸弊,非止一端,以致边廪空虚,军饷缺乏,好生不便!恁部里便出榜京城,并各边张挂晓谕,多人知道。除已往的罢,今后遇有开中,都依户部奏准事例,并不许内外官员之家中纳包占,其客人引数亦不许过多。附近的赴户部报名,路远并见在各边居住的,赴巡抚等官处都要报名,审勘明白,与定数目,依期上纳。不许转卖与人,及听人包揽。所在监临等官,务从公道,不许扶同作弊,亏损边储。如违,在内从户部并户科给事中参奏,在外从巡抚并巡按御史纠察,都治以重罪不饶。钦此。①戴金著,蒋达涛、杨一凡等点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8《盐法》第6条《禁约内外官员家人包占盐引数过多转卖与人例》,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7~818页;朱廷立:《盐政志》卷5《制诏》,《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页。
各个边镇开中盐粮,因为势要“诡名开报”“包占盐引”等现象,①此处的“势要”指有权势的内外官员。明代禁止公侯伯及四品以上官员之家开中,但是未能阻止他们参与开中,同时,有权势的宦官也参与盐法开中。在明人看来,势要对盐法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导致国家“边廪空虚,军饷缺乏”,于是官府决定加以打击,规定以后凡遇开中,都需要向户部或者巡抚等官报名,然后约定好上纳数目或者盐引数目以及上纳期限等事项,然后商人前去上纳,并且商人报中的盐引数目也受到限制。如果有不遵守规定者,会受到官府的惩罚。这条材料应该能够证明在明代某些时期,在开中程序中存在“报名”环节。
但是,“报名”环节是成化四年(1468)三月二日以后才有的吗?应该不是,在此之前,即成化四年(1468)二月二十四日,户部尚书马昂在一份奏疏中提道:
辽东各仓,近年开中盐课,(谏)[办]共三百八万余引。中间有报名上纳未完者,亦有全曾纳者。自文书到日为始,俱限六个月以里完纳。若有仍违限(右)[不]中及捏故告与别商顶纳,即系“买窝”之人,巡抚官即便擒拿,解赴部转送法司问罪,枷号示众。遗下引盐,另行招商顶中。其未曾来报名者,止许有(衙未)[司来]人运赴该仓临近军民之家囤放,报该管粮官亲诣勘验是实,收具寄住邻佑人等重甘结状,方许运进该仓,随即督同官攒,斗级监收作数。②戴金著,蒋达涛、杨一凡等点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8《盐法》第5条《禁革盐法诸弊事例》,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5页。《明宪宗实录》卷51,成化四年二月丙辰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46~1047页。
在辽东各仓中存在“报名上纳未完者”,也有“全曾纳者”,并且官府规定了完纳期限,如果超过期限,商人还未完纳粮草,就会受到官府的惩罚,其报中的盐引也由别的盐商“顶中”完纳。这证明此时是有“报名”环节的,并且报名和上纳粮草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官府还规定,没有报名的商人,需要先运到粮仓附近“军民之家”囤放,由管粮官勘验,还需要当地人作担保,才能纳粮上仓。由此可知,没有参与“报名”这一环节的商人,尽管也可以上纳粮草,但是需要经历一些复杂的程序。
嘉靖年间也有相关史料。嘉靖四年(1525)杨一清上疏:
自正德二年至正德十二年止,俱为旧引;正德十三年见开未完并以后年分开中者,俱作新引另召。不拘新旧商人,许令告报。每引照正德元年事例,纳银二钱五分到于卸盐处所,仍纳卧引银一钱。愿中商人俱于环庆兵备处报名,银两发庆阳府收贮,取实收类赴布政司填给引目下池,旧引三分新引七分,俱挨次开放。①杨一清:《为条陈盐池开中事》,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117(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06页。值得说明的是,杨一清此疏在《明经世文编》中并未标注年月,但是在《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年十月癸卯条记载了此奏疏的缩减版,故将之定为嘉靖四年(1525)(参见《明世宗实录》卷56,嘉靖四年十月癸卯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363~1364页)。
杨一清建议将灵州大小盐池正德二年(1507)以后的盐引分为旧引、新引,新引重新召商中纳,不管新旧商人都可以到环庆兵备处报名,商人纳过银两后,凭实收到布政司填给引目,下池支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此处的开中程序的确存在一个“报名”环节。
另外,隆庆三年(1569)庞尚鹏在《清理辽东屯田疏》中提道:②庞尚鹏此疏在《明经世文编》中并未标注年月,考之《明实录》,《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五月己未条所载奏疏应是此疏的缩减版(参见《明穆宗实录》卷32,隆庆三年五月己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840~842页)。
据辽商告称:两淮引价,见蒙题准则例,官民两便。今岁户部衙门开派盐引,即大家小户争报名投纳,以致人多引少,上纳利微,愿革去小户,惟大户各给千引以上,庶不徒劳无益。①庞尚鹏:《清理辽东屯田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58(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66页。
根据庞尚鹏的观察,因为官府对两淮盐引交易定价,使边商有利可图,于是隆庆三年(1569),在户部开派盐引时,当地商人争先报中,以致盐引供不应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九月,官府在开中法中推广“抢上之法”,但不知道此后的情形如何。在此可以看到,在隆庆三年(1569)庞尚鹏观察到的辽东开中程序中,盐商无论大小仍然需要报名。
另外,同年庞尚鹏在《清理蓟镇屯田疏》中提及:
访得本镇有卖窝奸徒,抑勒各商阻坏盐法,除臣另行拿究外,自今承认之后,若两月以上粮不到仓,即系光棍包揽,许别商另投甘限认状,依期完纳,仍查原报姓名,访拿重治。②庞尚鹏:《清理蓟镇屯田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58(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8~3859页。《明经世文编》并未标注此疏年月,《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二月癸未条载有此疏缩减版,故将之系于隆庆三年(1569)(《明穆宗实录》卷29,隆庆三年二月癸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760~762页)。
庞尚鹏为了打击蓟镇买窝卖窝奸徒,③此处的“买窝卖窝”是明代开中法中一种常见的非法买卖盐引额度的行为。在开中法中,一些势要或商人通过某些手段获得一定量的中盐额度并将之转卖给无权无势的商人,并由这些商人进行上纳粮草、支盐等一系列后续的活动,这种行为就是买窝卖窝。明朝政权经常打击买窝卖窝的行为,但效果并不明显。规定盐商“承认”盐额之后,如果两月之内未纳粮上仓,便被视为“光棍包揽”,允许别的盐商投“甘限认状”代替其上纳粮草,并且还要将原报名的商人治罪。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此时在蓟镇开中程序中,应该是存在报名环节的;二是商人报名似乎需要投“甘限认状”之类的保证书;三是庞尚鹏打击买窝卖窝,涉及报名环节,说明报名环节与“窝”存在一定联系,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还会加以论述。
不过,不应忽视的是,同样在隆庆三年(1569),庞尚鹏在讨论宣府大同屯田事宜的奏疏中提道:
奸商射利之徒,凡遇开派盐粮,辄夤缘占中,有斗粟不入而坐致千金者。宜行各守巡兵备及管粮郎中,凡遇开中,先期榜示所属,明开盐引数目及时估价值,各商赴仓上纳。其粮未入仓而先告认状者,不得徇情听受。①《明穆宗实录》卷34,隆庆三年闰六月甲辰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873页。
庞尚鹏为了打击占中转卖的奸商,建议各监中官凡是实行开中,必须让盐商赴仓上纳粮草。而没有上纳粮草就先“认状”的商人,监中官不得接受“认状”。根据庞尚鹏的建议,似乎应该先纳粮再“认状”,那么庞尚鹏似乎排斥事先报名,而与“抢上之法”比较相似。或许,不能排除“报名”与“抢上之法”同时存在于不同地区的可能性。
至此,本文认为在成化四年(1468)三月初二日宪宗圣旨颁布后的一段时间,应该是有“报名”环节的,而在此之前至少在某些地区也存在“报名”环节,嘉靖四年也有报名环节,隆庆三年(1569)同样也存在“报名”环节。那么,别的年代,是否也有可能存在“报名”环节,至少是存在“报名”环节的一些蛛丝马迹呢?
正统八年(1443)有一段材料:
先是户部奏准:正统六年(1441)关给中盐勘合,未曾上粮者住中。至是,陕西按察司副使傅吉言:旧召商李恭等,收籴米麦三千余石运至宁夏,僦屋安顿月久,未与收受,宜令其上粮支盐,公私两便。②《明英宗实录》卷109,正统八年十月辛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213~2214页。
户部奏准让中盐商人还未上纳粮草者停止上纳,而陕西地方官员反映,当地应召商人已经买好粮草运到宁夏,等着上纳,应该让此商人上纳粮草。尽管这段材料中没有正面提到“报名”环节,但是“旧召商”数语值得注意,或许指的就是已经报名的商人。前面已经提到,在成化四年(1468)的例子中,报名和纳粮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那么李恭等人则很有可能是已经报名而未上纳粮草的商人。所以,“报名”环节可能在正统八年(1443)时就已存在。
正统九年(1444)也有一段材料:
敕户部曰:朝廷令人易纳马草关中盐粮,本期资国便民。比闻各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贪图重利,令子侄、家人、伴当假托军民出名承纳,又行嘱托规从轻省之处,如东直门牛房岁计用草止十五万,今添纳至三十余万,积聚既多,久则必致下人乘隙侵欺。①《明英宗实录》卷115,正统九年四月壬辰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322页。
材料中提到,朝廷实行纳草开中,但是中纳之人多是势要和负责官员的亲人仆人之类,他们假借军民身份承纳,并且利用关系只去便利的仓场上纳马草,以至于有些仓场所纳草束已经远远超过所需。值得注意的是“假托军民出名承纳”数语,应当是指假托军民身份报名,认纳一定数量的粮草。至于势要为什么要假托军民身份报名,这大概与明代禁止公侯伯及四品以上官员之家中盐的规定有关。②(万历)《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十七年令: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申时行等:(万历)《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0页。
以上两则材料似乎能显示:在正统年间,至少是正统朝的某些年份,开中程序中可能已经存在“报名”环节了。
景泰二年(1451)官府规定:
令各商报中盐数,迁延一年之上不报完者,即于常股盐内派拨,挨次关支。①申时行等:(万历)《大明会典》卷34《盐法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8页;(嘉靖)《惟扬志》卷9,《扬州文库》第一辑第1册,广陵书社2015年版,第79页。值得注意的是,(正德)《大明会典》中此句为“令各商报占盐数”,但只有一字之差,不影响大意。李东阳等:(正德)《大明会典》卷36《盐法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3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3页。
官府为报中的盐商规定了一年的完纳期限,否则由原本的存积盐不次关支,变为常股盐内挨次关支。②明代盐引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存积盐,一种是常股盐。一般来说,报中存积盐的商人,人到即支盐,不用排队,而报中常股盐的商人则需要按照顺序,慢慢等待支盐。即官府用改变支盐速度的方式来惩罚违限的商人。官府为商人规定完纳期限,那么官府是如何知道哪些商人违限呢?应该是由于商人事先已经“报名”,所以官府才拥有商人的信息。
如果说上面的材料还比较隐晦,那么下面一条材料会稍微清楚一点:
宁夏右参将都指挥王荣言:分守花马池兴武二营征操官马,岁用料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余石,今二处所贮仅十之一,用数不敷,请召商中纳盐粮。户部覆奏:恐客商先执虚名,延至秋成上纳,有误边计,官移文镇守陕西侍郎耿九畴,督同布按二司管粮官分籴粮银,内支三千两收籴应用。从之。③《明英宗实录》卷216,景泰三年五月己酉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664页。
景泰三年(1452)宁夏将领请求在当地实行开中法,解决军队马料问题。户部认为商人有可能会“先执虚名”,然后到秋收粮价便宜的时候,才上纳粮食,缓不及事。于是让当地管粮官员用银籴粮。其中商人“先执虚名”,然后秋季上纳,大概指商人参与“报名”环节,与官府约定好盐引数、纳粮数,然后再籴粮上纳。这与前面提到的成化四年(1468)的开中程序十分相似。
景泰三年(1452)还有一则材料可供参考:
户部奏:宜将两淮运司盐召商于宣府纳豆及草,豆每引六斗五升,草每引三十束。不分大小官员、军民人等报纳,限一月内完,不次支盐。①《明英宗实录》卷221,景泰三年闰九月甲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793页。
因为漠北使臣前来进贡,其所带马匹在宣府寄养,导致宣府马料不足,于是户部紧急开中,突破公侯伯以及四品以上官员之家不得中盐的禁令,准许大小官员、军民报纳,但给他们规定了一个月的完纳期限。正如前面所说,官府规定了期限,如何知道报纳者是否违限呢?大概就是因为存在着“报名”环节。
景泰六年(1455)也有一段材料:
户部言:近因湖广五开等处苗贼弗靖,肆为劫掠……请驰传往谕巡抚都御史马昂、蒋琳……先于贵州开中淮浙等盐三十万五千八百八十余引,有纳米未完者,就令琳催完……从之。②《明英宗实录》卷260,景泰六年十一月丙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5572~5573页。
官府因为湖广苗民起义,军队急需粮草供应,于是命令巡抚蒋琳催促报中但未上纳粮草的商人赶紧完纳。巡抚要催促商人完纳粮草,如果没有商人的信息,官府如何催完呢?那么就有可能是商人事先报名,但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完纳粮草,官府因为军需紧急,所以派人催完。
所以景泰年间,在开中程序中也可能存在着“报名”环节。
天顺年间也有一则与之相关的材料:
敕谕文武百官曰:朕缵承洪业,奉守祖宗大法,将以理正天下……近闻皇亲、公、侯、伯、文、武大臣中间,多有不遵礼法,纵意妄为:有将犯罪逃躲并来历不明之人,藏留使用者……有诡名中盐,挟制官司,亏损国家之课者。①《明英宗实录》卷290,天顺二年四月乙酉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6203页。
天顺二年(1458),英宗颁布敕谕警告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因为他们中有人违反官府法律,牟取私利,其中一项就是“诡名中盐,挟制官司,亏损国家之课”。值得注意的就是“诡名中盐”四字,前面已经提到,明代禁止势要中盐,所以有些势要便令家人奴仆,假借军民身份报名,认纳一定数量的粮草,以此参与中盐。那么此处的“诡名中盐”很有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或许能间接显示“报名”环节的存在。
以上笔者根据掌握的材料对成化四年(1468)以前的情况进行梳理。通过梳理,笔者推测:正统、景泰、天顺年间,至少是其中的某些年份,在开中程序中可能存在“报名”环节。
那么成化四年(1468)以后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成化十二年(1476)有一则材料:
户部议覆大学士商辂等所言修省事,欲会计西北各边积蓄多寡之数。缘各边粮草稽核其数大约有余,但恐用兵调度所费无穷,贼入之处亦无定所。请移文各巡抚官催征每岁逋负及中盐未纳者。仍开中淮浙运司见在存积盐二十万引,命陕西送银十万两,分拨于榆林、甘肃、宁夏。本部复遣官运银五万两于辽东,六万两于大同,四万两于宣府。制可。②《明宪宗实录》卷156,成化十二年八月己卯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845~2846页。
户部因为大学士商辂的建议,对北边各镇的粮饷进行统计,发现各边粮草尽管较足,但是可能会因为调兵等因素而导致粮饷不足,于是通过开中法、运银籴粮等方式加以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官府为了补充军饷派巡抚官催征“中盐未纳”者。正如前面所说,如果官府没有商人信息,官府如何催征呢?大概就是因为有“报名”环节,所以官府才能够催征,催征才具有合理性。
成化十八年(1482)也有一段材料:
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阮勤奏:陕西、榆林、固原、宁夏顷以边储不足,召中两浙、两淮盐。今淮盐多报纳而两浙犹有未中者,盖以时方米贵,则例过重也。然存积盐每引例折收银止一钱七分,常股盐又减四之一。若依本处时价,则每引可加二之一。乞令以两浙盐凡未中并已中未纳者,差官于本处,督同运司召商鬻卖,送运陕西各仓,或淮折官军俸粮,或籴买粮豆。①《明宪宗实录》卷225,成化十八年三月戊戌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870页。
陕西等处边储不足,两浙盐引还有很多未曾报中,而如果在当地直接变卖的话,会更加有利可图,于是陕西巡抚奏请停止开中,将未报纳的盐变卖银两籴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巡抚要卖的盐包括“未中”和“已中未纳”两种,这就证明“中”和“纳”应该是开中法程序中的两个前后相继的环节。根据前面对成化四年(1468)例子的分析,我们知道“报名”和“纳粮”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那么此处的“纳”则应该指“纳粮”,而“中”则应该是指“报名”。
通过对以上两则材料的梳理,大概可以看出,在成化年间“报名”环节应该仍然存在着。
接下来,本文分析弘治朝的情况。弘治元年(1488)户部的一份题奏中提道:
其余客商虽报军民籍贯,亦有势要顶名报中,必须运司清查,方得(其)[真]伪,明白案呈。合无本部差人赉文前去,各该巡盐御史并管盐按察司官,督同运司官员,除事已完结,人无见在外,将前项势要顶名报中之人,逐一查审,要见某商保、某官弟侄儿男家人中支,是何年分引盐,中间有无顶名报中,俱要从实审出。①戴金著,蒋达涛、杨一凡等点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9第1条《巡盐御史查究势要顶名中盐例》,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34页。
户部因为势要中盐,侵夺商利,于是决定加以清查。其中,势要中盐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顶名报中”,所以官府对“顶名报中”的情况加以审查。那么正如前面提到,势要采取“顶名报中”的形式,一方面是因为官府禁止势要中盐,而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为“报名”环节的存在。
弘治末年户部尚书韩文在奏疏中提道:②此奏疏在《明经世文编》中并未标注年月,本文将其定为弘治末年是基于如下三个理由:一是奏疏中有“近者庆云侯周寿家人周洪,奏买两淮残盐八十万引;寿宁侯张鹤龄家人杜成、朱达等,奏买长芦两淮残盐九十六万余引”句,这些事发生在弘治十六年(1503)一月和十一月,那么这道奏疏当作于弘治十六年(1503)十一月以后;二是奏疏中有“臣等职司邦计”语,这大概能显示此时正是韩文担任户部尚书时期,而韩文任户部尚书在弘治十七年(1504)十一月到正德元年(1506)十一月;三是奏疏中提到“自弘治十九年为始,今后每年额办盐课……”这是韩文提出建议,希望从弘治十九年开始实行,而孝宗在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驾崩,武宗在当月就宣布明年改元为正德,所以此疏只能作于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驾崩之前。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推测,此疏大概作于弘治十七年(1504)十一月之后,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之前,故本文将其定为弘治末年(参见《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戊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593页;《明孝宗实录》卷205,弘治十六年十一月癸未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815页;张廷玉等:《明史》卷112《七卿年表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438页;《明武宗实录》卷1,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2页;韩文:《题为钦奉事》,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8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51~755页)。
近年以来,势豪之家往往主令家人诡名报中,及至赴官上纳则减削价值,下场关支则不等挨次,货卖则夹带私盐,经过则不服盘诘,虚张声势,莫敢谁何。以致资本微细者敛迹退避,不敢营运;着实济边者坐困岁月,不得关支。①韩文:《题为钦奉事》,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85(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52页。
据韩文观察,在弘治末年的开中法中,势要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他们让家人“诡名报中”,上纳粮草时缺斤少两,而在支盐时不按秩序支盐,甚至夹带私盐。势要如此胡作非为,让很多小资本的盐商不敢参与开中,也让那些已经获得盐引的盐商迟迟不能关支食盐。其中,势要先让家人“诡名报中”,然后在上纳粮草时做手脚,那么这应该能够显示“报中”和上纳粮草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也应该能显示“报名”环节的存在。
那么,“报名”环节在弘治年间应该也还存在着。
正德年间也能发现“报名”环节的一些痕迹。正德五年(1510)武宗在一份大赦诏中规定:
各处商人先年报中,粮草已纳在官,未给盐银者,照数给与,见监未结者,悉皆释放并免追陪。②《明武宗实录》卷62,正德五年四月辛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374页。
大赦诏规定,报中的商人,如果粮草已经上纳,官府还未偿付盐引或银两者,都要偿付给商人。③在开中盐引时,一般是商人上纳粮草,官府给予获得支盐权利的凭证。而此处官府给予商人银两,所以,这些商人可能不完全是中盐商人,也可能包括籴粮商人。那么,在此处报中商人存在“粮草已纳在官”的情况,似乎也在暗示着还存在“粮草未纳在官”的情况。也就是在暗示着可能存在“报名”和“纳粮”两个前后相继的环节。
嘉靖年间开中程序中应该也有“报名”环节。嘉靖七年(1528)巡盐御史魏有本上疏提道:
窃惟盐法之弊莫甚于占窝。凡占窝之人,非内外权势则市井奸猾,一闻开中,则钻求关节,伪写书札,相率趋之。监中官或畏其势,或受其欺,止据纸状姓名准中。商人挟赀冒险而无售,彼且勒取高价而卖之,空手而往,满箧而归。商人未纳官粮先输私价,是卖者之利,非买者之愿也。今禁例非不严,而此弊终不可革者,臣不知其故也。臣闻往年户部郎中李淮之在辽东验银开中,此弊遂革。臣乞令今后各边报中,俱限赍银称验,贮库准中,以三千引为率,不许过多,候各商上纳刍粟完日,给领勘合,其余不准。如此,则权奸无所容其计而商人称便矣。①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据魏有本观察,开中法实施时,势要或商人会通过找关系、“伪写书札”等形式,与巡抚等监中官联系,而监中官因为畏惧权势或者被商人欺骗,只根据所投纸状姓名,便允许来人报中。来人获得报中权利后,通过某种方式,将这种权利转卖给其他无权无势的盐商,让这些盐商去纳粮。那么,此处“报中”和“纳粮”同样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而监中官需要根据纸状姓名准中,可能就是因为“报名”环节需要商人的姓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魏有本建议仿行以前户部郎中李淮之验银开中的做法,让开中商人先把银两带来,向官府证明自己有上纳粮草的能力,并且将一部分银两放在官库中作为押金。还规定盐商中盐限额为三千引,不能过多。商人纳完粮草之后,官府再填给盐引勘合。而除此之外的商人,不准参加开中。魏有本建议的验银开中程序中,“报中”和“纳粮”同样是两个前后相继的程序,而让盐商交银作为押金,并给盐商规定中盐引数,似乎需要“报名”之类的环节。据实录记载,魏有本验银开中的建议得到采用并实行了十多年。①《明世宗实录》卷96,嘉靖七年十二月庚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253页;《明世宗实录》卷278,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戊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5427~5429页。
万历年间似乎也有“报名”环节。万历六年(1578)有一则材料:
户部题:万历六年正月内预开七年分各边常股存积盐数,照依时估,定拟斗头斤重召商,俱令上纳本色粮草,分贮紧要城堡,专备万历七年主客兵马支用。商人报中者,不许过三千引,输纳者不得过三个月,务趁时召中,不许折收银两。其一切病商亏国者,严行禁绝。②《明神宗实录》卷71,万历六年正月戊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540页。
户部给各边预先分配万历七年(1579)的开中盐引数,并且规定,只能收受本色粮草,不能折收银两。另外还规定,商人报中盐引数每人不超过三千引,并且输纳粮草时限不能超过三个月。正如前面多次阐述的那样,官府可能需要“报名”环节来与商人约定报中的盐引数以及输纳期限。所以盐引限额和输纳期限应该能显示“报名”环节的存在。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也有一则材料:
户部题:每年开派各边额盐,召商报中原系飞挽。军需例应当年完纳粮料,填注文册,缴部转发巡盐,查对该镇原填勘合仓钞,硃墨印号相同,方准关支。如违限不完粮料,即将原派盐引,追给早完商人接纳。③《明神宗实录》卷279,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5154页。
材料中,户部规定各边开中盐引,需要在当年完纳粮料,再由管粮郎中等官填好文册,上交户部,转发给巡盐御史,比对勘合仓钞信息,然后准许商人关引支盐。如果有商人超过期限还未完纳粮料,那么就要将派给该商人的盐引数转派给别的商人。官府在商人纳粮之前,似乎会给商人“派盐引”,让商人按照盐引额度上纳相应数量的粮料,如果商人违限,那么就会失去盐引额度。这应该能说明“派盐引”和“纳粮料”是前后相继的两个程序,而官府要确定商人违限和商人的盐引额度,似乎需要一些登记程序,那么“报名”环节就有可能存在。
综合以上考察,在成化、嘉靖、隆庆年间的某些年份的确存在“报名”环节,而在正统、景泰、天顺、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某些年份能发现“报名”环节存在的一些痕迹。按照历史思维,同一制度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年代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史料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十分有限的,而能流传下来的史料也是十分有限的,能为研究者所发现并运用的史料则更是十分有限的。本文并不能找到开中法实施的所有年代的“报名”环节存在的证据,也不能阐明“报名”环节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差别。但是,根据以上或完整、或只能称之为蛛丝马迹的证据,本文似可以作出推测:在明代开中程序中,可能长期存在着一个“报名”环节——官府发布开中榜文后,商人到监中官处报名,与官府约定好盐引额度、上纳数目、上纳期限等事项,并且写下“甘限认状”之类的文书作为完纳粮草的保证书,然后到指定仓口上纳。
那么,“报名”环节为什么会长期存在,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
笔者推测,对官府而言,最重要的是用盐从商人手中换得粮草等军需物资,那么官府就需要对整个过程加以监管掌控。在“报名”环节,官府与商人约定好报中的盐引额度以及上纳的仓口,那么官府就能知道盐引的报纳情况。如果报纳人数过少,官府还可以及时对开中则例进行调整,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商人报纳。另外,通过“报名”环节,官府可以掌握报中商人的信息,如果商人违限不完,官府就可以催促商人完纳,甚至对商人做出相应的惩罚,以保证军需的供应。
而对商人来说,可以通过“报名”与官府达成协议,获得相应的盐引额度,如果在上纳粮草过程中,官府政策发生变化,自己的权益也有保证。正如前面提到的正统八年(1443)商人李恭的例子,户部突然宣布盐引停止开中,如果李恭与官府没有事先约定,那么他为了中盐所买的粮食就白买了。另外,商人也可以通过“报名”环节了解报纳情况,如果报纳人数已满,那么商人就没必要去籴粮了,从而避免损失。
三、关于“报名”与“窝”关系的考察
“窝”是明清盐政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学界对万历四十五年(1617)纲法改革后的“窝”比较清楚,但是对这之前的“窝”的情况则有些模糊。前辈学者对“窝”的起源与演变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37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在研究清代盐法时指出,“在清代,领受盐引和卖盐的权利已经是世袭的,可以传之子孙。但是它并不始于清代,似乎从明代的某一时期起已经如此,明末似已形成这样的习惯”①加藤繁:《清代的盐法》,收入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33页。。加藤繁首先触及明代的“窝”的问题,启发了后来的学者。1940年中山八郎在其基础上发现,“窝”的买卖在成化时期就已形成,并认为成化初年的“势要占窝”必须得到皇帝的敕许,后来才演变成为商人的“买窝卖窝”,但是对于“势要占窝”如何演变成商人“买窝卖窝”并没有说清楚。另外中山八郎猜测“窝”可能是户部发给的一种准许开中的证书。②中山八郎:《开中法和占窝》,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34~243页。1963年藤井宏通过有力的证据否定了中山八郎关于“窝”是户部发给的准许开中的证书的看法,并且从语言学入手,通过查辞典认为:“窝”有“空”的意思,“窝”的流行与势要占窝使用空名有关。但是藤井宏也认为成化时期的占窝是以皇帝敕许为前提条件的,以“空名”为特征,而在万历中期以后变成了商人占窝,用的却是实名,不过藤井宏仍然没有说清楚敕许占窝是怎么演变成商人占窝的。③藤井宏:《占窝的意义及其起源》,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347~367页。1996年中国学者王振忠否定了藤井宏通过书面语来解释“窝”的做法,并认为“窝”起源于北方俗语,其意为“空缺”,并且认为明成化时期的“窝”与清代的“窝”的含义并无不同。另外,王振忠认为“窝”的出现与“抢上之法”的破坏有关。①王振忠:《释“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39~142页。亦可参考氏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一章第一节,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1页。
综观前人研究,王振忠强调“窝”的延续的一面,而中山八郎和藤井宏则强调“窝”的断裂的一面:他们认为成化时期出现的“窝”是以皇帝敕许为前提的势要占窝,万历时期的“窝”是商人占窝,两种“窝”存在转化过程,但是他们却不能解释这种转化过程。那么,这就不禁让人猜测:会不会万历时期的商人占窝在万历以前就已出现并且一直延续着?会不会成化时期不仅仅只有皇帝敕许的占窝这一种“窝”存在?
笔者推测,明代某些商人或势要可能会通过开中程序中的“报名”环节来实现占窝和买窝卖窝,并且这种形式的“窝”可能在成化以前就已存在并且长期延续着。
现在,本文重新审视一则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成化时期的材料:
今后遇有开中,都依户部奏准事例,并不许内外官员之家中纳包占,其客人引数亦不许过多。附近的赴户部报名,路远并见在各边居住的,赴巡抚等官处都要报名,审勘明白,与定数目,依期上纳。不许转卖与人,及听人包揽。②戴金著,蒋达涛、杨一凡等点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8《盐法》第6条《禁约内外官员家人包占盐引数过多转卖与人例》,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8页。
官府规定,以后遇到开中,商人都需要向户部或者巡抚等官报名,与官府约定好数目(疑为盐引数或相应的纳粮数之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官府警告商人,在报名后不要将盐引额度转卖与人。那么,报名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盐引中纳权,似乎能通过某种方式在商人中间交易。那么是什么方式呢?另外一则成化时期的材料可以给人启示:
辽东各仓,近年开中盐课,(谏)[办]共三百八万余引。中间有报名上纳未完者,亦有全曾纳者。自文书到日为始,俱限六个月以里完纳。若有仍违限(右)[不]中及捏故告与别商顶纳,即系“买窝”之人,巡抚官即便擒拿,解赴部转送法司问罪,枷号示众。①戴金著,蒋达涛、杨一凡等点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8《盐法》第5条《禁革盐法诸弊事例》,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5页。
材料中,官府催促那些已经报名还未上纳粮草的商人赶快完纳,给他们制定了完纳期限。并且警告商人,如果仍然违限,或者以某种理由自己不上纳,让别的商人顶替自己,就会被视为买窝卖窝。结合上面一则材料,可以看出:商人在报名成功后,可能会与别的商人交易自己的中纳权,交易成功后,报名的商人可能会以某种理由向官府申请,让别的商人顶替自己中纳。而在官府看来,这样的一种交易方式也是买窝卖窝。
另外,景泰三年(1452)叶盛在《军务疏》中提道:
合无将累次报中盐粮客商,该部通查拘送提督都御史处审勘,中间有力无力,听其转换与人,不许卖窝私贿,但系有米之人,准与更名填结通关,庶免久占无益。②叶盛:《军务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59(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67页。此疏在《明经世文编》中并未标注年月,质之《明实录》,《明英宗实录》景泰三年十一月丙戌条载有此疏的缩减版,故将之定为景泰三年(1452)(参见《明英宗实录》卷223,景泰三年十一月丙戌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847~4848页)。
材料中,叶盛为了解决军饷问题,建议对已经报中的盐商重新进行审核,如果中间有的盐商无力上纳,那么准许他“转换”给别的盐商上纳,但是不准趁机卖窝,如果“转换”之人确实是有米之人的话,那么就给他们修改登记的姓名,上纳粮草通关,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商人久占盐额却不上纳粮草的现象。其中,叶盛准许盐商将盐额“转换”与有米之人,为他们“更名”,并警告他们不要趁机买窝卖窝。叶盛的警告正向我们暗示了商人可能会利用“转换”与人的机会买窝卖窝。这与上面商人可能会利用报名环节买窝卖窝的推测较为吻合。
藤井宏为了说明“窝”与皇帝敕许的关系,列举了嘉靖时期的两则史料:
窃惟盐法之弊莫甚于占窝。凡占窝之人,非内外权势则市井奸猾,一闻开中,则钻求关节,伪写书札,相率趋之。监中官或畏其势,或受其欺,止据纸状姓名准中。商人挟赀冒险而无售,彼且勒取高价而卖之,空手而往,满箧而归。商人未纳官粮先输私价,是卖者之利,非买者之愿也。①朱廷立:《盐政志》卷7《疏议下》,《续修四库全书》第8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盖顷岁以来,所司固以商人困敝不得利,改议:每盐一引,止令输粟一斛,若银则四钱有半,此诚通商惠工之术,安边足用之道,其何不善之有?奈何法立奸生,利不归商贾之家,而顾以充豪猾之槖。闻之边人言:每岁户部开纳年例,方其文书未至,则内外权豪之家遍持书札,预托抚臣,抚臣畏势,而莫之敢逆,其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其余多寡各视其势之大小,而为之差次,名为买窝卖窝。每占盐一引则可不出大同之门,坐收六钱之息。至于躬身转贩真正商人,苟非买诸权豪之家丁,丐诸贵倖之仆隶,则一引半缗,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白得银六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致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②胡松:《陈愚忠效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246(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87~2588页。
藤井宏认为两则材料中所提到的书札,是从宫廷中流出来的特别文书,代表了皇帝的敕许。①藤井宏:《占窝的意义及其起源》,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357~360页。可是从材料本身而言,似乎难以看出这些书札与皇帝的联系。相反,这两则材料似乎指向另一个方向。材料中,势要和商人在开中之时,拿着书札(这书札更有可能是宦官或者高官的亲笔信之类)去找巡抚等监中官,监中官碍于人情或者惧于权势,便给来者一定数量的盐引。但是如何给呢,只是口头约定吗?似乎需要一些文凭来证明,不然如何买卖呢?而其中“止据纸状姓名准中”数语似乎表明:监中官给来人盐引的方式,或许就是报名登记。那么,这种找关系向监中官报名占窝的方式,是与皇帝敕许占窝不同的另一种方式。
隆庆三年(1569),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谈道:
照得该镇专利之徒所至有之,凡遇开派盐粮,辄请托钻求,先投认状,此卖窝故智也。②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359(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69页。《明经世文编》中未标注此疏年月,《明穆宗实录》隆庆三年闰六月甲辰条载有此疏与《清理宣府屯田疏》合并的缩减版,故将此疏定为隆庆三年(1569)(《明穆宗实录》卷34,隆庆三年闰六月甲辰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871~874页)。
庞尚鹏提到大同镇开中盐粮之时,会有“专利之徒”到处请托,先投认状的现象。庞氏认为这个就是“卖窝”的手段。其中“认状”值得注意,前面已经提到,在报名之时,盐商会写“甘限认状”之类的保证书,此处的认状大概就是此类保证文书。这就显示:有的商人会通过“报名”环节占窝、买窝卖窝。
万历年间也有材料,万历六年(1578)有官员提道:
边地本色,全赖盐商报纳之利。迩者,远商托赴镇乘贱多纳,假名截剩以图占窝,土商买之以希微利,既则远商去而土商为纳,不无负累。①《明神宗实录》卷73,万历六年三月庚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596页。
材料中的远商在边镇中盐,趁着粮食价格便宜之时,多上纳粮食作为预付的粮食,以此来报名认领剩下的盐引额度。而没有获得盐引额度的土商,只能向远商购买才能参与中盐。所以形成了远商占窝卖窝,而土商买窝上纳的现象。这也显示了“报名”环节与占窝、买窝卖窝现象之间的联系。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势要、商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优先报名,获得中纳权以形成占窝,并对中纳权进行买卖,也就是买窝卖窝。而通过报名方式的占窝、买窝卖窝应该也是长期存在的。
事实上,报名与“窝”的关系不限于开中程序中,也存在于盐的掣验环节中。
万历四十四年(1616)袁世振提道:
所谓虚单者,止据商人报名入单,上纳余银,而买引补单在后。初时亦谓既系预征,恐难并举,姑暂缓之,而非令其终不买也。乃各商乘此久不补空,徒为占窝。故谓边引之壅,动至数百万不售者,职此虚搭之故耳。②袁世振:《盐法议一》,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474(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08页。《明经世文编》并未标注此疏年月,但是考之《明实录》,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条简略记载了袁世振的《盐法十议》,所以此疏当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所作(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52,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429~10430页)。
按照一般程序,商人在支盐后,需要到批验所掣验,然后才能运销。所以商人到达巡检司后,巡检司会按照到达次序报名登记,制作“真单”,然后商人再到批验所按照“真单”次序掣盐。③具体情况可参见徐泓《明代前期的食盐运销制度》(《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74年第23期,第246~247页)。材料中,商人并没有买引支盐,直接报名入单,并且长期不买边引补空,袁世振称这种情况为“占窝”。可见在盐的掣验环节,报名与“窝”仍然联系紧密。而袁世振纲法改革,就是以报名“真单”中的商人作为纲商,为他们刊定十字纲册,作为“窝本”。①袁世振:《纲册凡例》,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477(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46~5248页。也应参考相关的研究,如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293页。
所以,开中法中的“窝”,不仅仅与皇帝敕许有关,很可能也与“报名”环节有关,而通过“报名”环节形成的“窝”可能更加广泛,延续时间也更长。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明代开中程序中可能长期存在着一个“报名”环节,而通过“报名”的方式决定哪些商人上纳粮草可能比“抢上之法”更加广泛,实行的时间也更长。而明代开中法中占窝、买窝卖窝现象的产生,不仅仅与皇帝敕许有关,还应该与“报名”环节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