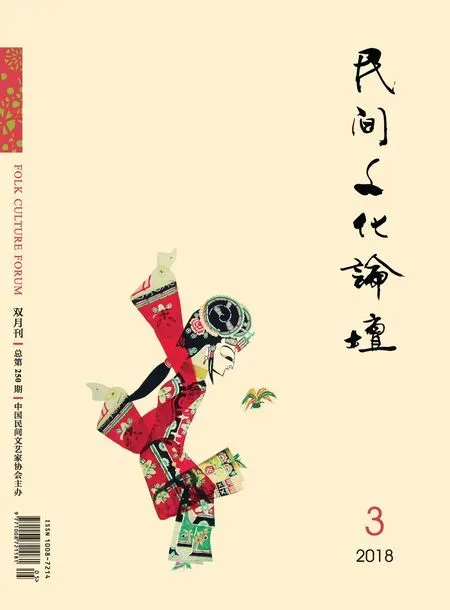民俗学的实践问题*
2018-01-23福田亚细男菅丰塚原伸治彭伟文
[日]福田亚细男 菅丰 塚原伸治 著 彭伟文 译
特别策划
关于日本民俗学何去何从的两代人之间的对话——日文版全书译文呈献
20世纪民俗学在其学科起步之时,提出“学问救世”的目标,并以“经世济民”为标榜,像宫本常一这样的实践派民俗学者辈出。此外,众多的民俗学者在学校、博物馆等文化公共机构展开与社会密切关联的活动。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学院派向民俗学的渗透,这种实践性的目标和活动受到了轻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福田氏指出了民俗学的实践的必要性。亦即恢复野的学问的精神,带着危机意识投入实践性课题,以批判精神进行问题设定的、有发言能力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的实践的方向性,与新的公共民俗学也是相通的。那么,日本民俗学“实践”的具体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呢?此外,对限定实践的立场性,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克服它呢?
一、对20世纪民俗学21世纪化而言的“实践”是什么样的?
二、恢复野的学问的精神,带着危机意识投入实践性课题,以批判精神进行问题设定,有发言能力的民俗学是什么样的?
三、纯粹学者?御用学者?政治家?地方的实践家(practitioner)?
四、与其他学问相比较,特殊的研究者属性和多样性,对学院派民俗学而言是负面的,但是反过来从与社会的关联性方面看,会不会是正面的?
五、这会不会正是民俗学在21世纪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方向之一呢?
六、是否有必要在认识、理解其多样的立场性和其任务所带来的差异的同时,克服相互间的差异?
七、如果说20世纪民俗学后半期的学院派化是学院派民俗学的学术主导权集中化、独占化的过程,应该也不为过。但是,现在是否应该对多样的立场共同谋划,共同发言,共同实践的学问——现代民俗学,以及支撑它的机构(学会)进行再建构呢?
八、那么,这种提高实践性的民俗学,仅靠对20世纪民俗学进行小修正是否已经无法实现呢?
失去实践性的民俗学
菅:20世纪民俗学在其起步之时,提出学问救世的目标,标榜经世济民,宫本常一这样的实践派民俗学者辈出。此外,众多民俗学者在学校、博物馆等文化公共机构展开与社会密切关联的活动。但是,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学院派向民俗学的渗透,实践目标和活动受到了轻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进20世纪民俗学的21世纪化,福田先生指出了民俗学的实践的必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中,也从多个方面提到了实践的问题。福田先生主张,民俗学必须恢复“野的学问”的精神,带着危机意识投入实践性课题,以批判精神进行问题设定,能够对社会发言。这种民俗学的实践的方向性,与“公共民俗学”(这是我所关心的方向)的根底是相通的。那么,福田先生所主张的日本民俗学的实践性,它的具体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另外,对限定实践的立场性,我们应该如何去克服它呢?
今天,直到现在我们一直以学院派民俗学的课题为主进行讨论。但是,最后我们想就多样的参加者所参与的民俗学的特殊性,以及它的潜力讨论一下。
基本上,我认为民俗学既有着巨大的问题,也拥有巨大的可能性。其一,是今天一直讨论的,学院派民俗学所存在的问题。
这也是福田先生一直思考的问题。福田先生一直主张,将日本民俗学建设成与其他学问相同的“普通的学问”。我也希望建设成“普通的学问”。如何才能让学院派民俗学成为“普通的学问”呢?作为“普通的学问”,应该是国际化、理论化、先锐化、学际化的,能够实现将不同领域的视角、方法等吸收进来的。从这一点上说来,学院派民俗学现在的状况必须彻底先锐化。
但是,另一方面,正如福田先生经常指出的那样,日本民俗学实际上原本有着非学院派民俗学的背景。日本民俗学原本是从实践的学问起步,并且是作为“野的学问”起步的。
也就是说,在肩负民俗学的人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不仅仅是学院派,还有来自公共机构的人。此外,还有虽然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对民俗学本身抱有关心、进行研究和实践的人。这个学科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学院派民俗学一方面必须是先锐化的,另一方面,则必须作为“大民俗学”将这些多样性的民俗学参与者包含进去。
我现在认为,正是凭着这种将多样的参与者结为一体形成的民俗学的特殊性,民俗学才能与其他学问相对抗。正因为这一点,民俗学具有很大的力量。这两者之间,有时会处于互相消长的关系,但是我想必须设法让这两者能够共存。
民俗学经常被说是实践的学问。关于这一点应该没有必要再说明。柳田国男先从事农政学,宣称自我内省、学问救世等,有人发现了这与民俗学之间的连续性。比如藤井隆至①[日]藤井隆至:『柳田国男経世済民の学―経済·倫理·教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的“经世济民”论等等。反过来,也有人从中看到了非连续性。如岩本由辉②[日]岩本由輝:『論争する柳田国男―農政学から民俗学への視座―』,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5。等。福田先生应该主张的是农政学和民俗学的非连续性。实际上我也是 这样想的。
很多人在柳田身上看到了实践性。确实,柳田也发表过实践性的言论。如众所周知那样,福田先生也就这一点曾经写道:“在精神上,柳田所提出的是名副其实的‘为世间为人们’有所贡献,实践性的学问。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与欧美的民俗学,或者是日本的其他类似学问有着不同的特质。”③[日]福田アジオ:「民俗学のこれから―柳田国男から宮田登、そして今後は―」,『二一世紀フォーラム』77,2001,第9页。
关于这一点,我也确实是这样想的。无论是美国民俗学还是德国民俗学,都没有在学科起步之时如此明确地表明实践性。实际上,这一点正是我执着于日本的民俗学,仍然将民俗学称作自己的专业的理由。同时正是这一点,有着巨大的学术潜力。
但是,柳田的话,我想接下来大家会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那不过是单纯的言说而已,从他实际的行动来看,柳田的民俗学归根结底和农政学是非连续的,不得不说他的学问是非实践性的。简而言之,如果从柳田的庞大的著作的各个论述来看,民俗可以归结为事实的变迁过程,并没有将民俗当作现实的、实际的事物。在这方面,我想福田先生恐怕也可以说跟柳田是一样的。
对柳田可以进行各种深入研读。比如,我在批评柳田的时候经常用作例子的是以下这一句话。当柳田谈到劳动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所想要了解的劳动问题,不是今天的所谓劳动问题。”①[日]柳田国男:『郷土生活の研究法』,東京:刀江書房,1935,第193页。在这里,他讨论的是ユイ和モヤイ②ユイ(結い)和モヤイ(催合),日本村落共同体的互助形式。数人或数个团体相互间以交换劳动力的方式进行互助称为ユイ,共同提供劳动力完成一项事务称为モヤイ。——译者注。
所谓今天的劳动问题,是指在资本主义扩张中出现的现代的问题,是在发生现实的劳动纠纷之类的时代的问题。柳田表示民俗学所要研究的不是这样的问题,将现实的问题排除在外。柳田自己也曾经说过,即使是在农业方面,所研究的也是很难看到其古老型态的,形骸化的残存问题,有意识地弱化问题。柳田所选取的,归根到底不是近在眼前的今天的所谓劳动问题。
排除眼前现实的民俗学
菅:福田先生说过“如果不是历史的话那就不是民俗学”,柳田也同样说过“今天的问题不是民俗学”,将今天的问题排除在外。所以,我在实践这个意义上,是不相信柳田的。
但是,另一方面,今天也到场的室井康成,在他的著作③[日]室井康成:『柳田国男の民俗学構想』,東京:森話社,2010。中,表示了以下理解:“柳田的学问,是企图培养公民、良好选民的政治学。”即,民俗学实际上是负责对正确地传承事实的方法进行实践。要言之,对柳田而言,所谓正确地传承事实,那就成为政治学,也就是说对这种方法进行实践的态度就是政治学。在读室井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也认为确实在某些方面可以这样说。
简而言之,通过柳田的著作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深度解读。
另外,室井先生还引用了桥浦泰雄④桥浦泰雄(1888-1980)是共产主义画家、民俗学者,1925年起师从柳田国男。作为“星期四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为民俗学的组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桥浦泰雄在柳田指导下的活动,鹤见太郎作过细致的研究(鹤见,1998、2000)。以下的话:“民俗学虽然是以幸福为目的的学问,但是如果要将这门学问的结论对常民实现具体化,则是政治家的责任。”⑤[日]橋浦泰雄:「連載インタビュー·柳田国男との出会い」,『季刊柳田国男研究』2,1973,第115页。这里所说的“政治家”恐怕按照今天的意义来讲,应该是带双引号的。他还写道:“如果学会员”(也就是民俗学者、民俗学研究者)“打算将研究的结果具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将不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政治家去实行。因此,应该以负责任的实践为目标。”⑥同上。。在以这个实践为目标的过程中,柳田以室井先生所分析的公民论的形式向社会发言,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实践。这恐怕也可以说是实践之一。
但是,我不太想把这个当作和我们当下应该关心的实践同样的东西。又或者说,也许可以把他做过的事当作实践,但是这恐怕不过是用语言表达程度的言说行为的实践而已。虽然实践这个词可以表达各种各样不同的行动,但是柳田的实践并不是我们现在真正必须做的,或者说是可以做的实践。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管怎样,随着20世纪民俗学的学院化,民俗学埋头于个别的事象,而忘记了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性。其结果就是根植于地方,以应用为重的宫本常一,从民俗学的正统史中消失了。从以历史民俗学派为中心的正统民俗学史中消失了。福田先生也经常说:“宫本常一在学术上的定位非常困难。”也就是说,他确实进行了实践,但是很难评价他在研究方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福田先生的著作《日本的民俗学》①[日]福田アジオ:『日本の民俗学―「野の学問」の二〇〇年』,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虽然也提到了宫本常一,但是我觉得对他并没有多重视。也就是说,就学院派而言,对他的评价是很困难的。
另一方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社会上宫本常一是压倒性的名人。不仅著名,而且在社会上评价很高,因为他带来很大冲击。简言之,就是一种学术上的价值和社会上的价值呈现明显乖离的状况。
民俗学如果从实践性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与其他学科相比是比较弱的。此外,刚才已经说过,民俗学里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存在各种各样的立场。然而,尽管应该超越多样的立场相互合作,尽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学院派民俗学研究者却被困在了一个限定的世界里。
本来,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里,有在野的研究者(也许可以不用“研究者”这样的表现)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现状是这些被割裂了,学院派民俗学者掌握了民俗学的主导权。一般认为,在“野的学问”时代,柳田和他身边的弟子们作为在野的民俗学研究者,虽然呈同心圆状态,但是互相接近。但是,实际上毫无疑问存在着由柳田国男、身边的弟子、地方的同志构成金字塔式层级结构的事实。然而,在其后的学院派化过程中,柳田身边的弟子成为了学院派的担当者。
那以后,如果从柳田国男死后人们的关系角度来说,形成了学院派和非学院派,职业和非职业的关系。而且,学院派的研究者逐渐成长,民俗学被割裂了。简言之,这种隐性的割裂、错误的二元论,导致了发言力、主导权不均衡的发生。
最后,学院派民俗学由于被从“野”割裂开来,虽然实现了制度化的建构,但是与社会产生了乖离。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人们中也出现了割裂,有人努力将自己的工作置于学院派当中,反过来也有人毫不在意学院派与否,按照自己的想法在当地进行民俗学实践。
这种割裂状态是当今民俗学所存在的一大问题。我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是21世纪民俗学的课题之一。作为其中一个方向,最近我提出了公共民俗学。我认为,必须实现公共部门的研究者、学者,此外还有刚才说到的非职业性的人们,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的民俗学。我从这里看到了民俗学的一种方向性和可能性。为此,我想用以下的公共民俗学定义,去和福田先生的定义对抗。
公共民俗学是,在理解并克服不同性质的立场,在自觉文化的所有权和表象行为的权威性这一困难的问题的同时,获得表象的正统性,介入面前的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将以这些人们的幸福作为存在目的的民俗进行客体化,参与到某种保护行为中,进而对整体性参与的自他双方的实践和研究加以回馈性的、顺应性的重新把握的民俗学的方向性。
这是“我所作”的公共民俗学的定义,今后很可能会出现关于现代民俗学的各种定义,正如刚才福田先生所说的那样,今后还会开始出现哪个定义具有正当性这样的主导权之争,同时也必须出现这样的争论。同时,我认为它的定义可以是多样的。作为其中的一种定义,我想在这里从公共民俗学的角度提出新的定义。这是我想创造新的民俗学中的一种。像刚才说过的那样,虽然现在民俗学的定义只有福田定义一种,但是今后必须有让这个定义成为one of them的行动。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我想是实践性的问题。恐怕其他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工作,我们必须一点点积累下去。
对福田亚细男的实践的提问
菅:接下来是提问。福田先生从20世纪末开始使用“实践”这个词。但是,在民俗学的21世纪化这个具体问题上,福田先生所认为的实践是什么样的?恢复“野的学问”的精神,带着危机意识投入实践性课题,以批判精神进行问题设定,能够对社会发言的民俗学是什么样的?是天真无邪的民俗学者站在上位立场进行启蒙发言,还是依附行政的御用学者式行为?又或者是作为像室井先生所说的那种所谓政治家?又或者说在地方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工作的,作为practitioner的实践家?在这一点上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此外,与其他学问相比,民俗学研究者的特异性、多样性,对学院派民俗学而言一直被认为是相当负面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参与民俗学,日本民俗学会里有各种立场、职业的人,从学院派这样很狭小的标准来看,一直被视作负面的因素。这种多样化的参与者,在日本民俗学会这里,通过杂志的同行评议等手段将他们排除了出去。然而,这些因素对学院派民俗学这样狭小的世界而言可能是负面的,但是从与社会的联系,或者是从把握实际人类社会的大的学问转换角度思考的话,是否毋宁说这是积极的状况?
简单地说,就是民俗学存在的多样的参与者的问题。这正是民俗学在21世纪具有可能性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有必要克服参与者之间的壁垒。
进而,像刚才说过的那样,20世纪民俗学后半期的学院派化,将民俗学的主导权集中到了学院派民俗学。也就是说,学院派民俗学独占了这一学科。现在,参与者的多样性还存在于2100人的日本民俗学会会员中,难道不应该构筑能够对这些参与者作为整体给予支持的学会吗?现在的日本民俗学会过度以学院派为中心了。不用说,学会杂志这样的学院派媒体,更为精致化地向着学院派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难道不应该提供一些像以前那样的不遵循学院派尺度的较为宽松的媒体等发表媒介吗?我想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福田先生在学会的学院化,或者说是现代化方面也一直有很大影响力。我也在一起担任日本民俗学会理事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情况,福田先生说向右,大家就都向右。这虽然不是福田先生造成的,但是他影响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福田先生承担着推进学院派化的一翼。
我的问题已经讲得太长了,但是还有佐佐木美智子女士提出的问题。这和我刚才讲的问题是共通的。
“众所周知,民俗学到目前为止得以维持其有效性,主要有赖于它作为历史认识的姿态。今后的民俗学,对历史认识是重视,还是将其作为重新认识的对象,恐怕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希望以下述三点,作为自己在以历史认识为基本姿态的同时注视当下的思考课题。
① 历史认识与个体的问题
② 学院派民俗学与实践性
③ 研究者的立场性问题
我想,这些是我自己的课题,同时不也是20世纪民俗学所欠缺的吗?也就是说,反过来看一下,就可以发现20世纪民俗学对个体的轻视、实践性的欠缺、研究者自身没有对当下社会主体性介入的自觉。简而言之,就是似乎在建构作为历史认识的民俗学的过程中,过分追求民俗的历史,而丢失了人的故事。先生是怎么看的呢?”
虽然问题大了一点,但是我首先想问,在将20世纪民俗学21世纪化的问题上,福田先生的实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多样的实践形式
福田:在回答之前我要先说一句。菅先生刚才的整理方式和我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简言之,菅先生把学院派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者等同起来,并以多样的参与者这样的表现形式说明还有各种各样从事民俗学的人。虽然说这也是一种整理的方式,但是我认为所谓学院派民俗学,是包含了这些多种多样的参与者的,简单地说就是在大学里进行民俗学再生产,并且对其加以系统化的,这样的就是学院派民俗学,而不是从职业,或者说是在某个位置上的人去划分的民俗学。恐怕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大学里学习过或者是修习过民俗学,才成为民俗学的研究者。在职业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大家都是在大学里经过再生产,由此知道了民俗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进入这个学科,其后也以各种形式在以大学为中心的研究体制里进行研究活动。在这一点上,学院派民俗学和它之前的“野的学问”之间很大的不同是,自己所从事的民俗学,不再需要通过自己的谋划或者努力去获得信息才能进行。这里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的状况。不管是以学院派,还是公共的说法去分类,我想都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点。
接下来,虽然涉及表达方式的问题,但是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有一点要说的是,民俗学这个学科,必须是综合各种研究的立场、形式、方法而成的民俗学。因此,是不是应该避免以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者概念去从立场对它进行定义呢?所谓民族、民族文化之类基层文化,基本上是已经在本身的意义上表明了一定的立场,因此我想我已经表达过了,不要将这些放到民俗学的定义里面,以这种形式让各种各样的人从各种各样的立场参与其中。所以,在讨论实践的时候,可以说实践是必要的,必须要加强实践等等,但是要这样做,基本上是从事民俗学、研究民俗学的人,正是从研究者的主体判断和行动出发,而不是在民俗学的名义之下去进行某种实践。或者说,不是以民俗学之名去达到一个特定目的。应该存在有多种多样不同立场的民俗学参与者,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会互相争夺正当性,但是应该首先在民俗学里面自己去对实践这一行动加以实现。这个实践的形式,按照你刚才的分类,有纯粹学者、御用学者、政治家,虽然这些说法听着是不太习惯,但是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立场。比如,上溯到柳田国男的话,柳田国男的实践之一,就是他持续发表论文《海上之路》,这与旧金山讲和条约之间是有关系的。我将这也解释为实践。所以,虽然他没有写到任何实践性的内容,但是读者通过认识到冲绳的重要性,开始在面对旧金山讲和条约时思考自己的立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产生了关联。此外还有一个实践的例子。跟前面的不同,在《关于祖先》的最后,谈到如何能让没有留下子孙就在战场上死去的人们获得幸福时,他提出一个方法是把这个人加入到其家族的同代人里去,又或者是把战死者作为第一代,收养一个养子创立家族,死者就能得到祭祀,他做过这种提出建议的实践。在他的各种实践中,既有具体的建议和提案,也有不作具体阐述,而是结合思想、信条等进行研究并发表成果,我想应该说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所谓实践,虽然是有点抽象的,一般性的说法,但是去实行它的是民俗学的研究者,必须由一个个研究者负责任地去获得实践性,并且去实现它。如果问我“那你干了些什么?”这方面深感惭愧,无法在这里堂堂地说出“我的实践有这个这个”。虽然不太好看,但我感觉是这样的。
就这样先告一个段落,你看怎么样?
菅:在这里的诸位,恐怕也有很多人会越是读柳田国男的著作,越会将柳田的行为理解为实践。这么说吧,政治学者本来就在研究中提出建议,但是恐怕仅仅那样不会被称为实践。虽然有学术实践这样的说法,但是不会被称为实践。而民俗学者只是发表意见,就算是实践了。简而言之,就是做做提供思想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现在地方上有一些人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实践。不是提出建议,不是整个日本的问题,而是投入到自己身边的问题当中。关于这样的活动,福田先生是怎么看的呢?简单地说,问题可能在于这些活动中是否有民俗学的背景吧?
福田:我想关键应该在于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立场,为了什么目的在地方进行活动吧。所以说,这是个人责任的问题,作为他们的具体行动的基准的发言,必须从他们作为民俗学研究者的成果,或者是构成他们的立场的相关信息出发。因此,像桥浦泰雄那样,他自己可能觉得是统一的吧,但是他在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和其他活动,尤其是战后作为共产党员的活动是不同的。后者对本人来说是实践,但是应该不能把它视作民俗学者桥浦泰雄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吧?这里必须要考虑什么是以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实践。所以,一方面作为个人加入民主党,另一方面从事民俗学,我想仅仅这样恐怕是不能称作实践的。
菅: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学术性背景下的实践。我想这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也很清楚,福田先生和我之间对学院派民俗学的概念设定存在差异。我所说的学院派民俗学的观点,是以美国民俗学的观点为基础设定的。在美国,这个划分是很简单的。这不是我想出来的说法。福田先生的意思是,您所认为的学院派民俗学的概念设定,简单地说,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福田:与其说是没关系,应该说是赞成也好反对也罢,都在这个体系里再生产这样一种形式。
菅:在这个体系里出来的人是这样。对那以后的肩负民俗学的那些人,以及生产民俗学者的场所,您是怎么想的呢?
福田: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后肩负民俗学的人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学院派民俗学。
菅:但是,那些并没有在大学里学过民俗学的人,他们也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福田:当然是这样。但是,基本上,至少在这数十年间,在自己住的地方发现民俗,自己想“我要研究这个”,以这种形式一路研究过来的人应该是非常少的少数。基本上是在哪里的大学,或者也可能是跟大学有关联的文化中心之类,在什么地方从学院派民俗学者那里听说了民俗学,学习过,自己也开始进行研究,这样一种程序。这应该是压倒性多数。
菅: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们有很多在参与实践。
福田:是的。
柳田国男的实践和宫本常一的实践
菅:这些不属于学院派民俗学的人们的实践,如何去评价呢?这也不过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是这样评价吗?
福田:不管是什么立场,我想都是很好的事情。学习民俗学,使自己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发挥作用,在各自的思想信条、使命感的基础上行动,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菅:福田先生在讲到其他国家的民俗学所没有的日本民俗学的特征时,列举了这部分的内容。作为欧美的民俗学所没有的部分,您列举了实践。然而,所谓欧美民俗学所没有的实践,就现在我们所说的来看,也不过就是政策建议。但是,就算是政策建议,也不是具体的,而是比较抽象的,比如家庭必须是这样之类,也就仅限于这种程度的建议。而且,这些恐怕也是柳田以外几乎没有别人做过。
福田:但是我想,应该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实践的。
菅:柳田以外很少有这样体现实践性的活动。而且,柳田的实践和宫本常一的实践是明显不一样的。
福田:是不一样。
菅:宫本常一的实践,反过来毋宁说是福田先生反对的实践。
福田:不是,我想不是这样。
菅:但是不在射程内。
福田:不是,没有这样的事。
菅:那是研究吗?
福田:那就变成对宫本常一的研究本身的评价问题了。但是,从宫本常一个人来说,他自己的民俗学研究,采取的就是到当地去提出建议,或者是给予指导这样一种形式。作为他自己,是基于民俗学的成果去提出建议。但是,要说宫本常一的民俗学成果,依我看来,那基本上都是无法验证的研究。只有宫本常一自己才明白。
菅:“研究”的评价标准,我觉得简单地说就是由学院派民俗学的尺度所规定的。
福田:我想,基本的要求应该是依据可以验证的成果去实践吧。
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学院派民俗学必须超越。刚才我将学院派民俗学以职业进行了划分,但是我认为必须构想超越这个区分的大民俗学。
至少,即使柳田有实践性的发言,但也不是脚踏实地的实践,结果基本上什么都没做。与其将柳田所说的视作实践,毋宁说宫本式的活动才是在现代社会被很多人承认为实践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福田先生所说的实践,在社会上到底还是被判断为“这些东西不是实践”。当然,还是会被承认是迂回式的高抽象度的实践。
福田:但是,问题是宫本常一的活动是否具有有效性。他到这个村子去,到那个村子去,提出建议,给以指导,这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做了事情这一点是可以给予高度评价的。
菅:确实,关于通常被美化了的宫本的实践的实际情况,今后应该再行检讨。我经常去的新潟县小千谷市的田野点旁边的旧山古志村,宫本也去过。他在那里也提过各种建议。然而,结果是他提出建议这种实践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当地对宫本的评价还是很高,现在评价也还是很高的。这样的高评价还存在于全国各地。那可能是仅限于当时的运动,一段时间啪一下就结束了,但是对当地的冲击和当地人对宫本的印象明显还是鲜活的,明显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柳田的实践,则只得到民俗学者的认可。一般社会上的人们,并没有将由于柳田的启蒙思想而受到公民教育等事实作为实践去评价。简言之,虽然民俗学者认可柳田的实践,但是普通社会并不认可。因此,我想柳田那样的实践方式是不是行不通呢?
福田: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级别不一样。并不是说只有在个别地方提出建议才是作为民俗学研究成果的提案。比较总论性的,一般性的,或者是所谓日本、世界、人类这些级别研究成果的建议之类的某种提案,我想就其本身而言也是非常具有有效性的。
菅:今后从历史民俗学会产生这样的实践吗?
福田:应该不是历史民俗学,而是从民俗学产生这样的实践吧。
菅:是这样吗?我认为,在历史民俗学方面,今后不会出现提出建议的人。还不如说,至今为止,柳田以外没有提出这样大型的、实践性的建议的人,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