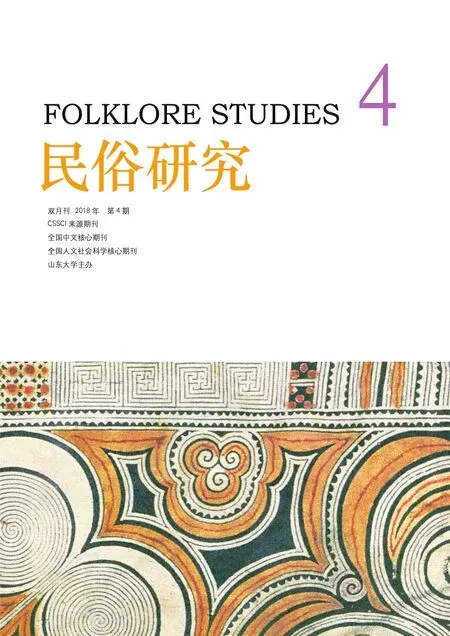壬辰战争:耳冢历史记忆的再建构、越境与交涉
2018-01-23赵彦民
赵彦民
一、问题的提出
壬辰战争是1592-1598年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这场战争涉及了中、日、韩三国。在日军侵略朝鲜半岛的过程中,秀吉的武将们把朝鲜军民及援朝明军的鼻子和耳朵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证据带回日本。今日本京都市东山区丰国神社门前的耳冢,就是埋葬朝鲜军民及明军的耳、鼻以及供养这些亡灵的地方。*以往的研究中关于耳冢内埋葬的是被掠杀的朝鲜军民及援朝明军的鼻子还是耳朵存有争议,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韩国学者鲁成焕的《耳塚の「霊魂」をどう考えるか》(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指出,耳冢内埋葬的不仅是朝鲜军民及明军的鼻子和耳朵,还有朝鲜将帅级的尸首。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为“耳冢”。耳冢作为壬辰战争历史记忆的其中一个表象,随着不同时代的变化,具有不同的内涵。本文主要以历史记忆为着眼点,探讨耳冢作为历史的再记忆化之过程。
在今中、日、韩三国社会中,耳冢的存在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有关耳冢的研究也屈指可数。1970年代,代表性的研究有琴秉洞的《耳冢》(1978,1994再版)一书。该书基于历史学的视角,从“耳冢的历史由来”“战时日军在朝鲜半岛掠杀过程中对朝鲜军民实施的割鼻切耳行为的整体性探究”“日本人和外国人对耳冢的态度等”“朝鲜人的耳冢观”四个方面展开系统化的梳理与实证性的考察。*[朝]琴秉洞:《耳塚》,综合社,1994年。管见,该书是这一时期关于耳冢研究的集大成者。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耳冢虽在个别研究中有被提及或关注,但大多被置于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中加以叙述,没有专门的论著。*例如,崔官:《文禄·慶長の役》,講談社,1994年;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耳塚」-江戸時代の「耳塚」観と壬辰·丁酉戦乱》,《秀吉·耳塚·四百年:豊臣政権の朝鮮侵略と朝鮮人民の闘い》,雄山阁,1998年,等等。在解释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倾向于认为,耳冢是日军为了炫耀强大武力和鼓舞军队士气而建。*[韩]鲁成焕:《耳塚の「霊魂」をどう考えるか》,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第3-4页。
近年来,韩国学者鲁成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民俗学的视角对耳冢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再检视,指出耳冢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炫耀武力与鼓舞士气,还与日本人的生死观和灵魂观等因素有关。基于此,鲁成焕从九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即(1)秀吉的家臣武将对朝鲜军民割鼻切耳的理由;(2)耳鼻是论功行赏的证据,但秀吉为何没有把它们随意处理,而是建造坟墓来供养;(3)埋葬的是耳朵和鼻子,为什么称为“耳冢”;(4)耳鼻以外还埋葬了哪些东西;(5)埋葬的耳鼻仅仅是朝鲜人的吗;(6)日本是如何利用耳冢的;(7)像这样的耳冢仅是京都才有吗;(8)看见耳冢的外国人的反应是怎样的;(9)建坟供养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民俗信仰。不难看出,鲁成焕从民俗学的视角对既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与实证考察,使耳冢的历史轮廓更加明晰化和全面化。
综上,以往研究主要从实证主义研究的视角出发,侧重于对耳冢这一历史客观事实的梳理、补充与明辨,以“还原历史”。与此不同,本文的研究焦点不是耳冢的客观历史事实,而是探讨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作为记忆是如何被建构、形塑和利用的,具有哪些时代特征。换言之,本文将耳冢作为探讨历史与记忆的一种媒介。历史与记忆不同,历史建立在单线性的时间之上,切割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但“记忆是鲜活的,总有现实的群体来承载记忆,因此记忆始终是处于演变之中,服从于想起与忘却的辩证法则,对自身连续不断的变形没有意识,容易受到各种利用和操纵,时而长期蛰伏,时而瞬间复活”*[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来捕捉不同时代耳冢记忆的再生产、再建构这一动态过程,同时考察在这一过程中,耳冢作为东亚社会的历史记忆在日韩两国之间出现的越境与交涉问题。
二、耳冢历史记忆的可视化
耳冢现位于日本京都市东山区丰国神社前,与方广寺的石墙及石塔一同被认定为国家史迹。*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死后,据其遗命埋葬京都东山阿弥陀峰的山顶,丰国神社是翌年1599年为了祭奠秀吉在东山的半山腰而建。方广寺是1586年由丰臣秀吉开始创建的天台宗寺院,寺院安放了当时最大的佛像,1596年因地震而受损,秀吉死后由其儿子秀赖在1612年重建完工。1969年4月,上述这些丰臣秀吉相关的遗迹包括耳冢都被指定为国家历史文化财。在耳冢的史迹前,有京都市政府在1979年设置的关于耳冢历史由来的说明板,其具体内容如下:
这座墓是16世纪末,统一日本后的丰臣秀吉试图把统治之手伸向大陆,试图进攻侵略朝鲜,即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史称壬辰·丁酉倭乱、1592-1598年)的相关遗迹。
秀吉下属武将取代过去以尸首作为论功行赏的方式,将朝鲜军民鼻子和耳朵割掉,用盐腌渍带回日本。据说,根据秀吉的命令这些朝鲜军民的鼻耳被埋于此地,开始了供养仪式。“耳冢”是与史迹“御土居”一同现存于京都丰臣秀吉的史迹之一,冢上的五轮塔,其形状在宽永2年(1643)的古绘图中可以确认,是在墓建成不久建造的。
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因为受朝鲜半岛人民坚决的抵抗以失败告终,战争留下的耳冢作为历史的教训,铭记着战争中朝鲜人民承受的苦难。*源于京都丰臣秀吉史迹的耳冢历史由来说明,原文为日文,笔者译。
从上述文字可知,耳冢形成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期间,埋葬的是抵抗日军侵略的朝鲜军民的耳鼻。具体而言,壬辰战争中,丰臣秀吉向侵略朝鲜的将帅们下达了“高丽国之军中御壁书之事”的命令,“割鼻令”源于此令中的第七条,即“修建异国军民的首冢,战场上斩断的尸首,老少男女僧俗不限,所有尸首带回日本”。*姜沆:《看羊录》,朴钟鸣译注,平凡社,1984年,第72-74页。但把朝鲜的军民的尸首从朝鲜半岛带回日本,存在诸多的不便,秀吉的武将们便向秀吉提议把朝鲜半岛军民的耳鼻切割下来带回日本。*[韩]鲁成焕:《耳塚の「霊魂」をどう考えるか》,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第17-19页。这点在姜沆的《看羊录》中有如下记载:
秀吉之再寇我国也,令诸将曰:人各两耳,鼻则一也。令一卒各割我国人鼻,以代首级,输致倭京。积成一丘陵,埋之大佛寺前。几与爱宕山腰平。*姜沆:《看羊录》,朴钟鸣译注,平凡社,1984年,第286页。
如上,受秀吉之命,其家臣们将朝鲜军民的耳鼻割下,用盐、醋、石灰等进行防腐处理后,把每一千个耳或鼻装入木桶中,运送到“军目付”*军目付,是指部队中的监察人员,不参加战斗,主要职责是视察敌情、监察战功、监督武将行为,等等。处,军目付对这些耳鼻进行核对,给提交者发放收领书据。据秀吉的武将们的家书记载,推算耳冢中埋葬有10万人以上的耳鼻。*日韓共通歴史教材制作チーム:《朝鮮通信使: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から友好へ》,明石書店,2005年,第25页。这些耳鼻从朝鲜运到日本后,在大阪汇集,然后换装更大的木桶,并在送往秀吉驻地的京都的路上作为战利品向民众展示,以显示胜利的战果和武力的强大。
这些耳鼻运到京都后,埋葬在方广寺(又称大佛寺)前。1597年,秀吉命相国寺的主持西笑成兑集京都五山僧众四百余人,在耳冢前祭奠、烧香、诵经、撒纸钱,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京都相国寺鹿苑院的僧录司日记对此记载甚详:
慶長第二曆秋之仲,大相國命本綁諸將,再征伐朝鮮國。於是大明皇帝運唇亡齒寒遠謀,出數萬甲兵救之。本朝銳士攻城略地,而擊殺無數,將士雖可上首功,以江海遼遠劓之,備大相國高覽。相國不怨讎思,却深慈愍心,仍命五山清眾,設水陸妙供,以充怨親平等供養,為彼築墳墓,名之以鼻塚。況又造立木塔婆一基,看看。此塔婆,喚作殺人刀也得,拈做活人劍也得,喝一喝。清風明月本同天,于時龍集丁酉秋九月二十又八日,敬白,如此書之。八寸方之柱三間,施食出頭,五岳眾來臨,堵物二結贈木食上人,一結遣雜職。午時施食,塚者在西,棚十條敷。盛物五種,餅、饅頭、飯、茄子、隨喜。箱者上三尺五寸,高三尺三寸。大旗者間逢紙十六枚充,緣以黑紙取之,予書之,以古帚為筆。大眾四百人,予燒香,清水大施食,北野經堂大施食者,兩度大施食燒香者。*迁善之助编:《鹿苑日錄》第二卷,大洋社,1934年,第368-369页。
结合上文和此处引文,我们能了解耳冢建立的过程。从中也可以看出,丰臣秀吉建立耳冢具有如下的动机:首先,向民众宣传日本出兵朝鲜取胜;其次,以耳冢作为战胜的纪念物;第三,遵循对战死者供养的传统;第四,含有“怨亲平等”的佛教思想;第五,超度冤魂以防作祟。*[韩]鲁成焕:《耳塚の「霊魂」をどう考えるか》,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第26-42页。由此建立的耳冢,在彰显丰臣秀吉强大武力的同时,也使其屠杀朝鲜半岛军民的行为变得可视化,耳冢也成为壬辰战争历史记忆表象的一部分。以耳冢的建立为开端,其历史记忆也在不同时期被形塑和利用,并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三、耳冢历史记忆的再建构
耳冢建立翌年(1598),丰臣秀吉病死。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德川家康铲除了丰臣氏遗族,一统日本。德川为了巩固幕府的统治和提高自身的权威,恢复了与朝鲜的通交往来。1607年,朝鲜使节初次来日,1609年日韩两国签署通商条约(乙酉条约)。*五味文彦、鸟海靖编:《もう一度読む山川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朝鲜通信使从1607至1811约二百年的时间里共来日12次,每次的使节团约400-500人。*日韓共通歴史教材制作チーム:《朝鮮通信使: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から友好へ》,明石書店,2005年,第61页。德川为了与朝鲜往来,否定了丰臣秀吉对朝鲜侵略的行径,废除了祭奠丰臣秀吉的丰国神社和与其相关的祭祀活动。然而,德川幕府并未废除耳冢,而是把耳冢作为与朝鲜交往的政治工具。朝鲜通信使来日时,德川政权以京都的方广寺作为接待场所,特意让朝鲜通信使看到耳冢,以此来震慑朝鲜。在《朝鲜太平记》中有如下记述:
秀吉公建此耳冢,传威武于后世。至今为止,每次朝鲜人来日至此冢,都会对日本的武力心存畏惧。*《朝鲜太平记》(第二十九卷),电子版。
在《绘本太阁记》中,也记有朝鲜通信使来日并在耳冢前祭祀的情景:
朝鲜通信使来日之时,见耳冢,痛哭流泪,此冢葬之耳、鼻者,皆我国忠臣,报效国家者,故来冢下,烧香、敬献祭文、吊唁,让世人皆知。*法桥玉山:《绘本太阁记》(七篇卷·十五),乐成社刊行,1884年。
在德川幕府时期,耳冢对于朝鲜来说是被日军侵略践踏、生灵涂炭的悲惨记忆,德川政权虽明确地否定了前代的行为,但在巩固自身政权上却有效地利用了耳冢这一历史记忆。德川政权对于耳冢记忆的政治利用,也使耳冢记忆作为战争被害的表象进入朝鲜社会。通过朝鲜通信使对耳冢的记录与描述,耳冢的历史记忆得以在朝鲜社会传播和再生产。*例如,姜弘重的《东槎录》、申维翰的《海游录》中都有关于耳冢的记述。
至19世纪中期,历时二百多年的德川幕府被明治政府取代。作为近代政权,明治政府从根本上否定了德川幕府时期的锁国理念,提出保卫国家独立与欧美强国并肩兴建强国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的设定如我们今天所见那样,主要体现在近代以后日本对朝鲜、中国及东南亚等国家的侵略行径。丰臣秀吉时代侵略朝鲜的历史恰恰为明治政府在对民众宣传对外侵略的思想与对自己行为正当化过程中提供了理论支持,由此对丰臣秀吉的历史进行再评价、再审视与再建构成为这一时期首要的问题。
明治元(1868)年3月,明治天皇在“行幸”(指天皇出行)大阪时,下诏给大阪神祇局和裁判所为丰臣秀吉修筑神社。再建丰国神社的“御沙汰书(根据天皇的命令或指示所形成的法令)”的内容如下:
显有功而罚有罪者,经国之大纲也。于国家有大勋劳者反无表无显,将何以劝励天下哉!丰臣太閤,起于侧微,攘一臂以定天下之难,继述上古列圣之伟业,宣皇威于海外,虽数百年后犹令彼胆寒,可谓于国家有大勋劳且超迈古今者也。抑武臣有功于国家者,皆酬劳其庙食。时朝廷既已追谥庙号,不幸天不祚其家,一朝倾覆。源家康继出,子孙相受,其宗祠之宏壮,前古无比。以丰太閤之大勋却委以晦没,其鬼殆馁,深可叹也!今般朝宪复故、万机一新之际,斯不可不兴举废典。加之值宇内各国相与雄长之时,以丰太閤之英智雄略,宜新兴祠宇,彰显其大伟勋烈,以期万世不朽。官员及士庶,蒙丰太閤之恩义者不少,宜共谋合力,始可报旧德矣。御沙汰候事。闰四月。*详见鳥井寿山人:《生ける豊太閤》,世界创造社,1939年,第44-45页;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从御沙汰书中可以看出,明治天皇对有功于朝廷、实施海外出兵的丰臣秀吉进行彰显,同时也含有明治政府对德川幕府的否定与贬低。应明治天皇的敕诏,同年6月,丰国神社被列为“别格官弊社(与朝廷渊源深远的神社)”。1875年,日本决定在京都方广寺大佛殿遗址重建丰国神社,1880年社殿建成。京都的丰国神社作为本社,同年在大阪建立了分社。1907年石川县把卯辰山王社改称丰国神社,爱知县在1885年也建成了丰国神社。滋贺县的蛭子神社在江户时期为供奉丰臣秀吉的神社,明治维新后改为丰神社。在此背景下,日本全国各地开始了丰国神社的建造。1890年,以举行“丰太阁三百年祭”和“修缮丰国庙御坟茔”为目的的“丰国会”成立,丰国会的成员大多由丰臣秀吉遗臣的后代组成。*高木博志:《近代日本と豊臣秀吉》,郑杜熙、李暻珣:《壬辰战争:十六世紀日·朝·中の国際戦争》,明石書店,2008年,第194-198页。
1898年,丰国会在丰臣秀吉三百年祭上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仪式。仪式由丰国会会长贵族院副议长、侯爵黑田长成主持,京都市政府全面后援,可以说是举国一大盛事。祭奠活动从4月1日至5月31日持续了61天,这一期间日本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地彰显秀吉的功绩,秀吉画像成为畅销品,秀吉的故事成为能剧、狂言、歌舞伎等题材流传于街头巷尾,享受丰臣舞乐趣的民众随处可见。*[朝]琴秉洞:《耳塚》,综合社,1994年,第113页。作为秀吉三百年祭的一个环节,秀吉的坟墓、耳冢及相关的建筑都得以修缮。现今耳冢前的石碑亦立于此时,内容如下:
耳冢修营供养碑
与邻敌交兵,欲宣国威而已亦,非恶其人而戮之也。春秋邲之役,楚人请筑京观,楚王不可,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於是有京观,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论者以为盛德,然未若我丰太阁之仁及枯骨,其德为更深也。按史,征韩后役,我军连捷,诸将有所斩获,截敌鼻献功,其数几万,公喜其胜,赏其功,而愍彼土为国致命,埋其获於京都大佛之前,为筑坟茔,立大卒都婆,名曰“鼻冢”。请五山僧侣四百人,大修供养,资其冥福,时庆长二年九月二八日也。相国寺承兑撰其文,美公之不分恩雠,不论彼我,深垂慈心,以设平等供养,夫恩及海外可谓广矣。况於交战之敌国乎。公比心谓之行。推公比心谓之行今日“赤十字社”之旨於三百年前,豈其不可哉!世徒谓公豪雄英武,夸大自喜,因以此冢比京观而谁知其慈仁博爱而有礼如此之深哉?冢后訛称曰“耳冢”,物换星移,丰氏绝祠而冢独儼存,巍然为平安之伟观四方,观光之客吊古之土无徘徊顾望于其下,钦当年之伟业,感丰公之慈仁者。此地旧属妙法院,故以时修佛事,而世变多故,久委荒残矣。今兹丰公功臣爱将之裔与同志者,胥谋将修公墓,以行三百年祭,而未及此冢,心竊恨焉。方广寺现董权大僧正泰良以此冢与大佛关系尤深,欲修营建碑,期丰公祭大修追吊供养之式,予亦以庙门,当掌丰国庙,尤喜其事,有所翰(应为“斡”,笔者注)旋,既得官准京都市给金若干元以助之,其就部内亦附以其前地,於是广慕资用,以起其役,乃筑乃修,材良工励,以题字,可谓荣矣。夫此冢者,邦威振张之符,表丰公盛德之遗物。而朝鲜者,与我辅车相依,唇齿相保,迩年我国率先万国,扶其危,匡其倾,明其独立,为之大战,以完邻邦之交谊,则於其旧事亦无感乎。丰公既行之于交战之日,今日则为友邦,豈可不益尽其道哉!呜呼,十万众生一视同仁,三界万灵,平等利益,希以此修营保其物,以此供养资其福。奋武之迹,慈仁之举,大显於世,且两国邻交益加厚,东洋和平永莫渝。乃记其事,勒贞珉,以垂不朽。
明治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陆军将大勲位功二级彰仁亲王篆额
前天台座主大僧正妙法院门迹村田寂顺撰文*[朝]琴秉洞:《耳塚》,综合社,1994年,第271-272页。
上述碑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丰臣秀吉建立耳冢的缘由,与楚王对比颂扬丰臣秀吉为敌建冢具有的慈悲心;第二部分记录了石碑建立的过程;第三部分体现的是耳冢面向未来,强调修复的意义,是展现国威和颂扬丰臣秀吉的象征;同时也是加深两国睦邻关系、不忘东亚和平的纪念物。如上所述,进入明治时期,在国家的主导下以重建丰国神社、举行纪念仪式等活动对丰臣秀吉的历史记忆进行了再建构,耳冢作为丰臣秀吉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重新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明治政府对于丰臣秀吉历史记忆再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彰显丰臣秀吉的“功绩”来否定德川幕府,并确立天皇制政权在近代国家中的正统性。同时,彰显秀吉“宣皇威于海外”这一点正好与明治以后日本向海外发展的思想相契合,即通过对秀吉侵略朝鲜的正面评价,为自己的对外侵略提供合理性解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
四、耳冢历史记忆的越境与交涉
战后,在日本进行民主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耳冢作为美化战争、涂炭朝鲜军民的象征,成为被忘却的记忆。与明治时期耳冢作为众所周知的观光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是在京都市编撰的《京都的历史》(近世篇)中,还是在京都的观光地图或《京都府的历史散步》等最基本的观光手册里都没有关于耳冢的介绍。*[韩]鲁成焕:《耳塚の「霊魂」をどう考えるか》,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第1页。如前所示,现今设置于耳冢前的历史由来说明板,是1979年由京都市设立,在此之前仅有“耳冢”二字,对于街区比较熟悉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不知道耳冢的存在。*[朝]琴秉洞:《耳塚》,综合社,1994年,第235页。
20世纪80年代以后,耳冢的历史事实被纳入到历史教科书中,成为更多的人了解耳冢历史的契机。另一方面,在地域社会中,围绕耳冢的祭奠活动逐渐组织化和定期化,耳冢发挥了历史记忆传承场所的作用。在京都耳冢前祭祀的群体,主要是以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形成的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和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等组织为主。此外,还有从韩国专门来进行祭奠的社团组织和个体旅游者。近年来,也开始有京都市政人员参与其中。这些祭奠活动使耳冢的历史记忆不仅局限于日本社会内部,也作为一种超越国境的历史记忆(transnational memory)存在,为当下日韩在认识耳冢问题上的冲突与龃龉提供了摸索交涉与和解的途径。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耳冢的祭奠活动在日韩间展开,超越国家地域间的祭奠活动加大了耳冢历史记忆在两国社会间的渗透与传播,同时也使其更趋向于多元化。1990年4月22日,日韩在京都的耳冢前和京都国际会馆举行了“日韩共同慰灵法要”。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把耳冢上的填土装到陶罐中带回釜山的东明佛院,目的是让耳冢的死者魂回归故里,在故国祭奠这些亡灵。在京都,日韩双方各有三十僧侣为死者进行了诵经、超度。*这里的日韩双方中的日方是指在日的韩国民团组织人员。耳冢的坟土被带回釜山的东明佛院后,有约两万人聚集于此,举行了“耳冢灵驾还国慰灵大祭”的盛大祭奠活动。*[朝]琴秉洞:《耳塚》,综合社,1994年,第232-233页。这样的祭奠活动,成为唤起四百年前在壬辰战争中发生的朝鲜军民悲惨记忆的契机,同时也强化了韩国社会对这一历史记忆的再认识。
另一方面,在京都耳冢前,每年都有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组织的祭奠活动。2007年11月7日的《联合新闻》报道了6日在京都耳冢前,日本大韩民国民团(简称“民团”)京都本部、在日本朝鲜人联合总会(简称“朝鲜总联”)京都本部和京都市国际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耳冢联合慰灵祭”。这次活动是作为纪念朝鲜通信使四百周年的一个内容而举行的,在追悼法事上,京都朝鲜歌剧团表演了Sarupuri传统民俗舞蹈,民团与朝鲜总联的青年团体代表逐一朗读了期盼和平友好的祭辞。对于这样的活动,民团京都本部的金有作与朝鲜总联京都本部的金学福做了如下阐述:“铭记把悲惨的历史转变为和平与希望的朝鲜通信使的意义,希望联合慰灵祭能成为与日本国民广泛交流的契机。”*《联合新闻》,http://www.wowkorea.jp/news/korea/2007/1107/10035324.html(2017年4月8日阅览)。
近年,韩国的团体组织来日进行祭奠也成为一种常态。韩国《中央日报》在2009年8月20日报道了韩国团体“发扬民族精神的国民运动总部”来日祭奠的情况。新闻主要介绍了如下方面的内容:对耳冢由来的说明;祭奠活动人员由主办方“发扬民族精神的国民运动总部”,协办方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大阪本部、京都本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组成;此外,日本京都文化财保护科科长作为日本官方代表首次参加并献花,其他日本参加者共计140余人;仪式活动的内容有韩国传统音乐“板索里”表演、南原国立民俗国乐院表演的“升天舞”“镇魂舞”等等。*《中央日报》,http://japanese.joins.com/article/458/119458.html?sectcode=&servcode=A00§code=A10(2014年3月3日阅览)。对于这样的祭奠活动,“发扬民族精神的国民运动总部”的理事长韩阳元做了如下阐述:
从朝鲜时代的壬辰倭乱至近代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时期为止,韩日关系是连续的战争与对立。这种关系也是在想通过战争与武力取得天下西势东渐时代的延长线上。但是,现今已进入东势西渐的时代。慰灵祭是为了消除历史中悲痛英灵的仇恨,面对新的未来。*《中央日报》,http://japanese.joins.com/article/458/119458.html?sectcode=&servcode=A00§code=A10(2014年3月3日阅览)。
“发扬民族精神的国民运动总部”的活动不仅限于来日祭奠耳冢,还设想把耳冢迁回韩国。为此,在2009年5月,该团体还到访了东京的文化厅,就耳冢向韩国迁移问题进行了咨询。韩阳元理事长与日本文化厅进行了交涉,提出了以韩国珍岛的日军墓地*在壬辰战争时期的鸣梁海战中,死伤的日军被冲到海岸,当时朝鲜的民众把这些日军的尸首埋于珍岛,现今在珍岛还有100多日军死者的坟墓,最近也有日军的后裔到访珍岛,进行祭奠。与京都的耳冢进行交换的提案。对此,日本文化厅给予的答复是:值得研究的提案,但耳冢现今被认定为国家文化财,如果不在国会上修改文化财相关的法规,耳冢难以迁移。*《中央日报》,http://japanese.joins.com/article/458/119458.html?sectcode=&servcode=A00§code=A10(2014年3月3日阅览)。
如上所述,在战后的日本社会,耳冢作为丰臣秀吉时代侵略朝鲜的象征、明治时期美化战争的素材而被否定,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被日本社会压抑和忘却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在日韩国人、朝鲜人和韩国团体为主的耳冢祭奠活动的实施,强化了耳冢历史记忆在日韩社会间的传承,同时也促使了耳冢历史记忆的越境和共有化。在未来这一历史记忆的归属问题上,双方正处于交涉过程中。
五、结 语
本文主要以壬辰战争中丰臣秀吉建立的耳冢为考察对象,探讨了耳冢的历史记忆在不同时代如何被建构、形塑和利用,具有哪些特征等问题。耳冢从丰臣秀吉时代建立至今约四百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德川幕府、明治-昭和、战后三个不同时代,每个时期耳冢的记忆表象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在此,耳冢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特征可以援用美国地理历史学者K.E.Foot的方法来诠释。通过分析美国在暴力或悲剧事件发生地修建的纪念碑的变化模式,Foot归纳有四个变化特征,即圣化(sanctification)、选择(designation)、复旧(rectification)、抹消(obliteration)。*[美]K.E.Foot :《記念碑の語るアメリカ》,和田光弘、森脇由美子、久田由佳子、小澤卓也、内田綾子、森丈夫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德川政权建立后,在对前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行为进行全盘否定的同时,又有选择地保留了耳冢,一方面与朝鲜保持往来关系,一方面通过前代丰臣秀吉的“武威”来震慑朝鲜,把耳冢作为与朝鲜交往的政治工具。明治时期,在明治天皇的倡导下,举国上下重建丰国神社和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丰臣秀吉的历史记忆得以复旧和圣化,即耳冢历史记忆的再建构,耳冢也被重新恢复并赋予了同样的意义。战后,耳冢虽没有被“抹消”,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被忘却的对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以在日韩国人和朝鲜人为主的耳冢祭奠活动的定期化,耳冢成为日韩所共有的历史记忆。在耳冢未来的归属问题上,日韩双方的交涉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