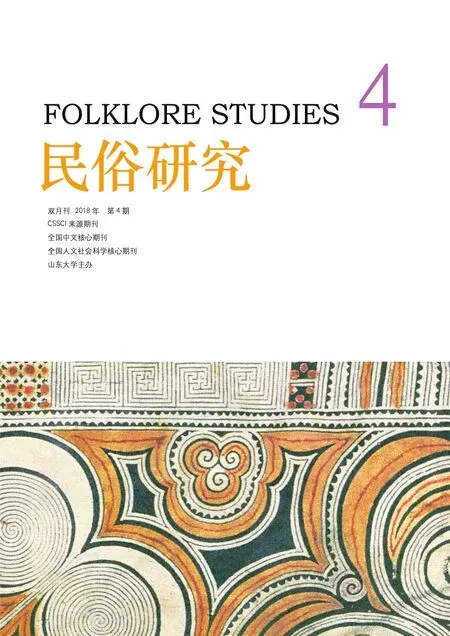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教育功能研究
2018-01-23王丹
王 丹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是指中国民间社会以语言、文字作为游戏的主要交流方式和媒介,或指民间游戏中主要以语言和文字或者语言文字为对象进行的嬉戏活动。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是中国民众代代传承的文化传统,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丰富多样,它不仅积累着民众的知识智慧,而且有效调节着民众的日常生活。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展现了中国异彩纷呈的语言文字知识,突出了民众运用语言文字的智慧,是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包含着丰富的教育内容,关涉到各民族各地区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于民众生命健康、人格健全、生活幸福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思维到语言表达
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作用的,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在训练人类思维和语言表达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儿童在学习说话的时期,成人可以利用语言游戏发展儿童的认知能力。比如“命名游戏”,可以让儿童来辨识物体,如成人与儿童一起辨别身体的各部位名称,一边说头、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部位,一边用手指迅速指向这些部位,这样在玩这个游戏的同时,儿童就识别了人体的不同部位,而手指的快速移动也能训练儿童的反应能力和思维能力。
语言是概括性较强的文化符号,它在相当多的时候代表了某一类事物的基本特性和文化涵义。因此,语言类游戏不仅是游戏本身,而且是在以语言为核心的游戏活动中学习语言,学习说话的方式,学习多种音节组合成的言语的表达方式,从而传达出思想和情感。语言类游戏提供了语言表达的环境,提供了游戏者语言交流的场合。游戏中的协作交流使得游戏者必须相互沟通,传递信息,练习以语言来传达心意,表露感情,也丰富着生活的词汇及语法的运用。语言文字类游戏中的游戏歌谣趣味性强,有节奏感,朗朗上口。比如“炒、炒、炒黄豆,噼呖吧啦翻跟头”的游戏歌谣既贴合动作的展示,又押韵生动。又如两个儿童在“拍大麦”游戏中,一边念唱“一箩麦,两箩麦,三箩开始拍大麦”,一边拍手。简单易唱的游戏歌谣不但增添了游戏的情趣和可操作性,而且游戏者能从中获得知识,进行情感交流。
语言是教育的工具,语言的习得过程从儿童掌握母语开始,并且语言的学习贯穿于生活的始终,贯穿于生活的每一个过程和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游戏歌谣歌词通俗、易懂,贴近儿童生活,为他们所喜爱。儿童在快乐的游戏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便能学会清楚、精炼、具体、形象的语言表达和口头讲述,极好地锻炼了运用语言的能力。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在提高儿童语言文字的连贯性上亦具有特殊的功能。儿童在语言文字表达时常常不能完整地表述一句话,总是用几个简单的字词或者只言片语来说明自己的想法,描述发现的事物。比如《从前有个老头》:“从前有个老头,他有一头小牛,童谣唱了半首,圈里牵出小牛,把牛拴在墙头,童谣已经到头。”儿童边拍手边听或者边拍手边唱,在节奏的配合下,便能顺利地演绎完这首歌谣,这个过程就是游戏活动。游戏中,儿童了解了牛的生活习性,练就了说话的能力。
玩耍是儿童的天性,他们在玩游戏中成长和进步。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有很多数数类、问答类、绕口令类、连锁类等游戏,均具有语言教育的作用。“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是一首绕口令,游戏者在念诵中须分清“板凳”“扁担”及其中容易混淆的字词的读音,并且要以最快的速度脱口而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训练了游戏者的吐词发音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语言类游戏中的语言是地方性语言,是民族母语,因此,语言类游戏必须以汉语方言或者民族语言来进行,否则就无法达到游戏的目的。比如湖北麻城的游戏歌谣《磨麦》唱道:“磨麦,请客,做粑,接嘎,嘎不来,一口吃它。”两位游戏者对面而坐,手拉着手,边吟唱,边拉着手前后摇动。歌谣是用麻城方言来演唱的,其中“接嘎”的意思就是“接外婆”。在麻城方言中,“嘎”、“嘎婆”即是外婆。这首游戏歌谣整体上押“a”韵,念唱起来简易、有趣,且意思浅白,游戏者在亲密无间中既知其意,又分享快乐,游戏易于开展,也能达到玩耍的目的。由此可见,语言类游戏实质上是在进行地方知识、民族知识的教育,有利于保护地方方言和民族母语。语言类游戏不仅传承了特色鲜明的地方语言、民族母语和地方、民族的音乐曲调,而且在提高游戏者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素质,培养游戏者的语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语言类游戏能为练习已学过的语言提供新的、有意思的语境,并在游戏过程中学到新的语言知识。
二、从心智到道德培养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是与人们发生关系最早的游戏类型。孩子从出生开始,家人就会给他唱游戏歌谣,等他能说话、会动作的时候,家人便以促进儿童成长的语言文字游戏与他戏耍,让他感受欢乐,也接受教育,大量的游戏歌谣包含着丰富的妙趣且道德化的内容。比如,“摇摇摇,摇元宵,我的元宵是宝宝。穿红衣,戴红帽,不说话,总爱笑。吃饭不让妈妈喂,走路不让爸爸抱。看见小鸟点点头,看见客人问声好。”这首歌谣是在“摇元宵”游戏中演唱的,游戏由两名儿童合作完成。歌谣与游戏融为一体,配合节奏性强的动作来演唱更加富有趣味。“吃饭不让妈妈喂,走路不让爸爸抱”传递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生活道理;“看见小鸟点点头,看见客人问声好”则教育儿童从小懂礼貌、彼此友善的道德情怀。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启迪游戏者的心智,得益于对知识的传授、认知和理解,如数数类《六字歌》。儿童在玩耍过程中念诵这首歌谣,其中的每一个数字都具体形象化为牛的身体部位:“一个头,两个角,三花脸,四只脚……”于是,他们既学会了数数,又认识了牛的身体部位特征。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以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传承民众对于生活的理解,传承祖先的智慧心声,将知识传承与知识教育结合起来,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在游戏中进步。比如“敲7”游戏是多人游戏,玩法是任意一人开始数数,1、2、3、4……数下去,每逢7的倍数(7、14、21……)和含有7的数字(17、27……)必须以敲桌子代替。如果有谁逢7却数了出来,就算输,有谁没逢7就敲桌子,也算输。这个游戏可以推广到“敲4”“敲5”等数字游戏。游戏者参与游戏活动,学习新知识,思考新规律,在热烈的气氛中反复练习,既增强了学习的灵活性,也提高了学习效果。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极大地激发了游戏者,尤其是儿童活动、思维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探索未知的兴趣,激励了他们的创造力,诚如霍姆林斯基所说:“游戏是点燃儿童求知欲和创造精神的火种”*[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的艺术》,肖勇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94页。。
“谐膜”是巴塘藏族的语言游戏,通常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举行。只要游戏者身上有一件心爱的物品,游戏就可以进行。游戏者围圈坐在一起,每个人把自己携带的心爱物品交给游戏的组织者。游戏的组织者拿着收集的物品在另一处坐下,在收集的物品中随便拿出一件,悄悄藏好。围圈的某个人说谐膜歌词,谐膜歌词每个人都可以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围圈的所有人一起唱所说的歌词,一般唱歌的调子固定统一。唱完后,圈中的长者就会讲解歌词的意义和寓意。这时,组织者把藏好的物品拿出来示众,表示是这位游戏者的谐膜歌词。这位游戏者想到什么歌词就唱什么,但不能与前面游戏者所唱歌词重复,歌词饱含了许多道德教化的内容:
长在石上的神树,已过千年万年,我的慈祥父母,希望如此长寿。
甘甜醇香的美酒,请朋友开怀畅饮。这是吉祥的美酒,也是团结的佳酿。*参见益西拉姆、向秋志玛:《藏族民间游戏巴塘谐膜的社会功能研究》,《青藏高原论坛》2014年第4期,第82-84页。
“谐膜”游戏中,有关孝敬父母、感恩长辈,亲朋友善团结、互助合作,以及爱护自然、关爱动物等歌词内容的吟唱无不是在传递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游戏者在玩耍过程中不断习得并熟悉“谐膜”游戏的传统方式,在亲切而流畅的游戏活动中自然而然地接受道德教育,相互鼓励,踏实前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德行。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是快乐的、自由的,并且以生活为依托,记录生活、反映生活。人们道德观念的接受、养成是从儿童时代的游戏开始的。诸多儿童游戏动手、动口、动脑,互相协调,游戏及其歌谣中闪烁着朴素的道德灵光,包含了明白易懂的道德思想、简单易行的行为品德,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在语言和身体活动中,启迪了心智,培养了道德,规范了言行。
三、从语言到文字传统接受
语言文字是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主要载体。中华民族多种语言文字游戏承载着多元、多层次的文化记忆,并且通过身体实践实现着以游戏为中心的语言文字传统记忆,进行着地方知识教育,进而丰富了我国语言文字传统。
民间游戏展示的语言文字智慧,在游戏的名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翻花”游戏流行十分广泛,深受游戏者的喜爱。“翻花”中不同的步骤翻出不同的图案花样,这些图案花样被命名为“牛槽”“五星”“螃蟹”“麻花”“手绢”“扫帚”“芥疙瘩”“织布机”等等。这些名称源于民众的生活,源于民众与自然的生活关系,可以说,“翻花”每一个阶段的图案花样命名都是民众基于生活的语言文字智慧。“自然界能够为语言的发展提供无以计数的差别与机会,特别是在孩子身上。自然界的多样性能够为成长中的孩子源源不断地提供具体实物,以便使他们在语言技能发展方面得到基本的理序、分类和命名训练。”*[美]S.R.凯勒特:《生命的价值——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王华等译,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0页。与自然的和谐交流锻炼了游戏者的语言能力,丰富了中国语言资源库,这成为地方语言、民族母语传统的重要表达形式。也因为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体现出来运用语言、文字的智慧,进一步充实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更启迪了游戏者的智力和情感。
语言文字类游戏传统的留存包含了语言文字的外在形式和语言文字意涵的文化人格。这类游戏含括着许多语言文字因素,诸如语音、语义和语言的结构,文字的多种读音带来的游戏效果,文字的使用技巧等,人们在传承和实践语言文字类游戏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对这些语言、文字关键性、细节性因素的不断学习和实践,从而使这些看似随意、散漫的玩耍活动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实现着人们对语言传统的记忆、文字传统的传递。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实现了关于语言文字形式的记忆。在诗钟、词语连缀、集句、联句等文字游戏中都保留了传统的诗词格律的创作形式。比如,诗钟是中国古代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限一炷香功夫吟成一联或多联,香尽鸣钟,以对仗工整为上,内容含蓄而极富文化韵味。像诗钟一类的文字游戏在唐诗宋词的鼎盛时期非常盛行,然而,这类游戏后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过其结构的汉语语言文字形式的精髓至今在民间流传。另外,谜语、酒令中也含有诸多精妙的语言文字形式。谜语的谜面通常由一些工整对仗的语句组成,还包括歇后语谜、诗词曲谜等特殊形式的谜语。酒令中的口令,又叫口头文字游戏酒令,专门以口头吟诗、唱曲、作对、猜谜等行令。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实现了关于语言文字意涵的文化人格的记忆。人类语言不是语法、语义和词汇的简单组合,不是抽象的概念丛,不是具体的声音和手势,而是涉及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社会、物理和心理等方面的行为和行为方式。语言为文化的记忆提供了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是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的储存器。汉族的象形文字,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发展成为一种表意文字。过去,受纸张稀缺和农耕民族含蓄内敛性格等的影响,汉语不但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形式传统,也具有了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性息息相关的含蓄婉转、言简意深、回环优美的语言特性。在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汉语的这种特性也通过游戏的传承实现了记忆的传承。比如谜语就是巧妙地运用比喻、隐喻、借代等手法对事物或文字特征进行形象描述的语言艺术;回文则是使词序回环往复的修辞现象,既可以顺读,也可以倒读,回环婉转,意蕴深厚。游戏者在传承这些语言文字类游戏时,就是对游戏语言文字中蕴藏的这份文化人格记忆的不断建构和重温的过程。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在民族、地方语言文字传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们通过游戏的方式将这些极具生活化、大众化的文化传统接受,并且传承下来,不仅继承和丰富了地方方言、民族母语,丰富了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普及方式,而且游戏者在实践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时既接受了语言文字本身的知识,也接受了语言文字涵盖的地方、民族民众的生活,这些构成了地方、民族认同的关键性传统。更为突出的是,游戏者借助语言文字游戏活动,学习并获得了以语言文字为载体传达出来的民众生活中的美好道德、美好品格,进而成为游戏者以及游戏者为代表的地方和民族性格、精神养成的重要教育资源。
四、作用于文学艺术的熏陶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以语言、文字为主要内容进行游戏活动,语言、文字的审美性、形象性和节奏感在游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且语言、文字具有的美育功能在游戏玩乐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游戏者,尤其是儿童游戏玩耍者,游戏语言适合他们的年龄及接受能力。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的游戏歌谣吟唱起来押韵,郎朗上口,儿童在玩耍时并非死记硬背,而是愉快地感受并获得。因为语言文字游戏的音乐性、节奏感,使之能与同伴紧密配合,在情感化的表达中得到认识,收获快乐。如《手指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这类语言文字类游戏配合舒展的身体动作,由语言、文字构成的意义和美感便沁入游戏者的心里,为其所接受和感知,亦培养了游戏者的语言文字美感。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能够启发儿童的思维,丰富儿童的语言,锻炼儿童的表达,引导儿童的想象。这类游戏涵括了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诸如比兴、比喻、夸张、拟人、排比、反复、顶真等运用广泛,这些手法并非高悬、游离于生活之外,而是紧密贴近游戏者,尤其是儿童游戏者的生活土壤,让他们在玩耍语言文字类游戏的时候,可理解、可接受、可欣赏。“巴塘谐膜歌词修饰非常丰富,通常运用当地社会生活的自然现象、生产生活、生活规律等事物来进行比喻,语义浓缩明快,地方口语特色浓,能激发人的思维和更多的想象力。谐膜歌词的修饰喻意对整个游戏起重要的作用,歌词的修饰主要表现在比喻上,游戏通过这些歌词的喻意来解释,反映社会生活、亲情、道德、爱情、伦理等方面的文化。”*益西拉姆,向秋志玛:《藏族民间游戏巴塘谐膜的社会功能研究》,《青藏高原论坛》2014年第4期,第84页。多种手法的灵活运用充分展现了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想象力。因此,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能够影响游戏者掌握语言、文字的使用方法,能够使游戏者受到春风化雨般的文学艺术的熏陶。
中国语言文字丰富多彩,民间游戏不仅在乡村社会广为流传,而且它蕴含的智慧是无界的,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也可以跨越族群和阶层。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有力地体现了中国语言文字的智慧,经过不同族群和阶层的运用和施展,也呈现出民间游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民众生活的多样性。比如,斗草游戏原本就是以“斗百草”为主要内容,游戏双方从野地里采来花草,进行比赛。游戏方法是游戏双方各挑选一根茎部有韧性的草,然后茎与茎环套在一起对拉,拉断的一方为输,这是以力量、技巧来进行的斗草游戏。还有一种是以说出花草名字为比赛内容,谁先说不上为输,比赛时不能重复,别人说过的就不能再说,这就要求游戏者有更丰富的花草知识,并且以语言的形式展现出来。《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有描述:“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满园玩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里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剪儿一花儿叫做兰,一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惠?’”*(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03页。《红楼梦》中的斗草游戏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清代女子玩耍这类游戏的情形。这种以花草知识、以语言智慧为内容的“斗草”深受女孩们的喜爱,斗草游戏中的语言智巧、优美,充分展现出文学的美感。从游戏来看,如果没有花草品种的多样性,游戏是无法进行的;如果游戏者没有花草知识的丰富性,以及通过语言说出花草,游戏者是很难取胜的。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使用的地方语言、民族母语及其文字建构的形象美、节奏美和意境美,成为游戏者接受美育思想、文学教育的重要途径。
五、走向文化认同的教育
民间游戏是民族或地域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是民众实践经验与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间游戏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内化为民众情感,承载着民众的历史记忆,成为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的文化传统。比如,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中的文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而且也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字作为汉语的交流手段、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在汉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汉族文化认同的标志性文化,汉字类游戏作为汉字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汉族文化认同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语言诞生与操持语言的民族形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民族因为生存、生活的原因不断分化,迁徙到不同地域,他们的生活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出现差异,于是,在母语基础上产生了多种方言,不同地区的方言以及在方言基础上诞生的语言类游戏成为当地人交流的手段和认同的文化。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文字的认同和语言的认同存在一定差异,文字可以超越语言障碍,尤其是跨越方言障碍,构成更为广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比如,同样说汉语,闽南人和西北人无法实现交流,他们以汉字进行交流就会十分流畅。讲述不同地区方言的游戏者,在一起进行语言游戏活动的时候就难以开展,但是,运用文字进行游戏却不会有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类民间游戏的认同范围比语言类游戏认同范围更为广大,认同的力量更加强大。这就形成了语言文字类游戏中以语言为中心的游戏活动范围小,情感却更为浓烈,游戏者在地方传统的作用下,交流更为顺畅,玩耍的时候更为快乐,并且成为地方知识教育、传承的主要内容,由此形成地方认同教育的途径和资源。文字类游戏的基本范围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在语言文字类游戏中,语言和文字常常是相依相伴,产生游戏快乐的效果,因此,文字类游戏的传承范围基本是语言游戏的范围,但是文字类游戏是识字者的游戏,由此造成了文字类游戏流传范围更为广泛,不仅在以语言为基础的范围内,而且跨越语言、地域和民族,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承。于是,文字类游戏更讲究技巧,包含更多、更深邃的含义,也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所以,文字类游戏表现出来的文化认同就不仅是地方性的、民族性的,而是建立在文字为核心基础上的认同。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认同教育是地方性的,也是民族性的,同时,还跨域了地方性和民族性,是以文字为核心构成的传统。无论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游戏,还是以文字为中心的游戏,在文化认同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文字符号上的认同。之于语言来讲,是语音,游戏者说同一种话,这些话是亲切的,是情感的,是具有传统的穿透力和现实的可接受性,由此,语音就成为认同的符号了;之于文字来讲,文字的结构、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字的读音等均成为文字符号认同的表现。
二是语言文字符号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以语言文字为主的民间游戏,对于游戏者来说是轻松的、快乐的,但游戏中的语言文字是有意义的、有内容的。这些内容包括地方、民族民众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生活、生产的经验,是地方、民族民众智慧的结晶,由此形成了民族特殊的文化情感和地方独有的知识表达。可以说,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认同力量源于游戏者血缘、地缘、族源基础上的生活关系和文化关系,反过来,游戏者在进行这些游戏的时候,接受了语言文字上的认同,强化了语言文字游戏中的血缘、地缘和族源关系,并且不断地延伸、扩大认同力量带来的人际交往关系。
文化认同教育包含了认同的根本就是地方知识教育。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储存着丰富的地方性传统文化,因此,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在地方知识传承上具有重要价值,成为培养地方情感,增强地方认同的有效方式。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含括了历史信息、文化传统、科技知识的教育功能。文化认同教育贯穿在民众生活传统中,贯穿在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历史传承中。清乾隆时期里人何求的《闽都别记》中记录了唐代福建观察使常衮的一首《月光光》,它以闽南土音传授:“月光光,渡池塘。骑竹马,过洪塘。洪塘水深不得渡,小妹撑船来前路。问郎长,问郎短,问郎一去何时返。”这首游戏歌谣在当今闽南各地广为传唱,其主题结构基本相同,只是歌词内容有所变动。《闽都别记》的创作基础是福州说书艺人所讲的大量民间故事,书中记录的民风民俗是真实可靠的,这些民俗大致是以清朝乾嘉年间为下限,上可追至明朝中后期。这些儿童歌谣、故事类的游戏演唱、讲述采用闽南语,游戏者是闽南人,由闽南语为根本组成的语言类游戏成为游戏者的认同文化,他们在玩游戏过程中,接受了闽南语的认同教育,强化了彼此文化上的关系。
游戏者在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的讲唱中,在语言的表述与文字的表达中不知不觉地掌握了知识和经验,因此,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不仅成为地方认同知识,生产着地方认同知识,而且有效地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和经验,同时进行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教育。
六、结 语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与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相伴而生。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人类文明诞生、发展以及文明教育、传承与游戏相关。荷兰文化史学者胡伊青加认为:“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活跃着某种游戏因素,这种游戏因素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很多重要形式。游戏竞赛的精神,作为一种社交冲动,比文化本身还要古老,并且像一种真正的酵母,贯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荷兰]胡伊青加:《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游戏及其内含的诸多因素不但衍生了多样化的文化表现形式,而且孕育了文化、文明生长的土壤。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来源于生活,也是民众生活最原始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这种教育依托于群体生活来实现。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最早的游戏者是母亲和孩子,在襁褓中,母亲就会与呀呀学语的孩子游戏,主要以语言的形式实现。文字类游戏则是在游戏者掌握文字之时或之后,以文字的形式表达生活的智慧和人类知识。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成为民族传统和生活文化的历史积淀与现实表达。
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富于娱乐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从语言文字的游戏生活中习得和掌握民族或地域中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与行为规则。这种认识世界和社会的方法,包括有关人生的价值观念均潜藏于游戏活动中,并且渐趋内化为以游戏者为代表的文化区域内的民众的自觉性思想与行为方式,进而形成民族或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民族或地域民众稳定的文化心理、家园观念。
随着中国现代化、城镇化不断向纵深发展,语言文字类民间游戏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现代教育体系极大地压缩了传统民间游戏的可能性,尤其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游戏者被迫“放弃了对与其他生物进行有意义的联系的深深渴望。也许,在我们选择孤立或是破坏这些从情感、智力和精神上给我们的生活以潜在意义的生命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将自己托付给了一种更深刻、更危险性的孤独”*[美]S.R.凯勒特:《生命的价值——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王华等译,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