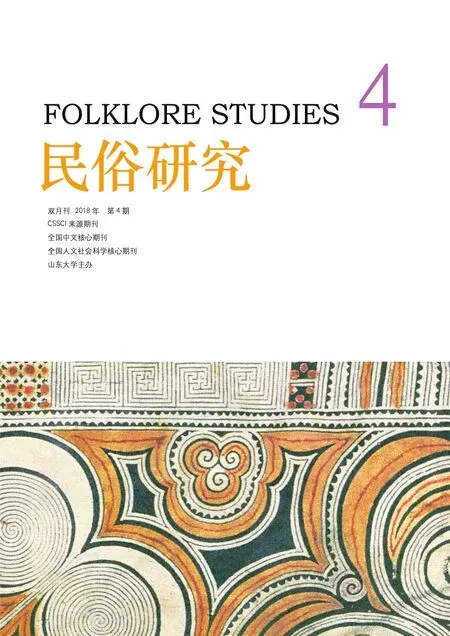他者镜像中的中国近代民间礼俗
——法国传教士禄是遒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与研究
2018-01-23彭瑞红
彭瑞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内忧外患震荡后,传统帝制国家发生了剧变。与此同时,原有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社会思想发生剧烈变迁。在此过程中,针对中国乡村老百姓的信仰及仪式实践问题,基本形成了两套话语体系,即“迷信”和“民间信仰”。作为话语体系,无论是“迷信”还是“民间信仰”,其背后都包含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精英改变社会的思想,都属于整个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两种不同表述的话语体系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分歧,实际上是“东方”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等二元话语结构的对立。而话语体系背后的具体实践,又是基督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的综合呈现。在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西方来华传教士通过他们敏感的笔触记录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信仰生活,并从“他者”的视角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与演绎,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不容忽视的历史角色。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历史较为久远,依据确凿文字记载,早在唐代便有来华传教人员。*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明末清初,西方对华传教的人员日益增多,至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的规模和影响渐至巅峰。正如不少既有研究所呈现的那样,来华传教士在传教之余,还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广建教堂、兴办各类教会学校、开设教会医院等,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很大影响。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障下,从通商口岸渗入到内陆的乡野田间,广泛接触普通民众,开展更为深入的传教活动,并由此亲身感受到当时农村地区的贫困落后及其信仰观念的独特性。不少传教士在传教同时,以其所观察到的当地民众生活状态为主题,对当时的中国进行各类书写,并将这些文字传到西方,成为西方社会了解和认知当时中国底层社会的主要参照,同时也成为早期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鉴于此,近代传教士对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及信仰观念的书写与记录,在整个近代时期中西方文明交流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书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对中国社会某些方面进行整体的考察与记述,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艺术、教育、风俗、宗教等各个方面。*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及其论著有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况》、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的《开放的中国》、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中国:现状与未来》、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的《中国与中国人》以及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二是从某一特定领域对中国社会进行横断式考察与记录。譬如,各国传教士在《中国丛报》《万国公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批判或抨击中国社会陋俗与封建迷信的文章;而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当属法国传教士禄是遒(Henri Doré)的十六卷本法文版《中国民间崇拜》(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在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中,禄是遒是为数不多的系统梳理和总结过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父,复旦大学李天纲曾评价说:“禄是遒对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信仰活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收集和描述。”*李天纲:《禄是遒和传教士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0页。长期以来,《中国民间崇拜》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民间风俗与信仰时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然而,在中国学界,对禄是遒及其论著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得到与之重要性相匹配的学术地位,相关成果屈指可数,《中国民间崇拜》的学术价值被长期低估。本文以禄是遒的《中国民间崇拜》丛书中《婚丧习俗》《岁时习俗》两卷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著作中婚丧、岁时内容的书写范式与评判标准,管中窥豹,以期解读传教士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想象与建构的过程。
一、禄是遒及其《中国民间崇拜》
禄是遒神父,1859年出生在法国,1884年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在上海、安徽、江苏一代的农村地区传教长达30多年之久。禄是遒是一位颇有学术追求的传教士,传教之余,他深入乡野田间,细致观察和记录当地民众的信仰实践,收集了大量的年画、神符、神像、经书以及访谈实录等“第一手”资料。
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作为神父的禄是遒记录中国民间信仰的动机也是因传教之需。正如甘沛澍(Martin Kennelly)在英文版序中所言,“作者出版这一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在乡间的同事们,即那些新近从西方到达,还不了解中国人宗教状况的传教士们。这些人总有一天会去和这个国家的迷信打交道。因此,他们必须对人们如何思想、信仰和崇拜有一定的了解。有此准备后,他们就会少冒犯一些当地人的成见,更好地推进将基督教真理植入这块土地的伟大工作。”*[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实际上,禄是遒的《中国民间崇拜》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尤其是法国社会引起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原定目标,爱尔兰籍传教士甘沛澍和芬戴礼(Daniel. J. Finn)将之翻译成英文版十卷本通行于世,法兰西学院也授予了他“一个特别奖”*[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
《中国民间崇拜》汉语本译自英文版,同样分为两大部分,共计十卷。其中第一部分总称“民间习俗”,第二部分总称“中国众神”。而其中第一部分中的《婚丧习俗》与《岁时习俗》较为集中地表现了其对中国传统“礼俗互动”的社会特质,以及对家庭伦理本位对民间观念影响的体认。通过梳理其相关内容的撰写,不难发现在看起来松散无序甚至内容有所重复的文本下,隐藏着某种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及学术界对中国形象的集体想象与个体投射。
二、禄是遒对中国“婚丧习俗”的书写
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部分总称“民间习俗”,主要介绍了当时中国乡村盛行的婚丧习俗、岁时习俗和符咒、占卜等信仰活动。其中第一卷为《婚丧习俗》。在这一卷中,禄是遒根据自己的田野观察和查阅文献资料,记述了诞生礼、婚礼和丧礼等习俗及仪式活动,并着重叙述并分析了丧礼上的各种符箓以及为死者服务的种种做法。
在诞生礼中,禄是遒分别从“出生前”“出生后”“孩童时期的迷信习惯”“过关”等四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当时能搜罗到的乡村育儿习俗。比如在“为祈求子嗣而特别受到崇拜的神”中,禄是遒描述了几位常见的送子神祇,其中包括送子观音、泰山娘娘(“天仙”)、天后圣母、保生圣母等。禄是遒还注意到,当时中国人为求子时所祭拜的对象不仅是女性神祇,还有男性神祇,他列举了安徽省繁昌县一带的宴公、官员和文人家庭祭拜的关公、吕洞宾、张果老以及麒麟送子等。在“其他一些迷信做法”中,禄是遒介绍了催生娘娘与安徽和州一带的产婆葛姑娘娘及其相应的祭拜仪式。他还提及产妇难产时所使用的福禄,以及测八字、算命、拴娃娃、将新生儿寄托给某位神祇及相关禁忌习俗。新生儿出生后的习俗及仪式包括“洗三”“七星灯”“桃木箭”“偷生鬼”“桃符”“狗毛符”“钱龙”“杀鸡”“畜名或丫头”“铃铛”“点朱砂”等。在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有“戴锁”“戴圈”“戴耳坠子”“戴钱”“戴八卦”“留箍”“穿和尚衣”“穿百家衣”“烧破鞋、挂渔网”“治小孩病符”“认干亲”“辫子上挂红布”“核桃锁”“床的制材”等。
在“红事”介绍中,禄是遒指出他一些材料参考了戴遂良《汉语入门》,当然在写作过程中着重叙述了他在安徽、江苏等地田野观察所得。因此,这一部分也较有资料价值。“红事”主要包括“订婚”“婚礼”等。在中国传统社会,婚礼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礼仪系统,禄是遒在介绍中,仅就其感兴趣或者感觉不可思议的部分进行了介绍。其中很大篇幅用来介绍婚礼前及婚礼仪式过程中的各种“婚帖”,同时对“新娘启程”和“新娘进新郎家”两个婚礼程序中的禁忌及习俗进行了描述。其中,禄是遒着重叙述了“闹新房”习俗,并认为“异教恐怖如此,甚至连最基本的廉耻观念都已经被摈弃了”*[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事实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婚姻是神赐的礼物,人们不能轻易亵渎婚姻。而在禄是遒看来,“闹洞房”中不少习俗,如老人当着新婚夫妇面说风流话是亵渎婚姻的表现,因此他认为这种行为已经摒弃了基本廉耻观念。不过禄氏对此问题并未展开进一步论述。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将中国民间信仰视为“异教”是大多数传教士的基本观念,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之外的一切信仰均为“异教”,与“异教”相应的信仰观念和仪式也被统称为“迷信”。因此,《中国民间崇拜》丛书无论是法语版还是英语版都使用了“迷信”(superstition)一词。可以说,将民间信仰视为“迷信”甚至“异教”是“基督教中心主义”观念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生活书写时的投射。
在《婚丧习俗》一卷中,禄是遒格外观照了“白事”。在这部分开始,他首先简单介绍了人们在亲友濒死前的努力,即“抬菩萨”仪式。接下来,他介绍了死者的穿戴问题,而后从“死后”“入棺”“下葬”“葬后”“葬礼上焚化的迷信纸”“死者之符”等五个方面,描述了当时中国乡村社会丧葬习俗的基本仪式及禁忌。其中,“葬礼上焚化的迷信纸”“死者之符”两部分,在文字描述同时还附有相关符箓式样,为关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学者提供了参考。“葬礼上焚化的迷信纸”部分,禄是遒主要描述了需要在葬礼上焚化的“纸马”,他指出“在这些纸上画着各种神灵或阴间小鬼,它们可以在阴间给死者灵魂提供服务。由此也可以让神鬼善待那位以其名义烧纸马的死者”*[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0页。。由于纸马种类繁多,他只从中选举出一些式样进行了介绍,主要包括“扫神菩萨”“冥王十府”“龙车菩萨”“孤魂菩萨”等。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禄是遒选取的这些基本都与佛教有关,而后面的相关描述中,也进一步表明,他对盛行于乡村的佛教非常不满。在“迷信纸”部分他还专门提到“买路钱”,并试图从《礼记》和《事物原会》中寻找该习俗起源。在“死者之符”中,禄是遒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见的死亡形式”;另一类是“用于特殊情形的符”。在这部分写作中,禄是遒敏锐地意识到,焚烧各种符是中国老百姓经常使用的一种策略,“焚化是现实世界与幽冥世界之间主要的信息传递手段。”*[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页。他列举了包括老君、阿弥陀佛、地藏王符、托生符、给亡灵的通关文书、路引、开坛、开天、告冥王之主书、亡灵临时座位、灵座子、给死者的纸衣、纸箱、救血湖符等十几种当时通行于安徽省各地的符箓。其中对“救血湖符”进行了详细介绍,他参照卢公明《华人的社会生活》中的相关记载,对焚化该符的巫术进行了分析,并将之视为“闹剧”。“特殊情形的符”部分,他主要援引《玉历抄传》之记载,对自杀符、解杀死伤符、解邪妖伤符等进行了简要介绍。
该卷最后一部分是“为死者服务的种种迷信”,在这部分禄是遒详细探讨了“木主”“叩拜亡人”“祭荐亡人”“纸钱”“撞梵钟”“纸房子”“纸幡子”“轮回”等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从其行文看,这一部分最具学术含量,禄是遒在对以上诸民俗事象描述的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其历史发展脉络,比如对“木主”的考据,即参考了《礼记》《通典》《白虎通》《中国词汇》《朱子语录》《中国文献记略》《读礼通考》《五礼通考》《礼记疏》等十几种经典文献,分别讨论了“尸”的观念及其基本观点和“木主”的象征意义及其形制等。在“叩拜亡灵”中,禄是遒再次以“基督中心主义”论调对丧葬习俗中叩拜仪式进行评论,他认为天主教禁止这种纪念方式是“被迫”的,原因是几个人“合乎常识的明智行为,对于驱散被数以千计,不,千百万人接受的愚蠢的幻想是根本无效的”*[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8页。。除此之外,禄是遒对“纸钱”也格外关注,他在梳理了以“纸钱”作为祭祀用品的大体历史脉络后,以类似“对话体”形式讨论了传教士对待“纸钱”的态度。
对于“轮回”观念,禄是遒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叙述策略,以题为“中国人反对西方极乐世界存在说的论点摘要”和“轮回说的扼要观点”形式描述了中国民众的两种不同主张,同时将自己反对“轮回说”的观点表达出来。源自于佛教信仰的“轮回”观念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甚至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正如禄是遒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民众对于轮回观念是暧昧不明的,甚至与其他思想观念相互抵牾。在禄是遒看来,这是荒唐可笑的,但对中国民众来说,这非但不可笑,反而突显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实践性和生活化特质。对老百姓来说,“轮回”是一种实践行为,信众不必讨论其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而是将之视为天然存在的、毋庸置疑的“常识”。正是这种常识性观念,指导着老百姓虔诚地举行各种仪式。显然,秉持基督教信念的禄是遒难以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这套有关信仰观念的地方性知识。
总之,在第一卷中禄是遒着重描述了其所观察到或从文献资料中搜集到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育儿习俗、婚俗及丧俗知识与仪式实践,其意义在于为后世学者进行研究保存了大量珍贵“符箓”式样,同时有些独特的问题视角也颇值得研究者关注,如他对“木主”的考据、对焚烧符箓的分析、对“纸钱”的讨论等,都为后世学者从“物的民俗”层面理解中国民间信仰提供了研究视角。不足之处:一方面在于在具体叙述中时有“基督教中心主义”倾向,同时为了达到“批判”目的,他在纷繁复杂的民俗知识和仪式系统中专门摘录相对较为鄙陋的部分加以详细介绍,这些都是以禄是遒为代表的近代传教士们经常选择的书写策略,而这些带有倾向性和片面性的描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知;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全面了解区域社会婚丧习俗,禄是遒在描述或记载中经常将个别民俗事象视为复杂的民俗事件本身,过分夸大婚丧习俗中的所谓“迷信”成分,同时又较多借鉴了其他传教士如卢公明或中国天主教徒如黄伯禄等人的著述,并对部分著述内容断章取义,或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改编,因而使得该卷的描述杂乱而缺乏章法,而这也是其他卷本常见的问题。
三、禄是遒对中国“岁时节日”的书写
《岁时节日》是《中国民间崇拜》丛书中第五卷。本卷主要描述“岁时节日习俗”,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崇拜仪式”,主要描述与魔法、巫术和妖术有关的各种民间习俗,其中包括“招魂”“抢童子”“香坛”“木人、纸人”“与建造房屋有关的迷信仪式”“许愿”“赌咒”“拜弟兄”“辟邪物件”“天信”“太阳经和太阴经”“玉皇大帝颁发的敕令”“佛珠”“烧平安香”“香及其用处”“打水椿”“做蛰子”“海州道奶奶”“中国的神佛圣诞及宗教节日历表”等内容。第二部分是中国节庆习俗,包括“新年过年”“大年初一”“农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农历腊月初八吃腊八粥”“赤豆粥的功用”等内容。第三部分是有关各种动植物崇拜的内容,包括了“龟”“狐狸精”“凤凰”“虎”“麒麟”“仙鹤”“龙”“公鸡”“猫子”以及“具有象征含义的动物”“神奇的树木和果实”“奇特的植物和花朵”等内容。
在这一卷的英文版序中,甘沛澍认为中国人制定的宗教性节日及纪念性节日是模仿基督教惯例,“基督教会每年都会公布整个一年内的宗教节日及圣徒瞻礼日,异教组织奇妙地模仿了基督教会的这种惯例,向广大信众提供了对虚假的神仙鬼怪、被神化的圣人和勇士以及民族英雄的崇拜,人们脑海中的错误由此变得根深蒂固。”*[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页。这种说法明显有失偏颇,而这种观点并非禄是遒的本意。事实也正如此,禄是遒在整本书的论述中,都非常强调道教和佛教对中国老百姓岁时节日习俗的影响,他指出“从摇篮到坟墓,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迷信习俗中”*[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4页。,并指出“本书作者认为绘制一份在中国受到崇拜的神鬼及被神化英雄人物的完整历表是明智之举”*[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4页。。在制定这一历表时,禄是遒广泛借鉴了《皇历》和《禅门日诵》。前者是道教及民间占卜时经常使用的历书,后者是规定佛教徒修行日课的经典书籍。不过甘沛澍认为“中国宗教之树大部分枝干是土生土长的,但在原有树干上也嫁接出了一支巨大的外国起源的宗教分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加入了释迦牟尼形而上的佛教理论,近代的道教从佛教中借鉴了许多东西。‘儒、释、道’三教中存在着一种互相嫁接与吻合的过程,从而出现了无数错误的三教混合物,以及数之不尽的众神”*[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甘沛澍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符合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宗教及民间信仰的主流观点和总体看法,他们注意到中国民间信仰杂糅了儒、释、道等多种宗教元素,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但他们并未将这种包容性置入中国社会传统观念中去理解和解读,而是站在西方基督中心主义立场上,将之斥为“错误”的“异端”行为而加以挞伐。东西方宗教信仰观念上的冲突是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在华传教时遇到的最大阻力和障碍。这使得传教士在通过各种公益性社会活动塑造基督教美好形象的同时,不得不对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及宗教活动进行理论上的贬斥。而这既是禄是遒调查写作《中国民间崇拜》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是其未达到“贬斥”效果而有侧重有选择的记载各种信仰事项的重要缘由。
实际上,比禄是遒稍早的丁韪良对孔子儒家学说及其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他在1890年第二次传教士联合会议上发表了《祖先崇拜—— 一个请予宽容的请求》中明确指出,孔子儒家学说是哲学而非宗教,儒学所倡导的祭祖是中国人宗教仪式中最重要最神圣的仪式,是中国宗教信仰的核心。*[美]丁韪良:《汉学精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沈宏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76页。并提议传教士应该采用变通的办法沿用传统的适应性传教策略推进在华传教事业。*[美]丁韪良:《汉学精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沈宏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83页。不过,显然这种与主流观点不同的论调,并未得到多数传教士认可,通过其后禄是遒的著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多数传教士的观念中,糅合了儒、释、道等多种宗教元素的民间信仰与基督教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非可以变通的策略问题。
具体而言,禄是遒在“崇拜仪式”部分中,着重描述和分析了“招魂”仪式。他首先梳理了“招魂”习俗的大体历史过程,其后介绍了几种常见的招魂方式。招魂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崇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为死者招魂和为生者招魂两种类型。禄是遒在书写该部分内容时,显然将二者混淆了,因此,看起来杂乱无章,内容之间逻辑不连贯。在上古社会,招魂是“丧礼”中必要之步骤,称之为“复”。《周礼》记载:“夏采掌大丧,以冕服,复于大祖,以乘车建绥,复于四郊。”关于为何要为死者招魂,在记述仪式行为规范的“三礼”中均未见解释,而郑玄在为相关仪式做注时指出“复者,庶其生也”,“气绝则哭,哭而复,复而不苏可以为死事。”其后孔颖达注:“凡复者,缘孝子之心,望得魂气复反。”有学者指出,郑、孔等人解释是错误的,认为古人招魂是因为“中国古人认为人死后神形仍应相依,认为无墓的灵魂漂泊不定要受苦,墓是灵魂的安居所,为了使灵魂不受苦,才举行‘复’礼。”*金式武:《招魂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无论哪种解释,“招魂”作为一种礼俗曾长期存在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并深刻反映了民众的礼俗实践,这是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
由于“招魂”仪式涉及到灵魂与身体关系的问题,禄是遒在卷一《婚丧习俗》中介绍之后,在卷五《岁时习俗》中又专门对其进行介绍。在禄是遒看来,“与其进行招魂仪式唤回人的灵魂,还不如赶走影响大脑的疾病,因为事实上,灵魂从未抛弃人的身体。”*[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页。从这里看出,实际上禄是遒对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也不甚明了,他不能否认灵魂的存在,却又难以辩驳“招魂”仪式的不合理性,只好借鉴哥罗特《中国的宗教制度》等书籍,从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支持和反对两派的观点找出些许语焉不详的依据。而这也是以禄是遒为代表的近代传教士在书写中国传统礼俗和民间信仰时经常出现的问题,即既不愿承认中国传统礼俗的合理性,又难以找到辩驳的工具,而只好将其归结为“这就是当今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页。。
禄是遒在介绍过“招魂”仪式及实践后,又分别描述了“抢童子”“设香坛”“木人”“与建造房屋有关的迷信习俗”“许愿”“赌咒”“拜兄弟”“辟邪物件”“天信”“太阳经和太阴经”“佛珠”“烧平安香”“海州道奶奶”“打水椿”“中国神佛圣诞及宗教节日历表”等内容。从内容排列来看,也是杂乱无章,可以看出禄是遒虽然在安徽、江苏等地进行过多年田野调查,实际上他对流行于这些地方的信仰及仪式实践体系仍处于碎片化认知阶段,即其未能将不同事象进行分类处理。这种书写传回欧洲,势必会对其汉学界将传统中国礼俗与民间信仰碎片化理解产生影响。不过,尽管如此,禄是遒在描述这些内容时,还是展现出一种相对客观的视角,把其所见所思结合前人研究进行了分析,这一点不可否认。
在岁时节日部分,禄是遒着重介绍了春节、元宵节、端午节、腊八节等传统节日,对其中一些涉及民间信仰的民俗事象进行了描述。其中不乏一些民间传说,及各种禁忌。最难能可贵的当属作者注意到春节中“乞丐群体”的生活状况。“新年里人们对于鬼神的畏惧心理正好被乞丐们所利用。乞丐们成群结队地到家世显赫的人家恭贺新年,同时索要一些糕点或钱作为新年礼物。”*[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禄是遒在这一部分中,还辑录了三段“莲花落”唱词,反映了当时春节时乞丐的行乞习惯。实际上,直到现在河北、山东一带不少农村地区,春节时仍将乞丐视为“送财人”,而给予较高待遇。
《岁时习俗》最后一部分是“被赋予神奇力量的动物、树木和植物”,在这一部分中,禄是遒分别介绍了麒麟、龙、凤凰、乌龟,还有老虎、狐狸、仙鹤、公鸡、松树等被民间视为祥瑞之物或邪祟之物的东西。他指出,“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吉祥的象征,其在传说中的出现也预示着贤明君王以及圣人的降生,关于其他的动物,特别是虎、狐、鹤、鸡,在中国普遍有许多带迷信色彩的错误观点。”*[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在关于“狐狸”崇拜的介绍中,禄是遒记录了数个相关传说,以及民间建立的狐仙庙,其中专门描述了一位“香头”(“仙姑”)得道过程,并在后面捎带介绍了黄鼠狼、神猴等信仰。不少文献资料表明,禄是遒在撰写《民间崇拜》丛书时,为增强其“学院派”气息,而对葛兰言著作多有借鉴,同时丛书在法国出版后也迅速引起法国汉学界注意。
禄是遒在《岁时习俗》最后指出,“在这一系列迷信介绍尾声之时,不需要读者掌握这些信仰、观点、习俗和实践行为,甚至可以说这些已经大量深入到统治者、文人和百姓的生活习惯之中,并影响着出生丧葬等一切行为。要根除这些就需要宗教和科学的力量相结合,当这项工程完成,社会将处处是真理,中国也会比过去更加繁荣昌盛。”*[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五卷《岁时习俗》,沈婕、单雪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如前所述,将民间信仰视为带有明显地贬义色彩地“迷信”,是历史的生成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概念至少包含着以下几种关系:(1)对于社会统治者而言,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皇权正统”与“淫祀”对立观念的延续,是上层精英文化对底层民众文化的统治与认定;(2)对于意在变革图强的社会知识精英来说,是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封建神权的对立,是现代科学与传统宗教的对立;(3)对于传教士来说,是东方多神崇拜与西方基督教一神崇拜的冲突,是“正统”与“异端”的对立。正如沈洁所指出的:“‘迷信’概念本身也应被视为经由历史建构的实践主体。不同的权力实体,不同群体中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同处一种社会语境之下,但对于个人、国家、理性、自然的观念却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决定了对同一话语资源的不同运用。”*沈洁:《“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史林》2006年第2期。禄是遒对中国婚丧习俗与岁时习俗中关于民间信仰的描述及态度,反映了当时不少传教士的看法,如何天爵就认为,“迷信在中国如同在天空中撒满一张张蜘蛛网”*[美]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107页。,卫三畏也指出,需要真正的宗教信仰来帮助中国人祛除因无知所形成的迷信和迷雾,以及因崇拜和恐惧所带来的精神虚无和迷茫感*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dom. New York: John Wiley, Fourth Edition,1859.pp.267-268.。正如杨庆堃所言,“那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首先发现了这种与西方基督教信仰迥异的情形,并因此将之作为传播福音的最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中国人信仰是迷信的观点在西方非常普遍,并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页。另外,将中国民间信仰视为带有贬义色彩的“迷信”的观念,并非以禄是遒为代表的近代来华传教士所独有。刊于1906年《东方杂志》的《中国宗教因革论》一文指出:
吾中国之下等社会则除迷信神鬼以外无事业,除徼福避祸以外无营求。而持齐捧经一术焉,而迎神社醮一术焉,而祀狐谗鬼又一术焉。一游内地,则五家之村、十室之邑,无地无淫祠,无岁无赛会。语之输资兴学则无以款对;而募化庙宇之疏一出,则布施山积矣。语之尽心爱国,则曰吾侪小人非所闻知,而迎神祀鬼之典一行,则奔走皆来矣。*佚名:《中国宗教因革论》,《东方杂志》1906年第10期。
由此可以看出,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剧烈转型时期,不同社会主体基于不同立场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剖析,并在某些基本点上达成共识,如民间信仰代表了东方的、农民的、落后的、野蛮的、下层的、农业文明的等诸多需要变革的社会事实,从而成就了“迷信”这一带有贬义且影响深远的概念。通过这些表述不难发现,被污名化的迷信话语,深受政治和权力关系影响,它成为事关国家是否能够图富强甚至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障碍。与现代国家政治建立某种联系,是迷信话语体系在其后走向社会实践时,作为被彻底否定和铲除的重要起点。自此,反对封建迷信、移风易俗,成为社会改良派的主要思想,也成为政府从文化与社会生活层面构建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在19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这种观念自上而下地传递到乡村地区,并借助政府行政力量,将极具否定意义的“迷信”观念植入民众意识中。
四、异邦的转述:西方化意象的书写与想象
中国传统社会是礼俗互动的社会,正如张士闪所说,“大致说来,无论是作为社会实在,还是话语形式,‘礼’‘俗’都代表了自古及今中国社会的某种普遍现象与社会思想的一般特征,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并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因而应该成为‘理解中国’的基本视角。”*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事实也正如此,近代来华传教士初入中国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正在于如何认识以及如何书写礼俗互动的中国社会。
近代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生活、民间信仰与传统礼俗的书写带有明显的“基督教中心主义”倾向,而这种影响深刻地影响了早期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想象,这种影响与“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相结合,形成早期汉学界将中国乡村社会和传统礼俗文化视为落后、鄙陋甚至粗俗文化的观念,又进一步影响到当时比较宗教学的相关研究,中国早期留学海外学习比较宗教学学者如江绍原在回国后进行的研究就对中国民间信仰及传统礼俗带有明显的偏见;同时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刻板信仰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早期天主教、基督教信徒,在他们看来中国民间信仰及传统礼俗都属于“异教”或“异端”,都需要铲除和消灭,这种观念对其后乡村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等社会实践中“移风易俗”提供了某种思想渊源。总之,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因其深入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大量田野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撰写的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和信仰观念的书籍,无论在中国早期社会知识精英群体中,还是在西方汉学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如前面提及的兼具传教士和汉学家身份的卫三畏撰写的《中国总论》,在美国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描述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孔陈焱:《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发端》,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54页。。因此,在讨论以关注民间信仰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近代起源时,有必要将传教士的相关书写纳入考核范畴。不过,较为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学界对以法国传教士禄是遒为代表的近代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及传统礼俗书写方面的关注还很不足。
如前所述,禄是遒撰写的《中国民间崇拜》丛书基本涵盖了其所认定的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方面,尤其对于仪式实践和符箓象征意义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对中国传统礼俗,如婚丧仪礼、岁时节日等进行描述时,他摘取其中与信仰观念和仪式实践相关的部分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其受到“基督教中心主义”影响,将之视为“异教”表现而进行批判的策略;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礼俗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的意义,同时还因为其未能真正理解传统礼俗系统,从而使得相关书写显得非常散乱无序,逻辑不清,甚至内容方面多有重复。禄是遒在关注中国传统礼俗时,并未将之置入整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而是对其中具体事象进行以偏概全式的分析,不免有失公允,甚至谬误百出。在具体分析时,“异教”“迷信”等词汇更是将中国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实践视为“异端”而大加挞伐,甚至许多礼俗实践也被视为落后的、愚昧的,是需要被批判且需要被铲除的。这种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分析,为我们研究早期传教士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构建过程提供了真实的资料。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崇拜》丛书除部分内容是禄是遒汇集的其在安徽、江苏两地多年调查资料外,很多内容摘抄了中国天主教信徒黄伯禄《训真辩妄》《集说诠真》等著述,这也为本书的相关价值大打折扣。
不过,“现代学者批评禄是遒的著作中有‘可怕的西方化意象。’”*李天纲:《禄是遒和传教士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0页。对禄是遒而言,作为传教士在观察中国社会时难免带有“基督教中心主义”倾向,但这种倾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价值判断,还需要在对其文本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与同时期中国传教士或学者对民间信仰的看法作对比,然后才能得出相对妥当的结论。否则,单凭想当然认定禄是遒因为将中国民间信仰称之为“迷信”就否定其研究的潜在学术价值,并非严谨的学术态度。事实是,当时不少中国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在反对中国传统礼俗和民间信仰方面,较之禄是遒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李幹忱在《破除迷信全书》中就曾说:“说一句实话,一部二十四史乃是以迷信为主脑编成的,如果将史中的迷信剔除,所剩的不过是枝枝节节。”*李幹忱:《破除迷信全书》,协和书局,1926年,第26页。
五、结 语
禄是遒的《中国民间崇拜》丛书结合文献研读和“田野调查”,用异域的眼光打量近代中国的民间信仰,在作品里勾勒出一幅其所理解的近代中国民间信仰图景,对该丛书的深入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想象与建构的过程。就《婚丧习俗》与《岁时习俗》两卷内容来看,《中国民间崇拜》丛书最大的学术价值是其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图片以及当时盛行于安徽、江苏农村地区的各种符箓,这些图片资料为学者研究当时相关民间信仰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另一方面,禄是遒在撰写相关内容时,意图通过吸收中国传统文献资料和西方汉学相关研究成果对部分习俗进行考源式分析,应该算是较早运用西方研究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的学术思考,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也为我们继续研究相关主题提供了思路。
学界至今对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丛书价值的低估,或许与其在书写中广泛借鉴,甚至抄录了中国天主教教徒黄伯禄《训真辩妄》《集说诠真》等著述有关,但无论如何,作为外来传教士,通过对安徽、江苏两省乡村地区民间生活与信仰观念的研究所完成的巨著仍然需要引起注意。这些研究既是近代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一种体认,又为后世学者研究当时民间信仰状况提供了资料基础。正如李天纲在《中文版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年人们习以为常的风俗、规矩、礼仪、祭拜、禁忌、符号都已荡然无存,只留在遥远的记忆中。现在要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追溯中国文化的来源,只能依靠这些纸上踪影了。”*李天纲:《禄是遒和传教士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法]禄是遒:《中国民间崇拜》第一卷《婚丧习俗》,高洪兴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0页。
总之,通过对《婚丧习俗》《岁时习俗》两书内容的梳理,有助于了解以禄是遒为代表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及传统礼俗的基本观念,同时以此为基础对于解读早期民俗研究尤其是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路径亦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