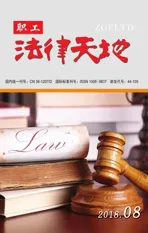侦查策略概念研究
2018-01-23向凯朋曹俊梅
向凯朋 曹俊梅
(201800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
一般认为,“侦查”是法定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为了查明案情,搜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性措施。[1]而“侦查策略”则一般认为是侦查主体为达到一定的侦查目标,在实施侦查行为的过程中对一定的侦查对象采取的灵活有效的方法。[2]
一、“概念”的语言哲学分析
所谓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3]内涵大致相当于一个词项的定义,外延是这一定义所界定的对象域。[4]在语言哲学中,“侦查策略”作为一个语词,不同学派的哲学家,往往有不同的观点。如密尔把绝大多数语词视为名称,名称对应于对象。名称是语词本身,而这个对应的对象根据情况,当名称为专名时,对象是现实中存在的与名称对应的事物;当名称为通名时,对象是我们所理解的与名称对应的意义以及现实事物。也就是说,通名既包括意义,也包括了指称。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既有内涵,又有外延。某一名称,或者某一概念,至少具备两个因素,一是这个概念作为语言时所代表的词语,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能为人们理解的意义,或者说它的指称。笼统地说,也就是具备内涵和外延,以及存在一个语言学上的词组。
二、“侦查策略”概念解析
如前所述,按照语言哲学理论,“侦查策略”无疑是一个概念,按照密尔的观点,“侦查策略”是一个通名。因此,“侦查策略”这一语词首先应当具有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作为人类语言的表达结果,“侦查策略”是言语。第二,是指“侦查策略”作为一个通名,应该具备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在使用“侦查策略”时,其所代表的东西,也就是内涵。第三,是指现实中实际存在的被我们称之为“侦查策略”的客观存在,包括了相应的行为等等,通俗的说法即外延。
(一)“侦查策略”的语义研究
对“侦查策略”的语义学层面的研究,百家争鸣:方案说、计策和谋略说、思想和原则说、策略措施体系说、灵活方法说、选择实施说等。语言是不断演进的,语义自然也会随之变化。但需要注意的,倘若从语义上解析“侦查策略”这一词语,则研究的对象应当是词语本身,而非以外延来替代名称。也就是从“侦察策略”这一词组字面的含义进行分析。语法上说,“侦查策略”是偏正词组,属于偏正结构,“侦查”是“修饰语”,而“策略”是“中心语”。因为在“侦查策略”这一词组属于定中词组,“侦查”作为“修饰语”充当了定语的成分。因此,对这一词组的考证,主要从“策略”二字出发。从字义上考证,“策”的最初含义是马鞭子,后引申为主意、计谋、方法;“略”则有计谋、方略的含义。在现代汉语中,“策”和“略”常互为解释,都含有方法、计谋的意思。[5]若从静态上讲,策略可以是认识主体思维活动最终的结果,即最终得出的方案或者方法。从动态上讲,策略是运用计谋的思维过程,这与选择实施说相契合。
(二)“侦查策略”的内涵研究
许多语言哲学家把“意义”问题作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仅仅对于“意义”,便有“意义指称论”、“意义观念论”、“意义途径论”、“意义的行为论”、“意义的可证实论”、“意义的成真条件论”等多种理论。研究“侦查策略”的内涵,首先应当厘清“内涵”的含义。
意义的指称论泛指研究语词和它所指称的东西的理论。主张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这个语词所指的对象。[6]密尔是这一理论的代表。密尔区分指称意义和蕴含意义。大多数名称指称事物但同时也蕴含事物的属性,而“意义”通常是被理解为蕴含意义的。[7]按照指称论,“侦查策略”的指称意义为其对应的现实中存在的方法或者行为。其蕴含意义,则是其具有的特有属性。
意义的观念论认为,一个语词的意义是它所代表的观念和意象。用洛克的话说,“语词无非是代表其使用者头脑里的观念……他用自己的一些观念来向自己表现别人的观念时,即使他愿意给这些观念以别人通常所使用的那些名字,他其实仍然在为自己的观念命名。”[8]按照这一观点,所谓“侦查策略”实际上是人们谈论到“侦查策略”这一词汇中,脑海中对这一词汇所存在的全部认识。按照这一理论,“侦查策略”的内涵也就无从讨论,因为每个人心中对“侦查策略”的理解必然不尽相同。
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无论语词还是语句,其功能都不在于指称外部的对象和事实,而是在于编织在生活场景中起作用。[9]也就是说,“侦查策略”的涵义在于我们一般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侦查策略”这个语词。“不要问意义,要问使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确定“侦查策略”的内涵时,应当考证现实中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侦查策略。而非想当然主观地为“侦查策略”确定内涵。笔者赞同意义的使用论。
除上述主要理论外,尚有意义的途径论、意义的可证实论以及意义的成真条件论。不再一一赘述。
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论,结合实践,我们对“侦查策略”的使用可以做如下总结:
第一,“侦查策略”并未局限于“侦查”过程中。按照现行法律对“侦查”的定义: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这就意味着“侦查策略”必然限定于侦查过程中。但现实是实务部门所提出的“侦防并举”、“将犯罪制止在预谋阶段”和“主动进攻,先发制敌”并没有以“侦查”为前提。这也就是说,倘若将侦查策略的内涵界定为“为了侦破案件”或者在“侦查过程中”,必然显得稍欠妥当。不难看出,在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矛盾。与此同理,“侦查策略”也必然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者某一类案件。因为“侦查策略”既可以针对某一案件,当然也可以针对某一类案件,甚至针对治安管控。如“阵地控制”。
第二,“侦查策略”主要作为名词使用,是认识活动的结果。首先,“侦查策略”必然不同于“侦查措施”,且不说“侦查措施”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即使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二者也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如同“军事策略”不可能与具体的“军事方案”划等号。“侦查策略”与“侦查措施”的区别,从“选择实施说”中可以窥见一斑。“侦查措施”是运用“侦查策略”的结果,可以看做是“侦查策略”的载体。但是“侦查策略”的实施却并不完全是“侦查措施”。同理,“侦查策略”自然也不能与“策略措施体系说”完全契合,因为“策略”和“措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其次,“侦查策略”并非一个过程。得出某种“侦查策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认识和思维活动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也并不等于“侦查策略”本身,这一点不难想象。然后,“侦查策略”也并非仅仅是一种思想和原则。思想和原则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指导性,事实上,正是侦查思想或原则指导侦查主体得出采取某种“侦查策略”的结论。“侦查思想和原则”可以视为侦查主体通往“侦查策略”的途径。最后,“侦查策略”并不完全是“方案”或者“方法”。尽管“策略”、“方案”和“方法”均是认识活动的产物,从这一点来看,“方案说”、“方法说”比“措施体系说”与“侦查策略”的本质更为接近,它们回答的均是“怎样”这一问题。然而,“方案”或者“方法”具有具体性、针对性、计划性,很强的可执行性。按照“方案说”的观点,认识活动必须拿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但宏观的侦查策略很可能只是一种指导性的思想。如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缉堵截采取立体的追击堵截。方案是“立体的追缉堵截”本身,但“侦查策略”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立体的追击堵截”。在这个问题上,“方法”与“方案”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方法”的范围比“方案”更为宽泛。最后,“计策和谋略说”把侦查策略定义为侦查的计策和谋略,在字面上,是最接近“侦查策略”本质的表达。但是“侦查策略”与“侦查计策和谋略”实际上只是一对近义词,就像说“侦查学”是“侦查学说”,并没有对“侦查策略”进行解释。综上所诉,对“侦查策略”本质的论述,笔者认为“选择实施说”最为接近。“侦查策略”必然涉及到认识主体的认识和思维活动,这一点与“选择实施”相同。只是得出“侦查策略”结论的过程也不一定是在选择实施,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并没有可选的余地。同时,“侦查策略”是认识思维活动的结果,这一点也符合“选择实施说”。但“选择实施”顾名思义,“选择”这一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存在一个对象可供实施。尽管“选择实施说”并没有把这个思维活动的对象局限为“方案”或者“方法”,但“侦查策略”发生作用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实施。有时某些“侦查策略”可能只是一种指导思想或者办事原则,并不具有可实施性。
因此,按照维特根斯坦意义使用论,“侦查策略”的本质实际上是侦查主体思维活动的产物,而这一产物的对象是可能存在的与犯罪有关的事物。
(三)“侦查策略”的外延研究
外延是内涵所界定的对象域。如两足无羽有理性是人的内涵,那么人的外延即是满足这一条件的所有的事物。小红和小明都满足无足无羽有理性的条件,因此属于人的外延之中。“侦查策略”的外延是所有的符合“侦查策略”内涵的活动。即体现着侦查主体以可能存在的与犯罪有关的事物为对象的思维认识活动的所有产物。所以不管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缉堵截还是决定怎样实施追缉堵截,均属于“侦查策略”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