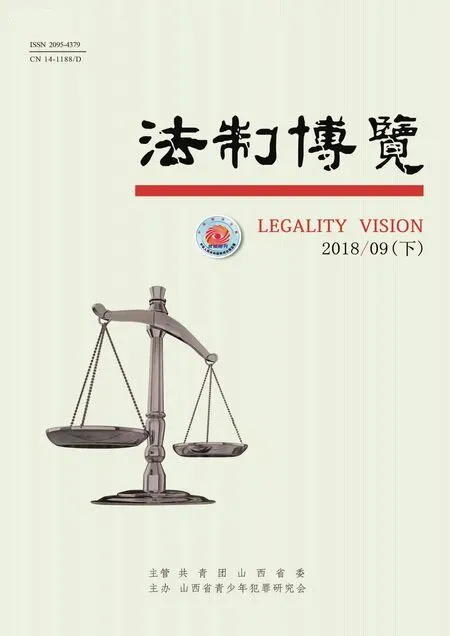两岸通讯监控制度比较
2018-01-22郭元斌
郭元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研究生部,河北 廊坊 065000
通讯监控(台湾法律中称为通讯监察),是现代刑事侦查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但由于其秘密性,且侦查时长较长,有可能会对公民的通讯自由与隐私权造成非常大的损害,如何在保护社会秩序与保护公民权利中平衡,一直是法律界讨论的话题。隔海相望的台湾地区在此方面立法已久,且已经完善多次。因此本文通过将两岸在通讯监控制度相对比,为我国大陆地区相关法律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两岸通讯监控制度现状
(一)我国通讯监控制度现状
在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颁布以前,只有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涉及到有关监听等通讯监控技术使用的相关规定。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设了“技术侦”一节,对公安机关使用的技术措施给予了较为细化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48条、149条、150条、152条分别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主体、适用罪名、实施限制、保密义务以及证据能力等。
(二)台湾通讯监察现状
台湾地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颁布于1999年7月14日,在此法颁布以前,台湾的执法机构已广泛的使用通讯监察,也在打击犯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台湾地区群众的人权意识逐步提高,群众普遍认识到公民的通讯自由与隐私权需要符合法律的保护,应该在法律授权之后才能实施该侦查措施。这是导致台湾《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出台的深层次原因。
二、通讯监控制度比较
(一)监控范围
根据台湾“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中指出,通讯监察的范围包括:无线电设备发送、储存、传输、接受的数据、文字、声音以及电子邮件、书信,日常的言论与谈话。在大陆地区,对于通讯自由保护的界定较为模糊,所包含的的范围和方式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66条所规定的“电信用户依法使用电信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形势犯罪需要,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的程序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的除外“这路所说的”使用电信的自由与通讯的秘密”显得过于笼统与宽泛。
(二)法律限制
根据台湾“通讯保障与监察法”规定:通讯监察必须目的合法、比例适当,案件的范围限于重罪的特定要件,案的内情有监察的必要。通讯监察能够作为通讯手段必须具备被监察对象有证据证明有重罪或者是特定犯罪的嫌疑,且有足够证据证明通讯的内容与案件有关。其中明确规定重罪是指“最轻刑罚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并明确了特定犯罪的范围。
大陆地区在法律限制上,新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自批准决定签发之日起三个月有效。对于不需要技术侦查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2]
在侦查材料的用途上。新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三款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只能用于侦查,起诉与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的用途。”[3]
事实上,公民的日常言论与通讯自由同样是需要保护的。因此“通讯保障及监察法”将日常言论纳入到保护的法律中较为合理。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将立法细化。
(三)通讯监控的协助对比
台湾地区的法律中明确规定了通讯监察协助的机构以及其相应的义务,法律中法规定电信及邮政实业有协助监察的义务,但以符合科技上及经济上的合理为限。该法还规定当需要协助时,执行机关应以相关法律文书通知电信、邮政或其他协助执行机关协助执行。
而在大陆地区,相关法律未规定通讯监控协助制度。通讯监控由技术机关执行,不需要电信及邮政的协助,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证据(邮件、电子邮件、书信等)有专门机关进行扣押。
在现实中,电信部门已经有能力进行监控,有专门的电信部门协助较为经济。因此大陆地区可以借鉴台湾地区法律,构建专门的协助制度。
三、完善建议
通过对比发现,要完善大陆地区的通讯监察制度,要在完善案件监控范围、法律限制、监控协助等方面的基础上,设立对监控人的告知、违法救济以及违法应当承受的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增加附属法律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