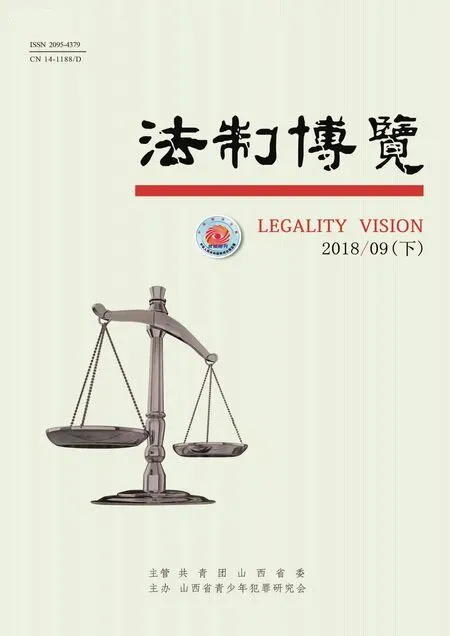矿业权财产属性还原的法律实现
2018-01-22孙哲
孙 哲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是制度转型,法律制度作为社会变迁的工具,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是达成社会现实的手段。[1]既然政府主导分配过程是导致页岩气矿业权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2]那么就应该通过法律转型,变政府分配为竞争取得,在矿业权分配环节构建竞争性市场,以实现矿业权公平分配的目标。
一、物权法将矿业权规定为用益物权
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在第三编“用益物权”中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受到法律保护,[3]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了探矿权、采矿权的用益物权属性。这一规定对我国矿业法律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明确了矿业权的财产权利性质
矿业权的财产权性质是矿业权竞争取得的前提条件,如果矿业权属于人身权或者行政权,则无法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进行分配。尽管能否将矿业权作为用益物权在学界存在争议,但是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却是毋庸置疑的。财产权的基本特征是权利可以转移,能够直接为权利人带来经济价值。[4]矿业权以勘探、开采矿产资源为基本内容,能够直接为矿业权人带来经济利益,且不以特定身份为前提,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流转,所以具有明显的财产权性质。作为调整财产归属关系的基本法律,《物权法》将矿业权规定为用益物权,既肯定了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又明确了矿业权的民事权利归属。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矿业权应该属于私权范畴。公权是指国家依法赋予的、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一种权力;私权是在公权的范围之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所享有的权利。矿业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但不同于传统的私权,矿业权是带有公权色彩的私权。将矿业权归类为私权,意在强调矿业权的取得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原则,只要当事人协商一致,意欲勘探、开采矿产资源的市场主体即可从资源所有权人处取得矿业权,无需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当然,基于矿产资源的稀缺性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矿业权在取得和行使过程中应该受到政府管制,以确保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现实中,这种政府管制通常表现为许可证管理,即政府部门向矿业权人颁发许可证,并对其生产过程实施必要监管。因此,矿业权这种“私权”带有一定的“公权色彩”,但是这并不影响矿业权的私权属性。
(二)为矿业法律制度转型指明方向
《物权法》是调整财产归属关系的基本法律,《物权法》颁布之后,《矿产资源法》的转型应该以《物权法》的规定为基本原则,逐步放松对矿业权的行政管理,还原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矿产资源法》与《物权法》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不能将《矿产资源法》视为《物权法》的特别法,不能适用“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5]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适用前提是两部法律属于同一立法机关制定的同一层级的法律。《物权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基本法律,《矿产资源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由于两部法律的层级不同,所以不能适用“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矿产资源法》必须遵守《物权法》的规定。
其次,单行法调整并不能替代一般法的调整。在《物权法》颁布以后,《物权法》已然成为调整财产归属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矿产资源所有权和矿业权的法律制度设计应该首先遵守《物权法》的规定。尽管《矿产资源法》作为单行立法已经对相关社会关系进行了法律调整,但是《物权法》的一般性调整应该优先于《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适用,只有在《物权法》未予调整的领域,才能适用《矿产资源法》的规定。
二、物权法规定平等保护所有财产权
(一)《物权法》确定平等保护原则
作为规范民事财产归属关系的基本法律,《物权法》为各种性质的财产权利提供平等法律保护。既然矿业权被纳入《物权法》的调整范围,那么无论何种性质的市场主体取得矿业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当他人的行为侵害矿业权人的权利时,矿业权人可以行使物上请求权,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
(二)企业矿业权应该受到平等保护
在《物权法》颁布之前,《矿产资源法》对国有矿山企业、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的法律地位进行了区别对待。现实中,政府部门据此不仅在矿业权审批过程中倾向于国有企业,维护国有企业对矿业权的垄断地位,而且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矿业权提供不同力度的保护,甚至肆意侵夺民营企业的矿业权,这在山西煤炭能源整合过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矿产资源法》根据所有制性质不同进行区别对待的规定,不仅违背了平等保护的民法基本原则,而且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成为为矿业权不公平分配的直接法律依据。
《物权法》中关于平等保护的规定,既弥补了《矿产资源法》的缺陷,又为《矿产资源法》的修订指明了方向。《物权法》的规定,一方面有助于激发民企活力,促其锐意创新,克服短期效益,进行长期规划,合理开发资源;另一方面,有助于国有企业回归理性,摆脱权力依赖,专注转型重组,再造治理结构,直面市场竞争,通过破坏性创新建构竞争优势。
三、登记取得适应物权法的规定
(一)矿业权准用不动产物权取得规定
尽管《物权法》将矿业权规定为用益物权,明确了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但是并未对矿业权的取得做出规定。如果将矿业权界定为用益物权或财产性权利,那么矿业权的创设和取得就应该准用物权取得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探矿权还是采矿权均与动产物权大相径庭,因此矿业权取得只能准用不动产物权的规定,以登记作为矿业权取得的标志。具体而言,当事人签订矿业权取得合同之后,受让人应该持合同到主管机关办理矿业权登记,[6]经记载于登记簿上时矿业权设立,之后主管部门应向矿业权人发放许可证。尽管我国《矿产资源法》也要求矿业权申请人在取得政府审批之后进行登记,但这里登记仅仅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并不具有创设矿业权的效力,登记之前的政府审批才是《矿产资源法》规定的矿业权创设行为,这就造成行政权力对财产权利的侵蚀。《物权法》颁布之后,矿业权的取得应该以《物权法》的规定为准,将登记作为矿业权的生效要件,解除行政权力对矿业权的束缚,还原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
(二)矿业权应适用物权法的区分原则
此外,矿业权取得应适用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区分原则。根据《物权法》第15条的规定,当事人签订变动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该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是否进行登记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如果将矿业权视为用益物权或财产性权利,那么上述区分原则当然应该适用于矿业权取得。具体而言,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的代表组织与申请人签订取得矿业权合同,该合同的效力不受矿业权登记的影响,即使未予登记,矿业权合同依然自成立时生效。登记之前,申请人的矿业权并未生效,任何一方违约,对方均可依据合同追究其违约责任;一经登记,申请人即取得矿业权,审批机关是否发放许可证并不影响矿业权的效力,但未取得许可证不能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四、登记对产权的羁束弱于审批
(一)登记的法律性质应为行政行为
从性质上来说,登记是一种行政行为,这可以从登记的主体、程序、效力等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登记的主体包括申请人和登记机关。申请人不能自愿选择是否登记,如果未按法律规定进行登记,则矿业权不生物权效力;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登记,无正当理由拒绝登记、登记错误、无故迟延等都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其次,登记的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审查、记载等几个环节,每个环节有严格的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无权进行变更。再次,矿业权登记的效力是矿业权的取得或设立,这反映了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处分行为的认可,当事人无权变更登记的效力。由此可见,登记行为无论是从主体、程序还是效力方面来分析,都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可能,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原则,应该认定为使一种行政行为。
(二)登记的法律效果在于事后确认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登记是行政许可的一种方式,同样,审批也是行政许可的一种方式,但是二者对产权的羁束力存在本质区别。尽管登记是一种行政许可,是矿业权的生效要件,但并不代表矿业权是由行政机关授予的,更不能说明行政行为是矿业权的来源和依据。矿业权登记是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确认,不具有变更当事人意思的效果,能否取得矿业权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相比之下,审批对矿业权的管束力远远强于登记。根据《矿产资源法》的规定,矿业权经过政府审批取得,政府有权决定是否授予矿业权。换句话说,能否取得矿业权并不取决于当事人意志,而是取决于政府意志,即使当事人满足了矿业权申请条件,政府也可以拒绝批准当事人的申请。这种审批制度使得政府在矿业权分配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造成矿业权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在《物权法》颁布之后,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得到立法确认。为了落实《物权法》的规定,应该尽快修改《矿产资源法》,变矿业权审批为矿业权登记,还原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为矿业权出让市场的构建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