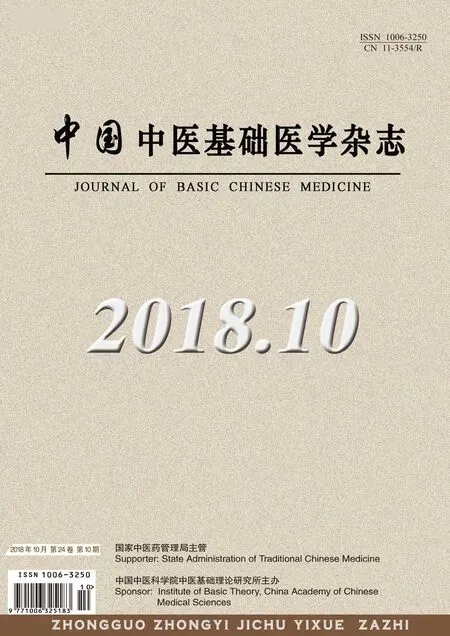中医“辨证”概念诠释
2018-01-22张宇鹏尹玉芳
张宇鹏,尹玉芳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2. 火箭军总医院清河门诊部,北京 100085)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区别于西医学最重要的学术特征之一。然而,“辨证”理论却是中医学中概念最为模糊、争议最多的理论,“辨证论治”所辨之“证”究竟所指为何?“辨证”与“辨病”又是什么关系?在历史长河中“辨证”理论是如何演进的?在临床实践中“辨证”理论又是如何具体运用的?这一系列问题始终都是众说纷纭,争议颇多。本文拟从“辨证”概念的辨析与理论学术源流角度,对中医辨证理论作一简要考察。
1 “辨证”概念的提出
“辨证”一词出现较晚,明代始见这一用法。该用法不固定,对于见证、辨证、凭证、因证等词汇的选择较为随意,基本上未形成固定用法的语言模式,其中“证”的含义大致包括证候、症状和疾病诸种[1]。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随着各地中医院校的建立与教材编写工作的推进,以秦伯未、任应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医学者开始对中医学术展开系统的整理工作,正式提出“辨证论治”的概念,而“证”的概念则主要是用以强调中医学把握疾病“性质”(本质)的学术特征,而辨别以八纲为基础的“病性”则成为当时“辨证”的核心内容[2]。此后,在国家统编中医院校教材中,“辨证论治”被正式确定为中医学重要的学术特征之一,如五版教材将“辨证”解释为“辨证,即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定为某种性质的‘证’[3]”。 此后随着中医学教材的多次修订,与中医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从而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中医辨证理论。
由上可知,在中医学中“辨证”概念的确立,实际上是相当晚近的事,而且最初提出“辨证”概念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说明中医有别于西医的学术特征而设立,而在具体定义概念时又不自觉地受到西医语境的影响(如“体征”等明显非中医词汇),因而“辨证”与“证候”的概念在中医学理论中始终充满了争议与困惑。多年来,对于中医“证候”与“辨证”的研究始终热度不减,国家已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取得的进展乏善可陈,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必须承认“辨证”概念本身的模糊不清,是影响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 “证”与“症”的概念辨析
在辨析“辨证”概念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明白“证”与“症”的区别。受教材对“辨证”解释的影响,我们今人对“证”与“症”二字的区别甚明,即“证”是指“证候”而言,“症”则是指“症状”。那么这两个字在历史上的用法又如何呢?“证”为古文“證”字的简体字,《辞源》释为:“病况。通‘症’。”而《辞源》中将“症”字解释为:“病征。古皆作‘證’”,说明“证”与“症”二字在古文中含义相近,常被不加区别的混用。然而仔细品味二者的用法,在细微之处还是有所区别的。
笔者找到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影印本《保幼新编》[3]一书为例,全书共3万余字,“证(證)”与“症”二字均多次出现,其中“证”字出现有20余次,“症”出现则多达30余次。归纳起来两字分别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用法:一是代指疾病名称,如暑伤诸症、热症、泻痢之症、雀目之证、龟背之证、脾疳之证等,这一类用法实际上均为疾病的病名,但不称“□□病”而成为“□□之症(证)”,此类用法“证”与“症”混用并无区别;二是作为代词,代指某一特定的疾病或患者的病情,如急症、危症、此症、诸证、危证、其证等,“证”与“症”同样混用难以区分;三是症状,如胎肿、口疳等症状,瘿瘤、马刀等症,其症面青白等,此用法专述某病所表现出的诸多症状,通常多用“症”字而不用“证”。但有趣的是,我们今人认为部分应当属于证候的名词书中却仍用“症”字,如半阴半阳症、表症头痛等,这也是古今不同之处;四是说明证候分型,如变生六证、惊有三证、搐有五证等,此类用法专为说明一病之中的证候分型,一般用“证”字而不用“症”。综合以上分析,“证”与“症”二者的区别已非常明显;“症”主要用于描述疾病的症状,而“证”则用于分析疾病的证候分型,而在疾病名称时则两者往往混用,不加区分。我们现代中医学对于“症”与“证”的区分也是据此而来。
“症(症状)”的概念较好理解,是指机体因发生疾病而表现出来的异常状态,包括患者自身的各种异常感受与医者观察到的各种异常机体外在表现。而“证(证候)”的概念则较为复杂。“证(證)”,《说文解字》曰:“告也。”《玉海》曰:“验也”,即为证明或验证的意思。据前文分析当用于分析疾病的证候分型时用“证”字,则“证”的含义即为此分型的结果。如《保幼新编》中曰:“惊有三证:急惊、慢惊、慢脾风也。”急惊、慢惊与慢脾风即为惊病所辨之三个“证”。 “候”则不同于“证”, “候”在《辞源》释为:“伺望”,即观察之意。如《保幼新编》曰:“惊有八候:一搐二搦,三掣四颤,五反六引,七窜八视。”这“八候”不同于惊病所表现出的症状,而是指医家诊断惊病所应注意的诊察要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证”是中医临床用以概括疾病过程中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病机(含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的诊断范畴,是对疾病不同证候类型划分的结果。“证候”则是证的外候,通常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是医家诊断患者所属何证所必须掌握的一系列诊察要点。
3 “辨证”概念的内涵
“辨证”即是认证识“证”的过程,就是将医者通过中医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切诊)收集患者的病史、症状等临床资料,结合脏象、经络、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中医理论,运用相应的辨证方法,对患者一定阶段的病情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明确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病机,以及患者当下的机体功能状态及邪正之间的关系等,是中医认识和处理疾病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医学心悟·入门辨证诀》曰:“凡看症之法,先辨内伤、外感,次辨表、里,得其大概,然后切脉、问症,与我心中符合,斯用药无有不当。”《类证治裁·自序》曰:“司命之难也在识证,识证之难也在辨证,识其为阴为阳,为虚为实,为六淫,为七情,而不同揣合也。辨其在经在络,在腑在脏,在营卫,在筋骨,而非关臆度也。”
“辨证”作为一个概念的正式提出,固然只有不过几十年的历史,然而在中医学中,用于分析疾病、指导治疗的辨证理论与方法却是古已有之,其渊源可以上溯至《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
在《内经》中虽然没有形成辨证论治体系,但其中有关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描述正常人体生理功能的理论,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等病因学说,邪正斗争、气机升降、阴阳失调的病机学说,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断方法,以及治疗与组方用药的基本原则等,已为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总结了病机19条,从脏腑病位、病因、病性等方面阐述了不同临床表现的病机归属,提示了治疗原则,并将之归纳为“审查病机”的原则,则是对辨证论治最早的表述形式。书中记载了许多中医证候的名称及其临床表现与治疗原则,可看作辨证论治最早的应用。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首先较为明确地提出了辨证论治的观念,明确了辨证论治的内涵。《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分别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和脏腑辨证论治体系,广泛运用表、里、寒、热、虚、实、阴、阳、脏腑、气血等概念,以此作为辨证的基本内容,并针对不同病机和证候采取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药,为后世辨证论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各篇均以“辨××病脉证并治”的格式为标题,就是张仲景对辨证论治思想观念的充分体现,也是后世“辨证”这一概念的源头。
此后历代医家又从不同的角度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辨证论治内容,如《中藏经》对脏腑病机的发展,《诸病源候论》对病候理论的创立,宋·陈言对病因学说的发展,金·刘河间对六气病机学说的发展,元·朱丹溪对气血痰郁理论的发挥,以及清代随着温病学说的形成发展,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提出三焦辨证等。还有的医家就辨证论治理论在内、外、妇、儿等临床学科中的运用作了专门的阐述,使辨证论治体系更臻完善。
4 辨病与辨证的关系
“病”即疾病,是指在六淫、七情、劳逸、外伤等致病因素的作用下,机体与环境的关系出现失调,机体内部平衡发生紊乱,正气受到损害,机体正常的生理机能与生命活动受到限制或破坏,并反映为一定症状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
中医学中 “病”的概念反映了某一类病理变化发生发展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和规律,一般都是有特定的病因病机及演变规律,有较明确的病理特点与固定的临床症状组,有诊断要点并可与相似疾病鉴别。中医的病通常是建立在症状学基础上的,是一种宏观上的病,中医学对疾病的划分与命名主要是依据对患者主要症状或症状组的综合概括,如麻疹、水痘、肺痈、痢疾、消渴等,另外一小部分疾病命名则是依据对特定病因与病机的归纳,如中风、伤寒等皆属疾病的概念。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古文语境中,“证”的含义相当于对疾病辨证分型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是对疾病阶段性本质的反映。简单的证仅指病情的某一方面,如就病位而言的表证或里证,就病性而言的寒证或热证,就邪正盛衰而言的虚证或实证。这些不同方面可以并存,因而有表实、里热等组合。而复杂的证则根据临床的实际需求加入了对病因与病机的分析,如心脾两虚证、痰蒙心窍证等,而某些时候也可以是对具有一定规律性病机症状的综合性概括,如痰证、血证等,但这一类证候与疾病的概念间界限较为模糊。
证与具有特定病因和特定演化模式的疾病不同,一种病可因具体条件不同而在不同人身上表现为不同的证;一种病对于同一个人也可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的证,而且这种证的转化顺序还常常表现出某种规律性。证是对疾病临床症状与病机的综合概括,包含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及邪正盛衰变化等多方面的内涵,故证能够揭示病变的机理和发展趋势,中医学将其作为确定治法、处方遣药的依据。
“证”与“病”虽然都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但“病”的重点是对疾病发生发展全过程病因病机及演变规律的认识。“证”的重点在于对患者现阶段健康状态的把握,“症”则是医者所诊察到的证与病的外在表现,有内在联系的症状组合在一起即构成证候,反映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各阶段或类型的证候贯穿并叠合起来,便是疾病的全过程。一种疾病由不同的证候组成,而同一证候又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过程中。
辨病与辨证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病是对疾病的诊断,其主要目的在于对患者所患疾病本质属性的确认,及对病情发展与转归的总体性判断;而辨证则是对患者当前证候的辨析,其主要目的在于对患者现阶段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功能状态与抗病能力的准确把握,并为最终实施治疗提供依据。
中医的诊断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结论,但由于对证候的判断是着眼于对患者当前病理状态及变化趋势的综合判断,因此在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实践中,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临床治疗方案的确定与实施主要是由辨证结果决定的。如感冒是一种疾病,临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但由于引发疾病的原因和机体反应性有所不同,又表现为风寒、风热、暑湿、气虚等不同的证。只有辨清了感冒属于何证,才能正确选择不同的治疗原则,分别采用辛温解表、辛凉解表、清暑祛湿解表、益气解表等相应的治疗方法给予适当的治疗。
中医对于疾病的诊断,通常是依据患者的主症来确定的,相对来讲比较明确,较少争议,但对于“证”的判断,则医家往往会根据其个人的学术背景与患者当下的实际健康情况,而选用不同的辨证方法,从而使得辨证的结果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而医家对具体辨证方法与辨证结果的选择,主要是为其选择治疗方法与处方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实践的基本原则,是中医临床诊疗疾病的思维与实践的过程,是中医学认识与处理疾病的基本方法,始终贯穿于中医学诊断、预防、治疗与养生实践的全过程中,指导着中医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而辨证和治疗则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而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而辨证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正是中医学术发展的主体。进入21世纪的当代中医,如何理解和对待辨证理论,是关系到中医学未来发展的前途与道路的大问题,当为我今之医者所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