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
2018-01-18刘畅
刘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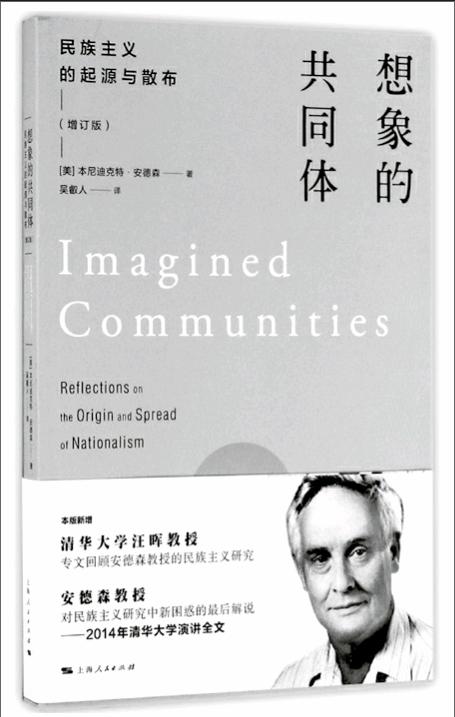
一
显然,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在他之前的有关民族或民族主义的研究是不满意的,其研究现状可一言以蔽之 —— 量多而质浅。对此种弱态,他是这样描述的:“民族(nation),民族归属(nationality),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几个名词涵义之难以界定,早已众所周知,遑论对之加以分析了。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与此事实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却屈指可数。” 例如休·赛顿-华生(Hugh Seton- Watson),这位关于民族主义的英文论著中最好、涵盖面最广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继承人,悲伤地说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
基于这种对研究现状不足的认识,安德森即将此作为自己研究突破的逻辑起点,即在对民族或民族主义的解释上有所创新。这种创新的欲望恰如他所言:
“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诠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都因为陷入一种‘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这个现象的努力,而变得苍白无力;我们亟需将理解这个问题的角度,调整到一种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
即强调哥白尼式的本质性的、突破式的创新。对此,安德森提出的创新点就是:民族不是一个物理、地理意义上的实体,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此,这种观点之所以新颖、新鲜,恰恰在于为 “民族”这一概念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喻体” ——“文化人造物”和“想象的共同体”,从思维逻辑上讲,这很像是一种比喻,其基本的思路是:到底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之谜”如何破解?这些,只停留在民族或民族主义本身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在目前诸多对于民族的解释之外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和突破口,于是“文化人造物”和“想象的共同体”就担当了这一重任。安德森说:“我的研究起点是,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于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我将会尝试论证,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于是导出了这样的认识: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 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显然,在安德森眼中,民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共同体而已,民族,是一種文化的人造物,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在此,将民族和民族主义比作 “文化人造物”和“想象的共同体”,不仅是构成全书的关键概念和核心命题,还是本书的创新思维所在。从修辞学的层面看,“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无疑是一种比喻,但这种比喻已经不是简单地进行局部的、片段的“语言修辞”了,而是构成了一种系统的、全面的、对解开“民族之谜”具有全局指导性的“思想修辞”;由此开创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虚拟”或“想象”的创新视角:
“它(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 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的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二
这种认识,显然和安德森的生长环境、个人经历及民族归属感密切相关。更准确地说,和他与“自然共同体”的联系有关,而这种认识,又和他异乡漂泊、居无定所、没有栖居于一个固定的“共同体”密切联系。而在此,若要理解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最好还要研读另外一本书—— 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的《现代世界的诞生》,其中论述到了与“想象共同体”联系密切的“自然共同体”。
所谓自然共同体,是指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有一定地理区划、物理形态的共同体,恰如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伦所论:“大多数人相信,历史上存在名副其实的共同体,人们确实居住其中。先有共同体,然后才有个人。有了村庄之类的物理地点,然后个人在里面出生、结婚和死亡,因此那是居住的共同体:既然祖先一代又一代寓居于此,村民们免不了发生纵横交错的血亲和姻亲关系,因此那又是血缘的共同体。村里有各种组织,有一个委员会、一个村长,有本村习惯和法规,还有一种本村感情。‘我们是这个共同体的人;‘你是来自别处的外人。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大家都同姓,比如在中国的某些村庄,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姓陈、姓阎,等等。”也就是一个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或曰“熟悉的社会”,据艾伦回忆,“这类表征,1968年我第一次访问一个尼泊尔村庄时见得不少,它们标志着一种大写词头的共同体,我们不妨称之为自然或真实共同体。当地村民被密密匝匝的亲戚包围,有些家庭在那里生息了好几代人之久。妇女尽管大都嫁到村外,也仍与她们的出生的村庄保持着牢不可破的联系。许多人终老于自己出生的村庄”。但是,英格兰的历史却与此不同,在此,这种“自然或真实共同体”的力量很弱,这样说是基于这样的对英格兰长时段历史的深入研究——endprint
“我对以往七百年英格兰乡村史的研究已经说明,英格兰从来不曾有过‘地方、血缘和情感意义上的真实共同体。可观的流动性、土崩瓦解的家庭体系、成熟的经济交换,这些证据无不说明,英格兰不同于中国、印度和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地区,回顾历史上的任何时刻,我们很难在英格兰找到任何‘自然共同体。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根状态其实是良有以也。英格兰自有独特的表征,它的民众从未包容于一个可以提供安全保障、却扼杀自由个人的共同体。相反,英格兰人寓居于暂时的、建构的半‘共同体,也就是朋友、同事、邻居、俱乐部会员组成的各种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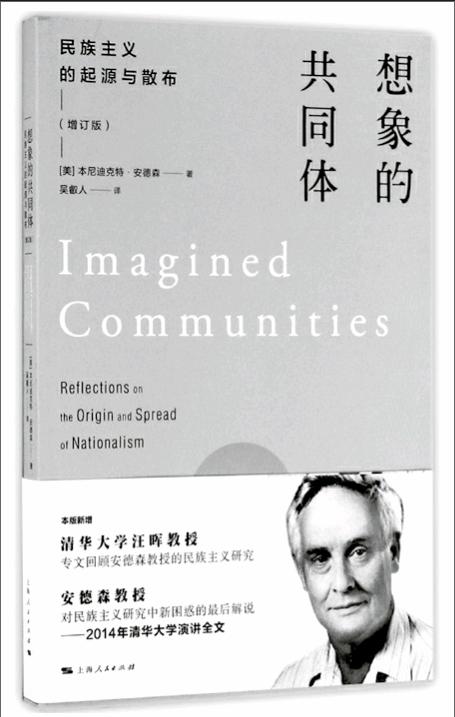
简言之“,家庭”“家族”“血缘纽带共同体”的缺位,使英格兰的孩子们很小就与家庭剥离,“切断”了与父母的关系,进入社会,或进入寄宿学校,或作佣工,或当学徒,涓涓细流,汇入社会这个公民社会的大海洋。“这些建制改造了一个人,使之不再依赖生来所属的那个单位,摆脱了梅因所说的‘身份关系,变成了一个自由漂浮的个人,随后进入各种契约关系,努力建立自己的地位。经过这道程序,个人变成了一个不得不以‘自由的、平等的公民身份去竞争的人”。显然,在家庭淡化、血缘抽离的社会和心理背景下,“自然共同体”的缺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而“自然共同体”的缺位,则为认识和理解其他“共同体”(包括“想象的共同体”)准备了条件。
三
据载,本尼迪克特· R.奥戈尔曼·安德森是一个与异乡和流浪有着深刻宿缘的人。某种流离失所的因子似乎早早就流淌在爱尔兰裔的安德森家的血液中了,而这样的流离失所又和大英帝国的盛衰始终相随。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國的高级军官,但祖母却来自一个活跃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奥戈尔曼家族。祖父在19世纪后期被派驻槟榔屿,他的父亲就出生于这个英属马来亚的殖民地上。在第一年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失败以后,他的父亲加入了在中国的帝国海关,此后在中国居住将近三十年,成为一个中文流利,事事好奇,十分热爱中国文化的人。1936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和大多数其他住在中国的爱尔兰家庭的小孩儿不同的是,本尼迪克特和他那位日后同享大名的兄弟 —— 被著名的左派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学家,《新左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 —— 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中国风味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而且他们的保姆还是一位越南女孩儿。战争结束,安德森家终于回到爱尔兰,但本尼迪克特从1947年起就在英格兰受教育。1953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Classics Study)与英法文学,奠定了良好的西方语言基础。
综上,安德森的人生经历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安德森具有英国背景,属于艾伦所说的那个淡化家庭、轻视血缘、地缘相结合的“自然共同体”的那一群体。二是安德森一生阅历广博,旅居国家较多。三是安德森成年后回英国接受系统教育,符合英国人“有一种将子女从帝国各地送回祖国的特殊习惯,所以英格兰被他们随身携带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而这种“全球性的国家”无疑是需要想象才能做到的 —— 如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所说:“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气氛,都使我感受到同一个国家;无论何处,无论在哪一条子午线下,我都在英格兰。”艾伦还结合自己的经历指出:“英格兰人在想象中建造他们的帝国,并且永远心怀‘祖国。…… 任何国家的人都会随身携带自己的文化,身在海外的法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印度人莫不如此。但是英格兰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采取了人为手段,刻意把子女从海外送回祖国,接受密集的‘英格兰性格的灌输达10年或以上。‘英格兰性格由是保持了鲜猛,孩子们基本上不会‘当地化。我自己就有这番经历:我从小接受如何做‘英格兰人的训练,学习英格兰的历史和文化,并且它们铸就我的人格。”这种“训练”之一就是培养对于国家的想象和对于祖国的忠诚 —— “用现代的行话来说,纵然面对千差万别,英格兰人还是‘想象出了他们的共同体。赫伊津哈深谙其妙:‘每一个政治实体,无论编织得多么绵密,本质上总是一个神话,只有它的信仰者愿意以它为生,并在必要时为它而死,这个神话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现实。无论他们选择将这种信仰镌刻在石碑上,抑或铭记在心里,都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这种信仰的强烈程度。”例如,“在中小学的日子里,我们学习的是如何辨认那些象征着我们共同的帝国身份的符号。正是这些共同符号,凝聚了一个共同体:旗帜、箴言、音乐、艺术、游行、盛会,将散落在远方的人们联结在一起。大家一有了共同的符号,就变成了‘我们,并且感到符号融入了自己的血液,将‘我们与那些拥有一套不同的符号系统的他者区别开来。因此,我们在学校里学习盛大和庄严,培养一种自认为统一的‘心灵习惯—— 尽管我们可能散落在6000英里以外”。
而这些元素,在安德森的人生经历中并不陌生,尤其是他那种四处漂泊、四海为家的国际经历,使得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当地化的“自然共同体”,而是为民族寻求另一种解释,这就为他探索和理解“想象的共同体”准备了条件。要之,要理解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就要理解其背后的那种以“地域辽阔”“想象”“神话”为纽带的“英格兰气质”,而纵观安德森的人生,恰好具备这样的气质,所以,把《想象的共同体》和《现代世界的诞生》结合起来阅读,不失为深入理解“想象的共同体”全貌的一种路径。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