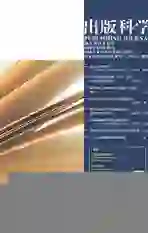论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读物编辑观
2018-01-17黄轶斓沈艾娥
黄轶斓 沈艾娥

[摘 要]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陈伯吹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他在创作、翻译、教育及编辑出版方面都颇有建树,以致被人称为“东方的安徒生”。在编辑出版方面,凭借丰富的儿童文学读物编辑经验,他曾写下多篇编辑出版方面的理论文章,不仅为后人洞悉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生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与蓝本,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第一套较为完整具体的儿童读物编辑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历史借镜意义。
[關键词] 陈伯吹 儿童读物 编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6-0038-06
Chen Bochui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Books Editing
Huang Yilan Shen Aie
(Literature of Department,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In the occurrence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Chen Bochui is an undoubtedly important existence. He was so successful in writing, translating, education, and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at he was known as “th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In the aspect of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he wrote many articles on childrens books editing. The editing theory of childrens books he proposed is useful today.
[Key words] Chen he proposed Bochui Childrens books Edi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作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陈伯吹(1906—1997)在儿童文学的创作、编辑出版、翻译理论研究及儿童教育事业上都颇有建树。他投身于儿童文学事业整整七十五年,是一位真正“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教育事业”[1]的人。他主编过《小学生》《小朋友》《少年画报》《现代儿童》等多个颇有影响力的儿童刊物,其丰富的编辑经验,不仅为后人研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生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维度,而且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我国第一套较为完整的儿童读物编辑理论体系,为今天的儿童文学编辑与出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1 儿童文学读物编辑经历的追溯
1930年,早在大夏大学就读时期,陈伯吹因向北新书局投稿《小朋友诗歌》而与书局创办人李小峰和赵景深相识,由此开启了儿童文学读物编辑之路,随后担任北新书局《小学生》半月刊的主编。在当时已有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等多个儿童名刊的情况下,《小学生》以精准的阅读对象,务实的编辑态度,对读者意见及与读者互动的重视,精心而全面的栏目设计以及颇有情趣的图画设置等,受到儿童极大欢迎,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1934年,因经理张一渠的邀请,陈伯吹来到我国第一家以儿童文学读物为主的出版社儿童书局工作。这一时期属于陈伯吹认定的儿童读物四个时期中的第三个时期,即科学常识时期(约1932—1937年)[2],所以在选编儿童读物时以儿童常识性读物为主。他先后与黄一德合编一套200本的《儿童半角丛书》,与梁士杰合编一套152本的《我们的中心活动》丛书,还与张一渠主编《新连环画》80册丛书。另外,陈伯吹还把儿童书局带有较强文学性、供高中低三个年龄段儿童阅读的刊物《儿童杂志》改为高中低三个版本的《儿童常识画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孤岛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日益恶化,陈伯吹的编辑出版工作被迫停止,但却在山城重庆得到了延续。1944年经中华书局金兆梓、姚邵华等人的再三邀请,陈伯吹担任了《小朋友》的主编。在1945年4月1日使这一停刊长达七年之久的读物终于复出,并借老舍的童话《小白鼠》来“以光篇幅,以资号召”[3],为战火中的儿童献上了一道道精神盛宴。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陈伯吹于1947年5月又接受《大公报》编辑王芸生、潘际炯的邀请主编副刊《现代儿童》。新中国成立后,陈伯吹先后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等重要编辑职位,继续在儿童文学读物编辑岗位上发光发热,一直到逝世。
2 儿童文学读物编辑的理论建构
五四后儿童文学期刊的兴盛催生了儿童文学读物方面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郑振铎的《〈儿童世界〉宣言》、周作人的《儿童的书》、鲁迅的《二十四孝图》,30年代尚仲衣和吴研因围绕儿童读物的幻想性发表的《关于“鸟言兽语”的讨论》、《读尚仲衣君〈再论儿童读物〉乃知“鸟言兽语”确实不必打破》以及茅盾的《论儿童读物》、鲁迅的《看图识字》、郑振铎的《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等系列儿童读物相关文章的发表,掀起了批判传统儿童读物、建立儿童本位文学观的高潮。陈伯吹凭着多年的编辑经验,再加上儿童读物的创作以及大中小学的教学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且富有特色的儿童文学读物编辑观。陈伯吹这时期发表的比较重要的相关理论文章多达8篇(见表1)。在这些文章中,陈伯吹从儿童读物的内容选择、用字用语、图文设置以及儿童读物对教育的价值意义等角度,力图全方位把握与建构儿童读物的编辑与出版。
2.1 儿童本位的编辑观
在《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中谈到儿童读物编辑的两个前提时,陈伯吹首先提到的一个前提就是“编辑给谁看”,随后他又明确指出“必须注意到儿童本位化”的编辑要求,并进一步阐释了儿童本位化的编辑观:“文字合于儿童的程度,事物合于儿童的了解,顾及儿童的生理和心理,以及阅读的兴趣,务使成为儿童自己的读物,而不是成人的儿童读物。”认为这些“实实在在是编辑儿童读物的基本条件”[4]。
正是秉持这样的编辑观,陈伯吹在1931年元旦到1934年初主编以小学中高级学生为服务对象的杂志《小学生》时,为了能更好地服务儿童,及时地了解儿童的阅读兴趣和爱好,陈伯吹先后共32次以“编者谈话”的方式积极反馈儿童读者的意见。他曾以编者的口吻写下下面的文字。
亲爱的小读者们:
第一件事要告诉你们的,我们的暑假特刊已决定出一厚册“童话特刊”来赠送给一万多个小读者,这是尊重大多数的意见。在答案中:要读童话的是最多,其次是诗歌,再次是图画,故事,小说;也有要我们出卫生的,国耻的,新闻的,美术的特刊,这都很好,可惜还是少数人的意见,我们只好再想法吧[5]。
从这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到陈伯吹在与小读者的对话交流中,充分尊重他们的兴趣和意见,体现了他儿童本位的办刊理念。
陈伯吹的儿童本位观还体现在他充分尊重儿童喜爱图画的特点上。正如他在《儿童读物编著与供应》中所说:“读物的形式对于阅读的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所谓阅读的形式,图画却占了大部分。图画对于文字,可以帮助想象,增进了解,提高兴趣,它在儿童读物上的地位,是与文字分庭抗礼的。”[6]为了更好地利用图画来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他提出插图“至少要符合下列六个条件:清晰、单纯、具体、彩色、式样的变化、排列的适当”[7]。他还从儿童读者的欣赏角度,列举了儿童对插图的六个方面的要求。
内容:儿童最欢喜“人”,次为“动物”,再次为“植物”。
笔调:照相画居首,钢笔画第二,毛笔画居末。因为前者明晰、准确、翔实。
大小:大幅(全页)最受欢迎,愈小愈不满意。
体裁:实体画为首,次为近乎儿童的自由画,象征画最不行。
繁简:有背景的插图,认为最美丽。
颜色:彩色画第一(但黑影画在高年级生中与彩色画受同样的欢迎),黑白画第二,轮廓画殿后。
此外,“故事性强的、动作较多的插图,也比一般的插图受儿童欢迎。”[8]
谈到封面时,陈伯吹把儿童读物的封面比作“一件灿烂的衣服”,认为“儿童读物的编辑者,不得不重视封面,不得不给予最美丽的设计”。具体谈到如何设计封面的时候,他这样说道:“彩色的(三色尤佳)要比单色的好,无可疑义。在彩色中间:年幼的儿童最欢喜红色,次蓝色,再次浅红。年长的儿童,渐渐欢喜蓝色和绿色了。”[9]
从这些对儿童读物形式上的要求,足可见陈伯吹处处以儿童生理和心理的接受特点为基础,彰显了他儿童本位的编辑观。在他主编的杂志中也体现了这样的思想。他主编的《小学生》《儿童常识画报》《小朋友》《现代儿童》,都聘请专业的画家参与封面、插图的设计和编排,保证杂志适合儿童的接受特点。比如编辑《小学生》《儿童常识画报》时就请当时名噪一时的装帧艺术家兼画家郑慎斋任美编,主编《现代儿童》时团结了张乐平、邢舜田等有名的画家,使得“连环画”成了《现代儿童》的固定栏目,连载了让人耳熟能详的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小茉莉得不偿失》等图画故事,翻译了《一只没有袋的袋鼠妈妈》《百万只猫》等今天深受儿童热捧的西方图画故事名篇,使得我国儿童读物与西方取得了一定的同步性。
2.2 现实主义编辑观
在《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中,陈伯吹谈到编辑的另一个前提是“编著给怎样的儿童阅读”,他认为当然是给“现代的中国儿童阅读”。在具体谈到编辑给现代儿童什么内容的时候,他认为要给他们“正确的认识与思想,科学的智识与技能,艺术的欣赏与创作”[10]。他把儿童对社会的“正确的认识与思想”放在第一位,充分说明他直面现实的儿童读物编辑观。正如王富仁在《呓语集》中所谈:“把现实社会不完满的地方当作完满的地方告诉儿童,不但是对儿童的犯罪,也是对人类的犯罪。”[11]面对20世纪30年代列强环立、内外交困的社会局面,尤其是日本对我国的步步侵略,陈伯吹从最初对童心的赞颂与讴歌转向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描述,以培养儿童正确的认识观和价值观。他分别在主编的《小学生》第16期、21期、36期上以“国庆与国耻专号”“科学与救国专号”“战争与武器专号”等形式集中介绍社会现实,试图把杂志办成面向社会的“人生教科书”[12]。正如他自创的重要长篇童话《阿丽思漫游记》在《小学生》杂志上陆续连载时,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原本想“塑造一个天真活泼,却又聪明能干的小姑娘的形象——中国阿丽思”的陈伯吹,在写到12章后,“再也不能循规蹈矩地继续按照原计划写下去了。阿丽思不再仅仅是正常的、健康的‘普通一女孩,她应该是反抗强暴的‘大无畏的小战士了”[13]。这种鲜明的现实主义思想不仅影响了陈伯吹的创作,也影响了他作为主编对刊登作品的选择。在《小学生》上,他曾在1931年第3期上刊登过陈醉云的诗歌《热烈与和平》,在1931年第16期上刊登过钱清萼的《国庆与国难》,1931年第18期、19期上分别发表了陈心一的故事《拔槍就打》和《我不吃敌人的糖果》,他自己也以翡翠为名,在1931年第16期上发表《有家归不得》和《复仇》等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儿童文学作品。主编《小朋友》杂志的时候,他曾在1945年第5期、6期上刊登黄衣青的《小朋友的灾难》《小朋友的地下运动》等反映战争对儿童的摧残和带来的苦难及儿童积极反抗的故事。在1947年主编《现代儿童》时,正处于国民党挑起内战,社会一片混乱的局面,激进的陈伯吹刊登了陈叔勉的《罗兰到上海来的故事》,抨击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物价飞涨,人们饥不果腹的生活现状;施雁冰的《爸爸回来了》,反映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四处抓兵,造成儿童家破人亡的惨境等黑暗现实给儿童带来的巨大身心损害和折磨。
陈伯吹的现实主义编辑观与当时左翼人士的观点一致,“给少年们以阶级的认识,帮助并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14]。试图通过对黑暗现实的反映,来培养少年儿童激进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3 “寓教于美”的编辑观
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陈伯吹,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深信不疑,提倡教育审美两者并重、“寓教于美”的儿童读物编辑观。早在1923年在宝山县杨行乡朱家宅第六国民小学任教的时候,他就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儿童教育小说《模范同学》,为其以教育为重的儿童读物编辑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教育的意义必须强调》一文中,陈伯吹旗帜鲜明地指出儿童读物的“教育意义必须顾到而且强调”,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宣传思想、教育人民的利器,儿童文学当然也如此”,并引用苏联儿童诗人马尔夏克的话:“儿童文学除了形式的美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具有教育的意义。”[15]在《小学教材与儿童读物的检讨》一文中,他指出儿童读物是“小学教材的温床”[16]。
但陈伯吹也强调“儿童读物必然是儿童文学的读物,不论它的内容是社会的或自然的,必须要依照文学的形式与艺术的技巧来编辑”[17]。为了说明这一点,他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儿童读物在教育与文学审美上密不可分的关系:“写作者对于题材的处理和结构,必须煞费苦心,遵循艺术的美感律,缜密地组织,像阿位(Arachne)——希腊神话中一个善织的女子——一样地编织精美的织品,把教育意义的光辉织入字里行间”[18]。
陈伯吹的这一编辑观与当时人们儿童文学观念的转变有较大的关系。在五四前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及霍尔的“复演说”是儿童文学界主要的理论话语。借助这些理论资源,周作人为代表的先驱们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为基石,找到了儿童与原始人、原始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内在一致性[19]。所以儿童成为他们口中的“小野蛮”,并认为那些民间、自然的童话更有意味,还提出了“有意味的没有意思”[20]的审美追求,强调儿童及儿童文学的自然属性。但正如批评家朱自强后来总结的:“在中国这块封建思想文化板结的土地上,在中国这块遭受外国帝国主义蹂躏的土地上,‘儿童本位论难以结出饱满的果实。”[21]儿童及儿童文学的社会属性必将得到重视,它的教育价值和政治功能必将得到强调。陈伯吹教育与审美并重的编辑观,无疑是对儿童及儿童文学属性予以正确认识的结晶。
陈伯吹教育审美并重的编辑观也影响着他作为编辑对作品的选择。在《小学生》上既发表有仇重的《雁子为什么到麦青时节才来》(1932年第39期,3—19页)这种注重儿童知识教育的作品,又有赵景深的童话《白丽》(1931年第1期,78—93页)、《聪明的女子》(1931年第5期43—50页)和郭沫若谱词、邱望湘谱曲的《月光娘娘》(1932年第32期,19页)这种注重幻想和童趣的作品。
3 儿童文学读物编辑的实践策略
陈伯吹“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不懈地创作和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少年儿童读物,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作出了可贵贡献”[22],总结起來,其丰富的儿童文学读物编辑的实践策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3.1 改编与自创并重
面对本土儿童文化相对匮乏和薄弱的现实环境,改编古今中外的优秀儿童读物成为当时编辑编选刊物的重要手段。这种改编传统可以追溯至我国儿童文学发生期——晚清及五四时期。从最早的儿童期刊即1875年外国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小孩月报》及1897年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蒙学报》旬刊大量刊登翻译的西方儿童故事,到1909年孙毓修创办《童话》丛刊改编来自古今中外的儿童故事,再到五四时期《儿童世界》《小朋友》《小说月报》等对古今中外儿童故事的改写与翻译,中国的儿童文学正是在改编与翻译的过程中逐渐走出了自己创作的道路。对在童年时代就浸润于西方改编的故事《无猫国》《怪石洞》[23]的陈伯吹来说,儿童读物的借镜文化已是烂熟于胸。因此在他主编的《小学生》上就曾连载过自己创作的脱胎于英国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阿丽思小姐》,在主编《小朋友》杂志时也曾把德国敏豪生的《吹牛大王历险记》改编成《奇怪的旅行》,还刊登过张竹孙根据伊索寓言《乌鸦和狐狸》改编成的故事《狐狸和乌鸦》等。
但另一方面,陈伯吹编辑刊物也很看重作者的自创作品。事实上,经过发生期的酝酿和模仿,20世纪30年代后本土儿童文学创作已初具规模,佳作不断,还产生了张天翼《大林和小林》这样成熟优秀的作品,儿童文学园地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创作团队。因此陈伯吹主编的刊物上除了发表改编或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外,还发表了大量本土作家创作的作品。比如汪岳云的故事画《香水要不得》(《小学生》1931年第18期,2—4页)、水丰的《鹿角速还狗哥》(《小学生》1931年第7期,6—9页)、卢冀野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散文《平凡的童年》(《小朋友》1945年复刊第9期,8—10页)、祁致贤表现战争残酷的故事《一个远征军的日记》(《小朋友》1945年复刊第2期,22—25页)等。
原创和改编并重,既丰富了杂志的内容,打开了儿童的视野,增加了杂志的深广度,也促进了本土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展。
3.2 注重与读者的对话
“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24],它以实体的方式承载着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但也是编辑乃至一个时期思想意识的体现。陈伯吹本着“儿童本位的教育观”这一办刊理念加上刊物对经济利润的追求,因此特别注重与小读者的交流和对话。
首先,杂志大量刊发小读者创作的优秀作品。如《小学生》创办《小学生园地》《小学生作文》等栏目,积极鼓励儿童原创作品,甚至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在51期专门出了《小学生作品的专号》。《儿童常识画报(高级)》开设《儿童创作》栏目,发表了许多小读者的作品。《小朋友》有《小朋友文坛》等栏目,发表儿童的原创作品。
其次,利用“悬赏”等方式吸引小读者参与刊物活动。为了吸引小读者参与和订阅杂志,陈伯吹精心安排了一些小栏目来激发儿童阅读与购买的兴趣。《小学生》不定时以“悬赏”方式提问,向儿童征集答案,并给予优惠订购杂志的奖励。悬赏的问题有对某一谜语的猜想、对作家某篇作品的理解、对生活中某一常识的认知,还有征集读者对本刊的意见等,如1931年第4期的“悬赏”就是陈伯吹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读者对刊物的看法。陈伯吹借助这种方式寻求与读者的多维对话,拉近读者与杂志的距离,实现与读者的平等交流。
第三,积极听取读者建议并及时反馈。作为自负盈亏的刊物,重视读者意见,倾听读者声音是杂志成功的不二法门。陈伯吹深谙此理,所以在主编《小学生》时多次以“编者谈话”方式积极反馈小读者的意见,并适时且合理地吸纳其中好的建议。主编《儿童常识画报》(高级)时,也曾专设《创立小小信箱:寄给小读者的信》栏目,加强与儿童的交流。正是因为陈伯吹秉持读者为先的编辑观,使得他主编的多本刊物拥有稳定且较为庞大的读者群,能在儿童杂志早已泛滥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屹立不倒。
3.3 组建专业化的创作团队
从主编《小学生》开始,陈伯吹就非常重视杂志创作团队的建构。1930年筹备创刊号时,他首先做的就是聘请沈百英、徐调孚、周向之、徐学文等27位作者为特约撰稿人,“把当时上海与儿童文学有关的作者、名流和业余爱好者几乎全部囊括了进来”[25],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杂志稿源的水准和质量。在接手由《儿童杂志》改版成的《儿童常识画报》时,因已建立了由“陶行知、吴研因、陈鹤琴、沈百英”等一大批知名作者构成的专业撰稿人团队,而未做改动。抗战时期在重庆接手《小朋友》时,陈伯吹把组建杂志创作团队当作头等大事,经他多方努力和联系,很快把何公超、仇重、黄衣青、贺宜、金近、揭祥麟等老中青作家紧紧团结在杂志周围,给战火中的儿童提供可贵的精神养料。抗战结束后,陈伯吹应《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邀请主编《现代儿童》时,因多年来集创、编、教三位一体的多维经历及“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的发起者身份,俨然成为儿童读物届的“带头人”。因此,这时围绕在《现代儿童》周刊身边的撰稿人员更为充足,不仅聚集了十多位有名的儿童编辑及作家、画家,而且得到了远在英国的朋友的支持,并于1948年4月17日以“特辑”的名义发表了来自大洋彼岸的来信。
正是因为陈伯吹对创作团队的重视,所以他主编的刊物不仅发表过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方轶群的《萝卜回来了》等经典名篇,丰富了儿童的精神生活,而且培养了揭祥麟、方轶群、鲁兵、圣野、任大霖等一大批后来颇有造诣的儿童文学作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本土儿童文学的发展,为我国儿童读物编辑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伯吹,不愧为“东方的安徒生”[26]。
注 释
[1][12][23][25]韩进.陈伯吹评传[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9:350,82,8,78
[2]陈伯吹.兒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N].大公报,1948-04-01
[3]陈伯吹.编者室讲话[J].小学生,1931(10):1
[4]陈伯吹.蹩脚的“自画像”[M]//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39
[5][6][7][8][9][10][17][18]陈伯吹.儿童读物的编辑与供应[J].教育杂志,1947,32(3): 69-76
[11]王富仁.呓语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6-17
[13]陈伯吹.阿丽思小姐·前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6
[14]沈起予,潘汉年,田汉,等.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J].大众文艺,1930,2(4):1241-1244
[15]陈伯吹.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J].中华教育界,1949,复刊3(5):19-22
[16]陈伯吹.小学教材与儿童读物的检讨[J].中华教育界,1947,复刊32(3):69-76
[19]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64
[20]朱自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1996(1):11-18
[21]朱学典.努力改造现在的儿童读物[J].宝山县教育月刊,1928(13):10-14
[22]乔文.美收藏家盛赞出版家陈伯吹[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10-25
[24]陈平原.报刊研究的意义[M]//文学的周边.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97
[26]何龙.追寻大师的足迹:记儿童文学作家、编辑家陈伯吹[J].出版科学,1998(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