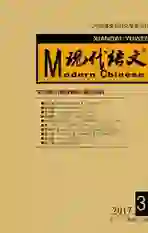白·夜·行
2018-01-17郭惠芬
摘 要:《白夜行》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享誉最高的一部小说。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白夜行》貌似矛盾实则巧妙的叙事技巧:拼图式的故事叙述、草蛇灰线式的线索串连、在凌乱中有序的时间呈现。文章重在从读者的阅读感受角度,论述了《白夜行》享誉的技巧原因。
关键词:《白夜行》 叙事技巧 拼图式 线索和时间
《白夜行》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享誉最高的一部小说,文题解释有二:1.在没有太阳的白天行走,纵使是白天,眼前的却还是无边无际的黑暗;2.在没有太阳但有白光的夜里行走。女主人公雪穗有段著名台词:“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1](P521)结合这段台词,那么应该是第二种理解更为贴切。但如果从《白夜行》的叙述技巧层面来讨论,这个文题还可理解为:白天和黑夜同行——作品正是运用了看似矛盾实则巧妙的艺术技巧,才使这部推理小说的魅力经久不衰。
一、拼图式的故事叙述
与传统侦探小说重情节轻文艺不同,《白夜行》的中心情节实在简单,就是讲两个童年受过心理疮伤的人如何扭曲地成长的故事,最后又揭晓了最初凶杀案的谜底,但是小说篇幅绵延了十三章三十五万,时间跨度二十年,众多“无关”人物在其间出出进进。如果你用阅读一般推理小说的期待心理去阅读《白夜行》,那么你可能会被第一章吸引,但到了第二章你会觉得在读另外一本小说,到了三四章你更可能没有了坚持下去的耐心了。整部小说没有一气呵成的故事,没有明显的一贯到底的线索,没有集中统一的主角,没有神化的侦探……似乎太没有吸引力了。但如果能够为了“东野圭吾”的名号而坚持,那么你绝对不会失望。因为它的美妙是徐徐向你展开的,只有对作者有信心的人才能够享用这种独特的美。你看的一章只是一幅完整拼图中的一张,单看它毫无特色,甚至也不大有美感,但却是全图必不可少的一环,你掌握的碎片越多,你拥有完美的概率就越高,你踏踏实实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这张地图的一小块,或是沟壑,或是河流,或是土壤,或是山路。所以,完整故事的阅读过程无疑是一次步履有些艰难但绝对是有趣真实的主观感受极强的推理之旅。
“碎片化”,是《白夜行》的一种叙事技巧。全书除了首尾两章分别以发案和结案的内容为主之外,其余各章都是以片段式的叙事为主,各章均只是片段、局部地呈现案情相关的线索或细节,而这种呈现又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而且几乎每章都变化叙述视角,上下两章之间又几乎是不搭界的。但每章节之间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是真的“失联”,看似闲笔的内容全都是刻意的安排。
比如第十一章,是以私家侦探今枝为视角的,主要通过他的行动和他与筱冢一成的对话揭示雪穗的“前事”,而本章最后,又以今枝的死作结,又引出谜题“到底是谁杀死了今枝”。而第十二章又完全宕开,第一节是以栗原典子为叙述视角,讲述了她与秋吉雄一(即男主人公亮司)同居情形,并回顾了她与秋吉雄一的初遇。而第二节又跳宕到了筱冢成一的叙述视角。之后的五小节,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视角的交替出现,前者为了讲述亮司,后者为了讲述雪穗。亮司被典子所逼,交代前往地点并带她前往大阪,而大阪正是他和雪穗共同的家乡,也正是雪穗因为母亲的病故而现在主要故事发生的地方。
真是这种“藕断丝连”的安排形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效果,而读者在通过各个片段的叠加和部分疑点的组合中会逐步意识到这种与众不同的叙述,就是提高不同的人物“破案”参与性,比如以今枝为故事视角的第十一章我们知道了今枝是在衛生间的马桶旁昏迷的,而以典子为视角的第十二章,我们又知道了秋吉雄一让典子提供氰化物并以小说为借口共同创作了“谋杀案”。于是,读者的愉悦感产生了,因为在整个“破案”过程中作出“贡献”最大的不是别人,真是读者自己。读者通过从片段的叙述中获得的零散的案件信息,将碎化的信息进行加工组合,从而尝试自己确定作品的主人公,并进行探案,最后去碎片化,完成“拼图”游戏。
二、草蛇灰线式的线索串连
中国古典小说讲究“草蛇灰线”的技法,反复使用同一词语,多次交待某一特定事物,形成一条若有若无的线索,贯穿于情节之中。而这种技法在《白夜行》中特别明显,结合“拼图式”的故事叙述,如果作者不进行“伏脉千里”的线索安置,那么故事必定会凌乱不堪而丧失阅读趣味。但这种安排只有到最后读者才会有恍然大悟之感,最初的感觉要么是有些突兀,要么是不经意地溜走了,这也是作者故意而为之的技法之一。
我们先来读一读雪穗和亮司的出场。这两位主人公并不是用全知视角和第一人称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而是用了限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出现的。第一章,通过警察笹垣,我们认识了后来才知道是主角的雪穗和亮司。“他往那边看去,心头一震。门后站着一个男孩,十岁左右,穿着长袖运动衫、牛仔裤,身材细瘦。笹垣心头一震,并不是因为没有听到男孩下楼的声音,而是在眼神交会的一刹那,为男孩眼里蕴含的阴沉黑暗所冲击。”[1](P15)而雪穗的出场更是令人惊异,当被问“你妈妈在不在啊?”再次询问“请问是哪位”而知道是警察后,她要求出示证明,而且邀请他们进屋,因为“在外面等,附近的人反而会觉得更奇怪”。这样老练的待人接物方式根本不像出自一个五年级小学生。从而在笹垣和读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为读者确定主人公作好了伏笔。
通过这样的出场方式,作者为读者巧妙地明确了后文“凌乱”故事的两条线索。一条是“白天”式的明线,即是警察笹垣润三坚持了二十年追查亮司父亲被杀案,但这条线索虽为明线,真如上文所说,也并未一直连续,而是断断续续,不断被其他人物、其他故事打断,但同时断中又有续,所有人物、所有故事又都是围绕开端案件被讲述、被展开。另一条则是“黑夜”式的暗线,即是雪穗和亮司的坚韧而绝望的爱情。虽为小说的男女主角,又是爱情故事,但小说却绝然迥异于其他小说,男女主角除了在结尾处从未在同一时空出现过,即使是最后,亮司已经成为了一具尸首,而雪穗也漠然地以“我不知道”拒绝了与亮司相认的可能,这样的爱情绝对的“暗无天日”,但在全文阅读结束的时候,读者又不得不为了这样的爱情而动容,他们正是为了追求“在同一轮太阳光下手牵手”的前景而一辈子做了在黑夜中偷生的老鼠,而雪穗更是明明白白地说了“因为有东西代替太阳……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亮司的死把她的太阳替代品也给夺去了,她连那一点点白夜之光也熄灭了,于是“她一次都没有回头”[1](P538)也便能得到解释。endprint
至于文中的《飘》、剪纸、钥匙、验孕管、雪穗缝制的绣有“RK”字样的小杂物袋、典子从医院拿回的氰化物以及她在大阪随手拍下的照片等等这些小物件则不必细说,它们更像是东野圭吾变戏法的小道具而已了。
三、在“凌乱”中有序的时间呈现
《白夜行》故事跨越了20年,从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写起到90年代,讲人物故事,也是讲时代故事,承载的内容丰富庞杂,像一部《茶馆》式的小说。但他又没有明显的“王利发”式的串场人物,也不像《茶馆》那样按照时间顺序写了三个时段的时代变迁。《茶馆》像中国古典大宅院式的建筑,庞杂而有序;而《白夜行》像日本的相朴火锅,荤素混杂、一锅乱炖,高营养、大份量。但《白夜行》到底不是火锅,它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事件叙述和场面描写中,有着像它的故事叙述与线索串连一脉相承的时间呈现特色,凌乱而有序。
小说最明显的时间标识,是通过社会事件来呈现。比如第一章里法院对熊本水俣病的判决,第二章电影《洛基》的上映,第三章漫画周刊《少年Jump》等等,本国读者从这些事件中不难知道时间的标点。即使不看这些具体的事件与细节,也可以从各个小章节中明晰辨认出各个时代的明显特征。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人性搖摆、心态失衡;80年代,电子信息行业异军突起,股市房市大热;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遗留下来的奢华风尚依旧残存,各类为年轻女性提供高级服务的行业依旧红火。依附着这些时代特征,故事一路前行。亮司和雪穗,70年代,一个丧父,一个失母;80年代,一个依靠电子信息大发横财,一个买房炒股不亦乐乎;90年代,一个依然在窃取信息,一个在商场大显身手,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戏场(其实是统一战线,只是读者尚未知晓)如鱼得水,无疑是人生赢家。到最后谜底揭晓,才明白东野的布局精巧细密,恰到好处。
作者的第二种时间呈现更为普通读者和非日本读者接受。他选取了男女主人公从小学、初中、大学以及后来结婚、离婚、再婚等片断,由他们身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旁人来讲述故事,通过其他人的眼睛,我们能窥见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生活轨迹。但这些讲述又并非常规,完全按照事件的发生过程而展开,而是不断地倒叙、插叙,要由读者重组才能真正理清,这也增强了在第一点已经论述过的读者参与性的强度。直到最后,读者才能真正完满地完成故事“拼图”。男女主人公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恰如白天和黑夜,永不相交,人生之路越走越绝望,因为他们等待的“白夜行”(白天和黑夜同行)永不到来,他们只能依靠“白夜”(有白光的夜里)之光,且行且自慰。
综上所述,《白夜行》多人称多视角的叙述是拼图碎片,而草蛇灰线的线索安排和隐而不显的时间呈现是拼图碎片的连缀,读者在作者的引导之下,冷静旁观、积极参与,将无望却坚守的凄凉爱情和执著而缜密的冷静推理完美结合成为了一次的艰难而愉悦的拼图游戏。
注释:
[1][日]东野圭吾著,刘姿君译:《白夜行》,广州: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版。
[2]侯立兵. 东野圭吾:《<白夜行>的叙事解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郭惠芬 江苏无锡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1415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