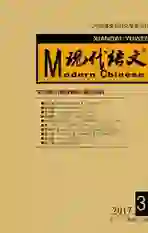海明威小说对话叙事技巧探究
2018-01-17张钧
张钧
摘 要:《祖国对你说什么》是海明威最具政治讽刺色彩的短篇小说,展现出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意大利社会情态。文中直接引语的人物对话,使不同人物在不同身份下的思想意识交流碰撞,构建起多声部的大型对白。同时,作者巧妙运用重复策略,使得转述时的人物对白和重复下的隐形对白凸显出语句的深层意蕴。本文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结合巴赫金的对白理论,深入探究海明威对话叙事中大型对白、重复技巧在叙事中的作用。
关键词:对话 大型 对白 重复
《祖国对你说什么》是海明威最具政治讽刺色彩的短篇小说,小说的原标题为意大利语:“Che Ti Dice La Patria?”译成英文是:“What Do You Hear From Home?”或“What Is the Coutry Saying to You?”小说的标题即已表明,故事发生在意大利,会使人联想起前法西斯时代和当今的现实。《祖国对你说什么》1927年首次发表时,是一篇名为《1927年的意大利》的纪实文章,记述了海明威与好友盖伊在意大利十天旅行的观感。后来,海明威将它作为一篇短篇小说编入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1](P12)原本是纪实文章的《祖国对你说什么》能够作为短篇小说编录入集,与文本中人物对话的叙事作用密不可分。
直接引语以引号为标志,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常见的人物对话形式。《祖国对你说什么》采用直接引语的人物对话进行叙事,以盖伊、“我”、意大利當地人三者之间的对话,还原出法西斯政权统治下意大利客观真实的社会情态。作品的不同人物间的对话具有突出的多声部特点,以及对话中的转述产生的重复现象,在叙事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方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大型对白
海明威曾经说过,他不仅向画家学习,而且也向音乐家学习。“我觉得我个人向作曲家学习的东西和从和声学及对位法学到的东西是很明显的。”[2](P64)海明威所学习的和声学及对位法,与巴赫金提出的“多声部”“复调”“对位法”理论遥相呼应。因为“对白”是作为“复调”的理论基础被提出来的,我们首先对巴赫金的“对白”理论进行简要阐释。
巴赫金认为,小说要描绘发展着的生活本身,生活的本身发展,不取决于作者,而有其自身的逻辑。他的小说对白理论把现实中的人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转化为对文学形式、人物结构的思考。即如果要使人物更加深入、真实地反映现实,就必须设法使被描绘的现实和人物,保持更大的客观性,为此,又必须通过加强人物的主观性、人物的复杂意识、多种关系的进一步相互渗透,亦即减弱作者的主观性的表露来达到。[3](P29)
巴赫金在评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进一步提出了“大型对白”的概念,指出“大型对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描绘发展的生活时采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大型对白”涉及小说结构、人物关系结构。巴赫金认为,小说结构的各个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白关系,这种结构法称为“对位法”。表现在小说结构上,对位就是用“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题目”,这也就是“多声部”现象。在人物关系的结构上,“复调”“对位”或“多声部”,表现为人物的对立式的组合。[3](P30)
值得注意的是,《祖国对你说什么》的人物对话中恰恰就体现出海明威在创作中对和声学及对位法的借鉴,体现出巴赫金“大型对白”理论中的“对位”“复调”“多声部”的特点。在意大利旅行途中,作为旅行主导者兼司机的盖伊不懂意大利语,因此精通意大利语的“我”为盖伊充当翻译,帮助他与意大利当地人沟通。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物设置,小说中同为德国人的“我”和盖伊与意大利当地人产生了具有“多声部”特点的对话。这一特点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斯佩西亚就餐记”尤为突出,大型对白呈现出“多声部”的复调特征,使不同人物在不同身份下的思想意识交流碰撞,发挥着情节叙述的作用,以具体真实的人物对话巧妙地传达出政治讽刺意味。
(一)搭车记:普通人与意大利法西斯党员
第一部分“我”与盖伊驾着一辆老师福特车在意大利北部旅行,中途遇到一个意大利年轻人“要求我们带他到斯佩西亚去”,虽然“我”向他说明车上已无空位,但此人态度强硬,宁愿站在车门外的踏脚板上也要搭车。
“照应一下,”他说。两个人把他的手提箱捆在车后我们的手提箱上面,。他跟大伙儿一一握手,说对一个法西斯党员、一个像他这样经常出门的人来说不会不舒服的,说着就爬上车子左侧的踏脚板,右臂伸进敞开的车窗,钩住车身。
“你可以开了,”他说。人群向他招手。他空着的手也向大家招招。
“他说什么?”盖伊问我。
“说咱们可以开了。”
“他倒真好啊!”盖伊说。[4](P86)
意大利年轻人明知车上无空位却强行搭车已是对“我”和盖伊的一种冒犯,而他以法西斯党员的身份强调自己搭车的合理性,丝毫不顾及开车者及乘客的感受的行为让“我”和盖伊对他更加反感。意大利年轻人与“我”“我”与盖伊之间的对话同样是传递着开车出发的信息,但意味却不同。通过“我”的转述引出乔伊对意大利年轻人“真好”的评价,这显而易见的反语显示出盖伊与我对意大利年轻人的讽刺,由此“我”、盖伊与作为意大利年轻人的关系构成了一种“对位”。正是这种“对位”人物关系和“复调”对话,彰显了作为普通人的“我”和盖伊对作为法西斯党员做派的反感和厌恶。
(二)斯佩西亚就餐记:德国人与意大利人
在第二部分“斯佩西亚就餐记”中,就餐时“我”告诉盖伊说,“墨索里尼已经取缔了妓院……这是家餐馆”,暗示了妓女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餐馆中公开招嫖,也解释了餐馆的侍女一直搂住盖伊的脖子,对他进行言语挑逗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我”、乔伊与侍女的对话似乎围绕着三人的国籍身份展开,似乎一直充满着政治意味,十分值得玩味。
“得,”我跟盖伊说,“你要找个地方简单吃一顿。”endprint
“这事不简单了。复杂了。”
“你们说什么?”那姑娘问。“你们是德国人吗?”
“南德人,”我说,“南德人是和蔼可亲的人。”
“不明白,”她说。[4](P89)
据黄伟芳对《祖国对你说什么》的译本研究,第四句“The South Germans are a gentle,lovable people.”中的“gentle”一词翻译为“守规矩的”更加贴合语境,张祥麟译本中把该句译为“南德人可都是些守規矩,可亲近的人。”更为合理,言外之意指“我们都是守规矩的人,请不要跟我们来这一套”。[5](P123-125)
“你们现在要在这里待一会儿吗?”
“在斯佩西亚这块宝地吗”我问。
“跟她说咱们一定得走,”盖伊说。“跟她说咱们病重,身边又没钱。”
“我朋友生性厌恶女人,”我说,“是个厌恶女人的老派德国人。”
“跟他说我爱他。”
我跟他说了。
“闭上你的嘴,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盖伊说。这女人的另一条胳膊也搂住他脖子了。“跟他说她是我的,”她说。我跟他说了。
“你让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
“你们吵架了,”女人说。“你们并不互爱。”
“我们是德国人,”我自傲地说,“老派的南德人。”[4](P91)
“我”与盖伊一进餐馆侍女对“我”与盖伊国籍进行确认,这一细节侧面体现出法西斯意大利政治气氛已然十分紧张。而面对侍女(实为妓女)多次挑逗的言行,盖伊频频提出离开,表现出鲜明的反感与厌恶,“我”则不断强调自己与盖伊德国人的身份,向侍女暗示二人对嫖娼并无兴趣。三人的对话围绕是否嫖娼这一问题展开,“我”与盖伊通过“老派的”“厌恶女人的”“守规矩的”南德人身份,与公开招嫖的意大利妓女形成“对位”关系。
“斯佩西亚,”女人说。“你们在谈斯佩西亚。”
“好地方啊,”我说。
“这是我家乡,”她说。“斯佩西亚是我老家,意大利是我祖国。”
“她说意大利是她祖国。”
“跟她说看来意大利是她祖国,”盖伊说。[4](P91)
在接下来的对话中,会说德语的侍女听懂了“我”与盖伊的谈话,将话题由斯佩西亚引向意大利,由家乡斯佩西亚下意识对意大利的祖国地位进行强调。而盖伊授意“我”向意大利侍女转述的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含有浓重的讽刺意味。侍女会说德语,她显然听得懂盖伊对她的明确反感与拒绝。虽然如此侍女却还是没有放弃对“我”和盖伊,仍旧增加着话语和肢体上的挑逗,这能够体现出她不得不靠卖淫为生的生活窘境。然而,侍女对直接造成她人生窘境的是取缔了妓院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却毫无感觉,已然被法西斯当权者狂热盲目的爱国思想宣传洗脑,在谈话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政治口号。作为意大利人的侍女与南德人“我”和盖伊的“对位”关系潜藏于“多声部”的对话中,体现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统治的罪恶与被统治者可悲的生存状态,蕴含着浓重的政治讽刺色彩。
二、重复
(一)对白中转述产生的重复
在“我”与盖伊的意大利之行中,“我”时常充当盖伊的翻译帮助他与意大利人交流。故人物对白中多出现转述,由此产生的重复是人物对白的另一突出特点。但对白中的重复并未带来语句的冗余,语句的深层含义反而在重复中得以凸显,作品主题与人物情感的表达也更为充分。
在第一部分搭车途中,由于搭在车外的意大利年轻人在下坡时加剧了车辆下行的速度,导致这辆老式福特小轿车差点翻车,“我”与盖伊也对这一场景做出诙谐的评价。
下坡路都是急转弯,几乎没有大转弯。每回转弯,我们这位乘客就吊在车外,差点把头重脚轻的车子拽得翻车。
“你没法叫他别这样,”我跟盖伊说。“这是自卫本能意识。”
“十足的意大利意识。”
“十十足足的意大利意识。” [4](P91)
搭车的意大利年轻人只关注个人安危和忽略了车辆整体的安全,“我”与盖伊将这种自私行为解释为“自卫本能意识”,盖伊更是诙谐地定义为“十足的意大利意识”。自卫本能意识,对“我”和盖伊一路旅行的见闻做出了合理解释。从小说标题的意大利语“Che Ti Dice La Patria?”到意大利市中心墙壁上粉刷的“墨索里尼瞪着眼珠的画像”、手写的“Vivas”(万岁)标语,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对国家安全的过分宣扬、对种族的盲目崇拜随处可见。我对盖伊定义的重复“十十足足的意大利意识”的强调,更是加重了这一短语的政治讽刺意味,二人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独裁统治的厌恶与讽刺一览无余。
第二部分“斯佩西亚就餐记”中,意大利法西斯当权者取缔妓院后,侍女在餐馆中公开招嫖维持生存。在三人的对白中,“我”对侍女话语的转述同样产生了重复现象。
“你们有什么甜食?”我问。
“水果,”她说。“我们有香蕉。”
“香蕉倒不错,”盖伊说。“香蕉有皮。”
“哦,他吃香蕉,”女人说。她搂住盖伊。
“她说什么?”他把脸转开说。
“她很高兴,因为你吃香蕉。”
“跟她说我不吃香蕉。”
“先生说他不吃香蕉。”
“哦,”女人扫兴地说,“他不吃香蕉。”[4](P92)
虽然侍女向“我”和盖伊表明她会德语,但是盖伊还是拒绝与她直接交流,而坚持让“我”转述。“我”的转述看似是简单重复,实则是对侍女的间接拒绝。在听完“我”的转述后,本打算吃香蕉的盖伊突然变卦,不为侍女留一丝希望。在这寥寥几句简单的重复将盖伊与“我”坚决拒绝嫖娼的态度展现地十分鲜明。
(二)重复中的隐形对白
斯佩西亚的餐馆中,侍女出于生存压力的不断试探不仅遭到“我”与盖伊二人的屡屡回绝,还受到了餐馆中一位“仪表堂堂”“穿套蓝衣服”的青年的回应。作为旁观者,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已经清楚察觉到了“我”与盖伊对嫖娼的坚决拒绝,因此多次劝阻侍女不要与二人继续纠缠。然而,他的劝阻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却实际参与到对话中,构成一种隐形的对白。endprint
“听我说,”仪表堂堂的青年在他写字的餐桌边说,“让他们走吧。这两个人一文不值。”
女人拉住我手。“你不留下?你不叫他留下?”
“我们得走了,”我说。……
“呆一小会儿也好嘛。”
“白天必须赶路。”
“听我说,”仪表堂堂的青年说。“别跟这两个多费口舌了。老实说,他们一文不值,我有数。”
“来账单,”我说。她从老太婆那儿拿来了账单就回去,坐在桌边。另一个姑娘从厨房里出来。她径直走过店堂,站在门口。
“别跟着两个多费口舌了,”仪表堂堂的青年厌烦地说。“来吃吧。他们一文不值。” [4](P92)
也许是在与“我”的对白中没有遭到直接拒绝,侍女对盖伊与“我”二人还抱有期待。她虽然因二人的婉拒感到扫兴,却还是坚持寻找挑逗成功的一线可能。虽然听到了那位旁观的青年的劝阻,但很明显侍女仍想做最后的尝试。因此,旁观青年的三次劝阻实际上参与到“我”与侍女的对话中。重复的劝阻向侍女暗示着失败的结局,“我”结账的言行回应着青年的劝阻,构成一种隐形的对白,同时加速了侍女与“我”对白结束的进程,衬托出侍女被迫求生的艰辛与无奈。
安德烈·莫洛伊曾这样评价海明威小说中的对话在叙事中的作用:“从独立的对话中我们可以辨别思想与身体的所有活动……欧尼斯特·海明威是纯粹对话之父。看看他写的最美的那些短篇吧,情节就隐藏在对话之中。”[6](P252)《祖国对你说什么》中,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独立引语的人物对白缩短了叙事者与读者的距离,真切地展现了法西斯政权统治下意大利的社会情态。海明威笔下的意大利社会情态构建于鲜活的人物与场景中,与人物对白的设置密不可分。在巴赫金的对白理论视角下,小说中具有对位关系的多声部对白,使“我”、盖伊与意大利当地人在不同身份下的思想意識得以交流对峙,助推情节发展,显示出鲜明的政治讽刺意味。同时,重复在对话中的运用也十分巧妙,既有由于转述需要产生的重复,也有构成一种隐形对白的重复。这种重复策略的使用凸显了语句背后的深意,描绘出意大利法西斯党员与被统治者的生存状态。正是由于这些叙事技巧的把握运用,海明威将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之下国民与国家的状态深蕴于的对话叙事中,表达鲜明的政治讽刺主题,“祖国对你说什么”的疑问更是促使读者展开对国民与国家合理关系的深思。海明威作品中出色精妙的对话叙事技巧不仅对其“冰山文体”的成熟完善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对于现代小说、现代叙事艺术的发展同样意义深远。
注释:
[1]吴健国:《同构对应 拟容取心——评海明威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海明威:《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2]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3]钱中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04期。
[4]陈良廷译:《祖国对你说什么》,海明威:《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5]黄伟芳:《〈祖国对你说什么〉中译本研究:关联翻译理论视角》,宿州教育学院院报,2006年12月,第9卷,第6期。
[6][法]罗杰·阿瑟里诺:《海明威灵活多样的写作风格》,杨仁敬编选:《海明威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参考文献:
[1]张金莲.简洁与重复——海明威小说的对话艺术[D].昆明: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黄伟芳.《祖国对你说什么》中译本研究:关联翻译理论视角[J].宿州教育学院院报,2006,(9).
[4][美]菲力蒲·扬.欧涅斯·海明威[A].张爱玲等译,[美]威廉·范·俄康纳编.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牛高妙 山东威海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文化传播学院 26420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