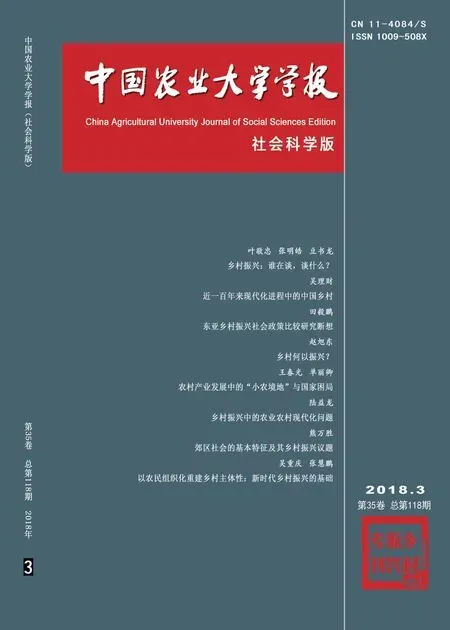田野工作与促进生命变革的乡村研究①
2018-01-16孙庆忠
孙庆忠
欢迎同学们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参加乡村振兴夏令营。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场域,走进报告厅就被热情洋溢的气氛包围着。大家为认识乡村、理解乡村而来,虽然与农大的缘分深浅不一,但在这里听闻的各种乡村故事,一定会激发你们的许多思考。我的专业背景是人类学,关注乡土社会、研究民间文化是这个学科重要的学术取向。我的讲题是“田野工作与促进生命变革的乡村研究”,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田野工作”,它是沉潜民间、建构学术新知的研究方法,也是人类学具有标志性的学科理念;第二个是“乡村研究”,中国农业大学是乡村研究的重镇,也是国内最早倡导发展研究的策源地。夏令营有体验乡村的环节,你们会在行动中重新发现乡村,也会体悟到中国乡村研究的诸多面向;第三个关键词是“生命变革”。也许在你们的想象中,把促进生命变革与乡村研究并置有些唐突,把它与田野工作放在一起也不大搭调。看似简单的田野工作,不过是和老百姓拉家常,怎么能够促进我们的生命变革,生命变革又何以成为乡村研究的主旋律?在我的思考和行动中,这三者是一体的,这也是我今天要重点讲述的话题。
一、昔日重来:田野工作的类型与印记
我自觉地梳理我的田野工作,第一次是2007年给我们学院发展系博士生做的讲座,题为《田野调查的技艺与修养》,第二次是2016年在贵州大学的讲座,名为《田野工作的信念与真情》[1]。每一次在讲这一主题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琢磨田野工作的真义到底在哪里。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下过田野,通常情况下,田野工作给我们最直观的认识是:第一,怎么进入田野,怎么收集资料?第二,如何把田野中收集的那些繁杂的,甚至有些混乱的资料,找到一个安适的学术位置,也就是说,到底怎么把田野资料放置在自我设置的学术命题中来。应该讲,我们对田野工作的理解多半止于此。那么,对于田野工作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吗?回首我自己下乡调查的日子,一幕幕都会清晰呈现在眼前。如果做一个大致的分类,我的田野工作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
第一,阐释文化特质的田野工作。1995年秋,我第一次下乡调查,目的是解释一些神秘的民间文化现象。那时候我已在沈阳师范大学教书,主要是讲授“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民俗学”课程。此后的三年,背包独行在辽北和辽西的几个村听闻民间故事和村中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那时候见识了一些风水先生和村里的“文化人”,每每想起都会让我对乡村肃然起敬,美在民间、智慧在百姓中间的感触时常萦绕心头。听村里的老人讲故事,冬日里坐在炕头上听他们讲村民的绰号,笑得肚子痛。那些兴奋得整宿睡不着觉的日子,是冬日里的温暖,也是初识田野的滋味。那时候,看什么都新鲜,尤其是我一直关注的民间信仰现象。所谓的“巫医神汉”,他们为什么会有特殊技能?神灵附体的大神大仙,为什么会在医疗卫生发达的时候在乡间还有广泛的市场?也许是因为没有过乡村生活的经验,我对乡民笃信的事实始终心存好奇,总是想去记录和分析。我把这种类型的调查叫做阐释文化特质的田野工作。对于我的民俗学专业而言,这是一个核心命题。我们要去解释那一方水土,那一个特定的区域文化里的人的生存形态,在他们的观念深处到底有哪些纷繁的文化现象还表现在日常的行为之中。那么,下乡的动力和目的是什么?真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我的课堂能变得美一些,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下乡”是为了我的课堂,希望我的学生能听我自己采录的民间故事和我对乡土社会的直觉描述。
第二,揭示社会问题的田野工作。1998年我到中山大学读博士,人类学专业的研读,让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去记录行将消逝的民间文化,与此同时,更希望从文化的视角来解释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我的田野点就在中山大学的近旁,名为鹭江村。1948至1951年间,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先生曾带领岭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在这里做社区研究。广州近郊这个普通的乡村聚落,因杨先生的著作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成了颇具影响的学术名村[2]。我在村庄进行追踪研究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广州138个城中村中的一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8条大街和150条小巷的村子不知道被我跑过了多少遍。无论是成为“食租客”的原住村民,还是栖身在都市的打工者,无论是“亲吻楼”呈现的村落形态,还是随处可见的小型作坊,都是我梦魇般的意象[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让我对乡村文化的重组、对城乡关系的未来心存忧虑。这项研究与2007至2009年带领学生追踪调查李景汉的京郊四村一样[4-5],意在呈现它们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因为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6]。回首这一阶段的研究,我觉得将其归类为揭示社会问题的田野工作是合适的。
第三,促进生命变革的田野工作。我从2008年开始关注农业文化遗产,希望通过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研究,重新发现乡村文化的内生性力量。但真正走入农业文化遗产领域,则得益于2014年组建的以本科生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在师生共度的田野里,一种社会使命感,一种对生活的热切关注,以及对于生命本身的关切,不仅改变了我田野工作的方向,也实现了一种生命的转型。因此,我更愿意把这几年的乡村之行,称为促进生命变革的田野工作。
以上三个类型实际上是我23年田野工作的主旋律。之所以要走到乡村去,一来是想保持对乡土社会的基本敏感,想保持我对所学专业的那份真情;二来是希望我的课堂始终是我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体验的真切传达。因此,每一次“下乡”我都觉得是和自己所学专业的亲和。当然,我多年的乡村之行并非是顺畅的田野工作,充其量是寂寞与欢悦同在。这之中,有两个意象是令我终生难忘的。
我早期的田野感受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清冷和寂寞。冬天的辽北是寒冷的,那时候没有手机,带上手电筒,背上大挎包,包上还系一个小铃铛,这是我多年都不忍心扔掉的铃铛。在那里我体会了伸手不见五指,体会了村与村之间三里地的漫长。一个人走在寂静的乡村里,只有那个铃铛与我作伴。丁丁当当的声响,好像是在告诉你自我的存在感,也好像一直在追问我到底来干什么。多年之后重温往事,好像只有那铃铛声记录了我最寂寞的田野。那里有恐惧和慌张,当然也有回归课堂之后讲述乡村故事时的片刻欢喜。在广州的城中村调查时,虽然与辽北的情景相去甚远,但许多感受却是相通的。而今闭上眼睛,每一条街巷里的独特建筑我都记忆犹新。村子里从早到晚是喧闹的,那是一个外来人的世界,人头攒动,拥挤而凌乱。在那里,我体会到的是喧嚣之后的冰冷与无奈。无论是城中村所展示的社会问题,还是打工者的生活际遇,都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我在杨庆堃先生的著作中寻找村庄的1949年,在我的调查笔记中记录着鹭江村的1999年。半世纪的跨度,物去人非,五十年的岁月,弹指一瞬。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是思考生活本真和生命意义的最佳场所。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与田野相伴随的思考,才让华南村落里的8条大街150条小巷与冬日里辽北乡村独行时的铃铛,成为了我生命里永远都不会被抹掉的田野意象。
23年走下来我能看到什么呢?今天早晨找到4张照片,看到这张2006年的照片很是感慨,时间好快,12年就这样过去了。我的田野工作从一个人的田野到带着学生赶赴乡村,从满头青丝到满头白发,这就是生活和生命的印记!这些照片里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瞬间里心绪的波动,都已清晰地印在脑海里。田野工作不是科学考察,面对的不是高山大川,而是社会生态,努力建立的是人和人的链接,生命和生命的链接。这份向内求索的工作与自然科学的攻坚虽有不同,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探索和发现之旅,这是我的田野工作。
二、乡村价值:回归土地的情感与力量
田野工作的目标是什么?于我而言,是重新认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作为认识乡村和重新发现乡村的重要方法,田野工作可以发掘老百姓积聚了千百年生活所存留下来的乡土知识和身处其中的地域文化。然而,它不仅仅是方法,它还可以培育和激发我们创造生活的情感和能力。如果田野工作缺失了这一点,所谓的发现不过是一篇论文、一种说法而已,那是远远不够的。在人与人的接触和问询中,我们所记录的除了他们的生活境况,还要走近他们的内心,去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那些乡村里的老人,他们可以为我们重现一个陌生的乡村,一段已经远逝的记忆。因此,我才把每一次乡村之行看作是寻找记忆的过程,一个寻找祖先的过程,也是一个重建我们和祖先对话能力的过程。今天快节奏的现代化,已经让我们背离了乡土,但这种形式上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诀别,否则我们就难以听懂祖先的话语,我们和自己的昨天也便失去了联系。其结果是我们无法破译祖先传递的生存密码,我们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之源。这就好比生活中的我们,如果一个人因失忆忘记了昨天,他也就不知道今天该怎么活了。以此观之,田野工作的确是情感的学问和实践。
当我们谈起乡土的时候,总有一个大时代的背景展现在面前。假如这是一个舞台,演员们穿着长袍马褂走上来,而舞台布景却是纽约的曼哈顿街区或是北京的王府井街头,你会觉得很滑稽,因为乡土社会有它独特的存生背景。我们的乡土怎么了?我们的乡村终结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颇有几分情怀才能走进乡村、守卫乡土?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81 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58.52%,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总量是28 652万人。面对这样的数字,再说我们是乡土中国就会受到直觉上的质疑,因为这些数字既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标识,也是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微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和城市化业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发展观念,农业和农村的凋敝是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乡村的未来有一个总体判断,然后才知道行进的方向和路径在哪里?这个暑期,我们学院会有百位师生赶赴各地调研,为乡村振兴寻找出路,这是基于学术判断的集体行动。
2011至2013年,我曾与朱启臻和熊春文二位教授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调查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这期间对我冲击最大的是乡村学校撤并后孩子们住校生活的一幕幕。或许他们享受到了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但却与家庭、与村落彻底疏离:孩子从6岁起就开始住校,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难以想象他们的乡村记忆还有多少,对乡土的情感是否依稀尚存;寄宿学校即使设在乡村,也多半形同军营,孩子们对村里的远山近水都无法亲近,虽然在乡村也会偶尔干点农活,但是对家乡的历史文化无知,对村落的礼俗漠然,对养育他们的这块土地几乎是无感的。这种研究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与我们的调研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全国流动儿童3 581万,留守儿童8 973万,56.8%的流动儿童与户籍地没有联系,一半以上不知自己乡镇的名字。这样的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判断——乡村已经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如果人口学家的判断无误,再过40年还会有5亿人生活在乡村,那么留住乡村的文化与记忆就是当务之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7]。在我看来,“失忆”就好像突然跌倒,醒来时妈妈不认识、太太不知晓,记忆全无。如果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历史忘却了,也就意味着没有可以期待的未来了。因此,如何进行乡土重建?如何应对凋敝的乡村处境?如何能够让乡村教育回归乡土以传承我们记忆的根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大问题。
接下来我常被追问的问题是,你极力倡导抢救乡土记忆,可是存留乡土有那么重要吗?2007年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我看到了法国人类学家玛丽·鲁埃的文章《依靠回归土地医治教育的创伤:老一辈克里人拯救迷失的一代》[8],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玛丽·鲁埃对加拿大詹姆斯湾的克里印第安人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我们所关注的传统农业的意义与乡土文化的价值。世代居住在詹姆斯湾的克里印第安人,是一个山林民族,以捕鱼、狩猎为生。政府为了让克里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很早就把他们接到大城市去生活。这些离开了祖居地的孩子,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甚至忘却了母语,忘记了故乡。他们在大城市里生活,又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双向的边缘人的处境,使他们成为城市犯罪的高危人群。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由于原住民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年轻的克里人不但在学校一败涂地,而且也没有能力获得打猎、捕鱼、设陷阱之类的知识和技能。双重的失败把他们推到了绝望和暴力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某些在狩猎营地继续其传统活动的长辈,将失足的青少年接到营地,引导他们“重归土地”开始新生,这些孩子们开始慢慢学习自己的母语,开始掌握祖先世代传习的技能,从而成功地重建了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老一辈克里人创造了奇迹,他们用回归土地的方式拯救了年轻一代。年轻人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找回了自我,建立了自身和祖居地之间的精神纽带。这个经典案例充分展现了自然和文化的力量,也为我们阻止农耕民族的“集体失忆”,重新认识乡土的价值提供了佐证。
当年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心潮澎湃,那一刻我看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曙光,也理解我们存留乡土社会的价值,它不仅仅关乎当下,更关乎未来。每一次提及这个案例,我就会联想到我对广州城中村农民工一代和二代的牵挂。20年来,我和当年走访过的四川打工之家始终保持着情感联系,每个节日都要传递问候。如今,农民工三代已在城市中成长,他们的命运对于未来中国的城乡格局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克里印第安人的故事会重新上演,还是城乡融合带给中国社会福音,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我们对于守护乡土抱有怎样复杂的情感,无论有多少人为我们冠以“田园牧歌”的标签,我们都必须面对当下中国的国情,必须看到农民的生存境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保护传统农业文化与社会系统的初心和行动,并非是浪漫的怀旧,而是恢复乡村活力、增进农民选择生活能力的重要策略。
最近几年,我对自己田野工作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也在跑乡村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2016年4月,我有幸到了贵州黔东南雷山县雀鸟苗寨和黎平县龙额侗寨。在一周的时间里,我看到了这里与绝大部分乡村相同的场景,年轻人流出,老年人留守,但是我也看到了另外一番风景。在雀鸟苗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组织起来,重走祖先迁徙路,探寻自己的根脉。而打工回乡的侗族青年,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起,以公益的精神和行动带动家乡发展。他们从2010年组织开展第一次“走进龙额侗寨公益行”助学活动,到2012年组织村寨大学生走访寨老、艺人,了解村寨历史、学习侗歌、染布等传统知识的“寻根之旅”;从2013年龙额青年乡村影像及能力建设计划启动,到2015年为村寨53个家庭拍摄并赠送照片,所有这些行动无不令我感动。我们的少数民族青年在用寻找历史的方式,重建文化自信,拯救家乡文化。2016年11月,我在云南玉龙县的石头城村调研,这个金沙江畔的纳西族村落,有着悠久的历史,元世祖忽必烈曾在此革囊渡江,越天险太子关南征大理国。村里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出去,居住在丽江或者去其他的大城市打工,但是村落没有因此而破败,老人通过一年一度重演祖先祭天的仪式,让漂泊在外的年轻人始终不忘他们祖先的历史,不忘祖先给他们身上存留下的文化基因。除了这些乡村内生性的力量,我也目睹了民间公益组织在乡土重建中的作为。2017年12月,我到广西扶绥县渠楠屯走访,这里紧邻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一家专注推动社区保护地的本地NGO,“美境自然”不仅是渠楠社区保护地的发起者,也是其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正是这一组织里年轻人的陪伴,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社区自治能力,也推动了自然教育和生态农业的开展。青年志愿者向农民传递的理念,感染着那里的村民,使这个小山村成为了村民自觉呵护的生态之地。
这些难忘的田野经历,总能让我在破败的乡村背后看到一线曙光,也因此不再理会凋敝的乡村到底值不值、能不能被拯救的问题。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可能会怀疑,当我们做一百件的时候,剩下的只能是欣赏。我和同学们分享我的田野经验,目的是告诉大家,当你把他人眼中浪漫的幻想转变成扎根乡土的实践以后,你的生活的境界也会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三、感悟田野:乡村百姓的生命与温度
2014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4年来我的田野工作始终有一个主要的目标,那就是要促进生命变革。到底促进谁的变革呢?这里的变革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作为乡村研究的行动者自身的变革;第二是我学生的生命变革,他们才是未来乡村发展的种子;第三是乡民和乡土社会的变革,也就是说,我们服务乡村的良苦用心,能否给那里带去一点希望,可否给那里的百姓带去一股清凉的风。这期间我的田野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乡村教育入手,建立学校与村落的联系,目的是使学校发挥其传播乡村文明的功能,实现乡土社会的自救,这是乡村教育现状调研的后续;其二是从农业文化遗产入手,通过文化干预的方式,培育村民对自身所属文化的保护意识,继而利用本土资源寻求自身的发展。
先来讲讲我的乡村教育实验。2011至2013年我们对乡村教育的调研发现,乡村教师有两种不稳定状态:一种是年纪大的,等待着退休;另外一种是年纪小的,等待着回城。再来看学校,大部分学校从乡村抽离,仅有的学校与乡村的关系松散,高墙大院隔断了它们之间相互滋养的可能。乡村的远山近水,但是孩子们无法亲近,这是我们乡村学校的基本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么让教师安守在乡村?怎么能恢复乡村学校原有的功能?基于这样的思考,2014年5月30日,在河南辉县南太行山区创办了一所以幼儿园为依托的川中社区大学。
为什么以幼儿园为依托?因为只有幼儿园阶段家庭、村落和学校之间才联系得紧密。上小学、中学以后,孩子们住校了,家长、村落与学校的连接很有限,所以以幼儿园为依托是我们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这所学校的定位是什么?虽然是一所乡村幼儿园,但是我们办的社区大学不是家长学校,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成人终身学习的学校。我们先让幼儿园孩子的家长走进来,再吸引村落里那些闲着没事的年轻妈妈走进来,进而让村落里寂寞的老人走进课堂。幼儿园能歌善舞的20多位老师是我们的义工团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中师生,但他们的本事是我们大学老师所不具备的。
受所学专业和农大社会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我的教育实验没有更多地关注学生,而是关注乡村教师及其背后那些生活在乡村里的妇女、老人,更多地关注学校和乡村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我要进行的是“上游干预”。孩子父母如果天天打麻将、把无所事事的愤怒之气发在孩子身上,教育的结局是可以想象的。从成人学习的角度来看,幼儿园的教师生活在乡村,每周回家一次,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在这种无奈之下,有没有一种可能让他们做一项自己觉得有意义又利于别人的事儿。所以我做的“系统干预”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让义工团队的幼儿教师能够在乡村教育里发掘自身的潜能,看到平淡生活里的深层意义;二是要让我们的农民学员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他们的生活不只是为那二亩地,也不是每天在愤怒中摔麻将,要让他们有精彩活过一次的感觉,要让乡土社会里日渐冷漠的人情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温暖起来。我的这些想法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影响一个人尚难,影响一个家庭、影响一个村庄进而影响整个地域社会岂不是梦想!因此,教育实验的第一年很多人认为可笑,第二年也有人认为是天方夜谭,第三年还有人认为不可持续,但是当第四年走过来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了,我们的幼儿教师团队也在这个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得了自信。今年5月31日的四周年庆典,我的心情异常欢悦。在孩子们和社大学员的欢笑声中,我看到了汇报演出带给他们的幸福,看到了他们在交流学习体验时的喜极而泣。在社区大学,65岁的老人可以学会写字,年轻的“宝妈们”可以书法作画,你难以想象梅兰竹菊、盛开的牡丹竟出自村妇之手,吹画、布贴画、太极扇、快板、甚至芭蕾,所有这些被称为艺术的东西和她们生命有了宝贵的连接,这就是变革的开始。当她们一次又一次诵读自己的作品,感受社区大学带给她们心灵冲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四年是多么值得,因为这里发生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变化,而是一个生命发生变化以后,带给整个乡土社会变革的讯息。
川中的教育实验,让我目睹了个人、家庭和村落因为教育的回归而带来的一线生机。这是一所乡村社区大学,虽然叫大学,但不是高等学校,它仅仅是以幼儿园为依托、以幼教团队为义工主体的乡村学堂。然而,这所学校目前辐射了周边11个村子,让252个学员在这里接受了新的教育,这也就意味着有252个家庭已经受到了社区大学的影响。而今,一些师范大学的研究者想来这里探问究竟,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社区大学在这里可以发生?为什么义工团队在奉献乡村的4年间没有拿一分钱报酬却可以持续?这样的追问和答案都有待别人去评说,我看到的是恰恰我所期待的生命变革。
下面再介绍一个案例,陕西佳县泥河沟村的故事。从图片上看,这里三面环山,面朝黄河,山水相依,宛如仙境。但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里的贫困村,从1955年就开始吃返销粮,直到1995年还在吃救济粮。这个村因36亩古枣园生长着1 100多棵古枣树,树龄最长者已经有1 300多年,2014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11月,又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然而,守着如此多的资源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裕的生活,学校的撤并、年轻人的外流,使这里缺乏了活力,这也是中国乡村的共相。那么,我们怎么把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转化成村落发展的资源呢?面对村庄的凋敝,面对农民的贫苦,还能否让农民心生一份对家乡的爱恋,进而利用自己的本土资源找到发展之路,这就是我们文化干预的内在诉求。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从联合国到中国农业部再到地方政府的一场自上而下的保护运动。作为一个学者,我很希望能借助这样一个机缘,给乡村注入一份力量。因此,2014年我组建了以本科生为主体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要在这里进行村落实验。为什么?作为大学老师,我一方面要在乡土实践中培养我的学生,另一方面也希望把我多年对乡村的理解转换成行动,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2014年6月,我试图带团队下乡之前,先带一个学生去村里踏查。在村里走访的时候我就想,与古枣园相伴的村落,它的历史文化积淀应该是很多的,遗憾的是,除了县志上的只言片语,这里没有任何有关村史村志的记载。我问村里有没有文化能人,大家都说当过大队长和小学校长的武国雄,当我满心欢喜打算拜望的时候,看到的是为他烧周年的儿子和老伴。那一刻我特别感触,乡村里一个人的离去带走的是几十年的生活记忆,与他相伴的往事从此就没有了!乡村是什么?中国的村落不是简简单单的屋舍和田园。乡村是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那是世世代代累积的,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沉淀的记忆和情感体系。因此,一个老人家走了,故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特别感慨的是——没有哪个老人等着你采访之后再赶赴黄泉。所以,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抢救记忆已经迫在眉睫了。
我们的田野工作就从这里开始。这个地方被称作“人市儿”,是老百姓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待的地方。这里有一个戏楼,大冬天的时候大家也在这儿站着,聊聊张家长,说说李家短。这是一个生起是非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平息是非的场所。据说这种传统由来久远,源头已无法考证。戏楼的后面都是连片的枣园,前面就是“人市儿”的核心。这个地方一开始很是陌生,后来人群里就有了我们,再后来我们就被拉回到他们家的窑洞里,坐在炕头上分享他们的故事。从此之后,这些老人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生存状态,我都清楚。像这样的人和事也因此和我们有了交集。
我们通过搜集老照片、老物件,通过口述的方式把父一辈、子一辈的往事统统留下,也因此让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庄有了自己定格的历史。口述史、文化志和影像集三本书[9-11],不是我和我学生的作品,而是我们和农民们共同整理的村落记忆。正是通过这种参与式的行动,我们的老百姓不再是遗产保护的旁观者,他们成了自身文化的讲述者,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往事转换成了把人、情、根留下来的集体记忆。这种社区感的回归正是村落凝聚和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也由此坚信,抗拒贫困、精准扶贫最根本的是精神上的扶贫,是扶人。改变人的生境,改变人的心境,才是乡村工作永不变更的主题。
2016年和2017年我们在那里开办了两期泥河沟大讲堂,不仅传播了农业遗产保护的理念,也让村民重新认识了自己家乡文化的价值。当在村的老年人舞起秧歌欢迎我们到来的时候,当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村观望的时候,我知道,“改变”已经悄然发生了。前不久的6月15日,我重返泥河沟,2018年的大讲堂开讲啦,尽管我们团队的学生都已毕业,但透过这一个人的大讲堂也让我看到,一个文弱的书生、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可以在这个时代里为落寞的乡村做一点事情。也许在你们的逻辑里乡村必然要死去,正如一个人的离去一样,但是让它能够有尊严地活过每一天,这是我们努力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守护的乡土,或许有一天真的会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彻底沦陷,但是无论怎样,在农耕文明几千年的最后时期,我为它守望过,我们也应该为拥有如此深度的情感体验而欣慰。如果中国农业大学在这个时候不能以此为业,还不能为乡村存留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那是一种罪过。
我们团队一起工作了三年多时间,在三个遗产地共驻村118天,其中在泥河沟村先后工作了65天。这段田野经历带给我和学生们的心灵体验非常丰厚,让我们对自己、对乡民的生命都有了新的认识。5月底,《中国慈善家》杂志的记者,在看了我们为泥河沟村老百姓所做的口述史之后发信告诉我,她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还生活在那里。她从中学开始住校,也曾一度厌恨家乡的贫穷、闭塞和压迫,也因此在情感上始终与故乡割裂。她很羡慕那些因我们而留有故事的村民,如果她的爷爷奶奶辈,那些不被重视的庶民,也能有这样讲述的机会,好像他们的一生也被温柔对待过了。看了她长长的微信,真的令我特别伤感,活一辈子,又有多少生命被温柔对待过呢!
四、告语青春:年轻学子的使命与作为
今天上午备课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刚刚离开的村庄——山东招远蚕庄镇山后冯家村。去年夏天,中国农业大学在那里建立了传统村落研究教授工作站,希望能够开启一个研究命题,在城市化发展快速的东部沿海地区,传统村落怎么保护?8月我还会到云南宁蒗的一个摩梭人居住区,去研究西南生态脆弱的干热河谷地区,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策略。也许有人会问,如此这般奔走于田野究竟想干什么?就是为了传递一份关注乡村的情感吗?不只如此,还想证明我对乡村的判断,想证明浪漫畅想和现实行动是可以在身体实践中高度统一的。前面提到的乡村教育实验,以及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扎根式研究,都想说明乡村的文化之魂尚在,因此,乡村复育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的乡土”,而是在行动中可以变成可触可感的现实。河南辉县的乡村社区大学,让我们看到了学校重新滋养乡民社会的希望。但有人质疑说,那里还有学校、有孩子、有年轻的妇女,因此让你看到了活力。那些没有学校、没有年轻人的乡村也有重生的可能吗?我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实验可以回应这个问题。陕北佳县的泥河沟村就是一个例证。我去调研之初,全村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158人中有111人是60岁以上的老人。也许有人会继续追问,这里的红枣毕竟是经济作物,管理树的成本与种植农作物的付出是大为不同的。尽管质疑者不知道当地人的生活状况,无法想象4毛钱一斤的红枣是难以维系村民基本生计需求的。我们权当这种追问是合理的,那么在以农为业的地区,在没有学校、缺乏年轻人的村落,是否就只能在落寞中等待一个结局呢?这也是我们走进内蒙古敖汉旗旱作农业区域和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的主要原因。应该说,在这些地域文化差异较大的地区,我都看到了乡土社会自身所蕴含的能量,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村落里都蕴含着自身的文化传统,都让我看到了诸多的可能性。作为旁观者,你可以有一百个理由质疑我们对乡村的梦想,但只需一个理由、一个个案便给了乡村振兴以重要的依据。路径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行动中!
十九大报告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你们是否意识到你们就是这“三农”工作队伍中重要的一极?如果没有这样的定位,你真的不应该来中国农业大学参加夏令营。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比任何时期都需要我们的年轻人为国家、为乡土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需要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仅有老师的迫切呼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师生需要情感的激荡,需要相互的砥砺,只有这样,才会给落寞的乡村带去希望。因此,跑乡村不是随机的,是有学术命题的,也是有行动指向的。只有在这个层面上,行动者才叫做研究者,田野之行才能和行动研究相提并论。
今日的乡村到底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又将在服务乡村的过程中获得什么?让我先来讲讲一代人的青春往事,再来讲讲此时我“身外的青春”。一周前我正在山后冯家村调研,有12位学生与我同行。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与这里1975年的知青见面,唤起他们的青春记忆,回望他们的乡村生活。我希望通过调动外部因素来启动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1975年8月29日到1977年12月17日,有16位青岛知青下乡到了山后冯家,他们的年龄在17至20岁之间,都是1955年至1958年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回城之后,有上大学的、有当工人的,而今都已年过花甲。而与我下田野的学生都是“95后”,他们曾抗拒驻村调研,但是在这里生活几天以后,从行为到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和当年的知青深度交流、畅谈之后,他们对田野工作和他们当下肩负着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我曾担心他们之间的“代沟”,却惊讶地发现,这些“50后”坐在“95后”的孩子们中间,欢悦的心情令他们手舞足蹈,好像他们又回到了18岁那一年。在他们的讲述中,40多年前的往事宛如正在上演,清晰得就在眼前。在他们激动的声音中,我听出了青春的旋律,在他们满眼的泪水中,我看到了年少的真情。与此同时,我也发现,曾经有几分刻板印象的“95后”竟然和“50后”同步潸然泪下,他们的交流好像没有年龄的代差,好像是一拨年轻人和另一拨年轻人的聚会。这样的情景看得我特别感动,也催促着我思考一个问题——回忆青春和正值青春差别在哪里?青春的激情和年少的童真何以持续?青春与青春相遇,他们永不变更的对话主题又是什么?
在村里的时候,我的学生被我称为“2018年知青”,他们和1975年知青在村里相遇,而且能在短时间内情感相互融通,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履历,都从17岁、18岁那一年走过。知青们讲1975年到村子后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们集体跑到望儿山上,向青岛方向高声大喊、跪倒哭泣的时候,我的学生早已泪眼模糊,因为想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当他们讲到老书记跑到海边给他们买大螃蟹做成蟹酱,为他们改善生活的时候,他们依然流泪不止,乡村带给年轻人的这份温暖从来都没有被遗忘过;当他们回忆起村里给他们做饭的王玉芳奶奶时,无不念起离村多年后他们集体为奶奶上坟,抱着坟头哭泣的场景。这些如在眼前的往事,就是他们的青春记忆,就是他们的乡村记忆。这份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让40多年前的岁月常在,也让青春不老。这是青春和青春相遇被激活的生命的力量。
在翻阅村庄档案和听知青讲述的过程中,我们分明会看到1975年在阡陌上劳作的青年。我的一个学生在乡村夜话分享调研感受时说:“老师拿着一卷档案向我们讲述了整理档案的逻辑思路,一个词紧紧的抓住了我的心——复活。我感觉到这件工作开始变得有些神圣起来,忍不住激动得热泪盈眶,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让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和存在过的人重现,心中不禁多了一份坚定与责任。……如果说阅读档案让复活的山后冯家有了血肉,那么和8位知青的访谈,让我触摸到了山后冯家的灵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知青愿意从青岛赶来协助口述史整理工作,为什么在谈及往昔时哽咽流泪,因为那是他们最宝贵的青春。也正是因为一份对过往的敬畏和感同身受的青春,才让他们有了跨越时空的畅快交流,才让40多年后的年轻人对前辈青春的交托有了一份郑重的承诺。那么,再过40年呢,或许会有一拨年轻人坐在“2018年知青”的面前,问询他们当年为乡村尽一份力量的心情,请他们讲述2018年山后冯家的青春故事。也许在这样的追问中,我们才能知晓年轻的生命从来没有间断过,一辈又一辈的青春在这个过程中接续着。因此,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才始终有希望,才始终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能量。
我的学生们说,40年后他们也已年过花甲。我说,日渐成熟继而走向衰老,这是无力抗争的事实。但是40年后你们却依然可以存留纯真的心态和青春的激情。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唯一的方法是让你们的灵魂生活变得有厚度,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始终保有一种能力,一种与前辈青春和后辈青春进行对话的能力。
在村里与学生交流时,我曾回忆起一种心情,两年前收听台湾文化学者蒋勋的演讲——“留十八分钟给自己”,那是他在中秋之夜的诵读。他为什么要讲这事儿?这人呐,一辈子被外力拉扯得不行,今天有多少人还能坐在这里安静地享受自己这生命里的十八分钟。有的人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睁眼一闭眼,一天就过去了。有的人感到时间过得慢,简直是度日如年。当这两种情形摆在那里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学生不要有度日如年之感,也不要有时间飘忽而过的忧叹。我想让你们做什么?留十八分钟给自己,让我们读诗。就像蒋勋所说,每天拿出十八分钟、每年拿出十八分钟来读诗,也许是奢侈的,但一生拿出十八分钟来读诗总还可以吧。可是,当我们退到这一步的时候你是否想到,对于那些身处战乱中的叙利亚人民来说,拥有十八分钟的诗句,生命的确是奢侈的!再来看看我们,生逢盛世,又正当青春,我们要做的不是拿出十八分钟读诗,而是努力让自己的生命本身成为诗,始终对生活、对生命充满积极的想象,这样青春就留住了。当你抱定这样一个信念开启人生之路的时候,即便50岁、60岁,抑或是古稀、耄耋之年,你依然不老,因为有青春为伴。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呼唤我们做什么?投入激情,服务社会,这是青春的旋律。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或许会问,中国社会如此庞大,我们的能力如此有限,我们能为社会做什么?2016年4月1日,我在贵州大学交流时,一位同行问我,“在你试图去寻求改变的田野工作中,当你的情感尽最大努力投入之后,仍然有人没有被感化怎么办?你期待的改变没有发生,自己感到难受吗?”我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我必须交代的事实是,不是每次田野都顺畅,那些令我们感动的瞬间不是生活的常态,但是做到疲倦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有这样一份感动,才让我们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2015年3月19日,温铁军老师在这个报告厅做题为“中国百年乡建——激进发展主义自毁与底层社会自救”演讲的时候,有人曾经质疑说:“今天搞乡村建设也不过就是在搞一个点,对整个中国有意义吗?”我觉得温老师回答得很精彩。他大致是说,我们回顾百年中国的乡建,会发现那些曾经有过乡建足迹的地方,它们经过了抗日战争、经过了内战,当如此大的灾难降临的时候,村民会自发组织起来,与那些没有过乡建的乡村相比,内发性的力量便会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点点滴滴工作最积极的社会效应。我曾经为我的田野失落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带着一份“把种子埋进土里”的希望,总是相信我们培育的种子,他年之后就会生根发芽,所以才走到了今天。
最后,我想和同学们说的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是一个思想者、一个行动者。从认识自我开始,才能“自立”,从行动起步,才能“立人”,才能促发改变,也就是说,在助人和立人过程中,我们才能获得一种自我存在的意义感,生命的底色才能会在悄然中发生变化。23年在乡村的田野工作,增进了我对乡土社会的理解,也让我对“有机地对待土地、有机地对待生活、有机地对待生命”,有了不断深化的认识。行动,构筑着我们生活理想,可以实现我们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蜕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期待改变的前提是我们个人生活的改变。
我特别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中国农业大学的夏令营,开启你们的乡村研究之旅,能在一次次赶赴田野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始终和别的人、和大社会有着神秘的链接。你的学术思考,你的社会行动,可以改变乡村的生活,可以提升乡民的生命质量。就让我们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个村庄开始,在实践中推动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我们却不能停止脚步。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执着的乡土眷恋者,我们不只在挽救乡村,我们更是在挽救我们自己,挽救我们的未来。2013年的12月7日,钱理群先生也是在这里做过一个演讲,他的结尾可能让我今生都难以忘记。他说作为一个践行者也许我们是孤独的,但请你不要希望去影响太多的人,就从改变我们自己开始,继而改变周遭,改变社会,实现悄悄的生命变革。
期待同学们也有勇气在自己的乡村研究中,体验这种生命变革的质感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