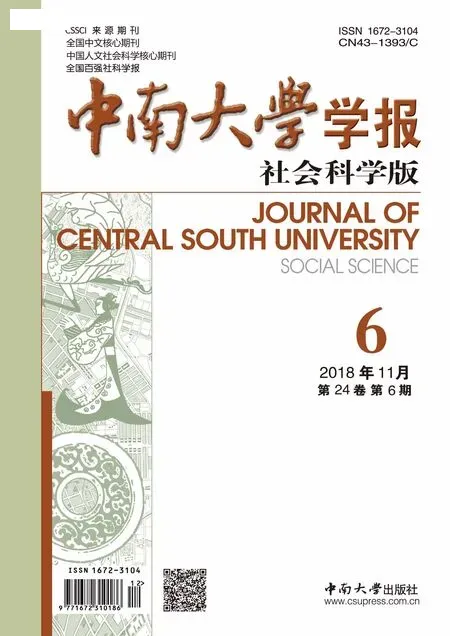R.S.托马斯的诗歌对转型焦虑的双重回应
2018-01-13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批评界已经注意到当代威尔士诗人R.S.托马斯(Ronald Stuart Thomas,1913—2000)诗歌中的焦虑,但是评论家或将这种焦虑归因于托马斯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忽视了这种焦虑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联;或者不明确焦虑的具体对象,而没有看到托马斯为化解焦虑所作出的努力。摩根(Christopher Morgan)认为R.S.托马斯诗歌中的焦虑主要是语言异化所导致的对“个人身份”的焦虑,以及对“英格兰化的文化”和“威尔士语文化”的认知所导致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并认为这种危机是托马斯诗歌创作的源泉[1](3-4)。尽管摩根意识到文化异化不是导致托马斯焦虑的唯一原因,但他明显忽视了这种焦虑与社会转型之间的重要关系。而且,将文化异化视为托马斯的诗歌的源泉,很容易导致读者误认为他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威尔士的食人魔”这种公众形象便是佐证[2](69)。更糟糕的是,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认为“R.S.托马斯的诗歌尽管表现了他在荒凉的威尔士田野和山区的焦虑,但最终是一种逃离与自然世界和现代世界的复杂关系的田园避世主义”[3](76)。吉福德做出这种有失偏颇的定论,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托马斯焦虑的具体对象,因此未能看到他的诗歌为化解这种焦虑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笔者认为,R.S.托马斯诗歌中的焦虑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对社会转型的焦虑,或者说是对现代性的焦虑,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所引起的焦虑。托马斯诗歌创作的基本历史语境和关注焦点即是现代化进程不断蚕食威尔士乡村,对这种社会转型的焦虑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另一个源泉。在自传体诗集《回声慢慢》(The Echoes Return Slow)中,托马斯写道:“在一个消解一切/的世界中,有哪些确定性/给自我。”①[4](28-29)这几行诗可以说是马克思(Karl Marx)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现代性的经典描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诗歌旁注。托马斯的焦虑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焦虑[5](111)。现代性的特征是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用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话来说,身处现代就是置身于一种“威胁着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熟悉的一切和所成为的一切”的环境中[6](15)。当传统的“可知社群”②以及其中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熟悉的经验都变得变动不居和陌生的时候,异化感、碎片感和焦虑感便侵袭而来。
殷企平先生曾指出:“就过去三百多年的人类社会而言,文化诞生于焦虑:社会转型引起的焦虑,或者说机械文明引起的焦虑……我们强调文化是对于社会转型的焦虑时,同时也暗示了文化的功能,即化解这种焦虑的功能。”[7](6-9)R.S.托马斯的诗歌完美地体现了这一文化命题,他的诗歌既是转型焦虑的产物,又是对焦虑的回应。本文旨在分析托马斯诗歌中的转型焦虑及其回应焦虑的策略,以期深入理解托马斯诗歌的缘起及其积极为人类构建理想社会的努力,并帮助揭去一些批评家强加在他身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逃避主义者”的标签。
一、社会转型:托马斯的焦虑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来都是英国文人深感焦虑的重要原因,也是英国文学浓墨重彩的领域。虽然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但是乡村作为一种“根本的生活方式”却在英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8](1)。“很多评论家认为英格兰-英国文化中的主导情感是反城市的,英格兰-英国民族身份的力量的真正源泉在乡村。”[9](55)这种乡村情结反映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便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及其相关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焦虑和质疑。
在R.S.托马斯看来,乡村是民族的根本,“一个国家的健康和财富取决于拥有强健、繁荣的农民”[10](23)。因此,他对社会转型持批判态度。在自传《无名小卒》(No-one)中,他写道:“R.S.将工业革命视为威尔士的主要灾难。”[11](98)通常认为,1942年托马斯来到蒙哥马利郡的莫那文村庄之后,他开始感受到现代性的威胁。这一时期正值工业革命的影响波及威尔士偏远山区之际,在这里,他“意识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看到]威尔士人背叛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去往威尔士浦、奥斯沃斯特里和什鲁斯伯里经商”[11](11)。1950年托马斯目睹“第一辆拖拉机开进莫那文”之后,他与“机器”的矛盾便开始升级[12](133)。托马斯前期的诗歌(1946—1968)主要包括《田间石头》(The Stones of the Field)、《一亩地》(An Acre of Land)、《岁末之歌》(Song at the Year’s Turning)、《稗草》(Tares)和《真理面包》(The Bread of Truth),这几部诗集集中描写了转型中的威尔士山村及农民的生活,充满了对工业化和旅游业的 焦虑。
首先,让托马斯深感焦虑的是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导致威尔士人口向工业城镇频繁流动,乡村共同体不断瓦解。托马斯在莫那文(1942—1954)担任乡村牧师期间,目睹了乡村的衰败。当他在山区散步的时候,他发现“当时威尔士高地地区残垣、荒村随处可见”[10](18),大量房舍被遗弃、年久失修,“门下的窟窿/是一张嘴,粗暴的风通过它发话/更凶更狠”(《山区人口减少》,Depopulation of the Hills)[13](62)。据《威尔士历史:1906—2000》(A History of Wales: 1906—2000)记载,20世纪威尔士经历了乡村人口的持续减少。在19世纪初,威尔士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到了 1911年左右,只剩不到 2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自19世纪开始,采矿业和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威尔士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在威尔士经济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工商业的繁荣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和相对较高的工资吸引着大批农村劳动力离开乡村,到城市和威尔士南部矿区谋生,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不断减少。此外,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导致了小型农场的终结,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在 1959年,威尔士每20英亩的耕地就有一辆拖拉机……1942年到 1960年之间,威尔士的拖拉机的数量增长了 6倍”,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14](145)。面对不断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威尔士农民对传统的背弃,托马斯深感焦虑和不安,呼吁“必须想办法让那些离开这片土地的人回来”[10](24)。
其次,R.S.托马斯倍感焦虑的是旅游业对威尔士乡村共同体的破坏。二战后,英国大众旅游迅速发展,威尔士乡村受到英格兰城市中产阶级游客的青睐,开启了向旅游胜地的转型之路,“1948年10月27日首个全国性的旅游组织在威尔士成立”[15](159)。威尔士乡村旅游的大力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威尔士作为英国的一个地域和“内部殖民地”③的双重身份推动的。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地域往往被视为低于大都市中心的文化标准;在殖民征服中,殖民地往往被认为劣于殖民者的现代性模式。在怀旧的英格兰城市中产阶级眼里,威尔士成为前现代社会的代表,威尔士乡村因此被视为治疗都市现代性痼疾的药方,成为英格兰城市居民的游乐空间。
旅游业导致很多乡村共同体被转化成旅游业的基础设施,迫使很多本地居民背井离乡,共同体遭受重创。R.S.托马斯对旅游业的发展深恶痛绝,得知桑德斯·刘易斯(Saunders Lewis)等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纵火烧毁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乡村的度假别墅,托马斯在采访中公开表示支持。在诗歌《陌生人》(Strangers)中,语者愤慨地谴责这些陌生游客的罪行,“我们不喜欢你们的白色小屋。/我们不喜欢你们的生活方式。/那些乡民罪孽较轻,他们/穿着你们不要的绿色罩衣。/他们骄傲地走了”[13](295)。作为英格兰的第一个殖民地,威尔士在1536年被兼并之后,便一直遭受英格兰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面对这些富裕的英格兰中产阶级带来的压力,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威尔士农民被迫离开乡村地区。内德·托马斯(Ned Thomas)也谈到了英格兰人购买威尔士度假别墅对威尔士共同体的破坏,“度假别墅的购买者将当地年轻的夫妇挤出了市场”[16](14)。
糟糕的是,旅游业在破坏传统共同体的同时并不会推动新的共同体的形成,涌入的游客并不是威尔士地方共同体的积极参与者。因为这种乡村旅游没有建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积极联系,而是在不触动现行体制的基础上对过去进行补偿性怀旧,以补偿现在的失落感。这种补偿性怀旧将乡村变成了城市的游乐场。对于城市游客来说,乡村并不是他们的家园,而只是文化怀旧市场上的另一种消费品。游客最终会离开乡村这个游乐空间,回到城市,威尔士的这种夏季旅游业导致乡村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空荡荡的。
二、反田园:转型焦虑的另类回应
面对以工业化和旅游业为代表的现代性引发的焦虑,在前期的诗歌创作中,R.S.托马斯选择了反田园书写④这种“另类”的方式来回应。所谓另类,是就它不同于传统的回应方式而言。在英国文学传统中,文人骚客往往以浪漫的乡村牧歌来应对转型焦虑,田园神话提供了一种历史连续性和共同体的幻象,成为转型焦虑的安慰剂。然而,这种理想化和浪漫化导致了乡村的去政治化,最终是种逃避主义,因此遭到了不少批评家的批判。特里·吉福德认为:“田园景象对自然的颂扬太过简单化,因此是对乡村生活现实的理想化。”[3](2)R.S.托马斯也辛辣地讽刺田园牧歌:“这样的意象/是供纯粹的臆想/玩赏的。看着威尔士/如今的遭遇,我宁肯/就事论事。”(《看羊》,Looking at Sheep)[13](317)这种意象不仅歪曲了民族历史,而且迎合了英格兰人对威尔士的刻板印象。因此,面对社会转型的压力,托马斯并没有诉诸田园神话,而是以现实主义的反田园书写直面威尔士乡村生活的凄苦、农事劳作的艰辛与乡村风景的暗淡。
笔者认为,R.S.托马斯的反田园书写是对威尔士乡村的再政治化,表达了他积极干预工业化和旅游业的政治诉求与现实关怀。首先,托马斯以反田园的笔调将以“伊阿古·普利瑟赫”(Iago Prytherch)为代表的、在穷山恶水的山区环境中艰难求生的威尔士农民打造成民族英雄来达到抵制工业化的目的。在这一系列诗歌中,贫瘠不堪的土壤、“被土地的艰难/剥夺了爱、思想和体面”(《那个山民说》,The Hill Farmer Speaks)的农夫等非人化的图景占据了威尔士乡村生活的前景[13](67)。乔纳森·阿利森(Jonathan Allison)指出:“如果田园暗示乡村生活的自由自在,那么反田园则宣称乡村生活是牢笼,农民像奴隶一般劳作。”[17](42)托马斯的反田园书写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乡村生活的艰辛,而是通过展现乡村生活的艰辛来反衬普利瑟赫这样的威尔士农民的坚毅品质——在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仍然坚守在乡村——为威尔士民族提供榜样,告诫他们,坚守威尔士的乡村传统比物质追求更重要,从而最终达到抵制英格兰的工业化殖民的目的。在诗歌《一位农民》(A Peasant)中,语者对威尔士人说道:
这就是你的原型,他,一季又一季,
与雨的围攻抗衡,与风的消耗战对峙,
保卫他的种群,一座坚固的堡垒
即便在死亡的混乱中也牢不可破。
记住他吧,因为他也是战争的胜利者,
奇妙的星空下不朽如一棵树[13](20)。
R.S.托马斯认为,普利瑟赫这类农民是威尔士人的“原型”和榜样。他坚定地“站在古老的生活的一边”(《记录在案》,For the Record)[13](344),日复一日地在乱石密布的田间辛勤劳作,尽管“年复一年。母羊在挨饿/没有奶,因为没有新草/我也在挨饿”(《那个山民说》)[13](67),但是他仍然坚守在荒凉的威尔士山区,赢得了这场对抗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市场价值观的战争。这种坚毅的品质甚至超越了死亡。
托马斯对这种顽强不屈的威尔士农民的颂扬是一种旨在重塑当下社会的政治策略。对于英格兰霸权文化对威尔士的工业化殖民,托马斯除了直接批判英格兰之外,更多的是谴责威尔士人自己民族意识的淡薄。他认为尽管是英格兰造成了威尔士工业化的扩张和乡村的瓦解,但是威尔士自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不抵抗主义(pacifism)的“萎谢之族”(《威尔士风光》,Welsh Landscape)[13](81)。对于捍卫自己的民族传统,他们并不积极,反而像诗歌《拖拉机上的辛迪兰》(Cynddylan on a Tractor)中的同名主人公一样,欣然接受工业化的入侵,充当了威尔士现代化进程的帮凶。这让托马斯非常气愤,在诗歌《小调》(Minor)中,他质问威尔士的不抵抗主义,“我们从容和平地(pacifically)/走向自己的毁灭?”[13](793)面对威尔士民族的麻木和忘本,托马斯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普利瑟赫这种坚守威尔士乡村传统的农民身上,认为他如果能够“据大地的法则/定下你的生活和信念,那么你当是/那个新社会的第一人”(《伊阿古·普利瑟赫》,Iago Prytherch)[13](37)。这个“新社会”或许就是托马斯后半生一直在寻找的威尔士乌托邦“阿布酷歌”(Abercuawg)。
其次,R.S.托马斯通过对威尔士乡村风景的反田园书写来抵制旅游业的侵蚀。在旅游业的符号生产中,作为现代性的他者的威尔士乡村的自然风光成为一个如画的、没有所指的能指,供文化消费。托马斯试图以反田园书写的手法来阻止旅游业的发展,其意图在诗歌《威尔士山乡》(The Welsh Hill Country)中表现得最为明确,语者讽刺那些带着浪漫主义先入之见的游客:
太远了,你们看不见
吸虫、腐蹄病和肥蛆
噬食着细骨上的皮。
羊群在法德文隘口吃草,
像往常一样浪漫地排布在
荒凉的石头背景上[13](51)。
这几行诗充当了反观光指南,谁会愿意在一个布满“吸虫、腐蹄病和肥蛆”的地方旅游?如诗中“你们看不见”“像往常一样”和“浪漫”所示,诗人采用反田园书写,一方面是为了解构旅游指南中广泛流通的关于威尔士乡村风光的商品化的、非真实的“类像”⑤,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讽刺英国文学经典中关于威尔士的浪漫主义的陈词滥调,达到抵制文学旅游(literary tourism)的目的。
威尔士乡村旅游业的繁荣,除了旅游业对游客需求的迎合之外,浪漫主义文学的推波助澜也不可忽视。韦恩·托马斯(Wynn Thomas)指出:“要了解威尔士,只需看它的风景——经典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殖民主义表征是将威尔士描述为缺乏本土文化趣味,仅仅因其风景而变得宝贵的国家。”[18](40)它们将威尔士再现成一个充满异域风情、风景如画的景区,以满足资产阶级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心理。关于异域的文学构成了一种虚拟旅游,而它一旦招来读者,就会促进真正的旅游。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指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19](55)浪漫主义文学和艺术便是文学旅游的典型例子: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雪莱(P.B.Shelley)的诗歌、透纳(J.M.W.Turner)的绘画、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的哥特小说、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以及其他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对威尔士乡村及其周围的河流、山脉等自然景观(如丁登寺、雪墩山等)的浪漫主义再现,将这些地方变成了英格兰读者想要到此一游的风景名胜,在威尔士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华兹华斯的名诗《丁登寺》就将这个地方及其周围的自然景观变成了闻名全英国的旅游胜地。“到1813年,到威尔士和苏格兰乡村或者湖畔地区欣赏自然风景的旅行就成为英国上层阶级文化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很难相信,大约50年前这些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20](102)随着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化,这种文学旅游推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兼游客来到威尔士。R.S.托马斯试图通过反田园书写来解构旅游业和文学话语中关于威尔士的刻板形象,从而阻止旅游业的发展对威尔士乡村的进一步破坏。
三、“阿布酷歌”:另类的乌托邦愿景
R.S.托马斯的诗歌对转型焦虑的回应经历了从积极干预现实的反田园书写到看似带有避世冲动的乌托邦憧憬的转变,这是他对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威尔士的文化、政治和环境状况的幻灭感使然。据《威尔士历史:1906—2000》记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威尔士的机械化程度达到历史新高,在用拖拉机的数量急剧增长,甚至超过了农民的数量。而且,由于汽车的大众化,游客的足迹越来越触及人迹罕至之地。托马斯在自传小说《无名小卒》中写道:“以前,利恩半岛对他来说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但是当他1967年调任此地一个偏僻的海滨村庄阿伯达伦时,他发现这里“夏天游客人满为患”,冬天街灯遮蔽了星辰与大海,“以至于乡村腹地的美丽和天然的孤寂荡然无存”[11](99)。乡村如今到处都是拖拉机、电视机和游客的汽车,民族英雄普利瑟赫最终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在1972年的一封信中,托马斯坦言他不知道如何将古老生活方式的残余同“电视天线和阿伯达伦旅游业廉价的小玩意协调起来,并以现代诗来书写它”[12](241)。面对这个没有灵魂的机械世界,托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诗歌中逐渐抛弃了对宏大历史现实的关注,转向寻找“我想象中的真正的威尔士”——“阿布酷歌” ——来化解焦虑[11](10)。表面看来,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是托马斯无力应对现代世界复杂性的隐退倾向的表现。实则不然,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作为一种非传统的、另类的愿景,“阿布酷歌”并不是一种逃避主义的冲动,而是另一种介入现实的策略,并且比反田园书写更具颠覆性和建设性。
R.S.托马斯的“阿布酷歌”愿景扎根于威尔士的文学传统,这个名称源自9世纪的一首威尔士诗歌《阿布酷歌的病人》(Claf Abercuawg)所描述的一个有布谷鸟歌唱的地方。托马斯在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的散文《美丽的威尔士》(Beautiful Wales)中读到这首诗时感触颇深,感觉“在阿布酷歌,布谷鸟在歌唱”这类诗句“在他耳朵里和心中如铃声般永久回荡”[10](164)。在1976年威尔士“民族诗歌音乐艺术节”上做题为“阿布酷歌”的演讲(后来转成散文)时,托马斯使用了这个典故。他将“阿布酷歌”描述为一个未受现代性污染的乡村乌托邦,“无论阿布酷歌会是什么样子,它都是绿树成荫,花团锦簇,阡陌交通,清溪碧流,布谷欢唱。我愿意为这个地方做出牺牲,甚至放弃生命”[10](158)。从“阿布酷哥”愿景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让R.S.托马斯焦虑的并不是威尔士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殖民问题,而是其现代性状况。因为他认为即便威尔士人“为他们所生活的技术和塑料时代的每一项发明创造都杜撰了一个威尔士单词”,这个现代化的威尔士都不是“一个值得去创造、值得为之做出牺牲的地方”[10](158)。
R.S.托马斯承认,《阿布酷歌的病人》启发了他在威尔士乡村寻找这个地方。经历了40年之久的离群索居、不断深入威尔士边远山区的牧师生涯后,托马斯于1978年退休后来到了威尔士最荒凉、最偏僻、最西端的地区,隐居在位于利恩半岛的萨恩山庄的一个拥有400年历史的村舍中。然而,很快他被迫面对梦想的破灭,即便是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也不是“阿布酷歌”。他在散文中写道:“没有听到布谷鸟的歌声,尽管有其他鸟在那里歌唱。但是阿布酷歌在哪呢?……我已经到达了但是尚未找到它。”[10](164)现代性的触角已经遍及威尔士的每一个角落,即便是穷乡僻壤也早已打上了资本主义、殖民征服与旅游业的烙印。在诗歌《阿布酷歌》中,托马斯再次发出叹惜:
阿布酷歌!在哪?
阿布酷歌在哪,在那个
有布谷鸟唱歌的地方?
我问那些教授。
喏!在这,喏!在那;
……
我
看着河水的表面,
但是我要寻找的地方
并未映现在那[13](691)。
梦想破灭后,托马斯的“阿布酷哥”变成了一些批评家所说的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欲望对象”[21](25)。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阿布酷哥”的缺席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策略。在诗歌的后半部分,他写道:
缺席让我们更加确定
我们需要什么。阿布酷歌
现在不在这,而在那,而且
那是一个不可界定的点
……
我是个寻觅者,
在时间里寻找
超越时间的东西。它无处不在
又无处可寻;之前不多于
之后,然而总是
即将存在[13](692-693)。
可见,“阿布酷哥”是一个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的空间,定位在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所说的“之外”(beyond)领域。它彰显的是与主导的英格兰工业文化的差异,占据的是阈限空间,位于英格兰霸权文化和威尔士弱势文化的间隙处⑥。借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作为“之外”的“阿布酷哥”,“表示空间距离,标志着进步,许诺未来;但如果不回到‘当下’,我们超越障碍或界线——即到“之外”的行动(going beyond)——的暗示便是不可知的、不可再现的”[22](5-6)。也就是说,“阿布酷哥”试图超越当下,超越以工业化和旅游业为主导的殖民现实,但是又与现实难分难解,作为英格兰霸权体制内的一个他者,不断动摇其稳定性。因此,“阿布酷哥”并不是处在遥远的时空中,而是当下的一股颠覆性的政治力量。
R.S.托马斯将“阿布酷哥”视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缺席”和“无处可寻”(nowhere),这种乌托邦思想与最近的乌托邦研究话语不谋而合。出于对传统意义上“乌托邦”概念所隐含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或者避世主义冲动”等负面含义的不满,最近很多关注空间的理论家对乌托邦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以重新思考乌托邦政治。乌托邦一词原本是由两个希腊词汇eu-topia和ou-topia合成,前者指“美好的地方”,后者指“乌有之地”(nowhere)。之前的理论家赋予“乌有之地”纯粹消极的含义——脱离现实、纯粹的臆想。然而,在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看来,这种“缺席”和“乌有之地”赋予了乌托邦独特的政治力量。他认为,城市中的“漫步行为是一次宏大的剥夺地点的社会经历”,但正是这种“乌有之地或梦想之地”的持续创造使得我们能够抵抗总体化的城市生活[23](180-181)。马林(Louis Marin)也认为乌托邦不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而是一个“处于地方之外的空间”,一个“他者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介于历史和地理之间的、缺乏地方的居间空间”[24](57)。简言之,这些理论都认为乌托邦所包含的“乌有之地”并不是纯粹的臆想,而是在当前社会结构内部创造“他性”(otherness)。这种“他性”意味着它实际上就在日常空间和实践领域的内部,类似于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异托邦”(heterotopia),“他性”既处于主导空间秩序的内部,又对其进行抵抗,是一种反霸权力量。
R.S.托马斯的“阿布酷哥”标志着与传统乌托邦愿景决裂、寻找另类乌托邦的冲动。尽管“阿布酷哥”保留了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所隐含的“更好的社会”这层意思,但是它不是将这个社会定位在脱离现实生活的遥远时空中,而是将其定位在日常空间中。托马斯认为,“阿布酷哥”必须从不断“干预当代的发展”这种意义上来设想,并且“是一个不断生成的事物,而不是一个一劳永逸地被冻结的事物”[10](131-132)。这说明乌托邦是一个位于现存秩序内部的、具有颠覆性的“他者空间”,以及马林所说的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过程”[25](417),而不是一个遥不可及、静止的理想世界。换言之,“阿布酷歌”是一个从当下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间隙中诞生出来的他者空间,在当前社会结构内部不断生成。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阿布酷哥”挑战了空间秩序的意识形态僵化,瓦解了总体化的工业体系的稳定性。
“阿布酷哥”不仅是托马斯个人和威尔士人的乌托邦,而且是整个现代世界的乌托邦。托马斯试图通过威尔士乌托邦来最终拯救“发生在英格兰的过度工业化以及如此之多的西方国家正奔向的无底深渊”,以确保“布谷鸟永远不会在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文明的丑陋不堪的高压线铁塔上歌唱”[10](174-180)。从反田园书写到“阿布酷歌”愿景,托马斯对威尔士的社会转型的关怀拓展到了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关怀。
四、结语
R.S.托马斯的诗歌既是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焦虑的产物,又对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贯穿其回应转型焦虑转变的主线是积极介入现实的情怀。作为对转型焦虑的另类回应,反田园书写体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将威尔士乡村政治化的策略,不仅颠覆了英格兰人对威尔士的刻板印象,建构了具有民族特性的乡村意象,而且表达了他抵制工业化和旅游业的政治诉求。与传统田园诗对乡村的去政治化和逃避主义冲动相比,托马斯的反田园书写的现实关怀更强烈。“阿布酷歌”作为一种化解焦虑的愿景,不仅延续了反田园书写的现实关怀,而且比前者更具颠覆性和建设性,并将这种关怀从威尔士拓展到整个现代世界。不同于处在遥远时空的、逃避主义的传统乌托邦,“阿布酷歌”就在日常空间中,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以其“他性”从内部不断颠覆工业资本主义体系,推动现代世界走向理想社会。因此,托马斯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逃避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文化批评家。
注释:
① 本文采用程佳的译本,个别地方译文略有改动。
② “可知社群”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完整的社群、完全可知的社群。
③ 关于威尔士作为内部殖民地这一说法,参见 Michael Hechter.Internal Colonialism: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1536-1966.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④ 田园诗(pastoral)和反田园诗(anti-pastoral)书写是就诗歌的内容和态度而言。通常来说,田园诗采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表征,美化乡村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反田园诗则采用现实主义的表征,承认乡村生活与自然环境的不理想的方面。当然,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互关联的,一些批评家甚至认为田园诗包括了反田园诗,反田园诗仅仅是田园诗的一个版本而已。
⑤ “类像”(simulacrum)是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用以分析后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术语,指的是后现代文化中广泛复制的、极度真实但是却没有任何本源和所指的图像或符号。
⑥ 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中,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和间隙(interstice)指的是一种过渡的、居间的状态和空间,充满着不确定性、矛盾性和杂糅性,具有颠覆和变革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