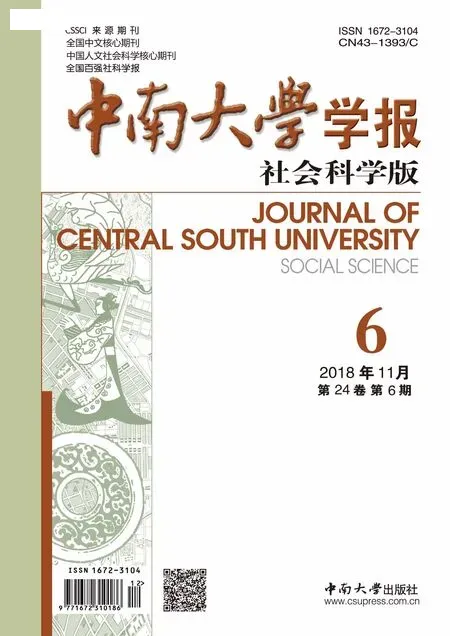论狄更斯“文学伦敦”中的街道美学
2018-01-13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齐名的伟大作家,从第一部作品《博兹特写集》(1836)问世伊始,其创作就备受评论界的关注。180多年来,虽然在西方关于狄更斯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迄今为止却鲜见以狄更斯的街道美学为论旨的文章。中国百年狄更斯研究的精神谱系是从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狄更斯是中国狄更斯研究的主流声音,也没有学者从街道美学的角度发掘狄更斯城市小说的现代性。狄更斯不是理论家,没有提出有关街道的美学理论,但是他用诗性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街道美学,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独特的街道美学。本文拟对狄更斯用生命创造的街道美学作一初步探讨。
一、“文学伦敦”:狄更斯街道经验的审美创造
文学空间是一种想象的建构,一个融汇着作者想象、文本描述和读者还原的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狄更斯在精细观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文学想象将 19世纪的都市伦敦建构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创造了“文学伦敦”。由于狄更斯熟悉伦敦的底细,因而他形象地写出了伦敦都市的真正蕴含,即这个世界以极大的人类苦难为代价而维持着,现实与非现实,物质与精神,具象与想象、世俗与超验的关系缺乏稳定性,并且只存在于虚构世界之中。狄更斯捕捉到了英国人的灵魂,“既有忧郁的沉思又有粗俗的幽默,既有诗情又有无畏,既义愤填膺又悲天悯人,既辛辣讽刺又自惭形秽……在关心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充满对超验世界的愿景念念不忘”[1]。
狄更斯的都市经验是伦敦街道的经验。对于狄更斯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九岁时最大的快乐来源于由罪恶、贫穷和乞讨所构成的“光怪陆离”的街道景观。12岁那年狄更斯被送到黑鞋油作坊当童工,这段经历在他的一生中总是挥之不去,以至于他从小就沉缅于街道闲逛。伦敦的修道院花园、泰晤士河、阿斯特利、格林威治博览会、沃克斯霍尔花园等地方尤其让狄更斯着迷。这些景观对于一个体弱多病、个子矮小、过于敏感的孩子来说,是可怕的,却又有着不可名状的吸引力。狄更斯总共只上了四年学,“没有哪个作家比狄更斯接受更少的教育了……他的大学是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警察局、法庭、报社办公室、议会新闻记者团,尤其是伦敦的街道。”①狄更斯的足迹踏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及其偏僻的郊区,他在伦敦街道的贫民窟里接受自己的大学教育。
童年时期在黑鞋油作坊的痛苦经历,一直萦绕于狄更斯的心头,可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童年经验的再现。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他借主人公之口回忆说:“我来到那安静的街道,那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是一本童年读过的书。”[2]第一部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萨姆·韦勒像狄更斯一样虽然出生于农村,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度过的,在他身上体现出伦敦佬的特点。他在伦敦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儿,做过货车夫的学徒,赶过大车,当过投递员和服务员,他熟悉桥下的拱道和小客栈。
“文学伦敦”是一个街道迷宫,迷宫意象是“文学伦敦”的显著特点之一。在《小杜丽》中,兜三绕四部、办公室、走廊、层次不等的官方当局等像迷宫一般纠结在一起。亚瑟·克莱南、丹尼尔·多伊斯等人物绝望地在兜三绕四部徘徊,填写难以数计的表格,起诉一个又一个讼案,却从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兜三绕四部是迷宫似的监狱,却成了政府的机构。
读者在狄更斯的街道迷宫中可以体验到潜藏于他心中的焦虑,如《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托杰斯公寓,“你在巷子和小道、庭院和走廊摸索一个小时,也摸不到一条可以合情合理地称为街道的东西。当陌生人穿过迂回的迷宫,突然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烦意乱,认为自己肯定迷了路,出出进进,兜着圈子;走到一堵空白的墙壁前或者被铁栏杆迎面拦住了,再悄悄地转回来,并觉得走出迷宫的办法可能到时候自然会出现,但是预测是没有希望的”[3]。托杰斯公寓的迷宫就是伦敦,犹如伦敦的迷宫就是整个世界一样。因为读者不可能将肮脏的都市迷宫与焦煤镇密密麻麻的庭院和街道的迷宫加以区分,也不可能与准时尚的公园巷的“荒原”加以区分,公园巷摇摇欲坠的出租屋用柱子支撑着,看起来就像大宅第近亲繁殖的最后结果。读者还可以在无以数计的修道院的室内体验到这种焦虑,在俾克史涅夫小姐们的房子里,读者可以看到两英尺之外的褐色的墙壁,墙壁的顶部有黑色的蓄水池,乔纳斯·朱述尔维特的污迹斑斑的发霉的房子像一个墓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赫克萨姆老头的小窝涂抹着红铅,到处是潮气,外观腐烂不堪。在《荒凉山庄》中斯墨尔维德爷爷的黑暗的小客厅比街道低好几英尺,这种黑暗、潮湿的内室无异于坟墓。
在敏于观察的狄更斯眼中,“七街日晷”以错综复杂而著称,他从观察者的视角对它作了细腻的描写,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去注视它。“看看这儿的市街布局。戈尔狄俄斯之结还是老样子。当时的汉普顿宫里的迷宫也好,如今的比尤拉游乐胜地的迷宫也好,也都是老样子。那些白色硬领饰上的领结也是老样子,要把它套上脖子极为困难……那个陌生人还是第一次进入日晷,他像贝尔佐尼那样,站在七个阴暗的街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想把周围的一切看个足够,以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新奇和清醒之感。街道和短巷从他身陷其中的那个不整齐的方形广场朝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直到他们迷失在悬在屋顶上的不卫生的烟雾之中,从而使这一片肮脏的景色显得既模糊又有局限性。”[4]七街日晷是复杂的伦敦迷宫的缩影,它既让人感到困惑,又感到它的局限性。对于站在七条交汇街道轴线上的观察者来说,街道和短巷从他身陷其中的那个不整齐的方形广场朝四面八方延伸出去,在此,街道成了视觉的辐射线,一个接一个的辐射线将观察者的视线引向屋顶上的水汽。
对街道迷宫最熟悉的莫过于城市的侦探。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城市侦探成了重要的人物,他们可以在茫茫迷雾中找到路,可以洞悉错综复杂的伦敦街道。英国的现代侦探制度建立于1842年。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拿德盖特侦探披露了约那斯谋杀泰格的秘密。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探长布克特的形象。因为布克特比埃斯塔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能洞悉匿名而神秘的城市,获取它的各种秘密并利用这些信息除恶助善。埃斯塔陪同布克特在城市中上下求索,寻找戴德洛克夫人的下落,并非是叙事上的偶然。在这里,狄更斯运用两个叙述者来处理城市中的公共机构和个人,也同时利用两个人物来破译戴德洛克夫人的失踪之谜。狄更斯呈现了城市街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阅读他的小说可以激发我们探索城市的秘密。狄更斯的侦探故事影响到了福尔摩斯小说中的伦敦,在福尔摩斯的小说中,伦敦有着迷宫般的阴暗和阴森可怖的魔力。狄更斯对古老的伦敦的描写,犹如华兹华斯对湖畔乡村景观的描写,他从独特的角度将伦敦街道永远镌刻在人们的想象中。
二、闲逛者和拾垃圾者:伦敦街道的现代性主体
“文学伦敦”是狄更斯创造的现代性文学空间,以伦敦街道为家园的闲逛者和拾垃圾者是伦敦都市的现代性主体。
对城市现代性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在城市街头漫步的闲逛者。伦敦让狄更斯学会闲逛,闲逛激发起他的文学激情。狄更斯作为城市经验的经历者与表达者,天生就是个闲逛者。街道闲逛是狄更斯的灵感源泉。“他(指狄更斯——笔者注)常常在整个闹市区到处漫步:从塔山和阿德门水泵房、伦敦城西门到河滨大道。王宫院、白厅、皇家马队营、詹姆士公园、金十字路、皮卡迪利大街、帕尔林荫路和里真茨大街等地方他都常去。对沃克斯霍尔园、骑士桥、证券街,林肯法律协会广场就更熟悉了。有时他走得很远,从汉普顿王宫、里奇蒙路到格林威治,从旧肯特路一直到北郊汉普斯特德区和伊斯灵顿区。他经常在黎明时分看见醉醺醺的汉子跌跌撞撞地走回家去,看见女人们挎着一篮篮水果到柯芬园市场。有时过了半夜,他还到马什门和柯柏皇家戏院,去看那附近卖烤洋薯和猪肝馅饼的小贩收拾摊子。”[5]狄更斯常常深更半夜闲逛到最难以想象的穷街僻壤去寻求安宁。“今天是我称之为开始工作前的徘徊日。我似乎总是在这样的时间里寻找着未曾在生活中找到过的东西。这种东西也许几千年后能找到,而且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谁知道……我将去位于蛇麻草园和果园之间的坎特伯雷公路上徘徊求索。”[6]狄更斯着手写第二本圣诞节读物时,虽然他已经选定了主题,却仍然觉得很难动笔。“他怀念伦敦的街道,当《圣诞欢歌》在他脑中酝酿时,他常常兴奋得深夜在伦敦的街道上走来走去。”[5]
童年时期的闲逛经历成就了狄更斯终生不变的爱好。在城市漫步,迷失在那些狭窄的街道里,偶遇最奇异的鲜明对比,每到一处就有美丽、丑陋、宏伟、令人愉悦和惹人不快的事情跃入眼帘。即使在国外期间,狄更斯仍然要去城市的大街小巷闲逛。据狄更斯自己描述,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漫步到了医院、监狱、陈尸所、歌剧院、戏院、音乐厅、公墓、宫殿和酒店。显然,这是一幅充满艳丽和恐怖景象的“全景图”,这说明狄更斯眼中的世界多么富于戏剧性,欣赏这幅色彩鲜艳的全景图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之一。他尤其喜欢独自一人去巴黎的“陈尸所”。狄更斯常去这个地方,因为太平间让他进入到“既令他厌恶又让他入迷的状态”,他坦承“我让一股无形的力量拽进了太平间”[1]。狄更斯曾经用恐怖的语言描绘过这一场面:“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床,浸透了水而有些膨胀的衣服,水从衣服上滴下来,滴上一整天,那上面还有别的湿透而膨胀的东西堆在角落里,像一大堆过熟的无花果给压碎了。”[1]
闲逛者狄更斯创造了众多的闲逛者形象。在《奥立弗·退斯特》中,弃儿奥立弗午夜来到伦敦街道闲逛;在《圣诞欢歌》中,幽灵领着斯克掳奇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漫步。《此路不通》记叙了狄更斯儿童时期在伦敦迷路的场景。在《小杜丽》中,狄更斯描写了女主人公穿过伦敦荒原的闲逛情节:悲伤的夜行、沉重的脚步声、昏暗的街灯、湍急的潮水、忧郁的钟声、无家可归的行人等。在狄更斯的作品中闲逛者形象非常之多,再如《董贝父子》中的佛罗伦斯·董贝、《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老古玩店》中的烹弗莱师傅、《双城记》中的悉尼·卡尔敦,等等。
拾垃圾者是屹立在伦敦都市风景线上的又一现代性主体。“文学伦敦”存在着大量的拾垃圾者形象,如《荒凉山庄》中的废品店老板克鲁克。狄更斯这样描写他的废品店:“铺子门上方写着:克鲁克——碎布旧瓶收买店。还有几个细长的字写着:克鲁克——旧帆具收买店。橱窗的一角有一幅画,画着一个红色的造纸厂,造纸厂门口有一辆运货马车卸下一包包的碎布。橱窗的另一角,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骨头。另一个牌子写着:收买厨房用具。又一个牌子写着:收买旧铁器。还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废纸。更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男女估衣。这里似乎什么东西都收买,可是什么也不出售。橱窗里还摆满了黑鞋油瓶、药瓶、姜汗啤酒、苏打汽水瓶、酸菜瓶、酒瓶、墨水瓶……这铺子在某些小地方,有一种同法律搭界的气氛,它似乎是法律界的一个肮脏的食客或是脱离了关系的亲戚。”[7]由于克鲁克什么都收集,因此他的废品店无所不有。克鲁克成天在旧的法律文件中翻找,试图找到能让自己发财的东西。他靠法庭的废纸过活,在生命临终时,他发现敲诈是大有希望的投机,但令人震惊的是,克鲁克最终自燃了。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对“拾垃圾者”形象的描写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这部小说中既有弱势群体中的“拾垃圾者”,如在泰晤士河打捞尸体的赫克萨姆老头、胡赖·赖德胡德等;也有在上流社会中的“拾垃圾者”,如收购股票的商号老板弗莱吉贝,市场投机的暴发户维尼林先生。拾垃圾的金人儿鲍芬是老哈蒙的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以前在老哈蒙家做雇工。老哈蒙靠拾垃圾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垃圾山,并因此发了大财。老哈蒙死后,他的垃圾山交给了鲍芬,于是这座垃圾山成了大家觊觎的目标,成了伦敦人“发财的猎物”。在伦敦城,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看门人和清洁工甚至于在路旁的排水沟中翻捡垃圾,寻找着可以变成金钱的东西。投机者维尼林先生“不必有祖宗,不必有确定的性格,不必有教养,不必有思想,不必有礼貌,有股票就行”[8]。也就是说,在一个拜金主义社会,股票万能,只要有了股票就可以通吃天下,可以把一切踩在脚下,为所欲为。这些体面的拾垃圾者把贱若蛆虫的贫民作为吞噬的对象,并用贫民的肥膏来养肥自己。
波德莱尔的诗《拾垃圾者的酒》描述了醉酒者在稠密拥挤的人群中捡拾着“历史的垃圾”,其中的拾垃圾者就是城市中的诗人。在本雅明那里,拾垃圾者是采集闲话与社会现实的收藏者,他们从收藏品中将一件件物品抽离出来,又将它们放进由收藏家创造的历史体系或星丛结构中,并对它们进行研究,使之升华为“一部关于时代、地域、产业以及关于物品的所有者的全部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与叙事者相反,收藏家把看似不关联的事物关联起来,即是说,收藏家把那些事物放在相互关联的体系之中。”②本雅明将波德莱尔称作拾垃圾者,他捡拾着偶然的、瞬间的意象和碎片。狄更斯热衷于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闲逛,因为闲逛能够观察人生世相,洞悉世故人情。狄更斯的闲逛显然是在收集垃圾的碎片,他凭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把整个伦敦纳入他的象征框架,从而将自己变成一个“拾垃圾者”。狄更斯笔下“拾垃圾者”意象的象征意蕴远远超过波德莱尔的《拾垃圾者的酒》。
三、伦敦街道:狄更斯崛起的舞台
在狄更斯笔下,伦敦街道是一个剧场,想象的景观和现代生活的矛盾在那里表演和展示,因此,都市伦敦的街道是白手起家的人表演现代戏剧的舞台。伦敦如同幻灯片展示之地,使得狄更斯陶醉于其中,伦敦的街道成了他崛起的舞台。正是童年时期在黑鞋油作坊中经历的贫困和心灵的巨痛才激励狄更斯奋发图强,通过旅行、在欧洲大陆生活以及学习意大利语和法语,狄更斯弥补了曾经与他失之交臂的学校教育。通过努力拼搏狄更斯在 40岁时获得了一位作家期望通过写作所获得的一切:他的天才获得了普遍公认,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人们的盛宴欢迎;他的作品广受欢迎,他因此成了大富翁,拥有了钱能买到的一切。45岁那年,狄更斯买下了乡间别墅——盖茨山庄。狄更斯是一个街道奋斗者,其伟大天赋在于将个人的精神创伤转化为卓越的艺术形式。街道是打开秘密走廊走进狄更斯世界的钥匙。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G.K.杰斯特顿指出:“做完工,狄更斯没有别的去处,只有游逛,他走过了大半个伦敦。他从孩提时代就是个沉湎于幻想的人,他比任何人都要关心自己那不幸的命运……他在黑夜里站在霍尔登的街灯下,在十字路口感觉受着殉教般的痛苦……他去那儿并不是像一个迂腐学究那样要去观察什么,他并没有注意那十字路口是如何形成的,也没有去数霍尔登的街灯来练习算术……狄更斯没有把这些东西印在心上,然而他把心印在这些东西上。”[9]正是在伦敦的地下世界,狄更斯发现了乌托邦:“夜晚的街道是上了锁的大房子,但狄更斯却拥有街道的钥匙……他能打开这个房子的内室——其门口通往秘密的走廊,走廊的四周是房屋,屋顶有星星。”[9]
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总是回荡着伦敦街头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实质上是他那焦虑不安的心绪的表征。在《老古玩店》中回荡着闲逛者的脚步声,“那种经常的来回踱步,那种永无休止的坐卧不安,那种把粗糙的石块磨得油光发亮的持续不断的脚步”[10]。在《双城记》中回荡着幽灵般的脚步声:“那个角落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脚步的回声,有的似乎在窗下,有的似乎在屋里,时远时近,时强时弱,有的嘎然而止,有的最后停住。所有这些声音都发自那那遥远的街上,然而望过去却又空无一人。”[11]在《小杜丽》中,“听到一阵慌乱的喘气声和脚步声,随后潘克斯先生便冲进了亚瑟·克莱南的帐房间。”那神秘的沙沙声和颤抖声使爱芙莱感到害怕,“仿佛脚步声震动了地板,甚至仿佛一只可怕的手掌摸到了她身上”[12]。脚步声在发出警告,预示着布兰德瓦在独自挣脱自己的罪恶时,那蛀空的旧房子最后机缘巧合地崩塌,砸到他头上。
1853年的夏天,狄更斯表现出深深的不满和无法平息的焦虑,严重失眠。有一段时间,狄更斯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一样在街头漫步,如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一样,“越走越快,仿佛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抛在后面”[6]。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内心的紧迫感渐渐增大,驱使他去追求更大的成就,最终导致他的早逝。
本雅明认为,“对闲逛者来说,他的城市……已不再是家,它为他提供一个展示地”②。这一表述深刻地揭示了情不自禁的闲逛与艺术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本雅明将狄更斯和波德莱尔的闲逛以及对城市街道的描写视为对精神压抑的释放,这种情不自禁既使艺术家负担过重,同时又消耗其精力,因此艺术家往往不由自主地浪迹街头,导致了其创新潜力的迸发。这一点尤其适合于狄更斯。儿童时期的狄更斯被迫往返于令他恐怖的作坊之间,他将街道变成了内室,以至于熙熙攘攘的街道成了他的家。晚年时期的狄更斯不得不再度回到他一直认为具有潜在危险的伦敦大街,他不听劝告,违背常识,超负荷地在一个又一个演讲大厅,在一条又一条大街朗诵自己的小说,到 19世纪60年代这种公开朗读甚至到了令他着迷的程度。“狄更斯对新奇事物的渴求如此不可抗拒,唯一的办法是走上大街。对他来说,街道经验不仅仅是创造的契机,而且也是他回忆痛苦场景的契机。因此,他几乎无法摆脱过度生产的负荷,也不能摆脱时代的焦虑,他陷入了恶性循环:难以释怀的夜间闲逛和对艺术创新的着迷耗尽了他的精力,最后在公共阅读中过早结束了他的生命。”[13]
伦敦的街道是狄更斯崛起的舞台。伦敦不仅仅是狄更斯作为小说家成功的城市,也是他童年时期受到羞辱、青年失恋让他痛苦的地方。这两大精神创伤是狄更斯在伦敦不断拼搏的精神源泉,通过拼搏他从一个只上了两三年学的穷小子成为举世闻名的一代文学大师。伦敦作为世界上第一座现代都市,既吸引着狄更斯,也令他感到绝望。二者对于狄更斯的想象都不可或缺。狄更斯是伦敦的现代艺术家,他接过华兹华斯的成长主题,然后让农村的孩子演变为都市中的角色,《奥立弗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中的主人公等都是这一主题的诗性表述。狄更斯凭借一支笔,摆脱了穷困,狄更斯的一生是在伦敦街道个人奋斗打拼的奇迹。
四、结语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狄更斯不是理论家,但他以自己的生命创造了自己的街道美学,以诗性的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街道美学。在他的街道美学中,街道-闲逛者-拾垃圾者-视觉-都市空间-现代性等构成了六位一体的体系。
“文学伦敦”是狄更斯创造的文学空间,伦敦街道是其始终如一的主题,“文学伦敦”是一个街道交织的都市迷宫,迷宫意象是“文学伦敦”的显著特点之一。首先,街道广场是需要身体体验的都市空间。19世纪的伦敦街道已经成为都市居民主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伦敦的街道上展示着目迷五色的都市景观:拥挤不堪的贫民窟、沿街叫卖的商贩、匆匆的人群、潦倒落泊的文人、行乞的乞丐等。其次,街道作为都市空间的重要场域,是闲逛者和“拾垃圾者”的生活空间,二者无疑是伦敦街道的现代性主体,因此,街道成为表征伦敦现代性的主要意象。闲逛与儿童时期的体验有相似之处。作为迷宫的都市与人们对过去的记忆紧密相联,桑迪认为,“城市迷宫在空间中存在,所以记忆随时间发展,从已经走过的道路中寻找着未来的轨迹”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城市里的废旧物品越来越多,因为废旧物品具有特定的再使用的价值,因此,拾垃圾者也越来越多。狄更斯凭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把整个伦敦纳入他的象征框架,从而将自己变成一个“拾垃圾者”。最后,人们对都市空间的体验活动即是“闲逛”。 闲逛者穿过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各种通道、地铁出口、人山人海的广场、喧嚣的火车站等公共建筑,熟悉了迷宫般的都市生活经验。闲逛者用身体体验迷宫般的都市是一门“看的艺术”,本雅明指出:“闲逛者的视觉,收藏者的触觉。”[14]从时空维度来看,视觉,说到底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的,即视觉是时间的空间化。
从世界文学的维度来看,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城市意象居于支配地位。巴尔扎克再现了城市社会的错综复杂及其流动不息,其形象虽然复杂但却清晰。陀斯妥耶夫斯基强调城市的神秘怪诞和陌生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隔离,这与狄更斯颇为相似。他与狄更斯的不同在于,他的认识并非来源于社会给人造成的窒息感,而是来自一种精神上的认可,来源于孤立绝望的另一面。
狄更斯使得“街道文学”成为独特的文学样式,他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伦敦都市的日常生活,运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为读者呈现出迷宫般的伦敦街道,赋予伦敦街道以丰厚的美学蕴涵:街道是闲逛的场所和空间,闲逛是对街道的体验,闲逛是时间的空间化,是一种视觉打量。都市空间、闲逛、视觉都有着现代性的特质。
注释:
① WILLIAM J.Carlton.Charles Dickens,Shorthand Writer(1926),from Charles Dickens:Family History.Routledge/Thoemmes Press,1999:45.
② Walter Benjamin.The Arcade Project,from 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I),Cambridge,MA,1996:279,437.
③ SZONDI P.“Walter Benjamin’ City Portraits”,from On Walter Benjamin:Critical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G Smith,MIT Press,1988:1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