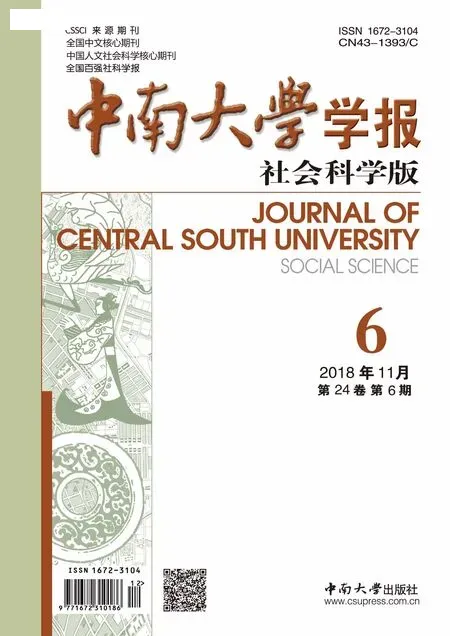论中国诗学中的事感说
2018-01-13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宇宙万物相感相应,世间万事相接相随。《朱子语类》云:“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如风来是感,树动便是应。”[1](1814)就诗歌而言,诗之所以产生与诗人的诗性感应有很大关系。“悲落叶于劲秋”是对物候的感应,“离群托诗以怨”则是对人事的感应。古往今来,贤人志士多致力于物感的研究,而相对忽略事感的开发。从中国诗学本土化、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不可否认,“人心所以动者,外物使之然”的物感说有很强的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但物感从根本上说是以事感或情感即人的感应为前提的。从广义上来说,物感之“物”亦可笺注为“事”,故“事物”多可以合称。黄宗羲就指出:“心感事而为物,感之之中,须委曲尽道,乃是格物。”[2](406)从逻辑发生的前提来说,事感是优于情感的。俗语“没有无缘无故的情”背后,其实就是以事感为基础的。陆时雍《诗镜总论》云:“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3](1404)深入发掘和研究事感,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诗学的传统,而且有助于中国诗歌多元的发展。
一、事感的史与论
事感是中国诗学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既有自己的历史风貌,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就历史渊源而言,事感是我国言事诗与缘事理论顺势发展的产物。从概念的角度看,事感较之于物感虽晚出,但从实际创作来看,触事感发的诗甚至要比物感之诗早得多。上古之时,火耕水耨,穴居野处,缘事感发,伏羲氏有网罟之歌,葛天氏有操牛尾之乐。东周列国“王事靡盬,我心伤悲”,诗多触事兴咏。秦汉已降,后世之诗即事兴怀者,亦多如牛毛。事感作为概念萌芽于汉代乐府诗兴盛之时。《汉书·艺文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学观念,可以说是事感的胚芽。及至六朝,钟嵘《诗品》在提出“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四候之感(物感)外,还提出了嘉会寄诗、离群托诗、楚臣去境、汉妾辞宫、解佩出朝、负戈外戍等感荡心灵的事感。伴随着前贤筚路蓝缕的开拓以及大量即事兴怀诗的涌现,“事感”这一概念终于在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孟棨的《本事诗》中被明确提出。“以事系诗”的《本事诗》共分七题,其中最重要的前两题就是“情感”和“事感”。孟棨《本事诗》自序云:“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4](3)据有关资料显示,七题各有小序,不幸的是,现已遗失。孟棨对事感的界定,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从事感在七题中的位置,我们可以揣摩到“事感”在孟棨心目中以及唐诗创作中的地位。自孟棨明确提出“事感”这一概念以来,事感就流行于诗歌创作与诗学的言说之中了。譬如宋代阮阅所撰《百家诗话总龟》,《前集》五十卷、分四十五门,其中就有“故事”“书事”“感事”和“用事”四大门类。
任何概念都有其外延的规定,也有内涵的框定。如果说事感概念在中国形成是中国诗歌创作对其外延历史演进的规定的话,那么事感为何能产生诗则是中国缘事诗学理论对其内涵的本质框定。事感概念形成的动力源于什么?又如何界定事感的本质?下面本文将从生存论的“事”和感知论的“感”这两个维度对事感加以分析和阐释。
第一,从生存论的角度看,事感是人类历事性生存的必然反应。众所周知,人是以一件事接一件事的方式生存的,人在事面前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有所感发的。这种感发不是人与物之间移情的浅表感发,而是人与事之间的深度感发。可以说,人对事的感发不仅是人类历事生存的本能反应,而且也是政治、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的文化反应。从诗产生的角度看,凡触事感发,形于诗赋者,古人皆称为事感。
“事”为何能感发人的意志呢?古人认为,一方面,事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我们无法摆脱事的袭扰。如《二程遗书》所说:“一事息,则一事生,中无间断。”[5](180)另一方面,心无尽无休地与事相遇着,心无所感绝无仅有。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说:“人心曾有一刻无事时?一刻无事是槁灭也,故时时必有事,……非可以有感而感论也。”[2](638)一言以蔽之,心与事是相互感发、相互磨砺的存在。人无事时,心寂然凝虑;人有事时,心则躁动不安。古人处事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无事之心,处有事之事。可以说,事是心性磨砺最好的试金石。黄宗羲指出:“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2](586)由此看来,王国维对“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的告诫,并非空言。
中国缘事诗学理论的事感概念是有着深刻的生存论基础的,这种基础就来源于人时时必有事,一刻无事是槁灭的事实。在中国古人看来,人需要在事上磨炼自己的心性,遇事应感而又安若无事是古人的最高追求。中国诗歌内蕴其事,却如水中着盐,就是源于事感的奥妙。白居易阅事渐深而用旷达之心感事,故其诗“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有旷达之美;孟郊阅事渐浅而用偏狭之心感事,故其诗“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则有偏狭之蔽。人都于事中生存,也都有所感,但与诗人相比,就没有那么机敏、深刻和诗性。
第二,从感知论的角度看,事感是人类自身感应的必然产物。在古人看来,天下万事万物,都有感通之理。凡有动则必有感,感则必有应。譬如“草上之风必偃”,风来是感,草偃是应。天地相感,万物化生。君臣相感,天下和平。物有相随,故有相感;人有耳目视听,故有感也必有应。程颢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5](198)
何谓感?感即动人心者也,物能动人心,事亦能动人心。如果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是物感的话,那么事之动人,缘事而发则是事感。按照朱熹的说法,感应有两层意思:一是“以感对应而言,则彼感而此应”;二是“专于感而言,则感又兼应意”[1](2438)。前者意在于:感与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互动。后者则意在于:心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有意向性的。对事感发要有历史感、诗意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有感有应的本能之上,而是要有心意审美的意向性和认知性。事感的美学高度就在于:事我两忘、异质同构、互渗互融的浑然之美。此如“思无邪,思马斯徂”,如果思马而马应,那么其思必无邪,其马必有疆。因此,创作出一首好的言事诗,不仅要求诗人在世事中磨砺而渐趋深刻、独到,而且也要求诗人对世事感发的角度独特、新颖。诗人与商贾、闾左的感事不同,诗人是用诗性的眼光看待事,用诗性的心胸来感应事。尽管诗发生的起点在于感,但并不是所有的感都能转化成诗。只有审美心胸加之“感又兼应意”,才能转化成诗。由此看来,事能否转换成诗,与事感的方式、角度以及人的心胸有关。可以说,事感对于诗尤其是言事诗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诗之为诗的第一步。
综上所言,事感作为诗歌发生的起点以及中国缘事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中国诗学的独创,它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演进轨迹,而且也有着生存论和感知论的理论基础。与西方模仿论的事感不同,中国的事感多指向事中的情,而西方的事感多指向事中事。一个强调“缘事以审情”,一个强调“事件的组合”。中国长篇叙事诗不发达以及言事诗的风格、形态多与事感的方式有关。
二、事感的类与质
事以感之,类以聚之。对事感分类,我们可以从事的类型着手,也可以从感的方式入手。就前者而言,由于事按时间先后可分为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三种,那么事感以此可分为:述事感思型、即事感怀型和托事感想型三类。就后者而言,由于感按感官不同可分为眼见为实的感和耳听八方的感,那么事感以此可分为:亲历的事感和途说的事感。
首先,依据事的类型不同,事感可分为述事感思型、即事感怀型和托事感想型三类。第一,述事感思型主要是对过去的事的一种感发方式。这种事感所述之事一般是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个人往事等已发生的事。譬如咏史诗、怀古诗多是这种类型。在中国古代,述过去之事更多地不是为了推演已发生的事,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以古来讽今。班固《咏史》之所以述“缇萦上书救父”之事,何尝不是自己身陷囹圄的感发;杜甫《蜀相》之所以讲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之事,何尝没有自己“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感触。中国古代这种事感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中国诗歌很难形成史诗的叙事结构。第二,即事感怀型主要是对现在即时发生的事的一种感发方式。这种事感所言之事一般是诗人所亲历的正在发生的事。杜甫逢禄山之难,颠沛陇蜀,以诗系事的“诗史”,可以说是这种事感的实践标尺;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学思想,可以说是这种事感的理论旗帜。即事感怀型的事感多是即兴感发,这种事感也多是对即时发生的事的回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譬如《本事诗》载:宁王强娶卖饼者妻,饼师之妻迫于强权而无奈,只能双泪垂颊。此时,宁王却命王维赋诗。其诗曰:“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王维这首即事诗对现实之事的感发可谓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第三,托事感想型主要是对将来的事的一种感发方式。这种事感所托之事一般都是未曾发生的想象之事。比如《诗经·硕鼠》“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就是对“食我黍”、却又“莫我肯顾”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之事的想象。在中国古代,纯粹描述将要发生的事的诗并不多见,但古代诗谶现象却是十分常见的,尤其是汉代谶纬之学盛行的时期。比如据《本事诗·徵咎》记载,刘希夷初春离世,与其诗《代白头吟》“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就有谶纬的关联。
纵观这三种事感,前两种事感即述事感思型和即事感怀型的事感在中国古代比较常见,出现的精品也较多。这可能主要取决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郁的历史情怀和现实关怀的国度,即诗的本事观念和功用观念相当浓厚造成的。中国没有形成纯粹的托事感想型诗歌与中华民族务实、不耽遐想的文化可能有关,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诗歌里就没有想象、虚构的事。事感究竟起于过去的事、现在的事,还是将来的事,不同的诗学观念就会有不同的回答。笔者认为,诗应该是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有机统一体。诗不是感于现实之事,其超越性又有何意义?同样,诗不超越于现实之事,其与现实又有何分别?叶燮“想象之为事”与亚理斯多德“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其实都有现实的土壤,而并非空中楼阁。因此,事感应观古今于须臾,抚未来于一瞬,挫万事于笔端,诗才能妙不可言。
其次,依据感官的形式不同,事感可分为验见型事感和途说型事感。第一,验见型事感是一种主要诉诸视觉感受事的方式。这种事感方式是从亲历者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以及审美观念真切地感受、理解、编排事件。因此,这种事感事真、景切,既有如临其境的现场感特色,又有独一无二的个性化特色。比如《诗经·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的事,决定了我的所见多是“零雨其濛”,所感自然是“我心西悲”。《诗经·采薇》“昔我往矣”“薇亦柔止”之事,则所见“杨柳依依”;“今我来思”“我戍未定”之事,则所见“雨雪霏霏”。这种事感所带来的是一种事景相偕的美感。第二,途说型事感是一种主要诉诸听觉感受事的方式。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其实对于述事诗来说,也不尽然是对的。不可否认,亲见的事是实,途说的事有虚。但途说中的事已是被认定有价值、可信的事,对这种事二度感发必然有特殊的审美价值。谢榛《四溟诗话》指出:“写景述事,宜实而不泥乎实。有实用而害于诗者,有虚用而无害于诗者,此诗之权衡也。”[6](12)亚理斯多德也认为对于诗的情节安排,“一件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件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7](68)。
综上所言,验见出实,途说有虚。“实”给人真切感,“虚”给人奇妙感。有实有虚,才有滋有味。验见型事感与途说型事感有着不同的品性与审美趣味,二者各有所长,又有其短,不可求全责备,偏一而用。对于事感,实者虚之,虚者实之,虚实相生为妙。
与生俱来,谓之性。事感作为中国诗学缘事理论的核心概念,与物感、情感和理感有着本性的不同。具体来说,事感不仅有时间性(事)的审美特性,而且还有空间性(感)的审美特征。
第一,事感的本质特征是时间性。尽管人们对世界的感受都是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进行的,但是由于事的本质是一种充实的时间,那么事感主要就是对时间的感受。譬如《诗经·采葛》中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虽然诗中有情,但整体而言,这首诗的感发主要还是事感。因为“如三秋兮”的感受主要是对“一日不见”之事的时间性感受,情只是事生情的结果。换句话说,事感之后所形成的充实性时间不过是事生情的产物。
当然,触事感发所形成的充实性时间感受除了事生情,还有事生事和事生理两种。杜甫《逢李龟年》从“岐王宅里寻常见”的过去之事感发到“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当下之事,是事生事的感发,此诗美的本质在于时间的流动美,即过去岐王宅里美好的记忆又在落花时节里重现,其事、其情得以诗性交汇而美不胜收。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刘禹锡、韦楚客在白居易居所以诗会友,谈及南朝兴废之事,其中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从“王濬楼船下益州”感发开始,最后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结尾。我们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是一种充实性的时间感慨,而之所以这种时间是充实的,原因就在于在这种时间性里说出了“理”。这种事感就是由事生理的感发,其美是深度的美,有内涵的美。总而言之,不管事感所引发的充实性时间的类型多么不同,也不管它们之间的审美感受有多么的不同,但事感的本质特性都是时间性,即事感是围绕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性展开充实性感受这一点是无疑的。
第二,事感的表现特征是形象性。中国古人对时间的感受与言事的方式具有独特的诗性价值。具体来说,中国人的知时、言事的智慧就在于让时间在空间中形象地显现。上古历象日月,敬授人时。东方曰星,其时曰春,东作之事,以务农也。正是由于这种时间空间化的独特认知方式,中国古人对“事”才不善于在时间性中展开,而善于在空间性中驻留。也就是说,中国人事的时间性并不在事件的铺排中展开,而是在空间的形象中显示。这些形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象,而是事象。譬如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时间的感悟、人情的体验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景象中显示的。对于这首诗的鉴赏,我们可以从“物感”和“物象”的角度加以品评,也可以从“事感”和“事象”的角度阐释。叶燮《原诗》就指出:“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8](32)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物感”与“事感”是两种不同的诗歌发生观念;另一方面,“物感”与“事感”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汉代经学家郑众就提出过“托事于物”的诗学思想。从创作的角度看,事感的表现特征尽管是“指事造形”即通过形象感发事义的,但这种形象不是“物象”,而是“事象”。“时间空间化”审美是中国事感的独特个性,同时也是中国叙事诗不发达的主要原因。
中国诗人事感的形象性特征与中国人的感发形式有关,同时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首先,从感发的形式来看,事感可以通过情节即事生事的方式表现,也可以通过形象即事生象的形式显现。西方热衷于前者,重情节而轻形象;中国热衷于后者,重形象而轻情节。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叙事长篇也有情节,但与形象相比并不是中国诗人的首要关切。与西方“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不同,中国古人更倾向于“假物象以明人事”。也许在中国古人看来,立象明事才有历史深度和美学意味。中国古人不善于感事后推演事,而善于感事后品评事。因此,中国诗人的事感的表现特征是形象性。
第三,事感的感发特征是深度性。众所周知,感知作为思维的前提,可分为浅部感知和深部感知两种。所谓浅部感知主要是指感官对事物的颜色、温度、形状等外在特性的把握,具有较强的直观性。诗学中的物感说主要属于浅部感知。譬如钟嵘《诗品》“四候之感诸诗者”——“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就属于浅部感知的产物。当然,浅部感知即物之感人后也会摇荡性情(比如“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但物感之初主要属于浅表的感知。与之不同,所谓深部感知主要是指感官对历史、文化、道德以及情绪等非直观性的人文和心理的感知,具有较强的深度性。诗学中的情感和事感就主要属于深部感知。就事感而言,“事”本身就内含着文化、道德、历史等观念,对其感发就不可能采用直观的形式,而是有一定的理性因素的渗入。
从物感与事感的差异来看,物感是浅部感知,有审美的自由性,而干预性不足;事感是深部感知,有充足的干预性,而审美自由性不够。李白《独坐敬亭山》在“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之后,可以尽情地享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带来的诗性的自由。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深情厚谊的事感相比,物感确实具有更多的审美自由。这也是中国诗学为何重物感而轻事感的主要原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物感由于本质上属于浅部感知,如果物感之后不继续深度化,就很容易堕入“极貌以写物”“穷力而追新”的泥淖。事感虽然本质上属于深部感知,但是如果事感之后力避说教、直白而加以感性化处理(比如指事造形),也可以走向审美的自由。譬如事感而生的《长恨歌》不也诗兴盎然吗?事感的优势在于自身的深度性,言之有物而不空洞。当然事感的不足也源于这种深度性。事感的感发特征是深度性,其美学的特征就在于这种深度美学的特征。事感所引发的伦理叙事、文化叙事、政治叙事等都是属于事感深度性感知的延展。
总而言之,事感作为一种深度感知世界的方式,以其时间性的本质特性以及形象性的表现特性成为中国诗歌尤其是言事诗感发的一种重要方式。可以说,事感建基于人类历事生存论和人性感应论的基础之上,它不仅是诗歌实践的起点,而且也是中国缘事诗学理论概念的起点。
三、事感的功与用
人在事中生存,不可能无动于衷,而是有感而发的。事感就是人类历事性、感应性生存的必然产物。观澜索源,研究事感对于人类日常生活诗性化以及缘事诗学理论的建构都具有积极的功用价值。如果说物感主要揭示人与物之间的诗性关系,那么事感则主要揭示人与人之间的诗性关系。也就是说,事感是对人与人之间行动结果的感发,它主要致力于人事的诗性化研究。具体而言,事感的功用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存论的功与用——事感诗性化能提升人类生活的品质,从而使日常生活审美化。毋庸置疑,人都生活在事件流之中,每个人也都会对事有所感发。但一般人对事的感发更多的是概念化、惯例化的感发,而深入灵魂的个性化、生命化的感发比较少。何以见得?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常人之所以“鹦鹉学舌”,就在于常人缺乏此在性,更多的是一种非此在的文化性生存。对于中国人而言,做事和言事的方式受儒、释、道文化观念的影响很大,甚至言听计从、概念化地看待和感受这个世界。不可否认,儒、释、道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所形成的事的观念,一方面促成了中国人历事生存的理念,但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人的日常生活。儒家多做、少说事,对事的感言不利;道家不做、不说事,对事的感受不利;释家四大皆空,空无一事,对事的感悟不利。与之不同,诗人的事感是在尊重文化、道德律令的基础上,对事的感受是源自生命本能,极具个人化的真切感受。这种感受既是此时、此在的感受,又是贯古通今、继往开来的感受,即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的诗性感受。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诗人在贫乏时代的职责就是要引领常人走出历事生存被抛的“沉沦”境域,而走向“诗意的栖居”。常人与诗人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常人时常“怕”和“畏”,而陷入“人云亦云”之中;诗人时常无所畏惧,而“执着于神的踪迹”。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众人匹之”“有所待”,“神人无功”“逍遥游”。与众人的事感不同,诗人事感由于主要是对人事的审美化感发,这种鲜活的、指向未来的感发对日常生活的品质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陶渊明感事尘网三十年,归园田居是一种诗性;欧阳修退居汝阴,以资闲谈也是一种诗性;苏轼谪置惠州,不言贬谪之苦,却自得其乐,“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一种诗性。这一切都是感事于诗的力量,这种源自世事的诗性力量对日常生活的惯例化、概念化有着天然的消解性。毋庸多言,事感除了有物感的审美价值外,还有日常生活诗性化、品质化的生存论价值和意义。
第二,创作论的功与用——事感实践化能充实和丰富诗歌的内涵,从而使诗歌更具现实性。一首诗是何种风格、有何价值,与其创作时感发的方式有很大关系。如果诗人采用物感,在物我交感之后,以外无物,内无我,物我两忘为上。这种感发而成的诗意超越了现实需要,将人引向纯审美的想象空间,其价值不在于现实性,而在于审美性。譬如王维的山水诗《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就是此类诗歌。如果诗人采用事感,在遇事感应之后,尽管也有坦然处事的诗性引导,但诗的内部总隐含着大我的现实关怀。比如王维的边塞诗《使至塞上》“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就是此类诗歌。由此看来,同一诗人采用不同的感发方式,诗歌的意蕴和风格就不尽相同。事感对创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的现实性上,以杜甫“诗史”为代表。
从古至今,诗总是在现实与非现实的轨道上游走,它们所创造的审美观念也各不相同。前者主要通过事感逼真地描绘,后者主要通过物感合理地想象。就前者而言,从《击壤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事感开始,到《诗经》“铺排其事”的十五国风,再到“即事名篇”的杜甫诗史,乃至胡适的白话诗等都强调事感重要。之所以强调事感,就在于事感是诗走向现实、走向大众的起点。这类诗主要关注诗的现实功能价值。不可否认,诗在现实与非现实的轨道上有时也相互融合,但更多的是矛盾和冲突。物感之诗指责事感之诗过于直白,味如嚼蜡;事感之诗则指责物感之诗过于含蓄,不知所云。其实这两类诗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由两种不同的诗学观念造成的,只不过在中国古代强调物感和情感,而相对缺乏事感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而已。可以肯定地说,物感发是诗,事感发也是诗。事感指向现实,其美主要在于对现实的再现之美,其功能主要在于对现实的宣泄和改造。下面以《诗经·北门》为例加以剖析,首句“出自北门,忧心殷殷”,开门见山地感发,为何有此感念?紧接着“终窭且贫,莫知我艰”有所点明,最后通过重章叠句、反复讽咏,“忧心”与“我艰”之事力透纸背,即“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这首诗不写物,只写事,百姓忧心之情、卫国乱世之音却可感可触。诗人从个人独特事感视角出发,真切地再现了社会现实,人融入其中而感同身受,现实就会被诗意化。《毛诗正义》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北山》,下怨其上,……言己独劳从事,则知政教偏矣,莫不取众之意以为己辞。”[9](17)事感对于创作的意义就在于:让诗具有现实的审美价值。
第三,诗学理论的功与用——事感概念化能支撑诗学理论,从而使中国诗学的缘事理论渐趋成熟。任何理论都起于概念,形于推理,成于体系。事感作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一种感发方式,自有诗以来就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只不过诗人日用而不知罢了。随着汉代乐府诗“缘事而发”观念的形成以及“以事释诗”诗学活动的展开,事感概念得以萌芽。及至唐代,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期,事感概念终于在孟棨《本事诗》中被明确提出。笔者认为,事感对中国缘事诗学理论的功用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事感不仅是缘事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也是缘事诗学理论的起始概念。也就是说,没有事感的概念化或事感的创作基础,缘事诗学理论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其二,事感不仅是缘事诗学理论的起始概念,而且也是事象和事境概念的源起概念,即事感之后,感而生象,事象生焉,象而生境,事境行焉。也就是说,没有事感概念,事象和事境概念就很难推演出来。
其三,事感不仅是事象和事境概念的源起概念,而且也是缘事诗学理论的审美概念。也就是说,事感的审美方式决定了事象和事境的审美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中西诗学审美观念的不同。
综上所言,事感是人类历史记忆、文化记忆、诗性记忆与生命体验以及生活经验感发的起点,它对于人类诗性生存、诗歌创作以及诗学理论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功用价值。很显然,我们当下已进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事感的诗意性和审美性的独特价值理应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