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结构的自组织知识解
2018-01-11张尚毅
【摘 要】制度对发展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其作用机制却不甚清楚。然而,人们所能构建的制度都应该是其所认为了解的制度,能够运行的制度都是在这个制度下人们所能理解的制度。因此,所谓制度说到底就是人们对其了解与理解,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制度的运行,而不论了解还是理解都归因于人们的认知程度,而且这个认知是具有价值判断性的认知。在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存在着具有价值判断性知识,而这成为制度建构与运行的基础。通过把这类知识从整个知识中分解出来,从给出经济制度构建与运行的机理,进而可以解释经济制度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关键词】自组织知识;技术知识;知识分布;制度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问题逐渐纳入到经济分析之中。但是,制度到底通过什么对经济起作用却语焉不详,这直接影响到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通过将经济制度结构解析为自组织知识水平,从而得出一个制度结构的自组织知识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揭开制度结构与运行机制的黑箱,指明制度对经济产生作用的路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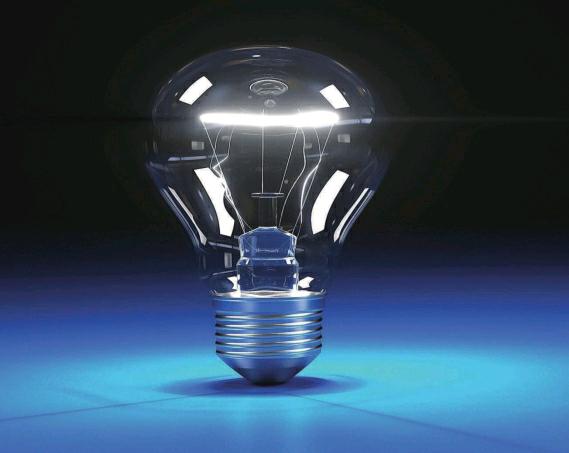
一、知识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理论反思
在西方经济学主流之外相对更为重视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表达较少,但也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中主流学派不涉及这点,如马歇尔就明确提出:“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1],但是,其后的大多数经济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这个论断。知识对经济的作用由奥地利学派特别主张,哈耶克就专门论述了经济学和知识的关系,他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就用了“经济与知识”这个题目,阐述了经济活动进行中的知识问题,在他的其他相关著作中也明确指出:“在经济理论中,经验因素——它是不仅涉及含义而且涉及原因和结果,并因此而得出结论的唯一因素——是由一些有关获取知识的命题所组成的”[2]。也即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知识贯穿于经济理论的全部逻辑之中。当我们将经济理论落脚到知识上来时,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于人类知识进展出现了问题,而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如此。
在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自己的行为的经济结果并不清楚,从而使人类的经济史相类似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反复,因此至少可以认为从长期来看,正如罗默所指出的那样:“长期增长主要由向前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所驱动”[3]。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就可以推导出一个知识对经济运行的效应。同时,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存在溢出效应,这点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而如果知识存在溢出效应,那么,对于处于不同经济体的個体说可能获相类似的知识,因而可能会出现相类似的经济运行效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考虑到知识的溢出效应,在相关知识对经济分析的理论中并没能够指出知识能够在一个经济体内具有效用,而应运到其他经济体中则达不到同样的效用甚至相反。对此,普雷斯科特作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其实各国的可用知识是相同。因此,一定存在其他的某个因素,或者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差异”[4]。这个因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因素在于人类的知识对经济的效用不能统而言之,必须加以分别研究,普雷斯科特所提出的知识更大可能性是技术知识。那么,问题就在于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由自组织知识所构建的制度结构,这决定了对待技术应用于经济增长的倾向。而对待知识应用于经济增长倾向的不同,使一个经济体所获取的应用于经济增长的技术知识存在差异性。也即是说即使各国可用的技术知识是相同的,但由于各国的自组织知识分布不同,其对待技术知识的态度也肯定会不同,因此,最终用于经济增长的技术性知识积累就不同。
这里,我们可以深化诺思研究的内容,将知识视为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而这种把握既体现为对关于自然的知识的积累,也包括对关于人类自组织知识的积累,从而使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成为确定。人类确定性地掌握知识,不仅可能适应自然的演变而且可能通过技术改变物质结构,形成适应人类的物质结构特征,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同时,使人类可能确定性以群体的方式实现经济活动的确定性进展。但是,这点也使人类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就是如何适应更为广大的群体性的行动,并使之成为确定性。对此,奥尔森认为规模越大的群体,越不容易实现集体利益。对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奥尔森只是指出了一种现象,并没有从自组织知识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解释其原因非常必要,这在于当群体规模增大时,自组织知识的人均水平会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到自组织知识的期望值与方差的变化,进而使规模大的集体行动难以进行。对知识作了关于人类的自组织知识与关于自然的自然知识这样的区分后,还可以观察到一种情况,即关于自然的知识是标量性的知识,而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是矢量性知识[5],这是因为自组织知识最终将给出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方向性的价值指向,进而构建起具有选择性决定的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类关于自身行为的不确性的确定,这种确定由人类自组织知识所表现,而在知识层面则以自组织知识体现出来,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会出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6],而这种选择取决于由不同的关于人类自组织的知识所构建的制度结构所决定,因此,如何发展出对自组织知识分布状况及确定性的理解,就成为理解制度结构的根本性问题。
二、知识分布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知识分布是依据一定规律形成的人群知识分布状况,而人均知识分布则体现了人群知识的平均水平状况。在进行论述时可以设定,对于某一个体来说其最初所获得一定存量的关于人类自组织知识的存量,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点。进行这样的分析是因为“分析人们将做什么只能从他们所知的问题开始”[7],而不是简单把分析建构在一个群体性的行动假设上,从而使分析的基础更接近于制度结构源于每个人的具体认知,并且不同的认知在群体行为上实现耦合这个事实。因此,关于知识对经济制度影响的分析就应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点也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制度是人类的创造物,它们演化着,并为人类所改变,因而,我们的理论必须从分析个人开始”[8]。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设定一个经济体具有足够的人群数量,通过对个体知识存量的设定可以知道,对于具有足够个体数量的经济体来说,其所具有的知识总量为所有个体知识存量的矢量和。之所以提出这点,是因为对于制度结构来说,人群数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制度结构必须建立在人群具有足够个体数量的基础上,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那样“一人世界没有社会,也没有经济制度”[9],简单的个体组成的小群体无法构建制度结构。所以,可以对具备制度结构可能性的群体设定为某一经济体中人群数量达到足够大,并且由于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内的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人群的自组织知识分布状况就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对于这点,在经济研究中虽然存在诸多的争论,但是,就内生性的制度的形成来说,始终该归因于人群数量及其知识分布状况。我们赞成梅纳德.史密斯的观点“个体选择并不必然导致最优或者次优的社会结果”[10],而取决于群体选择的结果,因为在制度结构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制度下的最优,而这个最优只能是个体所选择的最优,也即是个体在既定制度结构的情况下,由其所拥有的自组织知识所能够实现的最优的选择。endprint
这里还要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人群虽然都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当人群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近似地看作连续的函数系列,因此可以假设人群知识分布是连续的。从数理统计相关原理可以知道,对于任意总体只要数量充分大,样本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其均值也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在分析知识在人群中的分布状况时,我们也可以用正态分布进行研究,并从中确定由知识所映射的制度状况。对于前面我们的设定来说,这个经济体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平均水平即样本均值的经济意义,体现为经济体系所能达到的人均知识分布存量水平。由于从逻辑上来说,人们对未来的决策取决于对过去的把握,以及对其中逻辑规则的把握程度,而这种把握程度体现在人群水平上就是一个经济体中人均知识存量水平,这个人均知识存量水平也就是对人群自组织的确定性把握的知识水平,并由此确定出可能的制度结构优化度,最终体现为这个经济体中人群对经济运行所具有的预见水平。
我们所需要得到的就是一个经济体中人均知识状况所能体现的人群知识水平,进而得到由人均知识分布状况所决定的结构性约束,最终这个约束体现为制度规则。并且,随着人群自组织知识存量的增加,会不断改变人均自组织知识存量。而人均自组织知识存量的变化会引致制度结构演化,从而使“知识存量的累积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1]。这种潜移默化作用不仅体现为随着这自组织知识的增长,形成了具有共性的知识累积的强度,而且还强化了由自组织知识所决定的价值方向,而价值方向将对在这个经济体内的个體形成潜在制度性安排,从而使制度结构的演进具备了条件。这里,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当经济体人群数量足够大的情况下,个体所获得一定的自组织知识增量时,不论这个增量的矢量和取值为正或负,随机个体的自组织知识存量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人均自组织知识分布水平的变化,按照伯克利定理这只为制度结构演进提供了可能性,而不会必然地引致制度结构的演进[12]。也正因此,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所观察到的个体,往往存在着与现实的制度结构不相称的自组织知识水平,当自组织知识水平在人均水平上发生变化时,就有可能实现制度结构的演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自组织知识的人均分布状况将影响到制度结构的演化,进而形成影响经济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
三、经济制度体现人均自组织知识优化水平
在这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开始引进负知识这个概念。前面,已经确定自组织知识是矢量性知识,因此,当一部分自组织知识在推进经济制度演进方面起着相反作用时,那么,这些自组织知识就是负知识。福利经济学有关理论表明,并不是所有制度的演化都有利于改进人群福利状况,即使如希克斯等人所指出的弱化的福利改善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能实现,其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从自组织知识分布状况来看,一些经济体关于自组织知识对于制度演进呈现出反方向,当这些自组织知识在整个自组织知识体系中占有相当的份额时,可能会引致经济制度朝向相反方向演变,进而形成制度结构的退化效应。自组织知识既可能出现与制度演进方向相同,也可能出现与制度结构演进方向相反的特性,这也进一步说明所给出的关于自组织知识是矢量性知识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当自组织知识累积起来出现负知识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制度结构退化。
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自组织知识分布会发生变化。从人类制度结构演进的历史来看,由于自然资源短缺可能引致关于自组织知识的变化。为了说明这点,可以引用近代工业革命作为例证,工业革命之所在欧洲出现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人力资源的短缺,从而演进出新制度结构模式,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并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自组织知识,而自组织知识的演进导致了新的制度结构的出现,这正如赫拉利所指出的那样,“想像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理解,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像之中”[13]。而他所指出的想像实际上就是认知革命的结果,他将之归结为“文化正是认知革命的主要成就”[14]。这里所指出的文化,实际上就是维系人群秩序存在的由自组织知识所构建的制度结构。基于此,可以认为只要自组织知识朝向现有制度结构的方向积累,就有可能推进制度的演变。当然,这里存在的一个前提是原有的经济制度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在这样的条件下的自组织知识积累的过程就是制度演进的过程,反之则反之。于此可见,自组织知识的演变对经济制结构度的演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间接与经济增长相关联。
那么,人群知识状况又是如何促进制度的演进?结论是由于人群之中各个不同群体关于自组织知识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经济体自组织知识演变成为可能。诺思就明确指出:“知识的变化是经济演化的关键”[15]。当然,诺思并没有把自组织知识从知识总量中区分开来,当然也就不可能意识到自组织知识的价值性特征,而这也是困挠诺思新制度经济理论进一步深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诺思至少开始意识到这点,如他认可经济制度演化中“参与者的意向性通过他们逐渐形成的制度反映出来”[16]。诺思的意向性实质上就是一种知识的价值判断表现形式。这里,虽然诺思没有指明意向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将自组织知识作为建构制度结构的知识,从知识总量中区分开来就可以较好地进行理解诺思所指明的意向性问题。因为制度反映了自组织知识,所以当意向性发生变化时必然会促进制度结构的演变。
我们还将面临着“由于在历史上或在当今的世界,无不同时存在着成长的、停滞的或衰落的经济体??如果说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是阻碍成长的制度结构的牺牲品,那么制度结构是外部强加的呢?还是内生的?还是二者结合”[17]?对此,不少学者都存在着疑问。通过对人均自组织知识分布及其所映射的制度演进情况的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制度即可以是内生的也与外部强加相关。这是因为通过对知识积累的分析可以看到,制度的演进与一个经济体内人均自组织知识分布状况相关,而人均自组织知识分布状况最终取决于个体的自组织知识积累的总体水平。内生的制度结构来源于人均自组织知识分布状况,而外生因素生成的制度结构则以对自组织知识积累的方式影响到人均自组织知识分布水平。这点十分容易掩盖问题的真像,因为学者们往往将外部强加的方式导致制度结构演变视为当然,而没有注意到由于外生性自组织知识的影响使一个经济体内部自组织知识结构出现变化。同时,因为构成制度的自组织知识对经济体内部个体的自组织知识形成矢量和效应,从而在一种渐进的过程中影响到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外生制度结构总是通过渐进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并逐渐成为可以适用的制度结构。因此,当我们将着眼点放在自组织知识的分布上时,通过自组织知识对制度结构的演进作用,也就可以对外生性制度结构对一个经济体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做出合理性解释。还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人类的自组织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种不断交流和获得自组织知识的途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使不同群体及个体的自组织知识保持差异,作为后者可能在促进制度结构的演进上更为重要。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人们往往忽视这点,倾向于对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在不同区域的应用,或者倾向于对于在当前制度结构下获利个体的福利程度的保持或提高的制度结构的应用,而不能认识到制度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的作用在于差异性的存在。并且,正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制度结构演变成为可能,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可能性。endprint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参考文献:
[1][英]阿费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7页.
[2][奥]冯·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3][美]Paul M·Romer.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4][美]斯蒂芬·L·帕倫特,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通向富有的屏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5]张尚毅《人群知识分布与经济增长分析》,载于《探索》2014第5期.
[6][美]道格拉斯·C·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7][奥]冯·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8][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
[9]张五常《制度的选择》,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
[10][荷]杰克·J·费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11][美]道格拉斯·C·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12]张尚毅《人群知识分布与经济增长分析》,载于《探索》2014第5期.
[13][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14][以]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15][美]道格拉斯·C·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16][美]道格拉斯·C·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17][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的演进》,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张尚毅,经济学教授,中共重庆师范大学常委、纪委书记。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