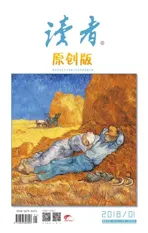我去到世界尽头,看到洪荒美景
2018-01-11祝羽捷
文 | 祝羽捷

在冰岛自驾的第五天,我已经疲惫不堪,可在我的司机伊瓦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城市病,我都没走几步路呢。
伊瓦是个身长1.8米的汉子,祖上数代都是冰岛人,没有丝毫移民血统,可谓正宗的土著。
我并不想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多待,首都往往不是一个国家最有魅力的地方,也不想只是泡在温泉里,脸上涂上矿物泥。
我有备而来,而伊瓦就是那个带我逃离城市的人。
一
我们几乎开车横跨了整个冰岛,伊瓦倒是一点儿也不累,适当的时候会告诉我需要补充体力了。
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羊腿和鱼吃,我们开车找到一家便利店,买到夹了芝士、西红柿、黄瓜的三明治和一点儿水果,以防在荒郊野岭时什么都没的吃。
他还会买当地产的一种巧克力饼干,形状像极了当地裹满苔藓的熔岩,饭后跟我分着享用。吃多了他会说自己胖,他不说我还没留意,他挺着一圈肚腩,走路的时候有些颤动。
他还有一脸络腮胡子,蔓延到脖子上。
他说他的胡子随他父亲。父亲的一嘴大胡子无比威严,肚子比他的还大,是一位威风的船长。听他的口气,我能感受到船长在冰岛是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
“我的家人都很有意思呢。”他微微有些得意。
路途遥远,我表示愿意洗耳恭听。他受到鼓励,继续用流利但口音奇怪的英语说下去,并下意识地用双手往前扯了下领子。
伊瓦说他还有一个同样当船长的叔叔和一个身无分文的叔叔。
当船长的叔叔参加过第二次和第三次“鳕鱼战争”,荷枪实弹地跟英国人打过仗。为了争夺鳕鱼,这些小渔船还真战胜了实力强大的英国海军。
而身无分文的叔叔被国家电视台采访过,那段视频在网上有4万多点击量,是伊瓦上传的。叔叔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冰岛的名人了——整个国家人口不过32万人。
叔叔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独居于自然之中,一切生存的必需品都靠自己的双手。没有钱,没有结婚,他过着原始生活,很享受孤独。
“电视台记者问了他许多很愚蠢的问题,而他也戏弄了记者。”伊瓦打开视频。
记者问:“野外的生活好吗?”叔叔回答:“没有那么好,但肯定比城市好。”
记者又问:“没有钱怎么生活?”叔叔回答:“用我的猎枪。”
这倒不假,他精通农耕和打猎,蔬菜、粮食自己种,用猎枪打来野鸭和雪白的狐狸。
冰岛的男人或多或少都保留着野性,热衷钓鱼,不过他们十分克制,就拿伊瓦来说,除了为圣诞节准备大餐,他平时从不举起猎枪。
“你的叔叔太幽默了。”
“没错,他虽然没有去学校,但是酷爱阅读,读过的书比我多多了。”
生活退回到最原始的状态,看上去是反人类文明进程的,可你不能说他是个野蛮人。
叔叔的眼镜片已经很厚了,视力越来越差,因为很少跟人交流,语言能力也开始退化。
他的收音机坏了就没有再修过,他认为这些节目可没有大自然的声音好听。
他的身体很好,从没生过病,或者说没有到要看医生的地步,所以他从未进过医院。
他是人类的边缘人,可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更是自己世界的中心。
人生来孤独,自己可以完成一生的旅途,运气好会碰到一些有趣、善良的人,并肩同行一段,但大部分人都会慢慢偏离你的路线,即使不舍也要祝愿彼此前程似锦。
二
即使不像叔叔这样独居,伊瓦也坚持住在城市外面。
“我只有五个朋友,其中一个是一起徒步的,一个是一起钓鱼的,总之我们也都离得很远。我不需要太多朋友,我更不需要知道镇上的八卦,我的时间只想留给孩子和钓鱼。”
有些人离群索居,或许正是看清了“人生的本质是孤独的”这一事实。
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人,都有各自的困境、各自的孤独。对于冰岛人来说,如果不热爱自然,就不能消解孤独。
在冰岛的每一天,我们都会经历四季,时而阳光普照,转眼又迎来劈头盖脸的骤雨,远处是万年不化的冰川,身边是遍地的黄色野花。
河流、湖泊、荒地、瀑布、裂谷……各种奇异的景观交替出现。
车上的温度计显示着户外的气温:时而温暖如春,时而接近零度。车后座上是我的棉绒大衣、雨衣、帽子、围巾,下车前随时调整保暖装备。
路过绝妙的景色,伊瓦总会提醒我看,自己也很陶醉,拿出手机拍照。
“你怎么没有相机?”他问我。游客一般都会带相机来,冰岛的风景无人不赞叹。
“相机在巴黎旅行的时候被人偷了。”
“Oh,shit.我们这儿只有500个警察,但是很少有人犯罪。”
每当有车子路过,伊瓦和对方都会不约而同举起一只手打招呼,并报以微笑。
一开始我以为是伊瓦太过热情,他见到“摩托党”会招手,见到自行车族会招手,甚至见到那些求搭车的背包客,也会招手以示不能提供帮助的歉意。
成人世界本就冷漠和善变,每次得到温暖都是幸运,唯有心怀感激。在很多地方,人们都会把同类当成竞争对手,在冰岛则完全不是。
陌生人之间被一种最简单的友好牵连着,我们都是祈祷好天气的普通动物,只有自然才是这里的主宰,人类只能相互取暖,敬畏自然。
三
我们经过不同颜色的平原,看见埋头吃草的羊群用圆鼓鼓的屁股对着车。这里的羊比人还多,它们偶尔会穿越马路,我们只好停下车耐心等待。
车子里飘进臭鸡蛋的气味,那是土壤里的硫黄散发出的味道,下车看,脚下是赤土红泥,寸草不生,到处冒着热气,雾气缭绕,宛如仙境。
那些喷着雾气的地热喷泉,隔几分钟就喷发一次。伊瓦告诉我,千万要留意风向,顺风而站可能会被沸水溅到。
要进入海克拉火山区了,伊瓦说这里是最危险的区域,上一次火山喷发是2000年,他们管这儿叫“地狱之门”。
路边停着一辆越野车,车窗摇下来,车上的男孩正在发呆。伊瓦又开始表现他那过分的友好,先是问人家需不需要帮助,接着又告诉男孩,进入火山区前需要给轮胎放气。
我们的轮胎已经放过气了。这些天,我已习惯伊瓦根据路况来调整胎压,而且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火山区一个人影也没有,唯一遇见的活物就是三只惊恐万分的羊,瞪圆了眼睛,转身扬长而去。
翻过火山,越过山脚下的小溪,溪水两旁是鼓鼓的青黄色苔藓。
我们的车一次又一次冲进池塘,眼看水就要没过窗户,车子又神奇地爬了出来,水花溅满天窗。
紧接着又开进一片不毛之地,沙尘暴咆哮着,这里是风暴的高发区,车窗上那些还未来得及干的雨水已变成黑色的泥丸。
很难相信,在这贫瘠荒芜中竟出现了蔚蓝色的湖泊——朗吉湖,我揉揉眼睛,以为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没错,它比蓝宝石还要清澈。
朱红色的山上出现了巨大的彩虹。这些天,在大大小小的瀑布前,我见了这辈子最多的彩虹,但还是因为山上这条兴奋不已。
“那不是彩虹,而是彩色的土壤,由不同的矿物质构成。”伊瓦解释道。
奇异的地貌,让我不停后悔小时候没有好好学地理,大部分时间都在应对考试。
“伊瓦,你学的专业跟自然有关吧?”
“我是学法律的,自然是最好的学校。”
伊瓦有着比我精彩万倍的童年,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他不可错过的快乐之源,我很难向他解释我们在城市里度过的童年。
我们只能在操场上堆堆沙子,在护城河上划划船,大部分的休闲时间都在上补习班,在少年宫里学一点儿才艺。
有很多次,我以为车已开到死路,没想到又绝处逢生,遇见一片活水和绚烂的植被。
伊瓦说那些路他已经走过千百次,但还是会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因为每个季节景色都不一样,每一天不同时段也不一样。”
这里的马匹身材并不高大,鬃毛飘逸,如精灵般安详。冰川下流动着浅蓝色的泉水,仔细看,每一块冰都有自己的花纹。
在冰岛,我总有一种不真实感,像是到了另一个星球。有多少次,我都恍惚觉得自己站在了世界的尽头,左手是冰川雪山,右手是雾气氤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