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外一篇)
2018-01-02小二
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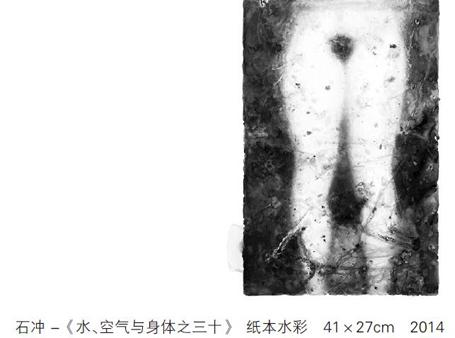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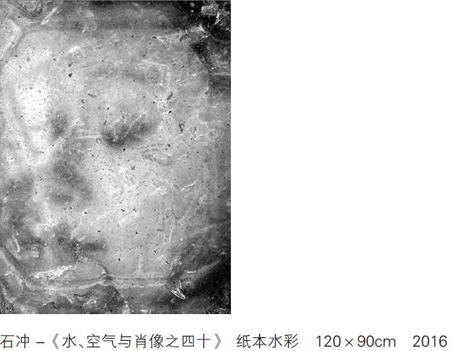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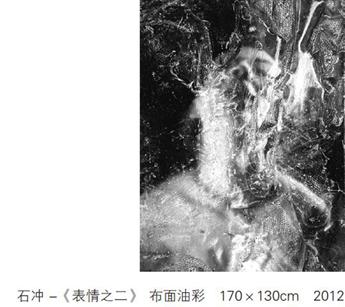
早上来上班,跟往常一样,干着例行的几件事,先去休息室泡杯茶,烤两片面包,然后回办公室,开计算机,刚想上网浏览一下当天的新闻,手机响了。
“早上好,韦先生?”
“早上好,我是。”
“我是安德森侦探。你认识桑女士吗?”
“桑女士?……不,不认识。”
“眯晓桑。”
中国人里叫眯晓的我倒是认识几个,可没一个姓桑的。正想告诉他,他那头又说上了。
“她的中文名子叫……叫晓……晓晰。”
这两个“X”开头的中文字让安德森费了点口舌。但我总算明白他说的是谁了。
“眯晓孙,我认识她。”
“眯晓桑。” 安德森纠正我道,并开始拼音,“S-U-N,桑。”
我忙说:“知道知道,我认识她。”心想这中国的“孙”子,一到美国就长了一辈,成儿子了(注:英文里儿子发音为“桑” )。
“你最近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间?”
“大概一年前。”
“你确定?根据她手机里的来电记录,你两周前刚给她打过电话。”
我心里一惊,出什么事了?连手机记录都查了,车祸?安德森还在电话那头等着呢,我忙回答说: “是给她打过电话,但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很少见面。”
说完很后悔,最后一句话像是在画蛇添足,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安德森倒是没我想的那么复杂,他告诉我眯晓桑两周前因用药过度不幸身亡,并说了一个具体药物的名字。因为说的是英文,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又说从眯晓的手机记录看到我是最后一个给她打电话的,所以向我了解一些情况。我当时吓了一跳,有点语无伦次,加上是说英文,费了半天劲才让安德森明白,我上次给眯晓打电话,只是为了交流对一部中文小说的感受。最后安德森给我留了个电话号码,说想起什么就给他去个电话。挂了电话才发现,因为太紧张,我连晓晰到底是怎么死的都没闹清楚。是他杀?自杀?还是不小心?
最后一次见到孙晓晰是在一年前本市举办的一次大型华人文艺活动上。那次主办者从国内请了一些名演员来,又租了一个能容纳一千多人的漂亮剧场,所以华人里面头头脑脑的人物都来了。中场休息时,我出来给儿子买饮料。走过一堆穿得漂漂亮亮的男女时看见了她。我知道她那时刚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但那堆人里并没有一个美国人。她也看见了我,冲我笑了笑。我因不认识和她在一起的那伙人,便只朝她挥了挥手,脚步不停地过去了,想不到那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五年前,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回国,和捷通旅行社的人很熟。一天,我吃完中饭,突然想到还有两周又该回国了,机票还没订,忙拐到捷通旅行社。平时,我总是找一个台湾来的黄小姐订票。进门一看,黄小姐的位子上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头发长长的,穿着一个类似连衣裙的衣服,脚上是一双拖鞋,还染了脚指甲。我问到黄小姐,她笑了笑,说:黄小姐已不在这儿干了。我有点好奇,想知道黄小姐去了哪里。她告诉我黄小姐出去开了自己的旅行社,又对我说,在哪儿订票都一样,手续费都差不多。我倒是不在乎手续费,反正是出差,只是习惯了和黄小姐打交道。不过也不想再跑了,就顺水推舟地点点头说好。她自我介绍说她叫晓晰。不过,她说,你若打电话来,最好说找眯晓,这儿的人大多数是台湾来的。
她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是大陆来的。普通话说得很地道。猜测她的身份却有点难。她看上去三十差一点,首先,她不会是还在上学的留学生,留学生不可能做这种每天坐班八小时的工作;而她的言谈举止又不像一些我熟悉的留学生太太。她虽是新来的,手脚倒是很利索,不一会儿就把票订好了。
一周后去拿票,见晓晰穿了件很奇怪的衣服,袖口像是被谁扯了几下,拖拖拉拉的。她在帮我打印行程那会儿,我瞧见桌上有本中文书,《马原文集》,我顺手拿起来翻了翻,才知道是一个名叫马原的文学作品集。里面有篇小说,名字叫《风流倜傥》,是这样开头的,“在小地方,作家这碗饭真不容易吃。你写出一篇东西以后,许多人都在揣测你写的是谁,以哪些人做模特……”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准备把这篇小说看完再走。晓晰过来说,你要是喜欢就拿去看,看完还给我就可以了。
在去中国出差的旅途中,我把《马原文集》看了一遍。其中几个短篇还看了不止一遍。我过去也看过一些新潮小说,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苏童的一些小说等。但马原写起小说来,对小说的内容一点也不关心,倒是很在意怎样写这件事。这有点像外科医生不关心病人哪儿病了,而是对自己的开刀术沾沾自喜。而且,马原写起小说来还常常跟自己过不去,后面写的东西把前面写的东西给推翻掉。他还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他的小说不怎么可信。在一个叫《西海的无帆船》的小说的结尾处,他这样写到,“为了写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似乎应该翻一翻有关的外科书籍……我决定省下这五元两角五,凭想象杜撰,我想我也许能行,虚构是我的天分。”
当我回来晓晰讲述我读马原小说的感受时,她笑着说,马原对中国的一代先锋作家都有影响,他应该是祖师爷一级的。后来和晓晰混熟了,她说我那天说到马原时的表情是这样的,两眼发光,嘴里吭哧吭哧的,没一句完整的句子。
来往了几次,就知道她是學文的。又上网看了她写的一些散文和小说,她文字很老道,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中的好几篇都像是个人经历。尽管在处理上比较低调,细看都还是朝阳化的较多。这也难怪,人写自己是很难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像卢梭那样写一本《忏悔录》,把见不得人的事都抖露出来。直到我和晓晰很熟了才知道,她在国内时,曾和一个很有名的先锋作家有过一段非同一般的友谊。看来要了解一部作品,得先对作家的生活有所了解。
又通了几次电话后,大概是受到我那种开门见山风格的影响,她告诉我她现在有个男朋友,刚毕业,正在找工作。听得出来,她正在和男朋友闹矛盾,好像经济也是原因之一。我有点诧异。她又无意问到我和太太的关系,我存了个小心,开始说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一天,晓晰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刚换了个工作,去一个中国人开的服装公司做出纳。我和她开玩笑,说:唷, 又高升啦。她说不是,拿的钱比过去还少,主要是身份问题。开始旅行社说好可以帮她办身份,后来又变卦了。现在这家公司同意帮着办身份。话中透着无奈,我开始后悔跟她开那个玩笑。聊了一会,她突然告诉我她是怎样来美国的。
原来她和她过去的先生是在网上的聊天室里认识的。当时他还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读书,隔着大洋聊了半年就结婚了。我过去听说过有在网上认识而结婚的,只当故事听了,想不到让我碰上一个真人真事。她对我说她开始真不知道出国有那么难,以为填张表就行了。对此,我不太相信,一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会不知道出国很难?碍着面子,我没好意思把我的疑惑说出来。
男人大多有倾诉欲,所以需要倾听者。有首小夜曲里就有这么一段歌词,“请你倾听我的歌声,带来幸福爱情。” 可见倾听者对男性的幸福是多么重要。两个男人在一起,别说是讨论文学,就是安排一个简单的出游计划也会吵得不可开交。相对来说,女性比较善于倾听。当然,倾听也有高低之分。晓晰是个水平非常高的倾听者。虽然隔着电话线,只要说上两三句,她就对你今天的情绪了如指掌。她的文学修养很高,但她并不因此就处处压着你。相反,她总是认真地听你的叙述,当你因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点张口结舌的时候,她会很随口说出一个于你来说像救命稻草一样的词,口气却是询问式的,“你是想说……是吗?”让你顿时有通畅了的感觉,没有下不了台的尴尬。于我而言,在美国,有晓晰这么一个高水平的倾听者,简直是一种奢侈。
有一次,晓晰和我谈到自杀,她暗示我她曾经不止一次企图自杀。我对自杀常持怀疑态度。记得小时候在农村,一堆人围着看俩口子吵架。女的说,我不活了,你们别拦着我。就有人上来拉住她。这时那男的说,都给我放开,大河又没盖盖子。大家一放手,那女的就势往地上一坐,哭道: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不想勉强自己,就在电话里打哈哈。晓晰听出来了,再也没提过这个话题。
晓晰离开旅行社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过面。有一次在我常去的中餐馆碰见她,她告诉我她和餐馆的老板是老乡。我和秦老板也很熟,这家餐馆就成了我们交换书籍的地方。我要是有什么书她想借,来吃饭时带给秦老板,她路过餐馆时放下我要的书,取走我留给她的书。
没多久,晓晰的工作又有了麻烦,那家服装公司知道她身份有问题,就欺负她,经常拖欠她的工资。男朋友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想去外州的大学继续念书,但也没资助,就想和她结婚,让她明正言顺地打工资助他上学。我想劝她小心点,但又觉得我说这样的话不太妥当。想不到她说,我才不会干这种傻事,等我辛辛苦苦打工把他供出来,我早成了个黄脸婆了,他找到好工作后,还会回来认我?
晓晰终于和男朋友分手了,她语调里有了多时不见的轻松。一天,她说要过三十岁生日了,父母远在天边,身边一个好朋友也没有。我说你要是觉得我俩交情还不错,到时我请你吃中饭。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那天,我特意选了家美国饭店,又是吃中饭,觉得碰见其他中国人的概率几乎为零。我还专门换了件衬衣,晓晰也穿得漂漂亮亮的。坐下后,她笑着说我现在可好啦,常有人请我吃饭。我说前两天你还哭着说没朋友,不然我会请你吃饭?她收了笑,说,这些请她吃饭的没一个安了好心。从她随口说出的几个名字中,我知道他们是几个本市华人中有头有脑还有家小的人物。我笑着说,你现在是块试金石,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在你面前就显了原形。又提醒她,你可得珍惜你的自由身,好不容易才出了狼窝,别又陷虎口里了,要先看清楚再行动。她说:有什么好看的,好的男人都已经结婚了。我想她是把我归入好男人一类了,心里觉得挺受用的。因为正好在美国餐馆吃饭,就建议她将来嫁个美国人,并讲了一大堆嫁美国人的好处。说你要是嫁一老中,不是他把你累死,就是你把他累死。她有点不明白,我只好说白了,中国男的很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同时满足她的要求。找个老美,不同文,也就没有精神交流这一说了。
正说着话,进来了一伙吃饭的老美,中间夹着个亚洲女性。我瞧着眼熟,她也看见我了,却赶快把头转了过去。这时我已看清楚她是我太太的一个同事。心里想这几乎为零的事竟让我碰上了,说话也就有点跟不上趟。晓晰看出来了,说,没事吧?我强打精神说,有什么事?朋友一起出来吃个饭有什么事?
没多久,晓晰真的找了个美国男朋友,说是在酒吧里认识的,比她小好几岁。我知道后吓了一跳,忙跟她说,这酒吧里能认识什么人?你可是要小心。她说她去的酒吧比较安全。Richard是个技术工,人很内向,俩人在一起谈得很开心。
我还是从秦老板那里先听到晓晰结婚的消息的。她结婚后快三个月才给我来了个电话。我说,好呀,吃水忘了掘井人,当初还是我给你出的主意找老美,结婚连个招呼都不打。她忙说哪儿的话,又说,Richard不太爱热闹,加上他俩也没什么钱,结果去了Richard妈妈在Ohio的农场,既算结婚,又算度蜜月了。
身份问题解决后,晓晰换了个工作。这次是去一家美国人开的公司,管理公司的进货出货。她很高兴,说,来美国这么久了,净给中国公司干活了,就跟没出国一样。我说就是,幸亏你嫁了个美国人,要是只和中国人作夫妻,不跟没来美国一样?她对我的玩笑并不在意,反问我有没有想过娶个老美做老婆。
晓晰结婚后,生活安定了一段时间。她告诉我她先生很尊重她,她去哪儿办点事回来晚了,他从来不问这问那的。他俩租了个一间卧室的公寓住着。我问她你们平时不上班都干些什么。她说也没什么,她晚上看看书,Richard喜欢玩计算机游戏。我说什么时候造个小混血儿出来,也给自己找点事干干。她觉得她和Richard都还没准备好,经济上也是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婚姻有点危险,不管是什么人,一点交流都没有不行。果然,不到一年,晓晰就和Richard分居了。
安德森再也没给我打电话,我倒是对晓晰的死因越来越放不下。我给秦老板打电话,約他喝酒。那天是星期天,不到九点,饭店的客人就走空了。秦老板亲自炒了几个菜,我俩就闷头喝上了。我带来的一瓶洋河大曲已下去三分之一了,也没说上几句话。为了打破尴尬,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晓晰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他告诉我晓晰的父母都来了,他还帮着安排他们的吃住,又告诉我死因最后定为吃抗抑郁症的药和安眠药过量,因为没有保险公司掺和,是不是自杀也无所谓。我听后一惊,说我从来不知道她在吃抗抑郁症的药。他说她已经吃了好几年了,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秦老板喝了一阵又说,我不相信晓晰是自杀,前段时间是她来美后心情最好的一段时光。她说她很快就要去纽约了,还跟我开玩笑说苦日子就要熬出头了。说这些话时,秦老板眼睛红红的,不知是心里难受还是喝多了。其间,老板娘打来电话,劝他少喝点酒,被他骂了一顿。我太太也打来电话,劝我少喝点。说要是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再开车。
晓晰想去纽约的事我也知道。她曾告诉我有个追了她快十年的最近给她打电话。那人的妻子和一个美国同事好上了,最近已离婚。在中国时,晓晰不怎么看得上他。后来他来了美国,毕业后在纽约附近的IMB工作。他妻子是他在美国上学时从国内找来的。晓晰说他对自己至今念念不忘。她想搬去纽约,俩人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感觉。
从秦老板那儿出来已是凌晨两点钟。虽然觉得没喝醉,还是怕被警察拦下来,所以车开得很慢。从餐馆到我家要路经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但都亮着些灯。我从一家家空无一人的商店旁开过时,不知为什么,心里竟有了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我突然为晓晰的死找到了一种解释。记得最后一次和晓晰通话时,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格非的小说《敌人》。晓晰觉得赵少忠在恐怖中咬牙度过大半辈子,这其实已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当最后一个恐怖被他自己消解后,他的生命也就到头了。我当时不同意她的看法,觉得赵少忠终于从恐怖中走出来了,他深藏多年的欲望复苏了。晓晰笑着说,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佣能整出什么故事来?
我曾听一个医生朋友说过,一些吃安眠药过量去世的人,临死前脑子都很清晰,他们处在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的求生欲望,他一定会醒过来。当晓晰决定去纽约后,她来美后的最后一个焦虑已被她自己化解了。她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归宿,同时也失去了继续挣扎的动力。那天,她也许比平时多吃了几颗安眠药,但决不是自杀的剂量。当她就要睡过去的时候,也许知道自己有点麻烦了,但她又一想,算了,其实这样躺着也蛮好的。
老 姚
老姚明年就五十岁了。他不黑不白,中等身材,略有点胖。戴一副近视眼镜,很典型的中年知识男性形象。但是,老姚有一个很不平凡的名字:姚谦书。没看出来里面的奥妙?你再大声念一遍:姚谦书,摇钱树。
别人第一次叫他“摇钱树” 时,老姚已经大学毕业、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了。老姚心想,工作和上学就是不一样,这名字跟着我从小学到大学,没人把它和钱扯在一起,我这才拿了几个月的工资呀。记得和本单位的小张结婚的那天晚上,客人走后,小张笑着对他说,别人都说我嫁了棵“摇钱树” 。这话在当时还算是基本正确。老姚参加工作的前几年,他的工资在单位同龄人里算是高的。后来单位里其他人经商的经商,下海的下海,就把老姚给比下去了。再后来,小张一开口就成了这样,“哼,还摇钱树呢……”
后来老姚出国来了美国。美国人是这样叫老姚的:钱树摇。往往在“钱树” 和“摇” 之间还有个小停顿。这次序一颠倒,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摇钱树” 是个名词,是个静物,说这三个字时你眼前可能会出现一棵挂满钱的大树。“ 钱树摇”给人的感觉则更像电影里的一组镜头。满树的钱都在晃动,你甚至都可以听见钢币碰撞发出的叮当之声。每当听到“钱树摇”这三个字,老姚的眼前就会出现妻子小张的一双大手和儿子姚尧的一双小手,还有几双不知道属于谁的手,都在拼命地摇他。当然,心情好的时候老姚也能看见树上晃动着的美元。这些年来,“钱树摇” 成了他的动力加压力,使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挣钱。
老姚现在正处在“摇钱树” 的一个特殊阶段。因为见过摇钱树的人还是不多,我只好用苹果树来打个比方。老姚这棵苹果树正处在深秋季节,满树的苹果已被采摘一空,只留下一些残枝败叶,离再次长出苹果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棵历经沧桑的老树,很有可能再也结不出苹果来了。美国是个文明国家,对这个阶段有个文明的称呼,叫它“ between jobs ”,直译成中文是“在工作之间”,意译的话就是失业了。
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一年多,名字成了老摇的心病。别人叫他“谦书” ,他马上在心里骂一句,你妈才是钱树。别人要是叫他声“老姚” ,他就在心里说,再摇,再摇我就×××。最让他上火的是太太小张的叫法。小张天生一副亮嗓子,一声“姚尧姚谦书,吃饭!” 老姚就觉得全身五脏六腑都在晃悠。心里骂道:别摇了,没钱!哼,姚尧,摇摇。我当年真是脑袋壳进水,给儿子起这么个名字。
每天早上五点差十分老姚准时醒来,误差不超过正负三分钟。这毛病是五六年前落下的。那时老姚刚去了家眼看就要上市的小公司,进去没多久,就有投资公司的人来给他们办讲座,教他们公司上市后如何兑现股票,如何投资等等。听得老姚贫血的脸上泛出了少见的红色,总觉得身上的骨头痒痒的,像一棵就要抽新枝的树。大家恨不得吃住都在公司里,累得不行时就互相说说,到时怎么花那到手的几百万美元。老姚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左右,周末起码加一天班。可是,不管多累多困,早上一到五点准醒,脑子里全是前一天没跑通的程序。为不影响小张休息,他开始工作日在楼上的客房里睡觉。
老姚百万富翁当然是没当成,不然的话我们的故事可以在这里圆满结束了。不到两年,那家有着一百来人的公司就倒闭了。后来,老姚又去了几家跟计算机有关的公司,这些公司对待雇员都像计算机内存对待数据一样:后进先出。老姚受雇的时间越来越短,最后一个工作,老姚刚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就被解雇了。
老姚再也不需要早起上班了,可他每天早上还是五点准时醒来,所以他还是睡在楼上的客房里。而且,不知从哪天开始,他连周末也住在楼上了。因为再也不用想程序,就用早上这段时间想些平时很少想的问题,过去的一些事情像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演着。
老姚原来是学机械的,来美后讀的也是机械方面的博士。小张在老姚来美一年后带着四岁的姚尧来了美国。小张国内电大毕业,学的是文科,就死了在美国上学的心。来了刚三个月,就找了家中餐馆打工。老姚是有资助的,白天除了上课,还得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回来一边看书一边看儿子。现在想想,老姚觉得那是一段最值得怀念的日子,虽然辛苦点,但有个奔头在前面。念到第三年,老姚看见先他毕业的师兄们找工作都很难,有的找不到工作,只好做博士后,就去计算机系修了一些课。五年后,老姚同时拿到机械系的博士和计算机系的硕士,并用计算机系的硕士学位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在校期间,日子过的很俭省,老姚的助学金养家也就够了,小张打工的钱全存着,几年下来,竟有三万多美金。小张对老姚说,买辆新车吧,这旧车三天两头的死火,上班怎么能行?
一晃,那么多年就过去了。老姚还记得第一次开新车时自己战战兢兢的样子,现在小张开的丰田面包车已是他们家买的第三辆新车了。儿子也已经十五岁了,明年该给他买辆车了。从上一年级起,儿子就成了小张的生活中心。老姚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是常事,加上晚上睡觉是分开的,他每天和小张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而在这一小时里,说的话三句里有两句和儿子有关。小张一点也不比老姚少忙。三年前,她在邮局找了份工作,算是铁饭碗。但每天八小时,一分钟也不能少。回来后,烧晚饭、检查儿子的作业、听儿子弹钢琴、收拾家。每天不到十一点上不了床。起先,老姚总对自己说这只是暂时的。他那时的口头禅是忙完这段就好了。累得不行的时候老姚常想,要是有两个礼拜不上班,什么事情也不做,会是什么样的日子?大概比神仙还快活吧。可老姚现在就处在这么个状态,他没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神仙,倒是蛮像一个活在暗处的鬼。
记得股票热那段时间里,小张常跟老姚唠叨的一句话是:要是真的发了,先把房子贷款还了。两年前,他们隔壁的邻居突然插牌子卖房。这对美国夫妇有对八九岁的双胞胎女儿。男的也在一家要上市的小公司做,而且是个副总裁。女的在家管孩子。小张和她闲聊后才知道,那男的工作的公司最近不太稳定,就决定先把房子卖了,免得到时有压力。果然,房子卖掉没多久,那男的就失业了。他们全家搬到附近的一家公寓去住了。有一次在小区公园碰见那女的,她正带着俩个女儿骑自行车。聊了一会,知道她原来是上过大学的,现在去了一家小学做代课老师。男的去了非洲做志愿工作,要一年以后才能回来。她说这是她先生从小就有的愿望,现在总算有时间来实现了。老姚心想,我的愿望是什么?有过吗?即使有的话,小张会让我去实现吗?我自己会去实现吗?
一天,吃晚饭时,小张眼睛看着别处,说:“听老陈说,他们那儿要一个装计算机的,一小时十块钱。” 老姚低着头吃饭,不吭声。小张又说:“就这工作,还不一定拿得到,好几个人都想去。” 老姚抬起头,冷冷地说:“待会我就给安德森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去他那儿做博士后。” 安德森是老姚念机械博士的导师,老姚毕业后从没和他联系过。小张放下碗,说:“你是不是早就想着要离开这个家了?”老姚说:“人家老安要不要我还不知道呢。再说,和别人争装计算机的工作,我有什么优势?”
第二天,老姚真的打电话找安德森教授,问他做博士后的事。安德森觉得老姚这几年在计算机方面的经验对他很有用,当场就答应了。讲好先干两年,然后根据情况再说。工资也给到学校的上限,第一年三万二,第二年涨百分之十。安德森让老姚和太太商量一下再给答复。老姚想了想,说,就这样吧,太太一定会很高兴的。
老姚把要去安德森那儿做博士后的事告诉了小张。小张说,你七年前第一份工作的工资都快是老安现在给你的两倍。老姚说,这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嘛。我现在在家一分钱也不挣。小张又问,两年后怎么办?老姚苦笑着说,想那么远干嘛?先把这两年混下来再说吧。
自从作了去做博士后的决定,老姚心里有了久违的轻松。甚至有了点当年离家去上大学时的感觉。一天,他还穿上运动衣,出门跑了一圈。没想到跑了不到一千米,已上气不接下气了。老姚想起大学时他还得过系里三千米越野赛的亚军呢。就下了个决心,到学校后,反正一人没事干,多锻炼锻炼。
临走前一夜,老姚正半躺着看闲书,小张推开客房的门进来。老姚忙欠起身,脸上挂着一点尴尬。小张在床沿坐下,说:“都收拾好啦?” 老姚点点头。小张又说:“没改主意?” 老姚忙说:“没有没有,明天我一早就走,要开快二十小时的车呢。你还要上班,就别起来了。” 小张又坐了会,开始用右手背抹眼睛。老姚说:“这不是暂时的吗,姚尧没几年就要上大学了,等把他供出来就好办了。” 小张说:“我知道我这一年多没少给你脸色看,你知道我这不是为自己。你说,跟你这么多年,我和你要过什么?”老姚从床上爬起来,和小张并肩坐在床沿上,說:“我实在是无用,这几年全靠你撑着这个家。” 小张叹口气,说:“其实,靠我的工资也够了,大不了换个小点的房子住,我们住公寓还不是住了那么多年。咳,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老姚看了看低着头的小张,见小张头上有很多上面黑,下面白的头发。就说:“你又该染发了。”眼睛就有点潮湿。想伸手去拉小张的手,却有了唐突的感觉,不由得心酸起来。想了会儿,说:“今晚你就住楼上吧?”小张想了想,说:“不啦,你明天还要起早赶路呢。”又说:“你跟老安说说,假期就不用做了,放了假就回来吧,姚尧在家也待不了几年了。”
小张下楼睡觉去了,老姚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不停地对自己唠叨,赶紧睡吧,不然明天开车真的要出事了。可是越急越睡不着,头开始发昏发沉。也不知过了几个小时,小张又推门进来了。她这次穿了件黑色的睡衣,上面还有些小洞洞。老姚不记得小张有这么件睡衣,问道:“上来睡啦?” 小张说:“不是。我不放心,上来看看你睡着没有。” 说完转身要走。老姚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把小张拖上床。然后用双臂把小张紧紧抱住,一句话也不说。小张开始在老姚怀里轻声抽泣,老姚也感到自己的眼泪沿着眼角往下流,一直流到耳朵里,痒痒的。老姚自语道,就这么一直躺着吧,就这么一直躺下去吧。老姚觉得小张的身子变得热乎乎的,刚想伸手去脱小张的睡衣,响起一阵电话铃声。老姚骂道:谁他妈半夜三更的往这打电话。铃声一直不断,老姚努力睁开眼,才发现原来是闹钟在响。天已经朦朦亮了,自己怀里却抱着个枕头,而头下的另一个枕头,早已湿了一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