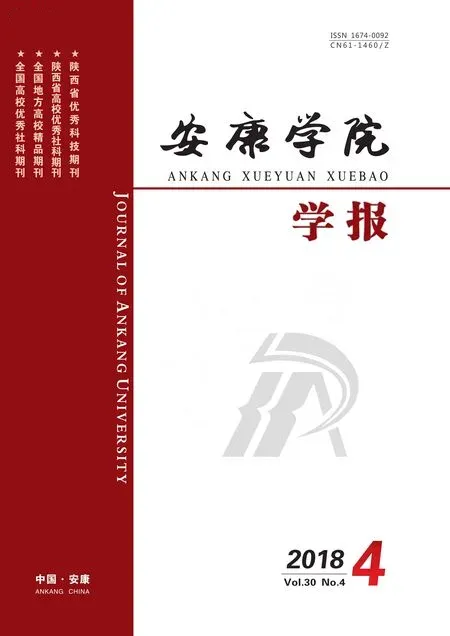美国少数族裔的认同困境与身份构建
——析菲利普·罗斯的“美国三部曲”
2018-01-01汪建丽
汪建丽
(西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一、菲利普·罗斯及其“美国三部曲”简介
作为美国犹太文学领军人物,菲利普·罗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以来已创作三十余部作品。其作品多以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犹太社区、家庭、个体为言说对象,反映了美国犹太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寻找自我归属而不得的生命历程。罗斯的“美国三部曲”包括《美国牧歌》(Am erican Past oral,1997)、《我嫁给了共产党人》(I M arri ed a Com m uni st,1998) 和 《人性的污秽》(TheH um an St ai n,2000)。《美国牧歌》立足于动荡的六十年代,以塞莫尔·利沃夫这一犹太家庭内部文化冲突为基点,展示了一个美国犹太家庭的兴衰。《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围绕艾拉·林格大起大落的生活和他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獗期受到的政治迫害展开故事。《人性的污秽》以1998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一案为社会背景,讲述了科尔曼·希尔克向往不受种族歧视的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而越界的悲剧故事。
“美国三部曲”的基本素材源自于美国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的生活,反映了少数族裔在民族文化和异质文化夹缝中的身份困惑以及各自所选择的不同的身份建构之路。《美国牧歌》中的塞莫尔·利沃夫极力掩饰犹太身份,刻意以美国正统白人主流社会认可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约束自己。《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艾拉·林格身为犹太人,不仅在种族身份上有异于美国主流社会,他的政治理念更是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妻子则冒充英裔白人新教徒,坚决否认自己犹太身份,成为反犹代言人。《人性的污秽》中的黑白混血儿科尔曼·希尔克在饱受种族歧视之痛下冒充犹太人进入主流社会,时时谨小慎微,刻刻处心积虑,最终还是家破人亡。
二、美国少数族裔的认同困境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几乎都对人的问题具有浓厚兴趣。建于三千多年前的希腊德尔斐太阳神庙前有一石刻的铭文:“认识你自己。”个体关于“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追问,从广义上来说,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震荡和精神磨难。“认同”(i dent i t y)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的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认同概念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同一性”概念。他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包括个体对其身份的自觉意识,个体对其性格连续统一体的无意识追求,个体对某个群体的理想和特征的内心趋同。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在其论著中将“i dent i t y”表述为“同一性”,即所谓的认同也就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居于主流地位的强势群体一般不存在认同困惑和身份危机,因为他们牢牢地控制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非主流的弱势群体处于失语状态,他们常常面临认同困境和身份焦虑。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 uart·H al l)所言,文化身份“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与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与权力的不断‘嬉戏’”[2]。
罗斯对于美国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刻体验和洞察,在“美国三部曲”中生动刻画了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犹太人在社会动荡中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和情感历程,深刻反映了这些群体及个体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困惑,剖析了身份危机及其与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宿命性纠结。
《美国牧歌》中塞莫尔·利沃夫的金发碧眼、健壮体格和运动天赋都使他在外形和气质上与正统白人相差无异。他的祖父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来到纽瓦克,在皮革厂恶劣的环境干着苦活;他的父亲成立女士皮件公司逐渐发达。其父辈努力完成自己成功梦想并极力维护犹太传统文化。塞莫尔·利沃夫继承父业,生活富足,追寻并建构着自己的美国梦。他的美国梦就是娶一位漂亮的白人新教徒而非犹太女性,居住在老里姆洛克的石头房子实现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他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新泽西小姐——多恩,并且无视父亲的警告举家搬至老里姆洛克的170年历史的石头房子。婚后育有一女取名梅丽,每当他看到挤着奶牛的妻子和荡着秋千的女儿,倍感幸福,感觉自己完美实现了梦想。他希冀女儿继承家业,沿着他设计的人生道路走向更大的成功。然而,生活在犹太教和天主教夹缝里的梅丽,先是莫名其妙地喜欢尖叫,又成为结巴,继而成为一个极端反战分子,最后在自我弃绝中皈依起耆那教。年仅16岁的女儿梅丽在当地邮局掩埋炸弹将塞莫尔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他的美国梦灰飞烟灭。妻子多恩背叛了他,投靠处处逊于塞莫尔的邻居沃库特,仅仅因为沃库特是新教徒白人,这让塞莫尔深陷失望与落寞,而女儿的所作所为以及自己生活究竟错在哪里更让塞莫尔至死困惑不已。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艾拉·林格出身贫寒,曾做过挖沟工人、侍者、矿工,在二战中成为共产主义者。二战后艾拉因长相酷似林肯成为广播明星并与知名女星伊芙结婚。苦难的经历使他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与自由,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然而,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仅限于客厅的辩论和夸夸其谈。他既不想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却又紧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放。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言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抵牾让他一生大起大落,凄惨而终。
《人性的污秽》更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犹太群体之外的其他少数族裔的认同困惑与危机。科尔曼·希尔克一家在他出生前就住在独门独户的房子里,作为黑人他们能够居住在白人聚集区并非由于享有特权,而是卖房夫妇由于对邻居恨得咬牙切齿才决心将房子售给有色人种以示对邻居的蔑视。科尔曼·希尔克成长过程饱受歧视:最好的白人朋友没有邀请他参加其生日派对;不能和白人学生在同一泳池游泳;白人运动员受伤家人拒绝他献血;在奇斯纳医生的拳击训练馆担任助理,白人孩子恨他、排斥他,不愿意他触摸,有的白人孩子退出仅仅因为有色人种的存在。然而,父母的护佑和哥哥的保护,尤其是他内在的自信和快乐的魅力使他忍受侮辱。他自童年起所向往的就是自由:不当黑人,甚至不当白人——就当他自己,自由自在。同样,出身于法国古老家族的德芬妮来到美国打拼,一心想功成名就荣归故里。她不到30岁就荣升雅典娜学院语言文学系主任,费尽心机想融入学院正统白人主流文化,结果却处处碰壁。她是完完全全独立的、自力更生的,同时她又凄凉地无家可归。这一切令她无所适从,进退维谷。
三、美国少数族裔的身份构建
福柯的自我建构理论认为自我主要通过支配技术和自我技术来构建。前者通过运用规训权力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定义与控制,使其服从并达到一定的目的,从而产生了规范化、可统治的个体。后者使个体内化了那些外塑的规则,凭借自我对自我的控制或认识使自己行为对象化,进而按照外塑的标准实现自我对自我的管理和控制,固定、维持或改变自己的身份。“美国三部曲”的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尤其是犹太人及黑人身处族裔文化与异质文化夹缝中,在不被接受和认可的惶惑与焦虑之下,他们不断地追寻着各自的身份定位,并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自己的身份。
《美国牧歌》中塞莫尔·利沃夫不同于努力维护犹太文化传统的父辈,他竭力摆脱犹太性,致力于完全美国化,做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过一种最简单、最平常的但按美国的标准最了不起的生活。他顺从社会的权力规训,用主流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对什么也没有异议,从不因自卑烦恼,也不因迷惑难受。生活在层层交错的权力网中,他成为自我压抑、自我舍弃的主体,正如其弟杰里就他对权力规训的妥协所言:“你做的一切就是妥协。你总是那么满足,总想找到事情美好的一面。举止适当,默默忍受一切,保持最后的礼节。你是个从不违规的孩子,无论这社会需要什么你都去做”[3]。即便塞莫尔运用自我技术监视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也难以融入美国正统白人主流社会。当邻居沃库特带他参观沃库特家族墓地炫耀其先人的历史渊源时,他意识到自家170年的石头房子没有根基、没有历史关联,根本无法与沃库特厚重的家族历史底蕴相比,他进入美国每走一步前面就有另一步要走,而人家早已经到达。塞莫尔深深迷失于权力所编织的巨型网络,在自我规训中迷失了自我。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中艾拉·林格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的人生、婚姻、政治都满怀憧憬。他通过个人努力和婚姻跨越种族与阶级界限进入上流社会,成功地塑造了令自己更加满意的自我。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言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抵牾使他深陷麦卡锡时代反共热潮的漩涡之中。艾拉之妻伊芙身为犹太人,坚决否认自己犹太身份,选择自我种族清洗冒充英裔白人新教徒。她不但精心编造出身重塑自我身份而且成为反犹主义代言人。她遵循这样的逻辑:“如果我恨犹太人,那么我怎么可能会是犹太人?你怎么可能恨你自己呢?”[4]她憎恨一切和犹太相关事物,甚至听到“犹太人”都会引发强烈的憎恶之情。艾拉与她婚姻破裂之际,她污蔑艾拉为苏联间谍并出版《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终结了艾拉的演员生涯乃至整个社会生涯。她费尽心机运用自我技术构建身份,甚至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将婚姻置于意识形态之中,最后身败名裂含恨而终。
《人性的污秽》中科尔曼·希尔克饱受种族歧视,决心不再服从于权力规训,踏上自我拯救之旅。进入霍华德的第一个星期,他在华盛顿中心沃尔沃买热狗遭拒并被叫做黑鬼。华盛顿特区的黑鬼,霍华德的黑人,这使他深刻地意识到不存在个体身份,“原始的我变成了牢不可破的我们中的一份子,他不愿意和这个身份或随之而来的下一个压迫性的我们沾亲带故”[5]。在霍华德读书期间,他认识斯蒂娜——冰岛和丹麦的美国后裔,其血缘可追溯到克努特王或更加遥远的时代,她是谁,从什么地方来,以及她为什么离家出走都是一清二白。他们相处甚欢,当他鼓起勇气带她回去见家人后,她发现科尔曼黑人身份即乘坐列车返回纽约,痛哭地说:“我做不到!”然后独自一人冲下火车,自此杳无音信。这两件事激化了科尔曼内心深处的身份危机,他不愿意自己的前途被种族这个专制的牌号加以不公正的限制,决心摆脱这个与生俱来的“污秽”身份,冒充犹太人重建自我。他于二战即将结束前在南方弗吉尼亚诺福克海军基地当水手时,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犹太人,又因为它太容易被当作黑人名字,致使他在一所妓院里,被指认为蒙混过关的黑鬼,给撵了出来。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无声的压制、监视性注视和规训性力量在现代西方文化和整个社会范围无处不在。”[6]冒充犹太人后,科尔曼在雅典娜学院担任二十多年古典文学教授并担任院长十六年,年逾七十的他却因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被冠以“种族主义者”撵出雅典娜学院,最终为反犹分子杀害。因为是黑人,被撵出诺福克妓院;因为是白人,被撵出雅典娜学院;因为是犹太人,丧命于反犹主义者之手。人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科尔曼身上得以充分体现,而他的生存困境更是美国少数族裔的真实写照。
四、结语
美国少数族裔经历着激烈的文化碰撞,面临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在探求身份的艰难历程中,他们徘徊于美国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而难得其所。“美国三部曲”刻画了美国少数族裔群体尤其是犹太人及黑人身处族裔文化与异质文化夹缝的艰难处境,展现了这些群体及个体不被接受和认可的惶惑与焦虑乃至自我毁灭,揭露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及其话语统治者所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虚伪性。正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14年针对多起白人警察对黑人滥施暴力发表谈话时所言,种族歧视和偏见深深根植于美国的社会和历史,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2017年8月美国弗吉尼亚州爆发的大规模“白人至上”主义游行更是令美国少数族裔忧心不已。显而易见,实现《独立宣言》所确立的“人生来平等并应有平等的权利”这一理想在美国道路仍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