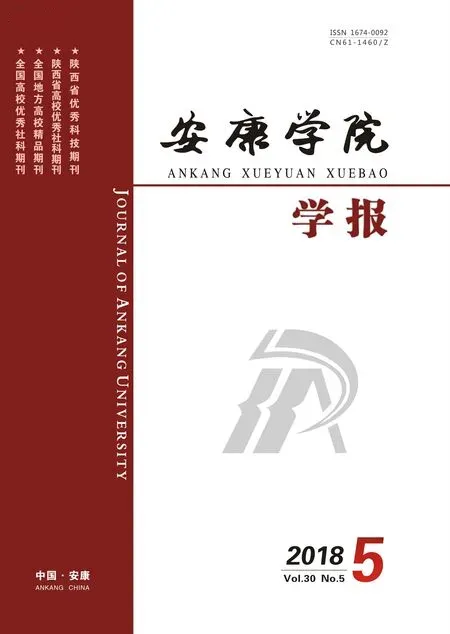想象父亲的方法:评梁鸿《梁光正的光》
2018-01-01王豪
王 豪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梁光正是作为父亲的身份,被描述和赋予深刻内涵的。在梁鸿的创作中,始终聚焦“梁庄”,《中国在梁庄》是庄里的“梁庄”,庄里的中国故事;《出梁庄记》是庄外的“梁庄”,庄外的中国故事;《梁光正的光》是家族里的“梁庄”,家族里的中国故事。这似乎在昭示着梁鸿的某种探索、某种追问。并且,新作在为我们展现家族里的梁庄时,以父亲为中心、焦点展开,在众多父亲群像之中,梁光正无疑是最闪耀的。作为统帅,一切的文学想象都围绕他进行。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儿女叙述者的“悬空”、父亲缺席的在场与大词生描三个层面来阅读她的想象,并通过文本提供的想象,来揭示梁鸿如何讲述家族里的“梁庄”以及家族里的中国故事。
一、叙述者的“悬空”:儿女适当距离的观看
一个有意思且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小说的叙述者“我”,以及包含叙述者的“我们”,在读者随故事深入时,发现“我”超出了自己的预想。不断转移的叙述视角,使“我”不能具体到某个儿女身上。这个不落地、悬空的叙述者,分明是以父亲子女出现的,但当我们排除了勇智、冬雪、冬玉,以至于冬竹时,心中不免疑惑,是否漏掉了小说细节。然而,无论是跟随故事到终了,还是重头来过,其答案是作为儿女的叙述者,没有以具体的人物作支撑,不能实体化。悬空意味着什么,或许需要我们追踪一下整个悬空的过程以获得理解。
小说叙述者第一次明确在场,是在开始的这一章节:“每当有不明就里的亲戚怀着上次见面时的热情来到穰县,并期待有同样的回报时,勇智充满了怜悯。父亲连见都不见。不管我们姊妹几个如何指责他,甚至求他,他就是不见。但是,当勇智姊妹招待得不太周到或不太热情时,父亲又愤怒地指责,说勇智姊妹薄情寡义,不懂感情”[1]13。很明显,这里的“我们”一词是包含式的,已经把叙述者涵括在内,但“我们姊妹”与“勇智姊妹”不仅仅是对姊妹的修饰限定的代词,而且变成了名词。在这里,叙述者“我”似已与儿女群体分别开来了。叙述者明确地在场,但未实体化,这种悬空便显现为由人称变换所造成的张力。它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包括渐次退隐的第一人称叙述。
叙述者第二次明确在场,是在小说里蛮子的章节:“你。你们。冬雪说的不只是勇智了,她也在说冬竹、冬玉。一从‘你’到‘你们’,冬雪的打击面就扩大了,她所要总结和控诉的不只是这一件事情,而是漫长的前半生中所有的事情,这可不是一两分钟能结束的。我们低下头,搓着手,做好持久战的准备”[1]61。这里,冬雪作为反身代词的“我”与排除勇智、冬玉、冬竹的“你们”划开了,点出了内部存在的巨大分歧与矛盾。比较暧昧的是,小说中这样表述:“我们低下头,搓着手,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里出现了话语内部排除冬雪的“我们”,与文本内部包含叙述者“我”即冬雪的“我们”混杂的局面。排除式的“我们”与包含式的“我们”暧昧地并存,进一步加剧和强化了叙述者与儿女实体的疏离。
叙述者第三次明确在场,“父亲拿手抹着眼,他很少提这件事。那个刚生下来就死了的牛儿哥哥在我们的日常感情中没有占据任何位置,冬雪是父亲的大女儿,我们四个是父亲的孩子。没有别人,牛儿也不行”[1]73。当我们结合文本语境,追问“我”是谁的时,给文本补充空缺只能是“冬雪是父亲的大孩子”与“除冬雪外,我们四个是小孩子,而且里面不包括已经死了的牛儿”。那只能说明叙述者的“我”如果作为人物即文本的内叙述者,就只能是小峰。但是,文本到结束也没有小峰的明确发声,他只是作为被看的对象,这就进一步将这暧昧的局面加深。叙述者“我”看似用第一人称在讲述故事,实际上是为了营造某种在场感,第一人称视角名不副实,而只可能是第一人称代词伪装下的第三人称讲述。小说中,本应该是第二、三人称的统统被替换为第一人称。这样做,实际上带来了儿女叙述者“我”的“悬空”。“我”作为叙述者,是存在的;作为儿女,难以具体到某个确定的人。
叙述者“悬空”在小说中并不是一贯的,存在一个程度渐进的过程,因而带来了不同的效果。其一,正如所论及的确定儿女叙述者是谁的过程,是深入了解梁光正父亲形象的关键。在没有父亲直接引用发声以表达自己思想情感时,对父亲的想象更多地落在了儿女们身上,进行想象拼图,这和这部小说的虚构不谋而合。其二,悬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至于作者的意图,除了在叙事创新外,还有可能是某种创作观念的延续或者变化。学者房伟就认为梁鸿小说《出梁庄记》叙述视角很独特:“梁鸿擅长用第一人称亲历者叙事视角,与外视点的第三人称视角。亲历者的视角,形成了内在的反省,而外视点的第三人称叙事,则力争客观叙述事实。”[2]如前所论,本部小说第一人称的视角名不副实,是第一人称伪装下的第三人称视角。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该部小说贴上了首部非虚构小说的标贴,但梁鸿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延续了她在“非虚构”作品中对视角的处理方法。梁鸿首先是以学者身份被知晓的;其次才是其系列围绕梁庄的非虚构写作。她也曾坦言:“我注意到,我总是不自觉地模拟一种情感并模仿鲁迅的叙事方式,似乎只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我才能够自然地去面对村庄。”[3]虚构的首部作品虽尝试创新,但仍难以突破其惯常的叙事手法。她在非虚构系列写作中,便已交织第一和第三人称视角叙述特色。在视角混杂下,亲身在场记述使客观真实性增强。自觉或不自觉地延伸到本部小说写作之中,虽然叙述者“我”是不在场的,落实不到具体人物,但同时“我”又是在场的,处处能看到事件发展的全貌。儿女叙述者们的“悬空”,意味着梁鸿以适当距离在对父亲进行着叙述。
二、缺席的在场:父亲形象的张力建构
小说在展开对父亲梁光正叙述时,他是缺席的,甚至如文本说:“我们并不了解眼前的这个父亲”。父亲,在故事里是不在场的,对父亲行动的记述也都是碎片化的,难以形成一个总体认识。作品一开始就为我们塑造了“寻亲”父亲这一形象。然而,又不能简单地把很少出现人物话语的父亲归类为绝对的缺席。事实上,作为父亲的梁光正是相对缺席的。这种相对的缺席,统统通过儿女的行为体现为在场,他是缺席的在场者。他的缺席的在场是和儿女叙述者的“悬空”相对应的。福柯指出:“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他说什么,而且还在于他怎么说,换言之,话语是否被接受为真理,不仅与它的内容有关,而且还与话语使用的意向有关。”[4]儿女叙述者“悬空”的叙述方式,势必带来不同于常的意义。冬雪家长式的风范、勇智不即不离的关系、冬竹冷静旁观的研究者以及总为父亲闯祸和不省心的小峰,无一不是父亲在子女性格中的在场。
在该部小说中,极少出场的父亲,一个在场的有力佐证就是:子女的性格。此外,由性格影响下的子女行动,是其在场的具体化体现。学者赵毅衡指出:“任何意义传达过程的诸构成成分,必有某些成分不在场,或尚未充分在场。有缺失环节,过程才具有展开的动势。缺席是一种姑且勿论,乐见其变,如长白山天池,边际齐全,即无运动,有缺口才形成瀑布,流成江河。而符号表意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解释意义缺场,解释意义不在场是符号过程的前提。符号等待着解释,意义要解释后才能出现。时间上,逻辑上,解释必须出现在符号被感知之后。”[5]在父亲寻亲及子女行动的意义阐释过程中,父亲是缺席的,这样子女的行动就成了阐释父亲意义的符号化活动。但梁光正并不是完全缺席,子女行动上是由他主导的,只是显在的寻亲中尚未充分在场,或者是在场的缺席。“寻亲”这件事上,冬雪是不情愿但又积极组成“姊妹团”去和父亲寻亲的。她的反对与支持也都最为彻底,往往经过强烈反对之后,回过头来衷心地支持父亲。她顾全大局、孝顺父亲,但不是无条件、百依百顺的。她是经过一番争论,让父亲认识到事情的局面之后主持正义的。勇智始终和父亲保持着适当距离,与父子间很难用言语表达一些微妙情感,这与天性有关。而母子是天然的接近,这刚好同冬雪与父亲的关系相对。但除天性使然外,不即不离的关系里,有父亲的影响在,即父亲的在场,不能只归结于勇智自身的性格。事实上,子女的成长始终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他表示反对意见,让冬雪给他发声。这行为的背后是对父亲的顺从,虽有对寻亲的不情愿,但毕竟没有和父亲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间接表达了诉求。冬玉、冬竹与父亲又产生了一定情感距离。然而,小峰却未在小说中得到自己的出场。不管是父亲寻妻还是小峰的残疾,以及父亲不遗余力地接济等,他只是诱发父亲行动的外在因素。
父亲缺席的在场,与儿女叙述者的“悬空”相应。叙述者的“悬空”是因,而父亲缺席的在场是果。无法具体化的叙述者,对事件的讲述只能是粗线条、一笔带过的。如果对父亲详尽地记叙,就使某个特定的子女成为固定的叙述者。在这固定的视角下,叙述者就只能表述他所知道的,而不能去表述别人的想法。叙述者表达了自身以外的东西,一种情况是叙述者入神入幻,另一种情况则是人物的越界叙述。显然,这样或营造出一种神秘氛围,或违背叙述常识,会给小说造成阅读上的困惑。梁鸿在处理叙述视角时,把叙述者“悬空”,子女对父亲叙述变成了散点透视式聚焦,每一子女都完成了对父亲的讲述,但侧重的点不同。因此,这种视角下,通过父亲缺席的在场,还原了有情有义、立体化的父亲形象。可以说,不同的儿女叙述者完成了对父亲完整形象的建构。整个寻亲围绕他展开,并且子女们或支持、或反对、或顺从的行为也都表现出他强大的“在场”,如光一样无所不在。小说中,与父亲有情感纠葛的女人好几个,但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她们的缺席无一不是完全和彻底的,作为在场的梁光正,这样非但无损于其形象,反而使得形象更加饱满、实在。粗略梗概式的提说与儿女眼中所见两两参互,最终实现了对父亲的想象。
三、大词生描:诚意地修辞塑形
小说语言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单元。作者有意地重复着某些语词方面的因素,这些重复都潜藏着一定的文本意图。我们试图挖掘这些重复点,来还原关于父亲的想象。冬雪的连语,一些场合的大词、姓名的“大”写的结构安排,都在修辞上完成对父亲形象的塑形。
冬雪的连语述说,整段整篇没有标点,仿佛一口气要说出千万言。这样的话语流,其内容可能没有多少价值,但其背后语气态度却值得去挖掘和重视。内容没多少价值的原因在于,该部小说不是意识流小说,因此不必去仔细分辨说了什么,而应当重点抓住出现连语的文本语境。这种类于意识流的话语流,都出自冬雪之口,且都是抱怨或者诉苦的文本语境。她用长段的话语流,表达不满寻亲的同时,怨气也随这股来势汹汹的话语流而消散。因此,冬雪立场动摇最快是有原因的。她陈说方式在实际效能上已把怨气发泄殆尽,剩下心力也只可能是顺父亲的心思。另一个隐蔽的原因是,子女如此这般不留情面地批驳,触犯了父亲的权威。在中国社会伦理下,不管抱怨也好,陈述事实也罢,已经使得原本平衡的局面失去了常态。因此,作为心理的补救与代偿,她也只能通过追随寻亲来弥合。
词语的选用上,某些场合下的词语用到围绕寻亲展开的行动时,都呈现出了“大”的色彩。革命词汇、战争词汇、官方公文词汇等一系列词汇,覆盖了寻亲始末,甚至对父亲死后的评定。这些词语使得平凡的生活化场景,有了不同的色彩。这是对常态生活场景的一种戏拟。这种带有戏拟色彩的词汇,已经和新的场景融为一体了,同时也就没有了讽刺意味,完全带给人的是一种新奇和鲜明的感觉。父亲行为的“土”,与词汇描写意义的“洋”之间形成了张力,贴切地塑造了有理有情的父亲形象。比如,小说在刚开始,说到勇智的打扫、浇花、扩胸、举哑铃时用了一个“章程”。父亲为了使子女同意并跟随其寻亲,动员时都要讲一个故事,词语用了“版本”,而且把毫无头绪的寻访的这件事用了“寻亲工程浩大”这样的字眼。再有,在蛮子这一章节中,为了说明女儿冬竹对父亲特别上心,用了一个“研究”,“冬竹研究了一辈子,还是研究不透父亲”。同是这一章节,描述父亲以前被人排挤和斗争的事时,用了一个“光辉岁月”。这样含义颇为庄严、雅正的词用在小人物的小事小情上,实现了一个场合向另一个场合的迁移。我们只清楚的是后一个场合,即小人物的行为举止的大词描述场合,它是确定的、唯一的。然而,这些词本身适切的场合却是不定的、多样的。传统意义上的戏拟,是带有反讽意义的。然而,这里因词语迁移和引用的戏拟,运用比较分散且没有实际内容确指,所以它的修辞效果不是反讽的。当剔除可能隐含的反讽意味后,词语生动、适切的修辞效果突出了,使行为者的动作、事件的评述更加地透辟。除此而外,这些大词却都指向一个核心人物:父亲梁光正。直接地评述或间接地通过子女行为状态评述,都始终围绕着这个核心。这说明子女对父亲的认识,是深刻而又贴切的。因为这些大词,已经在超越场合的情况下,对另一场合进行了适应,这必然是深入、形象与生动的。同时,围绕这个核心,尽管每个子女为我们拼贴了父亲的形象片段,但完整形象始终是难以穷尽的。每个片段下词语的移用,已经说明父亲形象之复杂。这也巧妙地和小说主题产生了隐秘的关联。光,是不可追寻的,且围绕发光体始终在扩散。父亲的生命情感就是这种光,爱情、亲情、友情是一道道强有力的光束,在时刻照耀着他的世界以及世界里的每个人。这里面所有“大”属性的东西,只不过是父亲生命能量之光的外化而已,它们都有机地统一于父亲的想象之中。
名字的称呼上也同样出现了某种“大”的意味。小说前面的各个章节,从未直呼父亲的名字,而在葬礼章节,开篇的第一句“梁光正躺在前院客厅的地上”就开始了对他名字的称呼。与此同时,几个子女也都被冠以“梁”这个姓氏,似乎随着父亲梁光正的离去,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都是大写的了。但是,巧艳妈、蛮子、小峰都始终没有姓,前来追悼的人被“有些”这样的词汇进行了分类。称呼的变化可能隐含着某种重要的信息,不同人的分类可能也隐含着某种特别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对长辈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也是不应该的。无论所称呼的对象是否存世,这样的做法都不应该,但一种情况就是墓志铭,属于盖棺论定式的总结,是可以称呼的。但在为尊者避讳、为死者避讳的文化心理下,这种盖棺论定式的叙述者,是不会出现在儿女叙述者之口的。前面我们论及所谓的儿女叙述者是“悬空”的,是不能确指和具体化的,而这里将所有的“梁”姓氏大写,则进一步把可能“悬空”的儿女叙述者排除在全知的叙述者外。与之相应,这或许是真正隐藏的叙述者,确证其身位的一种方式,通过排除可能的,进而确立自身。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时,文本之中是难以发现确切的叙述者的。可能的儿女叙述者以及看似定论式的评说,实质上都未能指出确定的叙述者。梁鸿在写作中的新探索,对难以穷尽的父亲形象,是最适切的叙述。
综上,梁鸿架起了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桥梁,纪实性在小说中与虚构性密切地融合在了一起。悬空,处置了客观叙述与主观想象之间的矛盾,在真实可感的故事框架下完成了对梁庄里父亲梁光正的想象。同时,由于客观叙述,父亲极少用直接引语来发声,而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儿女们的行动展开了对父亲的塑形。最后,服务于两者的大词的文本修辞,在集中指向父亲梁光正想象的同时,叙述者具体确指成了一个谜。这巧妙地回应了主题,父亲的光,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穷尽父亲的想象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