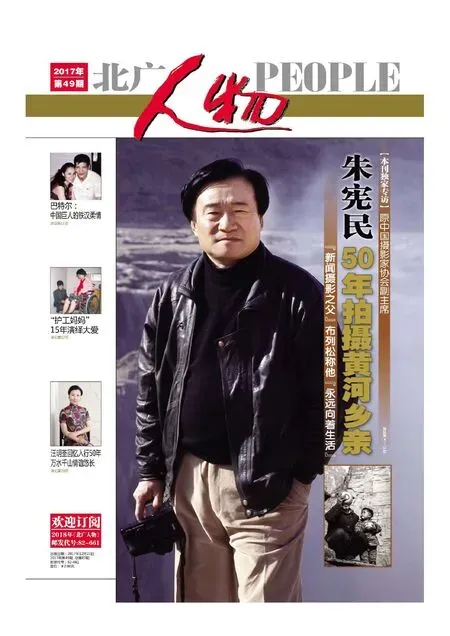【第十七辑】17 清末的京腔儿旗人话
2017-12-25
【连载·《北京话》】
【第十七辑】17 清末的京腔儿旗人话

《北京话》作者刘一达

插图李滨声
满足进入北京后,学说汉语北京官话,又把自己的满语音韵和发音习惯、特色文化词汇带入自己的满式汉语,经过上百年的融合,在清末形成了满汉语言成分融合的京腔儿旗人话。
老舍先生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里写道:“至于北京话呀,他(指书中旗人“二哥福海”)说的是那么漂亮,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语词收纳在汉语中,而且创造了一种清脆快当的腔调。”老舍先生说的正是带京腔儿的旗人话。
这种满语和北京话的融合,成为了现代标准的北京语言。满语的发音无声调,汉语的发音有声调,二者是有区别的。满语的词儿进入汉语后便有了声调,所以味儿也就变了。比如满语haicambi,其词义是“查看”,进入北京话,说成baicha,“掰哧”意思是“搜查”,“翻检”。
满语balai,义为狂妄。进入北京话就说成balie,“巴咧”,意思是“胡言乱语”,通常说“胡诌巴咧”。
满语 cangkai,义为“随意”,“只管”。进入北京话,说成 changkair,“敞开儿”,加儿化韵,意思仍然是“随意”,“尽管”。
有些满语,进入北京话后,原来的意思被扩展了,有的意思也变了。比如:现在北京人爱说的一个感叹词:yaohe,“呦喝”,就来自满语的waliyaha。它也是感叹词,但原来的意思是嘲讽讥笑。
又如 lata,“邋遢”,来自满语letelata。原意是“衣服破旧往下垂”或“累赘”。进入汉语后,意思变为“不利落”或“不整洁”。
再比 如 gezhi,“咯 吱”这个词,来自满语的gejihesembi。但这个词在满语里的意思是人们相互之间闹着玩儿,挠对方腋下或下巴颏的痒痒肉,使人发笑。进入汉语后,其原意又被扩展延伸了。现在这个词,在北京土话里除了原义外,还有“犯坏”,“给人使阴招”的意思。
因为清朝实行的是满汉分置,所以,住在外城的汉族人说的是正根儿的北京方言土语,而住在内城的旗人说的是融入了满语的北京话。在清朝三百年多间的语言交融过程中,这种区别虽然越来越小,但是有些方言土语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只有地道的老北京人才能听出两者之间的差别。比如“取灯儿”(火柴),南城人说灯字重,听起来好像没有儿化韵,北城人说灯字轻,儿化韵明显。再比如说“这人说话口罗嗦。”南城人会说:“这人说话勺叨。”北城人则说:“这人说话絮叨。”
这种差别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我小的时候,就明显感到住在菜市口、虎坊桥和花市的人,跟住鼓楼、什刹海、东单的人说话不一样。比如菜市口、虎坊桥、花市一带的人,管散步叫“拿弯儿”,“出去散步”说成“出去拿个弯儿”。北城的鼓楼、什刹海、东单一带的人则说“出去遛弯儿”。
我跟著名北京琴书表演艺术家关学曾先生是忘年交。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想写他的传记,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我每个礼拜至少有三天,到他家跟老爷子聊天,聊到中午,他必留我在家吃炸酱面。老爷子亲自下厨炸酱,他炸出的酱,是地道的老北京“小碗儿干炸”,让我齿留余香,百吃不厌。
有一次,我们爷儿俩一边吃着炸酱面,一边聊天,他对我说:“听过京剧《武家坡》吗?”我笑道:“没听过。”他说:“那出戏里有一句唱词儿:‘站立宫门叫小番。’这‘叫小番’三个字是突然上扬,甩出高腔,行话叫‘炸腔’。可是你知道戏迷管这叫什么吗?”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嘿然一笑:“炸酱!”我忍不住笑起来:“‘炸腔’变成了‘炸酱’。太逗了!”关先生笑道:“就是不能拌面吃。”
关先生的祖上是正蓝旗,住在阜成门一带,是地道的老北京,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北京土话。在跟老爷子聊天时,我发现北京南城人说的“压根儿”(北京土话:原来),到他嘴里就变成了“迄根儿”或“地起”。
其实,民国以后,北京已经没有内城的城里和城外之别了,这儿说的语言上的差别并不明显,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东西城的人口和南北城的居民流动日益频繁,这种区别也逐渐淡化了。当然,现在许多老北京人已经搬到城外住了,这种区别已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