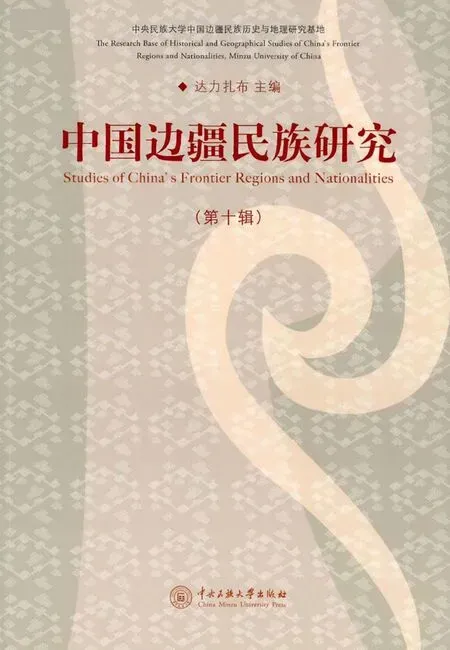东丹国南迁时间新探
2017-12-18耿涛
耿 涛
内容提要:东丹国南迁系契丹开国重要事件,事关耶律德光与耶律倍的政治斗争等诸多问题。耶律羽之墓志出土前,学界未对《辽史》所载的东丹国南迁时间产生质疑,但之后却一边倒的倾向于志文所载时间,皆因志文成文更早,缺乏深入的考辨。实际上志文所载的时间与东丹国南迁的事实有着诸多相悖之处,东丹国南迁时间仍当以《辽史》所载时间仍为准。
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因其成文时间一般早于史籍成书时间,更贴近历史“发生现场”,其价值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尤其对于史籍记录阙略的辽史研究来说,更是钥匙般的存在。1992年耶律羽之墓志的出土打开了东丹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根据志文丰富的内容,很多学者得以对史籍记载进行勘正。然而,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对墓志过度的推崇导致了对志文内容的盲从,形成了一股志文即信使的研究“潮流”,忽略了对志文内容客观的审视。
对于东丹国南迁这一重大问题,很多学者依凭志文内容订正了东丹南迁的时间。盖之庸先生提出:“羽之墓志中将进表年代明确于天显四年,国迁和升南京之事也当在其后。东丹国迁都时间当以墓志为准”。①盖之庸:《耶律羽之墓志铭考证》,《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齐晓光先生也曾提到:“其一,史载皆称天显二年进表,三年国迁,升南京的年份亦随之误载。墓志则将进表年代明确为天显四年,国迁及南京升设当于其后”。②齐晓光:《耶律羽之墓志对文献记载的堪补》,《文物》1996年第2期。然按志文所载的时间去推导东丹国南迁一事,会发现很多自相矛盾的事情,再联系朝鲜文献所载的渤海遗民迁徙记录,仍会发现志文的“天显四年”说存在问题。③《高丽史》和《东国通鉴》两本朝鲜文献均对渤海国遗民迁徙活动有过记述,详见下文。故此,在东丹南迁始末尚未完全搞清,仅凭志文一词便将迁都时间敲定的做法无疑有些操之过急。还有,为了夸大墓主人的功绩,志文混淆事实的情况屡见不鲜,耶律羽之墓志并非无懈可击,《辽史》的记述仍可视为信史。④对此问题,刘浦江先生也对志文记载的迁都时间表示怀疑,认为还应以《辽史》所载时间为准,但未有进一步论述,详见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3页。
一、史籍与志文的异同
关于东丹国南迁起始年份,以《辽史》为主的文献具体记载如下:
“天显三年十二月,时人皇王在皇都,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瞻而隶属之。升东平郡为南京。”①《辽史》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0页。
“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尽迁其民。又置卫士阴伺动静。”②《辽史》卷72,第1210页。“太宗即位,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东土,择贤辅以抚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国家利害,敢不以闻。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邀,即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乘其微弱,徙迁其民,万事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鱼之饶,必安居乐业。然后选徒以翼吾左,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表奏,帝嘉纳之。是岁,诏迁东丹国民于梁水,时称其善。”③《辽史》卷75,第1238页。
“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④《辽史》卷38,第456页。
而墓志则有着不同于史籍的记载:
耶律羽之墓志第13至15行载:“以天显四年己丑岁,人皇王乃下诏曰:‘朕以孝理天下,虑远晨昏,欲效盘庚,卿宜进表。’公即陈:‘辽地形便,可建邦家。’于是允协帝心,爱兴机构,公夙夜悟,退食在公,民既乐于子来,国亦期年成矣。”⑤齐晓光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附录《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文物》,1996年第1期。仔细比较《辽史》与志文的异同会发现,对于迁都结束时日的记载基本无差,均是天显五年结束。⑥志文所载的是天显四年开始,并期年而成,结束日期应不晚于天显五年。而以《辽史》为主的文献记载的东丹国南迁也是天显五年方才结束,因为天显三年十二月升南京并不意味着南迁活动彻底结束,据《太宗本纪》记载,直到天显五年,仍有“诏修南京”的举动。故以往研究将升南京作为南迁一事的终点是存在问题的,其实天显五年耶律倍的归国才是南迁一事的终点。真正的差异在于对起始时间的记录,史籍所载的东丹国南迁开始于天显二年,而志文所载的起始时间则是天显四年。针对史籍与志文存在的时间差异,刘桓曾根据《太宗本纪》的记载这样解释道:“东丹人皇王下诏及耶律羽之上表迁东丹民,均应是天显四年(929年)事,也许其事发生在是年年初,故误记在天显三年十二月”。⑦刘桓:《关于契丹迁东丹国民的缘起》,《北方文物》1998年第1期。刘氏将升南京与迁都的时间混淆,将二者视为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殊不知,升南京发生于迁都之后。《太宗本纪》这段描述的记史笔法确实容易引起误会,乍读下似是在叙述耶律羽之上表一事,但其实这段史料要记述的是升南京的事情,“时人皇王在皇都,诏遣耶律羽之迁东丹民以实东平”均是“升东平郡为南京”一事的背景陈述。也就是说,《太宗本纪》的记载与《辽史》其他记述的时间线是一致的,均是天显二年羽之上奏,三年升都城为南京。故此,志文与史籍记载相差的时间不是一两个月,而是一两年之久。
这样一来,按志文记载,迁都起于天显四年,并且“国亦期年成矣”,也就是说,东丹迁国从开始到事毕堪堪一年之久。而与之大相径庭,按史籍记载,天显二年,羽之上表,三年迁都,直至五年方事毕,耗时则长达三四年之久。
那么造成两者记录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两者的记录哪一方更可靠呢?对于这些问题,不妨将两种时间置于历史语境下顺势推导,露出破绽的自然是伪造的记录。
二、基于历史事实对志文所载时间的质疑
东丹国南迁后的都城,即后来辽东京,其规模十分宏大。据《辽史·地理志》记载:
城名天福,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八门……宫城在东北隅,高三丈,具敌楼,南为三门,壮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墙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内建二殿,不置宫嫔,唯以内省使副、判官守之。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在宫门之南。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驸马寺,铁幡竿在焉;赵头陀寺,留守衙;户部司;军巡院,归化营军千余人,河、朔亡命,皆籍于此。①《辽史》卷38,第456页。
虽然阿保机曾于神册四年对辽阳故城进行修葺,“二月丙寅,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②《辽史》卷2,第15页。但要宫城达到《地理志》记载的那般规模,自然需要长时间的修缮扩建。③显然,《地理志》的成书时间要晚于天福城的兴建,《地理志》的记载可能反映的是经过后世扩建之后的城址状况。但是地理志中提到了“大东丹国新建南京碑铭”,该碑是耶律倍归国后修建的,并且后文又提到了该碑“在宫门之南”,也就是说在当时天福城的内城已经建好,故其建设施工耗力之大仍可见一斑。故此,志文所载的“国期年而成”不免让人质疑,因为仅一年的时间从提议迁都到建出规模如此之大的宫城,时间很明显是不够用的,而如果按照《辽史》记载的时间来看,则充裕很多,至少不似志文那样“匆忙”。
除宫城的建制外,更让人不解的是,迁东丹国不仅仅是将都城迁走那么简单。这次迁都将渤海旧有州县几乎全部整体性迁移,于梁水流域重新置地建制,原住民也随之迁徙,“辽志东京道诸州县云,本渤海置,或本渤海某州某县者,除鸭渌府各州外,皆已南徙,语具地理考。此即天显三年,移东丹民,以实东平之事也。言东平者举一以赅其余,实则南迁之渤海人,已布满于东京一道矣”。④金毓黼:《渤海国志长编》,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第363页。有学者曾就此问题统计到:“从上述情况可知,辽东京道地区可以查实的由东丹国移民而置的州县,涉及原渤海国的二十九个州、三十九个县,大体六十八个行政区域,其中二十个有明确的户数记载,总数达二万一千一百户,其余州县的户数,史书无载。无户数载记的州县可能人口并没有上述二十州县稠密,但因其数量较多,所以保守估计,按照有户数记载州县户数的3/2估算,其余四十八个州县约安置渤海移民三万户左右。若按每户五口推算,那么被迫移民至辽东京道的渤海移民总数约为二十五万余口。”⑤孙炜冉:《辽对渤海人的移民即安置》,《博物馆研究》,2015年第1期。
王承礼先生则认为在东丹国南迁时迁入东京道的渤海人,约有四十余万人。⑥王承礼:《渤海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虽有争议,但不妨碍我们看出迁都事物之巨大,但如此庞大的工程量在志文的记录下却如不费吹灰之力一样,仅一年便完成了这一“壮举”。尤值得注意的是,志文记载的是天显四年耶律倍才开始下诏书,并不是迁都正式开始,就算耶律倍于正月即下诏,但由耶律倍下诏给耶律羽之,再到耶律羽之请表耶律德光,最终耶律德光决定迁都,这期间自然又会消耗不少时间,也就是说,若按志文所载的时间,实际迁都时间一年都不到。这不禁让人疑惑,时间这么紧迫,迁都工程量又这么大,志文所谓的“期年国成”是怎么实现的呢?如此看来,史籍记录的时间明显更加客观,更贴近迁都徙民这一所需时间甚多的工程。
总体来看,志文所载的内容明显与宫殿的建制以及迁都的规模格格不入,与之相反的是,史籍的时间线与两者的契合度颇高。
三、徙民活动反映出的东丹南迁日期
根据《太宗本纪》的记载可知,迁都一事引发了大规模的徙民活动,故徙民兴起之时自然是迁都进行之时,这便为找出东丹国南迁起始时间提供了一个解答方向。
《辽史》记载了渤海很多遗民逃奔新罗的历史,按图索骥,不难发现《高丽史》对该阶段逃亡到高丽地区的渤海遗民有着更加详细的记录,根据《高丽史》所载:
高丽天授八年九月丙申,渤海将军申德等五百人来投。庚子,渤海礼部卿大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谟、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民一百户来附……十二月,戊子,渤海左首卫小将冒豆干,检校开国男朴渔等率民一千户来附;十年……三月,甲寅,渤海工部卿吴兴等五十人,僧载雄等六十人来投;十一年……。三月,甲寅,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七月,辛亥,渤海大儒范率民来附……。九月,丁亥,渤海人隐继宗等来附;十二年……六月,灰申,渤海人洪见等,以船二十艘载人、物来附。……九月,丙子,渤海正近等三百余人来投;十七年……七月,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十二月,渤海陈林等一百六十人来附①郑麟趾:《高丽史》,世家卷,奎章阁藏本影印版。
孙炜冉还根据同为朝鲜文献的《东国通鉴》制作了下表:
渤海亡国后渤海遗民第一次流入高丽高潮期的情况(部分,有删减)②孙炜冉:《渤海国遗民及其后裔流入朝鲜半岛诸事考》,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编:《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5辑,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2页。

序号 时间 流亡者 人数1 925年(九月初六) 将军申德 500人2 925年(九月初十) 大和钧、大元钧、大福谟、大审理等 100户(以每户5口计)3 925年(十二月廿九) 冒豆干等 1000户4 927年(三月初三) 吴兴、僧载雄等 50+60=110人5 928年(三月初二) 金神等 60户6 928年(七月初八) 大儒范等 ?7 928年(九月初五) 隐继宗等 ?8 929年(六月廿三) 洪见等 二十船人(以每船100人计)9 929年(九月初十) 正近等 300多人
两者文献所记载的人物与人数基本无异,可见基本为同一史源。可以看出,渤海国被灭前后曾引发一次徙民浪潮,东丹国建立后这一趋势有些减缓,但到928年开始再次出现徙民浪潮,并在929年达到高潮,继而又归于缓和,直到934年才又出现大规模的徙民记录。928年再次掀起的徙民浪潮与《辽史》所载迁都造成的大量徙民情况不谋而合,①由于史籍记录的问题,很多民众自发性的零散迁徙很可能未被记录在内,所以无论是总体人数还是具体年月的人数均应在此之上。大量的渤海遗民苦于迁都之事,无奈背井离乡,逃奔高丽。但由于迁都并非一蹴而就,而且遗民的迁徙又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这次浪潮发端于928年,在929年达到顶峰并迅速结束,这个趋势充分体现了迁都一事由起到兴的全过程。所以志文中所载的天显四年只能体现这个趋势的峰值,并不能体现出这一趋势的起始点。即在天显四年之前,已出现了徙民浪潮,徙民的事实与志文所载的时间是相悖的。
故仅从徙民情况来看,志文所载的天显四年系东丹国迁都开始年限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而史籍所载的时间则相对更为准确。
四、结论
综上所述,志文的记录并非属实,但志文的记载为什么会出错误呢?
答案其实在志文里面即可找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志文对耶律羽之在迁都过程中的表现不吝滥美之词,甚至捏造出“民既乐于子来”的太平局面,虽然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因诏困乏不能迁者,许上国富民给瞻而隶属之”。②《辽史》卷3,第30页。所以说,志文所载的天显四年很可能是为了凸显耶律羽之的功绩而故意缩短了时间,是为了满足“期年国成”而作的讳笔,但由于东丹国南迁事毕的时间比较固定,只能在起始年份上“做手脚”,故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体现耶律羽之能够在一年之内完成如此大的功业所做的谀墓。③之所以说东丹国南迁一事结束时间比较可靠固定,是因为东丹王耶律倍于天显五年十一月就南逃后唐了,此前他归东丹国后,曾诏令修碑铭,筑楼藏书赋诗,这都消耗了大量时间。如果时间定在天显四年,又不能期年而成,那么这些既定史实则需要全部延后,故不可能起于四年。所以,天显四年是为了凸显期年国成而做的伪史。
进一步说,《辽史》所载的迁都时间正好发生于耶律德光刚刚继位之时,耶律倍刚刚失位,心存不满,若让耶律倍归国无异于放虎归山。故德光选择在此时迁都,此时迁都不仅可以把耶律倍在东丹国的势力连根拔起,更终结了他争位的可能。所以说,德光甫立便将耶律倍控制在身边,另一边遥控心腹耶律羽之去操办迁都一事。迁东丹国是辽太宗巩固皇位的一个重要环节,并非独立事件,所以将其置放在辽初历史大背景之中会发现,《辽史》记载的时间更加符合事态的发展,而志文的“天显四年”说实难以立脚。
依靠墓志堪补史籍之遗确是治史的好方法,但无论何种方法均有一个度,过度盲从于志文记载自然会出现“尽信书不如无书”的状况。针对墓志提出的质疑,目的不在于否定志文的价值,而是旨在唤起对墓志的重新审视。无论何种墓志都不是无懈可击的,直接引志文内容为信史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