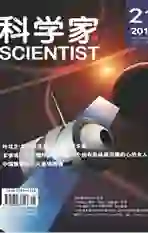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一个拥有晶体般闪耀的心的女人
2017-12-14小时
小时
诺贝尔奖从1901年设立,迄今为止已经有800多人摘取了这一举世瞩目的桂冠。在人们的印象中,男性一直是诺贝尔奖的主宰,而女性获奖者则是凤毛麟角,获奖的女性——尤其是在科学类奖项中——不足5%。我们也许会对居里夫人的名字耳熟能详,但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这个名字又有多少人知道呢?而她——英国杰出的女化学家,就是那个在居里夫人光辉名字之后第三个拿到并且独享化学奖的女人。
独立精神的根源
对于每个人来讲,家庭是成长的摇篮,童年是人生的起点。
多萝西的父亲约翰·温特·克劳福特与家族成员一起,生活在贝克尔斯一个繁荣的小镇上。家族里的幼子们当牧师几乎成为一个传统。但约翰·克劳福特没有选择家族中任何一种传统职业。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古典学专业,是布雷齐诺斯(Brasenose)学院的高材生,1896年毕业时得到了高级休姆奖学金。这使他得以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游览希腊、塞浦路斯和小亚西亚(今土耳其),同艺术史家约瑟夫·斯特雷高斯基一道发掘早期的基督教堂。他在英格兰那朴素庄严的哥特式教堂建筑艺术中成长,对那复杂明快的拜占庭式嵌花设计颇感新奇。地中海东部的景色、声音和民族也令他着迷,使他沉浸在衰亡中的奥托斯曼帝国的文化里。回到英格兰之后,他暂时在伯明翰大学做古典学讲师,但很快便为了重返中东的机会而放弃了正式的学术生涯,并在多年后最终成为了一位研究古典艺术品的学者和考古学家。
约翰·克劳福特与妻子的相遇是在一次舞会上。格蕾丝·玛丽·胡德(Grace Mary Hood,人称茉莉)生于1877年,她的父亲辛克莱·胡德(Sinclair Hood)是林肯郡的一位乡绅,她是家中的长女。茉莉曾在巴黎的一间女子进修学校念了一年的法语、音乐和绘画。茉莉的兴趣广泛,既喜欢骑着马带着猎狗去打猎的这种乡间绅士活动,又喜爱音乐和舞蹈的这种优雅的淑女活动。茉莉是田野俱乐部的积极成员。1906年,俱乐部考察一个洞穴,寻找据说可能生活在那里的盲甲蟲。但茉莉听说这地方也以新石器时代的遗迹著称,便决定做进一步调查。在考察中,茉莉不畏困难,在当地少年的帮助下,找到了人类骨骼、加工过的打火石、骨制的坠子。她还多次造访这个洞穴,与当时顶尖的史前文化专家通信讨论自己的发现,最终得出这个洞穴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结论。
为了奥托曼帝国的文化而放弃学术生涯的约翰·克劳福特与美丽坚韧的茉莉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重视学习与智力探索的价值,而看轻社会地位或规矩习俗,也正是因为这种默契,二人在1909年7月结婚。1910年5月12日继承了父母优良基因的多萝西·玛丽·克劳福特(多萝西·克劳福特·霍奇金是她婚后的名字)出生。
多萝西还有三个妹妹,多萝西出生后的头4年里,一家人享受着悠闲的生活。他们舒适地住在开罗,“住的地方可以看到金字塔”。为了避开埃及炎热的夏天,每年多萝西的母亲茉莉都会带着她和妹妹们回英国过上3个月。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这种有规律的生活终止了。茉莉相信英国会比任何海外国家更安全,所以将女儿们带到了英格兰,自己回到开罗陪伴丈夫。
在多萝西余下的童年里,她和妹妹们与双亲同住的时间从未连续超过几个月,且总要在长久的分离之后才能有一次难得的相聚。多萝西后来认为,这种分离所磨练出的自立,是“她的独立精神的根源”。
当多萝西因使用X射线衍射技术,研究测定出青霉素及维生素 B12等复杂晶体和大分子空间结构而荣获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获得这项殊荣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女科学家之一时,她深深地感谢自己那个虽不富裕但却和睦幸福的家庭带给自己的一切。
“我这一生为化学晶体所俘虏”
多萝西·玛丽·克劳福特在一间小小的私人课堂里开始了她的科学生涯。来自安布尔塞德的夏洛特·梅森(Charlotte Mason)小姐创立了全国父母教育联合会(ParentsNational Education Union)成为地方政府建立的学校之外的另一种教育孩子的方案。教学大纲规定给12岁以下的孩子上课,这套课程包括一个学期的物理和化学。多萝西10岁的时候进入了这样一个小课堂,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制取明矾和硫酸铜溶液,用以生成晶体。在此后的几天里,她们瞧着溶液慢慢蒸发,晶体逐渐显现,像珠宝一样有着许多切面,闪耀着光芒。多萝西被这个景象迷住了,“我这一生为化学和晶体所俘虏”,她后来这样写道。为了满足女儿对于晶体的浓厚兴趣,多萝西的母亲为她在阁楼布置了一间实验室,任由多萝西做实验。“倾斜的屋顶,一扇小窗,角落的一张木橱里搁着多萝西的藏品:父亲发掘出来的罐子碎片,苏塞克斯唐斯(Sussex Dsowns)的打火石,鸟蛋,冷杉的球果。桌上有一架试管,和其它一些化学器皿。瓶子里装着各种晶体、粉末和溶液,是她做实验用的。她屏住呼吸,把小小的酒精灯火焰里的白金丝转了一下,它的一端渐渐出现了一个彩色的珠子。”那年多萝西11岁。
18岁的多萝西不负父亲的期望,于1928年考入了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学习化学。同年,她的父亲在非洲发现了一个地下古教堂遗址。这座古教堂建筑华丽、装饰优美、雕刻精致,需要做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因此多萝西也被父亲分配担负一部分玻璃镶嵌物的登录、绘图工作。这项在其他人看来繁琐而枯燥的工作,在多萝西眼里却十分难得。她认真地投入到其中,并利用牛津的实验室对这批五光十色、瑰丽多彩的镶嵌物的化学成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鉴定,取得了许多极其难得的数据。这份整理研究工作虽然辛苦,但多萝西却从中得到了无限的乐趣,萌发了对结晶学这门学科的憧憬和爱好。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努力追随赫伯特·马库斯·鲍威尔(Herbert Marcus Powell)教授学习结晶化学,并在实验室里独自进行一些探索性的试验。因此在牛津当学生时,她在结晶学方面就已经小有名气了。
不过,世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牛津这所古老的学府当时保守的学术思想,致使更多的毕业生不能够留下来搞科研工作。就此,多萝西在她父亲朋友约瑟夫的介绍下到剑桥大学与贝尔纳教授合作。当时的贝尔纳已成为第一批用X射线晶体学研究生物分子的人之一,最关键的是,他用这一技术解决了有机化学家之间关于固醇——许多生物分子(如某些维生素和性激素)以固醇为基础——结构的争端。这也正是多萝西想要做的工作。
贝尔纳善于使用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来研究重要的复杂的有机分子。贝尔纳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导师,他组织了一批有朝气的科学家来研究特定的技术。在贝尔纳的小组里,多萝西大概是最有天分的,不过多萝西比贝尔纳更为专注,因为贝尔纳后来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史学研究,并写出了经典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当多萝西开始她的研究时,晶体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它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的交叉科学。贝尔纳给了初出茅庐的多萝西以必不可少的点拨,还慷慨地让多萝西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他的论文上。他们记录了一个球型蛋白的第一个X射线衍射模型。通过与贝尔纳的合作使多萝西在一批打破化学与生物学界限的科学家中处于最突出的位置。
1964年,多萝西荣获诺贝尔化学奖,她的女性身份备受关注。她是史上第五位,也是英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科学家。英国的《观察家报》(Observer)在一篇特写报道中说,“看上去和蔼可亲的家庭主妇”霍奇金夫人“因为一项完全不属于家庭主妇的技能”而获奖,这项技能是“寻找有重要化学意义的晶体
结构”。
她为世界而生却情倾中国
多萝西是一个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女性。她没有敌人,即使在那些科学理论被她推翻、或政治见解与她对立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如同她的X射线照相机展露了事物粗糙表面下的内在美,她待人的温暖与亲切展露了人们——即使是最冷酷的科学骗子——内心深处某种隐藏的善良。
她在埃及、苏丹等几个国家生活和接受教育,加上母亲的影响,所以多萝西一生都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推动国际和平和理解,虽然为此她受到舆论的批评指责——说她宣传共产主义,但是她仍然坚持推动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和理解,并乐此不疲,直到生命终结。
以往,我们只要一谈到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时,常常提到我国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的牛胰岛素结晶的重要成就,但很少人提到多萝西对我国学者那诚挚热情的帮助。
当年,廖鸿英、唐有祺、梁栋材这几位研究胰岛素的科学家,都曾经先后在牛津大学多萝西的实验室工作过,得到过多萝西的悉心指导。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时,多萝西与英国一个观礼团来到我国。她最关心的就是与廖鸿英等中国科学家的会面。因为当时在西方杂志上是不允许中国人发表文章的,这次与中国科学家的会面,对于多萝西而言,能够听到中国科学家对于胰岛素的研究,是这次非凡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
1965年,多萝西到日本进行为期两周的讲座,在旅途中她又迫不及待地顺道访问了中国。因为她知道中国有一个小组在尝试合成胰岛素,她还知道,如果她不来中国,谁也不会知道中国小组的进展。所以当她到上海以后,得知这个小组成员王应睐等人已经合成了牛胰岛素,但是和美国、德国的小组一样,也还没有成功地使之结晶。多萝西热情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并强调了X射线分析对于比较天然胰岛素与合成胰岛素结构的重要性。
一年后,多萝西又尝试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在埃克塞特大学举行的一个会议,并提出要承担这次旅费的支出。那时的中国正经历“文革”,所以中国科学院谢绝了多萝西的邀请。但即便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研究胰岛素的小组也将这项工作坚持了下来。据当时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顾孝诚回忆说,这项研究能坚持下去的唯一原因是:“政府说‘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也要继续进行一些基础研究,以表示我们对促进基础发展高度重视。”
经过4年的努力,中国小组独立地解决了胰岛素结构问题,虽然比在牛津的多萝西小组晚两年,但分辨率稍高一些。1971年,多萝西又设法在去日本途中来到中国。在详细了解了中国小组的研究成果以后,她非常高兴,立即给牛津小组的同事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他们(中国小组)的工作非常漂亮,值得我们效仿。他们培育出了很大的晶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小组。”
到了京都后,她立即在國际晶体学大会上对中国小组的胰岛素研究作了热忱和全面的介绍。她的发言被印在大会新闻公报的头版上。至今,我国的一些科学家还珍藏着这个新闻公报的
副本。
遗憾的是,到1971年,我国这个已经走在世界前面的研究小组也终于逃脱不了被解散的厄运,它的成员都发配到各地农场接受“再教育”。此后世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我国的科学家是完全不可能知道的。此时的多萝西仍然在为中国小组制造声势。1975年的《自然》(Nature)上,她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胰岛素研究”的文章,引起了世界晶体学界的注意。在文章中她写到:“北京小组这张分辨率1.8埃的图,是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今后可能长时间一直如此。”
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一年,多萝西迫不及待地又一次来到中国,她迫切希望中国科学家加入国际晶体学联合会。她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78年,由唐有祺率领,包括顾孝诚在内的一个代表团,到波兰的华沙参加了第11届国际晶体学大会。顾孝诚在回忆中说:“我们很惊异地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研究小组。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啊,我们最早是从多萝西那里听说的。这就是她的影响。她对把中国晶体学研究介绍给全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们夸多萝西,说她有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前一分钟还在和丈夫子女嬉笑,下一分钟就在书房里聚精会神,她一生中的每一分钟都是充实高效的。虽然,最崇拜多萝西的人也必须承认,对于公众而言,她的名字并不像玛丽·居里那样如雷贯耳,但是,用她同事菲利普斯勋爵的话来说,她不仅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更是晶体学家中的晶体学家。她研究的物质——青霉素、维生素B12和胰岛素,都在医学上有重要意义。
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