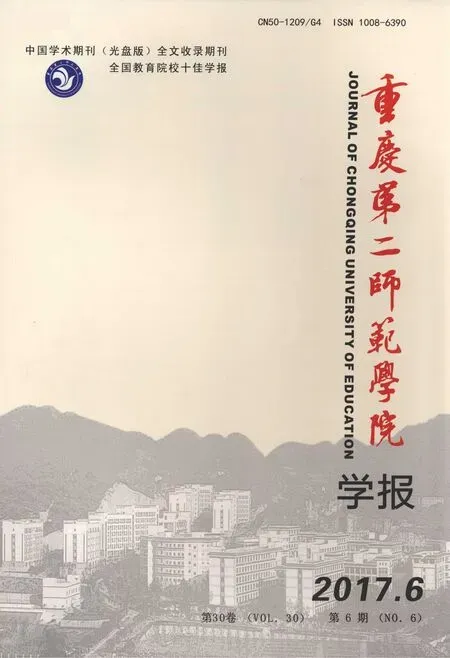试论吴歌的语言风格美及其成因
2017-12-14史灿方
史灿方
(江苏开放大学, 南京 210036)
试论吴歌的语言风格美及其成因
史灿方
(江苏开放大学, 南京 210036)
吴歌是首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吴地文化遗产。本文探究了吴歌的四大语言风格美,即音律的和谐美、用典的意趣美、修辞的含蓄美、平实的质朴美,并对其两大成因——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
吴歌;语言风格;非物质文化遗产
吴歌,顾名思义,是指吴语地域的歌曲。“吴地的歌谣,即太湖流域的歌谣。”[1]历史上吴语地域包括环太湖流域的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和浙江湖州、嘉兴地区,以及上海地区。吴歌历史悠久,吴歌越吟可追溯到黄帝时代的《谈歌》(又名《断竹歌》:“断竹、断竹,飞土,逐肉。”),流传至今已有3000年。吴歌越吟历经东晋南朝和明朝两次兴盛,尤其是明代,民歌享有“我明一绝”的美称,各类文献中所收录的民歌达2500多首,且许多民歌传播甚广,家喻户晓。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当时两淮与江南之地对于《打枣竿》《挂枝儿》等小调“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六朝吴歌和明朝吴歌,在语言表现风格上,呈现不同的特质:六朝吴歌,受当时文风和文人加工的影响,尤其讲究声律、用典和含蓄,而明代吴歌,追求口出真声、清新自然,具有平实、质朴的特点。综合吴歌的语言表现,古代吴歌的语言风格大抵形成了四种美感形态,即音律的和谐美、用典的意趣美、修辞的含蓄美和平实的质朴美。本文结合具体作品,对吴歌语言风格形态及其成因进行简要分析。
一、音律的和谐美
吴歌的音律曲折细致,柔美和谐,这与吴歌的载体——吴方言语音的特殊性有密切的关联。
吴方言,古称吴语,俗称江南话或江浙话。吴方言的语音,与现在的普通话相比,保留了更多的古音。吴方言有27个声母,43个韵母,7个声调。[2]吴方言特有的语音系统,为吴歌自成一格的音律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吴歌字调和旋律具有一致性,在音律上呈现曲折细致、轻快柔婉的风韵,得益于吴语独特的声韵调各元素的协调配置。
吴语的声调类型较多,平上去入四声和各声之阴阳调类丰富。每个声调的调值在音色表现上各具特色:“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明释真空《玉钥匙歌诀》)平声属于高起高收,音长舒缓;上声低起高收;去声自高而低,音响悠远;入声一发即收,短促顿挫。吴语基本延续了这四声八调,较之北方方言,它保留了入声韵,以及浊音声母。由于声调类型丰富,各字声调有机组合,自然生出抑扬顿挫的旋律来。吴歌中的旋律大多是顺从字调而起,音调与字调大体吻合,咬字行腔,腔随字走,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本色美。
吴语的韵母数量很多,尤其是单元音较为丰富。元音属于乐音,音乐性强,具有声音响亮、可延长的特点,可以在不借助伴奏乐器的情况下直接吟唱。吴歌丰富的元音不仅造就其歌曲的音色极为圆润华丽,而且更易表现出江南水乡细腻、柔媚的音响效果。
吴歌在音韵上颇讲究押韵,而且还讲究韵之平仄。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六朝民歌的“吴声歌曲”,列举了《子夜歌》42首,《子夜四时歌》75首,《读曲歌》89首,《懊侬歌》14首,《华山畿》25首,《碧玉歌》6首,这些吴歌的押韵已经开始讲究平仄。如《碧玉歌》:“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芙蓉凌霜荣,秋容故尚好。∥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二、四句押仄声韵)《子夜四时歌》:“秋爱两两雁,春感双双燕。兰鹰接野鸡,雉落谁当见。” (一、二、四句押仄声韵)《懊侬歌》:“江中白布帆,乌布礼中帷。撢如陌上鼓,许是侬欢归。∥月落天欲曙,能得几时眠。凄凄下床去,侬病不能言。” (二、四句押平声韵)
到了明代,以“山歌”为代表的吴歌仍重视押韵,但对平仄等要求没有六朝讲究。冯梦龙在《山歌》中注曰:“凡‘生’字、‘声’字、‘争’字,俱从俗谈叶入江阳韵。此类甚多,不能备载。吴人歌吴,譬诸打瓦抛钱,一方之戏,正不必钦降文规,须行天下也。” 如冯梦龙《山歌》卷一“私情四句”:“笑东南风起打斜来,好朵鲜花叶上开,后生娘子家没要嘻嘻笑,多少私情笑里来。”由此可见,明吴歌虽然讲究押韵,但押韵并不固守当时的官韵。吴歌押韵,是以吴语区的吴方言读音作为基础的。冯梦龙收录的作品,大多采自民间的“矢口成言”,保持原作原貌。原作的作品是用吴方言所创作,押韵自然以吴地语音为准了。此外,对于有些纯民间创作的吴歌而言,复沓句式较多。其韵脚常常有重字韵,比如上述冯梦龙《山歌》“私情四句”中第一句韵脚“来”和第四句韵脚“来”就重字,这在民歌中比较常见。
吴歌的音律节奏简洁明快,多用四字句和五字句,这是分别受到《诗经》和汉五言诗的影响。有些诗句还讲究调配平仄,匀称节奏,加上合辙押韵,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听起来则悦耳动听,富有音乐美。
二、用典的意趣美
吴歌虽然属于民间乐府,但其实有许多实为文人拟作,其中不少篇目以典入诗,别有意趣。诗文用典,或引用成句,或吸纳成词,或化用诗意,将原有的人物史实故事,或有来历有出处的词语佳句,有机整合到吴歌之中,以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愿望。这种用典修辞法凝练简洁,含蓄典雅,言近旨远,极富想象力和表现力,给读者留下联想和思索的空间,易于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吴歌兴盛于魏晋时期,魏晋文人好用典,常以前人成句入诗,如曹操的《短歌行》,诗中就直接引用了《诗经》中的成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吴声歌曲中类似截取前人诗句直接入诗或袭词化用的现象,并不鲜见。
如《子夜冬歌》之十四:“白雪停阴冈,丹华耀阳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比较左思的《招隐诗》(一),可以看出《子夜冬歌》四句引用和化用了《招隐诗》的第五、六、九、十句:“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再如《子夜秋歌》之九:“金风扇素节,玉露凝成霜。登高去来雁,惆怅客心伤。”首句直接取自张协《杂诗》(三)的首句:“金风扇素节,丹霞启阴期。”第二句“玉露凝成霜”是化用《诗经·蒹葭》中的“白露为霜”句。
又如《子夜夏歌》之六:“含桃已中食,郎赠合欢扇。深感同心意,兰室期相见。”这四句中袭用了“含桃”“合欢扇”“同心”“兰室”,这几个词语都有语源典故,镶嵌句中,化用其意,匠心独运,精妙至极。其中,“含桃”,即为樱桃。此语出自《礼记·月令》:“羞以含桃,先荐寝庙。”“樱桃”又名“莺桃”,因这种小果实常被黄莺含食而得名。《淮南子·时则训》有记载,高诱注:“含桃,莺所含食,故言含桃。”“合欢扇”,语出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南朝梁刘孝威的《七夕穿针》诗“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也用过“合欢扇”这一词语。“同心”出自《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兰室”出自《孔子家语》:“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大戴礼》:“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兰室”由“芝兰之室”或“兰芷之室”紧缩而成,后表示“芳香高雅的居室”。古诗中有“卢家兰室桂为梁”,西晋张华的《情诗》“佳人处遐远,兰室无荣光”,陆机《君子有所思行》“邃宇列绮窗,兰室接罗幕”,均可一斑窥豹。
用典无论是袭用前人诗句,还是化用前人的诗意,需一定的文学修养,从这个角度看吴歌确是“均非民间所能为”[3]。但是,对于文学而言,民间文学主要传唱于民间,为百姓喜闻乐见,只要百姓能乐见的语言形式、表现内容,即便有文人再加工也无妨。
三、修辞的含蓄美
吴歌柔美风格的形成,除了与使用的吴语方言的自然特性有关,还与其手法之委婉曲折有关。吴歌中大量使用比兴、双关等形象生动、委婉曲折的修辞方式,以表现其绵柔、含蓄的抒情风格。
其一,比、兴手法的运用。“比、兴”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传统中最重要的两种表现手法,吴歌在创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国风”广泛使用比兴手法的传统。所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吴歌地处江南水乡,其比兴多采用与水乡有关的意象。如《子夜四时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这里用“花”之“媚”起兴,“鸟”“风”为呼应,写少女怀春多情,思念情郎的心理。还是《子夜四时歌》:“秋风如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这首诗用“秋风”起兴,“罗帐”为呼应,天涯共此时,“明月”千里寄相思,写出了“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的思念之情。
吴歌的内容以爱情题材为多,诗歌中的表情达意一般都不是直白式,而是婉曲式。相应地在修辞手法上多采用比喻法,或比喻双关结合法进行表达。如《山歌·画里看人》:“画里看人假当真,攀桃接李强为亲。郎作了三月杨花随处滚,奴空想隔年核桃旧时仁。”这里用“三月杨花”“隔年核桃”做比喻,把这多情女子失恋后对薄情郎幽怨愤恨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子夜歌》:“玉林语石阙,悲思两心同。”“黄檗郁成林,当奈苦心多。”前两句为隐喻,“玉林”“石阙”相关语为“碑”,又“悲”谐音“碑”,双关。“玉林”和“石阙”对语,悲凉无奈,喻相思而不能相见,两心悲凉。后两句中的“黄檗”,皮黄而苦,暗喻“心苦”,女子的相思之苦。
其二,谐音双关的运用。如《子夜歌》:“寝食不相忘,同坐复俱起,玉藕金芙蓉,无称我莲子。”以“莲”谐“怜”,表示怜爱、怜子的意思。《子夜歌》:“今夕已欢别,会合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棋。”以“棋”谐“期”。《子夜歌》:“前丝断缠绵,意欲结交情,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以“丝子”谐“思子”。例中谐音的本体“棋”“丝”“莲”都源自日常生活中的习见事物,分别用有关联意义的“期”“思”“怜”等表情动词相对应,既生动又贴切。谐音双关取其巧妙暗合语意的手法,委婉含蓄,机智而富雅趣。
六朝吴歌因多用谐音双关作诗,形成一道风景,唐人把这种诗称之为“风人体”诗。关于“风人体”诗的特点,后人多有描述。所谓风人诗,宋代笔记小说《类说》中载:“梁简文《风人诗》,上句一语,用下句释之成文。”(《类说》卷引唐吴兢《乐府解题》)南宋词人葛立方道:“《乐府解题》以此格为‘风人诗’,取陈诗以观民风,示不显言之意。”(《韵语阳秋》卷四)南宋文学家洪迈则云:“自齐梁以来,诗人做乐府《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之。”(《容斋三笔》乐府诗引喻)谐音双关在六朝吴歌中俯拾即是,习以为常,其“不显言之意”的委婉表达,与江南水乡的绵柔性格相吻合,使得吴歌无论在音韵上还是文意上,显得更柔润、细腻、含蓄,增添了歌曲的地方风味和特殊的方言韵味。
四、平实的质朴之美
吴歌在语言上体现了直白质朴、流畅自然的风格。吴歌的“直白”表现在表达上的“直”和语言上的“白”两个方面。
表达上的“直”,指的是表情达意所用的词语手法,不加修饰,朴实无华,类似于白描、工笔手法,直截了当表达,体现一种明快清新的美。比如《吴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他州。”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战争使多少人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游子思妇终年相思愁苦,难以排遣。诗歌表现了百姓的无奈,也隐含了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吴歌大多以爱情和婚姻为题材,以情为主题,在平实质朴风格的吴歌中,爱情婚姻的表达更为直接大胆。明代冯梦龙所编辑的《山歌》,收录了原汁原味的吴地民歌,其中叙事主体多为女性,其私情表达甚为直接。如《山歌》:“清风三月暖洋洋,杨花落地笋芽长。记得去年同郎别,青草河边泪夕阳。郎捉篙儿姐放船,两人结就好姻缘。生来识得风波恶,不怕江湖行路难。”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相互倾慕,情感表达如此大胆、直率,语言泼辣、热烈,表达了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山歌》:“西风起了姐心悲,寒夜无郎吃介子亏。罗里东村头,罗里西村头,南北两横头。二十后生闲来答,借我伴子寒冬还子渠。”这位女主人更为直接,大胆而泼辣,竟然要借“二十后生”来陪伴她度寒冬。情感表达毫无掩饰,张扬而热烈。

五、吴歌语言风格美的成因
一方面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也是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类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的文化虽然是人创造的,同样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不仅“离不开”,甚至在众多影响因素中,“自然地理”因素举足轻重,人文地理学就把自然地理视为人类文化的第一推动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许多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现象都可以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得到解释。19世纪法国批评家丹纳说过:“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环境就是风格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品种。”同样,地理环境也决定着语言的种类,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的风格样式。地理环境对人类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影响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在我国,北方地区平原辽阔、气候寒冷、水资源缺乏、植被稀缺,自然环境相对严酷,形成了“北方的豪健、中原的淳朴敦厚”,富有阳刚之气,其民歌多慷慨激昂,朴实厚重;而南方则多为丘陵,气候温润,尤其是江南一带,雨水充沛,江河密布,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江南人的阴柔个性,故江南民歌多缠绵婉转,柔美清丽。吴歌源于江南水乡,“水乡地方,河流四通八达,这环境娇养了人” 。[4]姜彬认为:“吴歌是长江三角洲(古称吴地)的歌,这个地区是我国著名的水乡,水是吴地山歌的重要生态环境,离开这个环境,吴歌就不能产生,至少它不会是这个样子。”[5]这水乡的环境,是生活的不竭源头。水,孕育了丰富的物产,带来了便捷的交通;水,滋养了娇丽的容貌,塑造了柔美的性格。所以吴歌大多婉约清新,以抒情见长,表现浓郁的水乡风情和温婉的纤柔之美。这与自然环境的影响不无关联。
另一方面是人文环境的影响。吴越所在的江南,它不仅是一个特定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在这个文化地理区域内,历史上互为邻国的吴、越国,语言相近、习俗相通、信仰相同,正所谓“吴之与越也,接土为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吕氏春秋· 知化篇》)东晋至南朝汉族政权南迁,中原大批贵族士人随迁江南,促进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南史》卷七十二:“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是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吴越所在的“江南”,不仅成了“风景优美、物产富饶”的代称,而且也成了“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胜地。六朝建都江南的中心城市——建康(今南京),不仅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了文化中心,文学、艺术、史学出现了新气象,文化得以大发展。尤其是吴越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弘扬。由于受江南文化大气候的影响,吴越文化开始由尚武向尚文转变。江南成了文化中心后,文学、艺术、音乐、雕塑、舞蹈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儒释道文化的传播日趋世俗化和通俗化,逐渐渗透到士人和民间生活,深入人心,这对江南人温婉细腻、内心稳重、幽雅重礼的性格特质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吴歌之所以形成委婉清丽、温柔敦厚、含蓄缠绵、隐喻曲折的风格特点,除了江南水乡柔韧的水文化的浸润和儒释道思想文化的熏染外,还与古典文学的影响分不开。东晋南朝时期,江南成为文学中心。“永明体”的倡导,诗歌朝声律化方向发展,许多文人开始注重诗歌格律声韵、对仗排比、遣词造句、意境营造,比古体诗更为严整工巧、精练华美。尤其是许多文人受《诗经》比兴手法、汉乐府五言诗格式的影响,在吴歌中出现了大量的“五言体”民歌,如《子夜歌》《华山畿》等;吴歌中大量使用的比兴手法,与《诗经》和汉乐府的影响不无关系;吴歌中的用典和声律,与六朝时期文坛倡导“永明体”的文学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尽管用典和声律后来渐渐淡出民歌,但比兴这种手法,在明代以后的风格明丽平实的山歌体中,依然常被运用。可见,人文环境对吴歌的委婉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87.
[2]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79.
[3]翁其斌.“吴歌”“西曲”文人拟作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3):23-27.
[4]丰子恺.塘栖[M]∥丰陈宝,丰一吟.丰子恺文集(6).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5]姜彬.《中国·白茆山歌集》序[M]∥姜彬文集:第五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16.
[责任编辑于 湘]
2017-09-15
史灿方(1961 — ),男,江苏常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修辞学、语言规范、语言文化。
I207.7
A
1008-6390(2017)06-00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