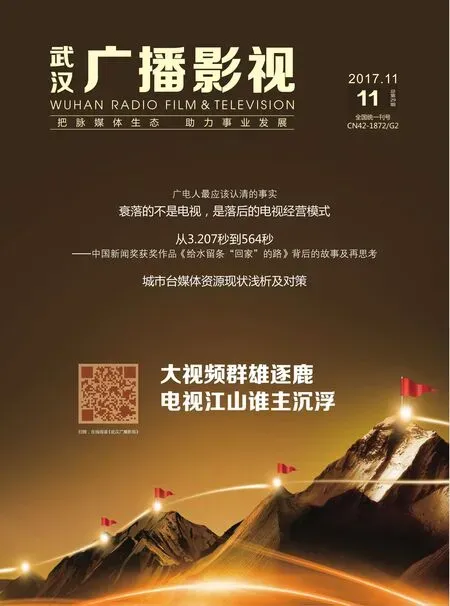时代落差下的许冠文
2017-12-13徐沛泽
徐沛泽
时代落差下的许冠文
徐沛泽
许冠文是香港喜剧电影的一个分水岭。他上承李翰祥,从恩师的“风月笑片”中截取了其拼盘似的电影结构;下启周星驰,为其无厘头喜剧的创作提供了范式——小人物“作践”自己以博君一笑的方式如出一辙。但在20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许冠文却成为另一个脱节的李翰祥,被周星驰取代,至今鲜有作品问世。这种代际之间的接力背后是导演个人在创作上的固守和局限以致无法适应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
喜剧电影 “风月笑片” 无厘头 李翰祥 许冠文 周星驰
前言
多年后邵逸夫回首往事,承认自己一生看错了两个人,一个是李小龙,另外一个便是许冠文。正是这二人让脱离邵氏不久的嘉禾从此立稳脚跟,带领香港电影进入黄金时代。1973年,不甘心只做演员的许冠文拿出《鬼马双星》的剧本,向邵逸夫表达了合资拍摄、利润均分的意愿,被邵逸夫一口回绝。时值邵氏与嘉禾龙争虎斗之际,李小龙的去世给嘉禾带来了巨大损失,为使嘉禾继续保持强盛的竞争力,邹文怀独具慧眼,从邵氏挖走了许冠文,并协助其建立许氏兄弟电影公司。“许氏”负责制作,嘉禾负责发行放映,双方利益分红,这一举动不仅使许冠文变成嘉禾与邵氏逐鹿香江的重要砝码,“许冠文电影的诞生,也标志着香港喜剧电影的转型,从此香港文化从岭南文化中脱颖而出,开始实现自我认同与自我肯定”。[1]
由于以周星驰为代表的无厘头喜剧占据了喜剧电影研究的绝对份额,因此作为香港喜剧电影承上启下的人物的许冠文长期处于大众视野的边缘。今天,对于许氏喜剧风格的研究不仅有着本体论的意义,更是厘清香港喜剧电影逻辑关系的重要一环。许冠文上承李翰祥,截取其“风月笑片”中拼盘似的电影结构;“下启”周星驰,小人物作践自己以博君一笑的方式如出一辙。然而,物转星移,在李翰祥淡出影坛的20年后,许冠文很快又变成另一个脱节的李翰祥,为周星驰所取代,这种代际接力的背后不仅折射出香港社会时代风俗和审美趣味的变迁,也彰显着香港电影工业的强大生产力。
一、许冠文与李翰祥:扬长与避短
从1972年开始,许冠文相继出演了李翰祥的四部“风月笑片”:《大军阀》《一乐也》《丑闻》《声色犬马》,这是许冠文与喜剧电影的初次结缘,他本人也因在片中饰演的光头司令形象而获得了“冷面笑匠”之名。许冠文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从李翰祥身上学习到了许多电影表现手法,但也看出后者与时代脱节的毛病。他在恩师的基础上更新电影观念和电影手法,不仅完成了喜剧大师间的代际交接,而且成为香港流行文化的缔造者,协助香港电影业由国语片成功回归粤语片时代。
许冠文的喜剧才华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出演“风月笑片”时获得的灵感。“风月笑片”是李翰祥独创的一种电影类型,擅长将奇闻趣事艳情怪谈共冶一炉,情节松散,如同折子戏。影片往往在一个统一的主题下,由几个互不相干的小故事组成。譬如《大军阀》主要分为“叔嫂对簿公堂”、“军阀姨太偷情”两个部分,《一乐也》由富翁嫖妓、警长贪污、老妇治病和剪发学徒守夜四个章节组成。许冠文将这种重桥段、轻结构的传统顺延到了自己的创作中。70年代的五部影片《鬼马双星》《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摩登保镖》皆由不同的案件和独立成章的笑料堆砌而成,包袱不断,故事利落,迎合了香港观众业已形成的审美习惯,十分讨巧。
尽管电影形式出奇地相似,但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二者有着各自的文化诉求。李翰祥出生内地,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他的影片风格古朴典雅,形式唯美考究。“风月笑片”虽然在题材上为人所诟病,但和黄梅调影片、宫闱片一样,重视审美趣味,画面精致,布景考究,俨然一幅市井风情画。“风月笑片”多以过去的时间和内地的场景为主,通过民国初期滑稽、荒诞的人和事,反映时局的荒谬和可笑,近似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传说和演义。六七十年代初的香港,大批内地人来港,移民们始终怀着对故土、对家乡的思念。李翰祥的国语片在特定的时代满足了内地移民对故土和家乡的思念,因而受到追捧。时间进入七十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飞速发展,港人的身份逐渐确立,开始自觉地建立本土流行文化,李翰祥的宫闱片、黄梅调影片、“风月笑片”便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加上70年代,邵逸夫入主无线电视台,将工作重心向电视产业转移,李翰祥转战大陆继续拍片,他和他的喜剧电影也就逐渐淡出观众视野。正当邵氏仍游离于香港这座城市之外时,许冠文的适时出现使香港迎来了喜剧电影发展的又一座高峰。
许冠文出身底层的生活经历使他了解普通百姓尤其是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的教育背景则使他选择借助电影和流行歌曲窥视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打工仔的劳资对抗、市井功力心态的盛行、港人急于确认自我身份。因此,在形式上许冠文的电影以粤语片为主,充斥着本地俚语,并配以许冠杰演唱的粤语流行歌曲;在内容上他将镜头对准当下,描绘香港底层市民的生活,关注转型时期香港人面临的价值选择。在他的创作脉络中,主角性格表现出前后的一致性,他们既不是上流人士或中产阶级精英分子,也不是底层边缘人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努力在商业浪潮下求得生存的个体户和小有产者。正是这些人一方面绞尽脑汁压榨员工,排挤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作为普通民众中一员他们又深谙生活的艰辛,保留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才有了电影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打闹和打闹过后人性的回归与顿悟。他的影片无疑让香港观众加强了对于“香港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和肯定,推动本地化、城市化粤语片的形成。
“风月笑片”的另一个特点是情色。在这类影片中,邵氏艳星胡锦卖弄风骚,凭借她欲仙的表情和欲死的声音,再加上李翰祥高超的摄影技巧,营造出令人血脉喷张的感官刺激。这些场面大多与情节发展无关,成为李翰祥电影最为人所诟病之处。许冠文巧妙地规避这些不利因素,在李翰祥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他摒弃了“风月笑片”中的情色元素,男女关系之间多了几分挑逗的情绪和暧昧的情愫,风花雪月之事主要为影片的笑点服务,许冠英、许冠杰兄弟二人为美女争风吃醋的情节使影片增色不少。在邵氏体系下运作,李翰祥的作品艺术水准参差不齐,既有造诣高深的艺术片,也有低级庸俗的商业片。身为“徒弟”的许冠文归入嘉禾旗下,有着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能够平衡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外有喜剧类型片的模式包装,内有观照现实生活的意义裹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喜剧样式。

《鸡同鸭讲》
二、许冠文与许冠文:固守与转变
好景不长,《摩登保镖》大受欢迎之后,许氏兄弟分道扬镳,而新艺城又推出了《最佳拍档》系列,对嘉禾造成不少冲击。此后,独闯江湖的许冠文经历了数年的低潮期。1984年,《铁板烧》不敌许冠杰的《女皇密令》;1986年,《欢乐叮当》恶评如潮。同年,终凭《神探朱古力》2200多万港元的票房摆脱挫折,重振旗鼓。1988年与高志森合作《鸡同鸭讲》连登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电影之列,荣获拉斯维加斯国际喜剧展“最佳男主角”等奖项,许冠文再度迎来事业巅峰。纵观整个八十年代,许冠文一方面固守已有的电影习惯,另一方面抛弃了个人喜剧电影最为特色的一面,结果两面不讨好。虽然九十年代后许冠文重新回到《大军阀》时代的演员本位,但影片仍然带有强烈的许冠文印记,我们仍然将这部分视作许冠文的电影作品。
《摩登保镖》之后的许氏电影风格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发生了重大转变。叙事模式上不再采用早年情节松散的拼盘结构,开始讲述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密集的喜剧笑料丢失严重。其次,由于许氏兄弟各奔前程,三人你来我往的口舌之争演变为单口相声,情况就如同周星驰需要有吴孟达相伴才可以发挥梦幻组合的威力一样。“进入单口相声阶段,虽然充分显露出应变和智慧,同时也反映出个人封闭的表演模式。在他的电影里,其他角色往往是供他发挥的对象,如《神探朱古力》里的梅艳芳和《欢乐叮当》中的钟楚红,反映他只能在过往有限的素材和套路中重复挖掘新意”。[2]再次,影片的格局发生了变化,由对社会现实精准的捕捉和丑恶现象的讽刺向以家庭为单位的合家欢喜剧转变,少了嬉笑怒骂、打打闹闹的恣意和放松。最后,许冠文在电影中的形象逐渐走向正面,成为一个与社会、家庭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不再具备香港小市民的特质。《铁板烧》中受惠于岳父的他在人前是对妻子和岳父唯唯诺诺的草包,人后却是时刻偷欢并与二人斗智斗勇的风流男人,毫无新意可言。《合家欢》中的笑料基本来自作为内地乡下人的他与香港都市之间的冲突,他甚至成为为了妹妹的保险金而自我牺牲的烂好人,确不如当年那个自作自受的吝啬老板来得可爱。
无论如何,许冠文电影中始终不变的还是他个人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虽然由某种程度上的“坏人”变为“好人”,但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他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居高临下的姿态,然而那一面已在银幕上被惩罚到有点闷了。进入新世纪,许冠文仅以演员的身份参演了《煎酿三宝》和《宝贝计划》,片中导演更是明目张胆地偷工减料,《煎酿三宝》中许氏以往的痕迹随处可见,譬如将三人伤残的下场作为和解、人性反省的转折点显然是许冠文惯用的伎俩。虽然《煎酿三宝》的导演并非许冠文本人,但他始终没有为自己已走到的困境稍作转型的思考。
三、许冠文与周星驰:反思与反叛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回归疑虑始终萦绕港人心头,面对社会现实表现出“逃离心态”和“放逐意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入正好让大众找到宣泄的出口——颠覆传统、嘲笑权威,周星驰以及周星驰电影的出现正好扮演了领军者的角色。此时,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道德问题已经不再构成困扰,许冠文却仍秉承相对严肃的喜剧精神,以不温不火的创作态度不厌其烦地对观众进行道德训诫。相比之下,周星驰的恣意妄为、天马行空无疑比许冠文更具吸引力,于是在经历了70年代的卖座期后,在80年代末许冠文迅即成为另一个脱节的李翰祥。1991年,在那部拥有空前绝后的豪华阵容的影片《豪门夜宴》中,许冠文与周星驰针对一个鸡头展开争夺,两代笑星的短暂对手戏似乎对这一过渡做了最后总结。从许冠文到周星驰,香港喜剧电影最终完成了自身由市民喜剧向无厘头喜剧的转型。
许氏电影中的人物市井气息浓厚,虽然有诸多的性格缺陷,但人物塑造更加朴实,贴近生活,是一批为利益所驱使的市井小民,他们的行为更具说服力。导演通过他们表达了对唯利是图价值观的讽刺。尤其以许冠文饰演的主角为代表——斤斤计较、吝啬贪财,爱耍小聪明却往往作茧自缚,《鬼马双星》中坑蒙拐骗的老千、《天才与白痴》中费尽心机寻宝的精神病医生、《神算》中浑水摸鱼的算命先生、《欢乐叮当》中盗取他人身份泡妞的音乐人皆是如此。除此以外,电影中常出现炒股,买马等极具香港特色的桥段,《天才与白痴》中的精神病人至死都不忘关心恒生指数的涨幅。如此种种,皆讽刺了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时期港人急功近利的赌徒心态:一方面事事见钱眼开,投机倒把以期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另一方面“亦尝试用‘赢咗得餐玩,输好都唔驶庆’(赢了继续玩,输了莫生气)来自我调适”。[3]因此,影片结尾处许冠文永远不忘道德训诫,主人公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周星驰电影中主角的身份定位是草根,他们大多穷困潦倒、怀才不遇。但却极尽癫狂之能事,在旁人异样的眼光和质疑声中勇敢地追逐梦想,打破常规。这些人物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他们身上映射了更多导演个人的成长经历。
语言是喜剧电影的一大特色。周星驰的无厘头笑话是“去逻辑性”和“无意义”的,纯属于语言的狂欢。与之相比,许氏语言对白多了几分逻辑性,甚至有其合理性,“他深谙李翰祥把歪理推至极端所制造出来的强调讽刺及爆笑效果”,用智慧来创作喜剧效果。事实上,许冠文对语言的掌控能力除了来自李翰祥电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外,也与他早期在电视台主持脱口秀节目时所受的高密度笑料的喜剧训练分不开。《半斤八两》中许冠杰饰演的打工仔向老板抱怨一天2元钱的伙食补贴太少,连米饭都吃不起。老板却说多食米饭无益,会得癌症。因为身患癌症的人都吃米饭。许冠文通过一句话的智慧将一个压榨员工劳动力的吝啬鬼形象刻画地淋漓尽致。此外,许氏电影对白的幽默还来自一句话里的突转。《天才与白痴》里,许冠英扮演一位送餐服务生,给客人送去一包烟。客人抱怨道:“一包烟要半个小时,难道去美国买?!”服务生不卑不亢的回答:“对不起,原来你才等了半个小时,那边有等了三个小时的,这包烟还是先给那边的客人吧。”显然,许冠文这种理性的语言幽默在后现代语境下已经有些死板,这也是许冠文落后于时代,为时代所抛弃的重要原因。
除对白外,许氏电影的喜剧效果还来自于你追我打的闹剧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外形俊朗的许冠杰负责所有打戏。不同于李翰祥与周星驰,许冠文非常注重道具的运用,包括动物、食物等,排除单纯的胡闹搞笑,这些道具或是用来借物言志或是包含深刻的暗讽。《神算》的结尾,黎明对税务局的单调工作倍感厌倦,抱着骑牛找马的心态应付,作为长辈的许冠文对他训诫道:“每只牛都要当马骑,这才会骑车火花。”看似通俗易懂的语言的背后饱含教诲,身体力行地劝诫他们干一行爱一行。动物可以代表贪婪、仗势凌人、弱肉强食,在《卖身契》和《铁板烧》中动物甚至成为一种符号学的标识。《卖身契》中两家电视台的台标被设置为猫和老鼠,暗示电视台之间的恶性竞争,电视台女导演的宠物鹦鹉更成了她为虎作伥的工具;《铁板烧》中爷爷的猫经常被拿来做挡箭牌,而女婿对狗和鹰的攻击实则代表了对以岳父为首的家庭强权的抗争。许冠文上瘾似的用动物来比喻人世,嘲笑人性沉沦于兽性的境界,探讨人类尊严与动物的对应。
许冠文早期电影的人物关系是兄弟三人的家族戏,多半以雇佣关系出现,借以反映劳资对抗下打工仔的辛酸历程。三人各司其职,“冷面笑匠”许冠文负责扮演尖酸刻薄、自私自利的小商人,歌手许冠杰继续发挥偶像派的演技,兼有成龙功夫喜剧的特色;许冠英则利用他的天生衰样跑龙套,即使不言不语也能引人发笑。周星驰的电影多以与吴孟达搭配的二人组合为主,亲兄弟的搭档组合自然比周吴二人的配合更加浑融,此所以后来周吴二人因为关系的不断恶化而影响电影创作。
同是在展示底层人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许冠文竭力捕捉小市民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时价值观变化的动态,“帮助”他们摆脱道德困境,通过影片主角的价值取向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周星驰则非常急切地想借他人之口表达对权威和崇高的蔑视,以“立一家之言”,完成所谓“屌丝的逆袭”。显然,二人的喜剧电影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许冠文重在反思,周星驰意在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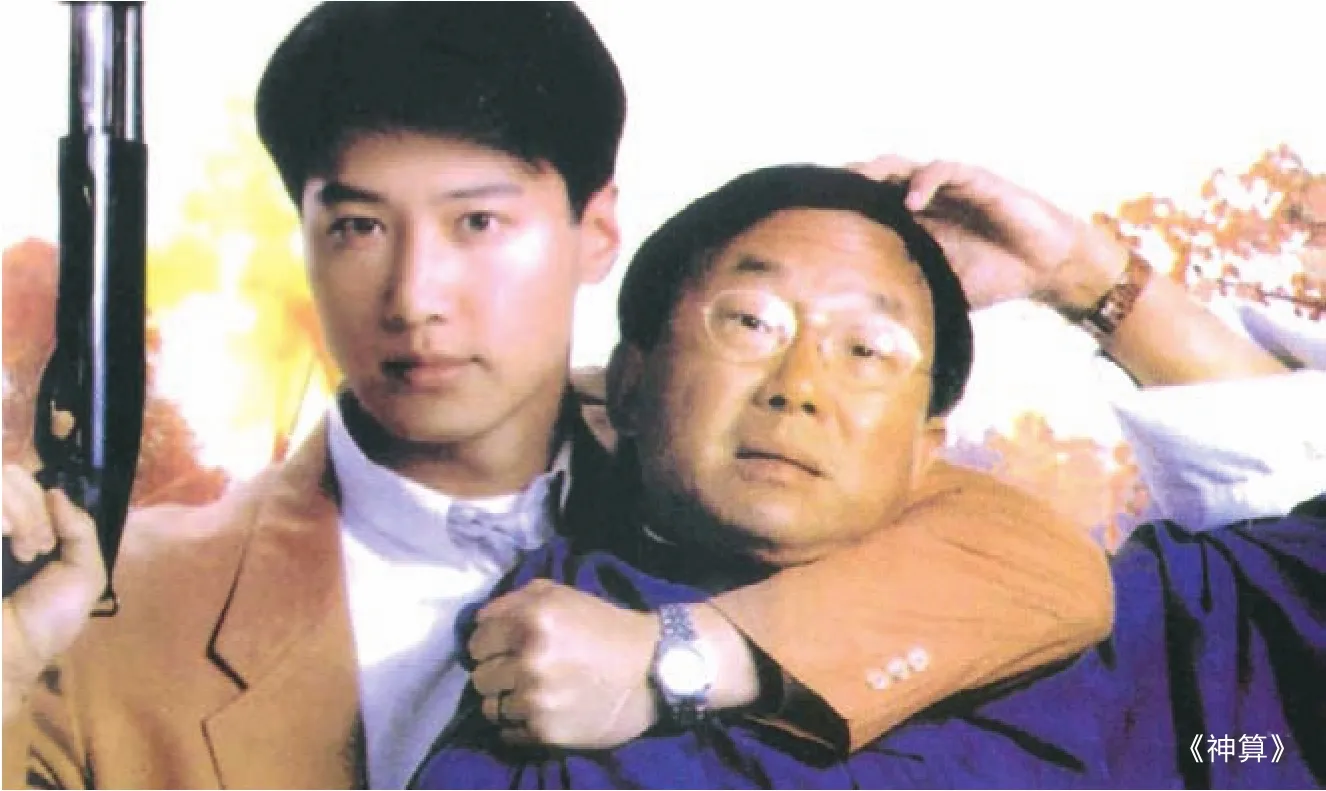
《神算》
总结
香港喜剧电影始终呼应着香港社会历时性发展的时间轴。从李翰祥到许冠文再到周星驰,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对时代脉搏的拿捏和对观众心理的把握,而这三人之所以最后为时代所抛弃也是由于对这一信息的判断失误。回溯历史,中国喜剧电影向来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第一部初具雏形的喜剧电影《劳工之爱情》便是反对封建婚姻、倡导婚姻自由的发声,也因此赢得了第一批初生的电影观众。于嬉笑怒骂间横眉冷对才是喜剧电影的生命力所在,任何脱离时代背景的喜剧电影只能是自贬身价的恶搞和丧失自尊的胡闹。
电影与时代的互动关系如此密切,重视社会心理走向,尊重观众审美趣味,或许才是香港喜剧电影复活的关键。
注释:
[1]张黎.许冠文“城市喜剧”的社会文化意义[J].上海大学学报,2007(3).
[2]汤祯兆. 香港电影血与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76.
[3]汤祯兆. 香港电影血与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76.
本文是2017年湖北省黄冈师范学院校内高级别培育项目《互联网语境下中国故事片内容生产的创新路径》(2017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武汉大学艺术系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朱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