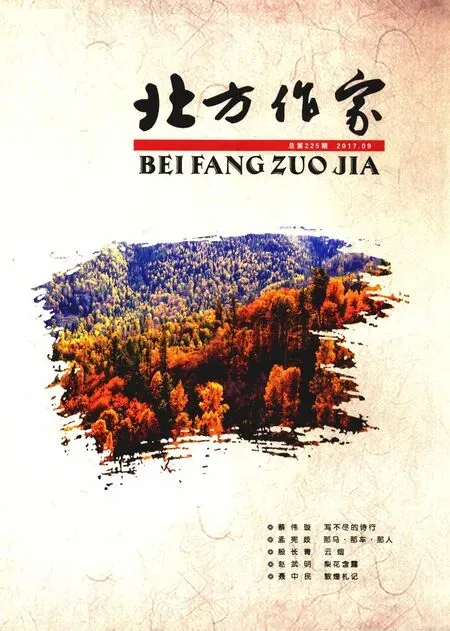写不尽的诗行
2017-12-12蔡伟璇
■蔡伟璇
写不尽的诗行
■蔡伟璇
1
江水混混沌沌漫长的一觉,被空空荡荡运行多时的胃,像拧干一条毛巾那样绞醒过来时,她以为又回到那些秋夜抽了整整一夜烟的清晨。其实,此时已是除夕的下午,雾霾浓重的除夕下午。秋夜也已回云南老家去过大年了。江水弄明白眼下处境的时候,也想起来,她的上一顿饭,还是昨夜后半夜的冷饭。
江水虽然好几天足未出户,但她感觉神经的末梢,依然准确地捕捉到这座大都市的空,更加的空。饥饿的胃,则不管不顾地折磨她,催促她,要她快出去买点菜回来做饭,就算一个人过年,不吃年夜饭,晚饭也得吃。
北京的冬天黑得早,江水出去买菜时还不到四点,但眼看天就要暗下来了。
江水匆匆喝下半包速溶麦片,便臃肿地走出来了。江水那件长及膝下的肥厚的大衣,自然是把她的好身段一网打尽了。其实,江水的身材,是很灵秀的。这几乎也是她身上,从长辈们的眼光来看,唯一让人一致认为美的地方。不过,江水最迷人的,还不是她的身段,而是由她动态的身段,制造出来的身姿:无所顾忌的肆意挥洒中,藏着一些清新,是嫩绿的草、斑斓的花那样的清新。秋夜第一次和诗友坐在那家酒吧的时候,便是被来来回回服务他们的江水的走姿,吸引住的。江水的脸,则就像“江水”这个名字,你说不出它是意味无穷还是粗糙直白那样,你无法一下就说出江水是长得疏眉淡眼,还是别具韵味,江水的眼一点都不美,既无双眼皮,也不是大眼睛,只是眼神特别清亮,像石缝里澄澈的泉水。而像泉水中黑鹅卵石般的瞳仁,则总是隐藏在微厚的上眼皮下,乌溜溜地打着转,仿佛总在悄悄地打着什么主意。此外,江水的脸上,除了一口白亮的贝齿,以及还算周正的鼻子和嘴形之外,真没有秀色夺人之处。但是,就是这些普通的五官,它们布局协调地呈现在一张十分光滑的土豆皮肤色的杏子脸上,再加上匀称灵巧的身段,这就有了一股很不一般的魅力。
这样的江水,让认识江水父母的人,在初次见到不常回家的江水时,都惊讶无比。
江水的父亲江大力,常年扣着一顶滨海人叫“兵帽”的旧草绿帽子。这一扣,已经扣了三十几年了,因为,他自二十几岁起,就长着一颗几乎掉光了头发的脑袋。秃头的江大力是个勤勉的人,他把自家的地都种了蔬菜,每天到离菜地十几米的江里,挑水来浇菜。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吧,江水生下来,就叫江水。江水的母亲周芹菜,常年在离家不远的城里农贸市场卖菜,卖江大力自种的蔬菜。她个头矮矮墩墩,容貌普通到濒临丑陋,与芹菜这种身形颀长、浑身清香的蔬菜,实在相去甚远。
2
一个包裹得像只粽子的妇女,正双手通红地在撬开冻在一块的鱼。江水想买几条鱼,也想买一点卤料。江水等她撬冻鱼时,凉凉的眼光朝外瞥向那个福建老乡的卤料摊子。江水意外地看到,那卤料摊子的位置,换成一个妇女在卖水果。江水想,老伯大约是回福建老家过年去了,而她,其实也不需要卤料——像滨海人那样,喜欢就着卤料喝夜酒的秋夜,也走了。恰在这时,水果摊上的灯亮了。江水往灯下瞅去,她吃了一惊,那个卖水果的妇女,竟有几分像周芹菜!江水鼻头酸了一下,她丢下卖鱼的妇女,朝水果摊走去。江水两年前决心北漂的时候,根本不屑把北京的干燥考虑在内,现在,每天却不能不以多喝水和多吃水果,多种形式地来补充水分。江水走近水果摊,一眼就看到水果摊上的“姑娘”!“姑娘”这个词刺痛了江水的心,江大力和周芹菜家的“姑娘”,现在已是明日黄花!她与男人同居一年多,一个多星期前做了人工流产,男友本来说好要一起过年,现在却撇下她,自个回老家去了。
“姑娘”是江水很喜欢吃的水果,柔软薄韧的干叶子,严实地包着一枚汁水丰盈、黄橙玲珑的小果实。大约是这个样子像“养在深闺人不识”吧,大家叫它“姑娘”。
江水要了半袋子“姑娘”,又切了几根香蕉,挑了五个桔子。
江水回到家里,解冻一条鱼,煮了一碗面条。医生交代过,“人流”后,有伤口,别吃海鲜。可江水还是吃了鱼面。从小江大力和周芹菜就把最鲜美的鱼,留给她吃。现在已经八九天没吃鱼了,江水特别馋鱼。江水灰心地想,吃吧吃吧,吃死了算了!
江水吃下一碗鱼面后,就又躺倒到床上。墙上的电视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地开着,江水昏昏沉沉又睡了一觉,睁开眼来,电视里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所有的人吃了大剂量的兴奋剂一般地在倒计时。江水又饿又渴,眼光扫过桌上下午买的那半袋子“姑娘”,便挣扎着,用手指头去够过来。江水靠在床上剥“姑娘”吃,眼前又浮现那个像周芹菜的卖水果的大婶。小半袋“姑娘”既解渴,又饱腹。江水吃完“姑娘”后,拿过手机,点开携程网,居然还有一张明天早班飞滨海市的廉价机票。江水毫不犹豫地,把卡里的钱全付了机票款。
大年初一凌晨,江水两手提着满满当当的行李出门之际,空洞的眼光最后掠过窗台上的那盆冬眠的玫瑰时,玫瑰背后熹微的天光,让江水的脑中闪现出秋夜无数次对她说过的话: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江水撂下手上的行李,一把把玫瑰花搬下来,搁到房东老阿婆门口,送给她。
大年初一的中午,灰惨惨的江水走进家门时,正在吃饭的周芹菜目瞪口呆地盯了江水好几分钟。待回过神来,周芹菜赶忙安顿江水到她自己的房里歇下,又连忙宰了一只鸡,加了好些人参下去炖。一个小时后,江水的床头,便有了一海碗浓香滋补的鸡汤。
3
周芹菜见病恹恹的江水,每次上卫生间,总有一星半点没有冲净的血迹,她明白了,江水恐怕不是经期,而是吃了男人的苦头。周芹菜不声不响地,赶忙熬龙眼、干枸杞、红枣,给江水当茶饮。亏得有周芹菜这样入骨的爱,江水日后的生活,才得以顺遂许多。
江水日日躺在床上睡觉,即便醒了,也是躺在床上看手机。软的床和暖的被窝,是江水的温泉。江水在这里,越陷越深。
忽有一天,江水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上海的一对夫妇,拥有三套房子,辞职在家,不与人交往,不买新衣服,一年只花2万元。江水想,这便是传说中的“岁月静好”了。这时候的江水,特别想永远就这么躺下去,不要见任何人。
周芹菜每天夜里,还都要给江水煲她爱喝的番鸭汤。江水看手机看饿了的时候,周芹菜的滋补热汤也飘起香来了。江水松松垮垮地出来喝了汤,再回去倒头睡下。江水看上去虽还是灰白颓废的样子,却渐渐有一些亮亮的光,在她披洒的发丝间闪烁,像枯草间钻出的新绿。
又忽有一天,江水在手机微博里又刷到一句话:“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愿意替她负重前行罢了。”江水便想到了周芹菜。
这一天清晨,乌云翻滚,寒雨不停,周芹菜依然挎了篮子去菜地里摘菜,回来时,江水已睁开惺忪睡眼,伸手在床头柜上找保温杯喝水。周芹菜听见声响,慌忙中,连菜篮带雨伞一齐提着进江水的房间,问她中午想吃什么?江水眼瞅着周芹菜衣裤潮湿颜色模糊,雨鞋上粘着泥巴,手里一把旧伞往地上滴着水珠,便皱了眉,说:“随便。”周芹菜惶惶地退出去,她菜篮子里芹菜的清香却袭过来。芹菜当名字是太土气了,可作为蔬菜,却储满了江水童年时美食的记忆,江水的心,因此明朗了一下。周芹菜退出到门边,就要替江水掩上门时,又想起了什么,惴惴地折回来,告诉江水,说姑姑打电话来,请他们去吃酒席赏花灯。姑姑嫁在泉州,她的酒席和泉州正月十五的花灯,是江水童年里的奢华。江水乌溜溜的瞳仁,在微厚的眼皮下转了转,便爽快地说:“好!”这让忐忑的周芹菜,很是喜出望外。
4
江水的这一觉,睡了快半个月。她起身跟周芹菜去泉州的时候,素着的脸上,已有些南方早开的桃花梨花的芳菲了。
姑姑掌勺的酒席,并不随姑姑的年老而色衰,家常菜品依然还是一流的好滋味。席间,和江水坐对过的小伙子,是姑姑夫家亲戚的儿子。江水注意到他虽木讷少言,眼光却会不时迅速溜过江水土豆皮肤色的脸颊。每看一眼,脸上便泛起一层微微的红。江水起身离席取个物件上个卫生间,他的眼光便偷偷地追逐着江水的走姿。江水乌溜溜的瞳仁,隐蔽在微厚的上眼皮下,转出一些不屑。经历了秋夜,其他男人,便除却巫山不是云了。
饭后,周芹菜帮小姑子收拾厨房;江水犯困,跑去躺在姑姑的床上,一躺倒,便迷糊睡去。等姑姑来叫她,要她跟她去看她亲戚家的新房时,江水困劲已过,便爽快地跟了姑姑出去。
姑姑亲戚家的新房,离姑姑家不远,转了两条街便到了。那房子有四层半,楼下是三间大店面,已经出租,热气腾腾地做着生意。二层住着江水姑姑亲戚老俩口,三层住着他家老大一家三口。爬上四楼,江水意外地见到中午酒席上,坐她对过的那个木讷的年青人。这一层和楼下一样,单卫生间就两间,一间在主卧内,一间在客厅,客厅的卫生间大得像人家的小房间。卧室是三间。客厅大而空,像在做着某种热切而茫然的等待。
江水想起和秋夜在北京的出租房,即便是个老旧的斗室,也花光了江水所有的积蓄,让她此次回来,一贫如洗。
江水忽然明白了这趟泉州之行的目的。江水并不看那羞涩的小伙子,也不像周芹菜和姑姑那样,对这座阔大的房子啧啧称叹,只在心里冷笑了一下,脸上一副见过世面的淡然。江水这静水流深的漠然,对这小伙子,又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姑姑和周芹菜便迫不及待地跟江水提到了这事,说那个叫永平的小伙子,很中意江水。江水想起扔下三包劣质卫生棉便走的秋夜,便朝姑姑和周芹菜,硬硬地点头。姑姑和周芹菜十分意外,惊喜得不知如何是好,马上情绪高涨地转入对婚礼细节的热烈讨论。
5
永平在空阔的客厅里拙笨地拥抱江水,是又半个月之后。永平的第一次拥抱跟秋夜不同。扎着一把马尾又瘦又高的秋夜,无论把江水环在怀里,或俯身去吻她,都会撞疼她,但这一对瘦男瘦女的每一点磕碰,都会撞出电光石火。永平的怀抱则肉肉的、热热的,让江水茫然又惶惑。永平怀抱里的江水的视线,越过永平的肩头,直直落在大客厅朝阳的后窗上。江水小小地吃了一惊,她恍如又见到秋夜春天带回来的那一盆玫瑰!秋夜最初把玫瑰,搁在朝南的窗台上迎接春天的太阳,江水却不时把它拿下来,摆在秋夜的书桌上。书桌是家里最好的家具,要匹配家里最奢美的物品。这盆玫瑰,便从春到夏到秋,一直安静地开着明净芬芳的花朵,并不因这两个人的赤贫,而有一丝偷工减料。
永平第二次的拥抱,蛮劲使在手臂上,硌得江水的小蛮腰生生地疼。生疼的小腰确切地告诉她,她就要住进这豪阔的房子里了。她会不会也买回一盆春天的玫瑰,放在客厅朝南的窗台上,晒着太阳?
婚礼之前,对于永平热切的性的要求,江水还可以抵御推脱。婚礼之后,江水就没办法了,更没办法说刚人流过的事。因此,江水婚后的第一个月,经期便推后了。江水在经期推后的第十天,自己拿试纸试了清晨的尿液。当江水坐在宽大的客厅沙发上,手指头上捏着变了色的试纸,心中闪过秋夜念过的诗句: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对两三个月前才人流过的江水,这时候怀孕,在医学上是件违规的事,只是江水的内心里,一直是破罐子破摔的意念,因此,就任她的小蛮腰,迅速笨粗起来。
这时,江水过去跟着秋夜混熟的一个女诗友,从北京出差来福建泉州。女诗人跟江水一直有微信联系,知道江水结婚后住在泉州,就趁出差之便,来看江水。对于江水北京的那一段,永平多少有些知觉,心中多少有些不快,对江水外地来的朋友一律颇为防范。那天正好永平不在,江水才能若无其事地带女诗人,上下参观这个富足的家。参观完江水的家后,女诗人站立在江水四楼铮亮的客厅地板上,背诵了毛姆的格言:要时时刻刻为生计操心,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丢脸的了。那些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我就最瞧不起。他们不是伪君子就是傻瓜。金钱好比第六感官,少了它,就别想让其余的五种感官充分发挥作用。她在江水四楼的大客厅坐下来喝咖啡时,瞄了江水的腰一眼,然后说到秋夜。江水当时一气之下删除了秋夜的所有联系方式,并拒绝联络,便和秋夜彻底断了联系,这时心下倒希望女诗人能说说秋夜,但女诗人却说不清秋夜的具体情况。女诗人直到晚饭时分,才说要走,江水就请她到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西餐厅去用晚餐。餐后,女诗人才满足地离去。
兴许是因为周芹菜那一个月的竭力调理,江水的肚子很快滚圆起来,且并没有其他不适。这让周芹菜和江水的姑姑高兴得合不拢嘴,唯一的一点缺憾是,江水足月顺产下的,是一个七斤多的女婴。江水却不,她黑鹅卵石似的瞳仁,第一眼看到花蕾般的女儿,便给了她一个美丽的名字——罗斯。“罗斯”是英语单词“玫瑰”的译音。永平对这个名字摸不着头脑,但江水的主意他多半会无条件地接受。
江水抱着罗斯从医院回家,是除夕的下午。因为有亲戚前来看宝宝,婆婆为她们泡了咖啡,因此屋子里便氤氲着咖啡的暖香,袅袅香氛,拽着江水穿过嗅觉隧道,回到前年的除夕之夜。那晚,秋夜应朋友之邀,带了江水去参加除夕聚会,和几个诗人在藏族饭店吃藏餐。江水闽南人的胃,固执地拒绝了每一道菜,主人因此为她泡来一杯香浓的咖啡。江水在缭绕着神秘藏族乐曲的餐厅里,边喝咖啡充饥,边像个诗人那样,听秋夜他们谈论仓央嘉措。
深夜回家的路上,秋夜在天寒地冻里仰头吟诵:“春深微雨夕,满叶珠蓑蓑。秋夜又疯又傻地说,江水痴痴地听,倒仿佛真看到一树一树花开,燕在梁间呢喃!
那除夕夜咖啡的暖香,因此一直香暖在她的记忆中。
去年的除夕前夕,秋夜上午带江水去流掉胚胎,下午便跟了一个采风团,去西藏。江水苦求秋夜,至少第一个夜晚留下来陪她,但秋夜只为江水买来三包廉价的卫生棉,就挣脱江水拉扯他的手,说,他没去过西藏,他得去一趟。况且这一次出去,差旅费和一周的吃住,全有人埋单,家里可以省下一笔开销,怎可不去?请了一周假的江水,在这一周里,陪伴她的,唯有秋夜买来的三包劣质卫生棉。好容易盼到回来的日子,秋夜却告诉她,从西藏回云南,比起从北京回云南,可以省下不少钱,因此,他回云南去了,他已经三年没有回去看他母亲了。
江水把罗斯放在婆婆早已准备好的小床上,她又想起去年除夕下午买“姑娘”的情景。才一年,自己也有了“姑娘”!
永平暂时不打算出去做事,跟着江水在家带孩子。永平说,得生个儿子,家里的房子和财产,多个儿子多一份。
罗斯白天也一直是在睡眠中,江水便跟着睡。因此,夜晚便成了江水的白天。这天晚上,半夜时分,天下起了雨,江水想起去年三四月在北京的出租屋里,她已经睡眼惺忪了,秋夜的白天才要开始,秋夜朝着窗外霏霏细雨,吟诵杏花诗词。吟咏之间,秋夜回头见江水那黑鹅卵石般的瞳仁,闪烁着天上星子那样的光芒;那土豆皮肤色的杏子脸,此刻在白炽灯下,在枕上,慢慢绽开成一朵雪白的杏花。秋夜激情澎湃地坐到江水床头,伸手从被窝抓出江水的双手,说:“我们去天坛北门看杏花!明天、后天、大后天,你一没班,咱们就去!”在台灯最小档的微弱光线中,江水侧头瞟了一眼永平,他油光红亮、肉肉憨憨的睡脸,丝毫没有被屋外的雨声打扰。江水伸手关掉台灯,她乌溜溜的瞳仁,沉滞在暗夜的河底,怀想与秋夜共享“风吹梅蕊闹,雨细杏花香”的情景。
江水生下罗斯满月后,也过了正月十五了,街上的店面陆续全都开了。正月十五这天早晨,楼下的一家店面的店租就打来了。公公婆婆让没有工作的江水和永平,收取楼下一间店面的租金,应付婴儿花费和日常开销。看着短信通知的那一大笔足够让他们一年手头宽裕的钱,江水又想起前年的这个时候,那时,秋夜白天睡觉,夜晚抽烟、喝酒、编写诗集,给一个文化公司兼点文案,他所赚的钱,除了买烟买酒,已没有多少能交给江水安排日常开销。那一晚,已到了交房租的最后期限,江水只得把自己一年来的积蓄,全拿出来,交了房租。去一趟德令哈的希望,再次成了泡影。江水“北漂”的种种理想,和眼框边的泪珠,一起摇摇欲坠。睡足了一天的秋夜,则精神头正好,他安慰江水,等他的诗集成功出版,拿到稿费,就会好过些。他又给江水鼓劲,说咱们要坚持,要融入,要把北京当我们的故乡。北京的公共资源这样丰富,一张颐和园门票才三十元,可以逛上一整天;国博连门票都不要,大冬天里面暖气蓬勃,展品全部高大上;到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去听课,参加各种高规格的文学活动,地铁四通八达,公交开通夜班……哪个城市能像北京,这样价廉物华?”
江水想,没有历经人生的山寒水瘦,怎能明白这“春风草木香”的和暖明丽。
6
罗斯一满月,永平便迫不及待地附在江水耳边说:“再生个儿子!”他口腔浑浊的气味,喷在江水亮洁的额头。永平热火朝天地乞求江水紧抱他的后背,他火急火燎的鲁莽,却使江水很是不适。江水抱着永平肉墩墩的肩颈和后背,有些瞬间,她以为她抱的是一头食肉动物。江水暗暗诅咒,甚至狠推了永平一把,向着高峰冲刺的满头大汗的永平,却未察觉,江水只得无奈罢手,巴望永平快快了事。
夜不深,街的对面谁在放“昔日重来”,“Every shalala every wo'wo still shines .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
昔日重来?那散发着浓郁玫瑰精油香味的夜晚,可能重来?
江水想起秋夜第一次留宿她的住处,恰好也是一个秋夜!
江水读完一所二本大学后,不愿意回去天天见秃头的江大力和矮胖的周芹菜,便和同学北漂去了。她在南锣鼓巷的一家酒吧,找到一个服务生的职位。就是在这家酒吧,江水认识了诗人秋夜。这个诗人秋夜和江水见过的许多艺术家一样,留着长及肩头的长发,却又嫌长发碍事,又用一根皮筋在脑后把长发扎成一束。瘦高的秋夜身上有一种光,那光让江水想起家门口那条江,阳光下的粼粼波光。童年的江水,有着自己的“光阴的故事”,那就是,对于奔向远方的那一江江水的无数遐想。
那一夜,恰好合租的女孩上夜班。秋夜带来一瓶酒,江水从芍药居夜市福建老伯那里,买来下酒的卤料。秋夜先是和江水对饮,与她谈天,后来秋夜为江水朗诵海子的诗,其中有这样一首: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江水在手机里百度“德令哈”,原来那是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荒凉戈壁滩中的一个小城。德令哈取代了江水自童年起对那一江春水的遥想。江水更积极地存钱,她要去一趟德令哈!
夜深了,江水的舍友夜班不回来,加上酒精的作用,虽然彼此认识未久,江水还是让秋夜在她那里过夜。那一夜,秋夜彻夜对江水呢喃:也许世界上也有五千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秋夜洒落在江水光滑的土豆皮肤色脸颊上的酒气,就像玫瑰精油那般馥郁。那一夜,江水苗条的身体,真正是秋夜独一无二的一朵玫瑰。
那时,正好江水合租的女孩要搬到她男友那里,在诗友那里挤着的秋夜,便住到了江水这里来。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一诗成谶,比秋夜小十一岁的江水,从此扮上了长姐的角色,买菜、做饭、洗衣、拖地,江水样样都干,甚至在后来秋夜辞了工作,白天睡觉,晚上读诗、写诗、接点文化公司文案,稿费青黄不接的时候,江水也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支撑两个人的生活,甚至还挤出一点钱,为整夜写作的秋夜买烟买酒,不让他因断烟断酒,而断文思。
7
公公婆婆居住的二楼的大客厅,是儿孙们吃公家饭的地方。饭厅的另一边,则是公公的领地,一张巨大的根雕大茶桌,桌上总有一盆玫瑰,在俏丽地开花。罗斯满月后,江水有时候也抱她到二楼去看公公泡茶。公公每次见到江水抱罗斯下来,便一把掐掉手中的烟,并打开窗户散发烟雾。这总会让江水想起后来秋夜写一夜,在她身边抽一整夜烟的情景。那一夜的烟雾,比外面的雾霾还要浓重!公公是家里财富的缔造者,和永平不同,他是个有阅历、有见识的长辈,所以,江水喜欢抱着罗斯下二楼来陪公公泡茶。当茶汤中的那一缕玫瑰馨香,在舌尖缠绕,江水便能感知到,这是罗斯,进口奶粉,尿不湿之外的一个童话。
江水的婆婆,看上去比周芹菜更不像个女人。她大嗓门,每天起很早干活;乳房干枯下垂,上身和臀部之间基本没有过度,曾经饱满的大臀部则像一片快枯干的荷叶;身上尼龙类的衣物,纤维一律既粗且硬。江水嫁过来两个月后,发现这个婆婆,再忙碌,每天傍晚都必爬上天台一趟。江水悄悄尾随过一次,她无比惊讶地发现,婆婆竟在天台上种了大大小小二十来盆玫瑰!这些玫瑰有开花的,有不开花的,它们都在淡淡的暮色里,用轻快的颤栗迎接婆婆的到来;伸展着青翠的枝叶,汲取她馈赠的清水、晚霞和月光。后来,江水还发现,公公大茶桌上永不凋谢的玫瑰,亦是拜婆婆所赐。婆婆每隔一阵,便把天台上含苞欲放精神抖擞的一盆,搬下来替换。
江水从此后,便只在四楼大阳台晾晒永平的衣服,她自己的衣物,则要拿到天台,在花香氤氲中濯洗。罗斯满月后,邻居在自家的楼上,常会看到江水俯仰着一张婴儿肥的雪白的脸,在天台上白花花的太阳里,洗晒婴儿的小衣小裤,仿佛一辈子都洗不完似的。
这天,江水又抱了罗斯下来喝茶。屋外雨水潺潺,凄寒苦冷,根雕茶桌上玫瑰开得十分明艳。江水想,只有这样墩实的茶桌,才能够这样安稳妥帖地任这花轻盈芳馥地开。江水乌溜溜的瞳仁,悄悄拂过怀中婴儿酣睡的小脸时,心想,只有这样屋舍齐整,衣食无虞,她才能抱着粉雕玉琢的女儿,这样心无挂碍地坐在这里品茶。江水想,要对永平好一点,等到夏天,便把永平的衣服,也搬上天台去洗。
在天台晾洗衣服,就像是江水的一个梦想,她每天都得去触摸一下,才能安心。
进入春雨期后,天空总是阴雨连绵,偶然有个春阳露面的好日子,江水便要在天台上拉出好几条绳索,把她和罗斯的衣服都披挂上去。江水晾晒好衣服后,总要依在天台的围栏,瞟一眼阳光下的一排排衣物,嗅一嗅空气中那一缕淡远清芬的花香。有那么一些瞬间,江水看那一排排衣物,恍然就如自己写下的诗行——写不尽的诗行。
这一天,江水正在天台上晾衣服,邻居电视里降央卓玛的歌声,辽远低回地穿过排排衣物而来:“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江水尖锐地想起德令哈,她乌溜溜的瞳仁,瞬间有了薄薄的泪花。现在,即便有了钱,也无法去了,25岁的江水,她很快就要再当妈妈了!这估计是罗斯满月那一夜,永平兀自折腾的结果;也是自己大意地以为,哺乳期不会怀孕的后果。很快地,江水的腰又要令人绝望地笨粗起来,再走不出无所顾忌的肆意挥洒中,藏着一些嫩绿的草,斑斓的花那样的清新了。这一辈子,恐怕,就是这样了。
8
二十五年前,一对流浪诗人生下一个女婴,因为无力抚养,便听人指点,把女婴放到江大力的菜地里,打算送给结婚多年无生育,心眼又好的周芹菜。
当江大力把婴儿从菜地里抱回来,塞进周芹菜的怀里,周芹菜便拿眼珠子定定地凝视怀中婴儿。忽然,她颤着声音叫道:“真水(闽南话“水”同“漂亮”)!”说着,眼里有两滴泪珠轱辘掉下,落在婴儿雪白的脸上,就像雪地上的两枚珍珠。
这个女婴,叫江水。
这是江水这个名字的真正来历。后来知情了的江大力和周芹菜,也没有告诉江水她的真实身世,要不,江水便会明白,她从未出生,便注定,要有写不尽的诗行。
蔡伟璇,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21届高研班学员,研究馆员。著有《凤凰花地》等四部文集,获福建省第27届优秀文学作品奖等文学奖项30余次,并被授予“福建省职工艺术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