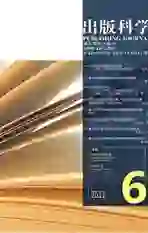出版在经典建构中的作用
2017-12-09周百义
周百义
近年来,鉴于阅读现状,社会上有一种呼声,强调读书要远离平庸,提倡阅读经典。其因有二:一是图书品种繁多,良莠不齐,人生而有涯,学而无涯,要注意提高阅读质量;二则无论高层还是有识之士,无不忧心互联网时代的浅阅读、快餐化阅读带来的弊端。对此,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接受腾讯网采访时曾指出:“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他呼吁青少年学生的阅读要从阅读经典开始,认为这关乎一个民族精神建设的大事。要通过对经典的原汁原味的阅读与理解,国人从中了解人类文明与智慧的优秀成果,体味人类文化与文学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1 关于经典阅读与经典出版
关于经典,从字面上看,经,指织布机上的纵线;典,原指放置于架子上的简册。《说文解字·丌部》称:“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1]陶东风则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 非功利) 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2]总之,经典要有一定的高度、广度和长度。“高度”,即思想学术价值,审美价值;“广度”,指作品影响的范围,不仅在本民族的文化语境下有影响,还要能为世界上不同民族所接受;“长度”即指作品经过漫长时间的检验,穿越黑暗的隧道而能传之后世。
世界不同的民族,在“轴心时代”(公元前6世纪前后)均产生了一批经典。因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最初成果,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称其为“元典”。如印度的《吠陀本集》《梵书》《奥义书》《佛经》,希腊的《荷马史诗》《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希伯来的《圣经》,中国的《诗》《书》《礼》《易》《春秋》[3]。这些作品经过后人不断地阐释与补充,成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代表之作。之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体裁,又涌现了一批被后人称之为“经典”的图书。如公元前6世纪至2世纪之间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等。史书从《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四史”发展到今天的“二十五史”。从实践中看,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典。从儒家倡导阅读的“四书五经”到历代学人开列的书单,以及今人遴选的“必读书目”,均反映了一个时代对经典的理解。
提倡阅读经典,是对阅读的一种科学理解。卡尔唯诺《为什么读经典》中说:“经典作品是一些能产生某种影响的书,它们要么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4]从荀子的《劝学篇》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先贤无不强调阅读经典的重要性,无不强调学以致用的必要性。同时,今天我们提倡阅读经典,则是对互联网时代泛阅读现象的一种反拨与补充。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倡导下,阅读经典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界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提供者,开始高度重视经典作品的开发与出版。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现当代有影响的著作,抑或是域外经典作品,都成为出版社关注和竞争的对象。特别是超过版权保护期,进入公共领域的著作,更是成为大多数出版社必出之常备书。也许是物极必反,重视经典出版却演变成了重复出版,各种版本不同包装的经典名著,在一定程度上“泛滥成灾”。据开卷信息系统统计,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一书,全国有186个版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一书,则有500多个版本。作为出版企业,从商业利益出发,开发经典名著无可厚非,但在一定程度上,出版社一窝蜂地争相出版,则说明出版资源的匮乏,经典名著的稀缺。
那么,何处去寻找经典呢?
近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经典和经典化的问题有很多讨论。1997年1月,荷兰莱顿大学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文学经典问题,会后出版学术论文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2013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研讨会,讨论“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问题。这些会议都涉及一个问题,如何来评价经典,如何来“经典化”现有的作家和作品。
2 关于作家作品经典化的思考
关于文学的经典化,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otosy)说:“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图书的销量,图书馆使用等)。”[5]童庆炳认为经典的构成有“六要素”: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他指出“‘读者和‘发现人是内部和外部的中介因素和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6]。这充分说明,作为“阅读”和“中介者”的出版機构,在经典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出版机构和编辑建构经典的实践,出版史上已经有很多范例。如名列“五经”之首的《诗经》,司马迁认为,是孔子这位大编辑家编纂修订而成的。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虽然人们对司马迁的判断还有质疑,认为《诗经》不是孔子整理的,三百五篇孔子出生以前已厘定,《论语》中他与学子的对话曾多次提到三百五篇,以此证明孔子没有参与《诗经》的修订,但这是学术探讨,一家之言,孔子对于《诗》成为《诗经》的“经典化”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学界则无异议。
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受命统领一批专家学者整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典籍。这些典籍是用简牍作为载体,因时间久远,编绳朽烂,竹简混杂,内容无法衔接;同一图书,因为抄写之故,各有异同。他组织众人“广辑众本,补缺去重”“校雠全文、厘定文字”“编定目次、确定书名”“撮其旨意、撰写叙录”“杀青定稿、缮写上奏”“剖判艺文、编成目录”[7]。经过20年的努力,众人前后整理出6大类,38种,634家,13397篇,图45卷著作,为中华民族保留了西汉以前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刘向将整理时撰写的叙录编在一起,形成《别录》一书,其子刘歆在其基础上压缩为《七略》。《别录》《七略》虽已亡佚,但在《汉书· 艺文志》中仍能窥其一斑。《别录》不仅开创了我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先河,也是西汉及以前学术史的完整总结。endprint
世界文学名著的经典化过程莫不如此。莎士比亚剧作成为经典,众多研究者认为,出版商、编辑和印刷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7世纪初,莎士比亚的才华因为缺少传播的原因,并不为知识阶层,特别是贵族阶层知晓,身份卑微的剧院演员、编剧莎士比亚甚至遭到不少人的揶揄和指责,直到出版商爱德华·布朗特(Edward Blount)和吉嘉德父子(William and Isaac Jaggard)为他印刷了对开本的两首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鲁克尼斯受辱记》,莎士比亚才受到伦敦知识阶层和贵族的关注。之后,他的18个剧本多次重复印刷,英国的知识阶层广泛地阅读、批评,这才标志着诗人“经典化”的成功。因为在此之前,雅致而稀有的对开本是印刷业对作家实行“经典化”的重要表征,此前,仅有乔叟、斯宾塞、本·琼生等极少数诗人印行过对开本。而19世纪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了不起的盖茨比》,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不朽经典,则得益于美国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功劳,特别是出版社“英雄编辑”珀金斯的慧眼才得以实现的。无论是菲茨杰拉德、沃尔夫,还是海明威,当初都是籍籍无名的初学写作者,是出版社不断地将他们的作品送到读者、评论家那儿,才使他们从无名作者变成知名作家,才使他们的作品历经考验终成为传世之作。沃尔夫在长篇小说《时间与河流》的扉页上献给珀金斯的题词,也许最能说明出版社和编辑在作家经典化中的作用——“献给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一位杰出的编辑,一个勇敢、诚实的人。他坚持与本书作者度过苦涩、无望和疑虑的日子,让作者在绝望之时也不放弃。”[8]
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出版单位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如作家莫言,1981年初登文坛,从在保定文联主办的《莲池》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到1985年《小说选刊》选载短篇小说《大风》始。据统计,1985年至2009年,《小说选刊》共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15篇。特别是1986年,《小说选刊》选载了他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及其他几部中篇小说,一下将莫言推到了全国读者面前。1985年,莫言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国作协为之召开研讨会。第二年,作家出版社将《透明的红萝卜》放在“文学新星丛书”第二辑中,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1987年,山东师范大学召开莫言作品研讨会,会议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1995年,40岁的莫言出版五卷本《莫言文集》。在此前后,莫言的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各种选本和文集相继出版,不少大学聘请莫言担任兼职教授。莫言从一个山东高密最初仅有小学学历的写作者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作家,并最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出版界功莫大焉。出版界的功劳,莫言在不同的场合,多次由衷表示感谢。
3 出版社要采取措施发挥“经典化”的功能
出版单位在作家和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发挥的基础作用和传播效能,已经毋庸置疑。但从过往的作家经典化的范例来看,仅仅印刷成出版物或者放在新媒体上,作家作品立即受到关注的时代已经过去。出版社不仅要出版经典,更要主动“建构”经典。建构经典是作家“经典化”的过程,需要出版单位在这个长长的链条中发挥主体作用。
任何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首先是通过出版发挥中介传播的效能,才让社会充分了解其独特的魅力。出版是桥梁,是助产士。但出版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通过编辑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加工,才使其达到出版水准。所以,是否能成为经典,出版还具有评判功能。世界各个民族最初的元典,是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抄写、雕刻、印刷,才可能让后人沐浴到先哲睿智的思想光辉。如贝叶上的《佛经》,羊皮上的《旧约全书》,竹简上的《诗》《书》《易》《礼》《春秋》。屈原啼唱了中国诗歌的先声,三百年后经过汉代王逸的选编与解读,通过佣工的抄写才让我们领略到《楚辞》的瑰丽。再如当代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题材新颖,立意深邃,因其相较以往作品的“陌生性”,多家出版社难识庐山真面目,最后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周昌义、洪清波慧眼识珠,才得以没有让这部经典作品明珠暗投。
随着出版图书的便捷,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作品数量呈爆炸性增长。中国的纸介质媒体每年出版的新书达到20余万种,新媒体上的作品更是多如繁星。何种作品具有经典性,对于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往往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找到经典作品犹如大海捞针。因此,出版社要掌握经典化的主动权,采取不同的措施“建构”经典。
创办选刊。新时期以来,各种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但由于品种繁多,优秀作品散见于各种期刊之中,于是,一種以体裁划分精选优秀作品的期刊应运而生。如中国作家协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分别创办了《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1981年,福建省文联创办了《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河南省文联创办了《散文选刊》,郑州市文联创办了《小小说选刊》。1990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创办了《微型小说选刊》。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中华文学选刊》,吉林创办了《杂文选刊》。2000年,河北省作家协会创办了《诗选刊》。虽然,选刊所选作品因为种种原因并非篇篇都是珠玑,或者说还有遗珠之憾,但各种体裁作品中的佼佼者,通过选刊的集中遴选,基本上尽入彀中。这些选刊不仅给出版单位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还对作家的经典化起到了化石点金之妙。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稿)》一书中指出选刊的作用:“它们受到读者的欢迎,也一定程度起到‘经典化筛选的效果。”[9]如莫言的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选载。莫言在谈到与《小说选刊》的关系时曾说:“创刊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选刊》,毫无疑问已经是当今的著名刊物。现在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大概都与这家刊物有过联系……如果有过两三篇作品被转载,那他或她,几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作家的桂冠戴在头上了。”[10]其实,包括莫言在内,作家们都以作品被选载为荣,他们在介绍自己的年度成果或者履历时,很多人都会写上某某作品被某家刊物选载。由于选刊集中了年度最佳作品,国内的各种奖项,如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包括后来的鲁迅文学奖,很多获奖作品都出自这些选刊。如1984年至1986年两届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所有的获奖作品《小说选刊》都无一遗漏地选载过。endprint
出版选本。从古至今,有识之士在某一体裁的作品达到一定的积累程度后,都会从中遴选优秀的作品,汇编成书而广泛传播。选家要么怀抱着理想,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挑选作品,借以传达自己的追求和倡导;要么从商业目的出发,将同一题材、内容、时间的优秀作品集中出版,虽然主观愿望不一,但客观上发挥了经典化的功能。如编选《昭明文选》时,梁太子萧统组织一批文人,针对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综而不分的现象,对文学性强的作品作了梳理和区分 。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 ,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 ,义归乎翰藻”標准的文章才能入选。《昭明文选》是我国第一部按体裁区分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 ,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再如《唐诗三百首》,编者蘅塘退士从唐朝289年间5万多首诗中选收了77位诗人的310首诗。因其诗体完备、作者广泛、琅琅上口、易于成诵,所以超过众多选本而流布甚广。到了近代,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由赵家璧主编的10卷本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胡适、郑振铎、鲁迅、茅盾、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负责分卷编选,蔡元培撰写总序。由于编者权威,选编精当,为新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不少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
还有一些选本,以时间为界限,持续出版,也较好地形成了一定的文学史效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0年代初曾经出版过一些年度文学选本,对于读者阅读当年度的优秀文学作品很有裨益。199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了年选的出版,与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合作,开始编选“文学作品年度选本”。其中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以后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又扩大到微型小说、随笔、儿童文学、散文诗、杂文、青春文学、故事等20余个品种。紧随其后,1998年,漓江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不同编者遴选的年度选本。这些选本因为从沙里淘金,汇集了年度精品,广泛受到读者欢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年选最初每本销售在3000册左右,到了1998年,平均达到万册以上,最多的曾销售到2万册。目前这种年度选本全国已有时代文艺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花城出版社等十几家出版社在编纂出版。在谈到为什么编选年度选本时,文学评论家雷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年度选本的《编选说明》中写道:“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11]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请王蒙担纲《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的主编,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的研究员们负责各卷的编选,又选编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散文诗、儿童文学、文学评论9种选本。这些选本总结了60年来中国文学除长篇小说以外主要的文学体裁的创作成果。那些经过60年漫长的时间迭次洗礼的作品,最后集结在“大系”中,留下中国文学一甲子的记忆。
编纂丛书。丛书,是指由很多书汇编成集的一套书,按一定的目的,在一个总名之下,将各种著作汇编于一体的一种集群式图书,又称丛刊、丛刻或汇刻等。形式有综合型、专门型两类。从出版的角度,丛书具有完整性与系统性,方便读者阅读,从“经典化”的角度来看,丛书还具有“择优汰劣”的作用。中国丛书的编纂始于宋代,盛于清代。宋人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可算为丛书的鼻祖。清代《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共36304册,约9.12亿余字,分经、史、子、集四部,是中国古代丛书之最。到了近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继编纂了按“经、史、子、集”划分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当代有影响的丛书编纂,始于1980年代。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策划的《走向未来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策划的《走向世界丛书》。前者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著作,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前沿思考,后者则集中了近代中国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官员和学子出访世界各国时的文字心得。除此之外,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成绩的,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编纂出版的大型文学丛书《跨世纪文丛》。
19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文学创作空前繁荣,作家作品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一批被雪藏的老作家焕发新生,一批年轻作家脱颖而出,总结文学创作成果,推出文学选本便应运而生。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陈骏涛主编的《跨世纪文丛》第1辑12种出版。第1辑收录了王蒙、苏童、格非、叶兆言、刘恒、贾平凹、迟莉、方方、陈染、余华、刘震云、陈村12个人的作品。《跨世纪文丛》前后出版了七辑,共收录了66位作家的作品集,凡新时期以来国内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基本都“一网打尽”。入选这套文丛的作家,很多是第一次出选集,不少作品带有与传统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先锋色彩。这套丛书出版至今已30年,今天来看很多作品都还具有一定的经典意义,成为入选作家的代表作。所以国内专家称赞丛书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座丰碑”,是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次确认。“在文学史、出版史、文学研究史上都是有重要价值的”[12]。当时,不少作家把加盟《跨世纪文丛》作为表明自己身份的一种标志。如张抗抗的作品被收进第四辑后,她在《越海之舟》一文中写道:“我已经出版过多种小说集。但自从得知《跨世纪文丛》横空出世,便在心里认为:自己若不跨入‘跨世纪文丛,一定是跨入那个新世纪的莫大遗憾……由于《跨世纪文丛》收入了几乎所有我喜欢的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更由于《跨世纪文丛》在如今商业气息甚嚣尘上的流俗文化中坚守了至今痴心不改、初衷不改的纯文学品格。”[13]endprint
出版评点本。评点、注释、疏证、正义、章句经典作品,是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传统。无论是最早对《春秋》进行演绎补充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还是对文学总集《楚辞》进行补充注释的《楚辞章句》,以及唐太子李贤注释的《后汉书》,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解读与评判,使其完成经典化的过程的。如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本被士人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汉书·艺文志》曾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为也。”但通过李贽、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等批评家的评点,明清小说的社会意义、艺术价值得到肯定,明清小说得以从“小道”而成为文学上乘。如毛宗崗本《三国演义》《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脂砚斋本《红楼梦》,李渔评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等,风行一时。这种评点本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批评,但有助于读者对小说的阅读理解,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今天,一些当代作家作品也相继出现了评点本。如贾平凹、陈忠实、金庸、二月河、孙皓晖、唐浩明等的作品,皆有今人的评点本出版。贾平凹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土门 》《浮躁》《白夜》《高老庄》评点本时在“前言”中写道:“参加这次评点的肖云儒、费秉勋、孙见喜、穆涛诸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他们有兴趣作这项工作,并十分地严肃认真,着实让我感动,向他们致以谢意。”[14]
加大图书的对外翻译工作。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中国作品,要成为世界经典,让各民族分享中国经典的价值,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达到目的。同时,很多作品,如果能受到异域读者的重视,也会加快在中国经典化的进程。中国经典译介到国外最早而且版本最多的是《老子》,17世纪末,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将《老子》部分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出版。斯达尼斯拉·于连(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在1842年出版了法文版《道德经》全译本。目前据统计全球有500多个版本,销量仅次于《圣经》。西方不少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文学家都曾多少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正是通过斯达尼斯拉·于连译本知晓了老子的思想,并深刻影响了他晚年的处世方式。但是,《老子》引起西方的重视源于传教士希望从中找到上帝的痕迹,起因并非重视东方的文化。因为语言、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诸多因素,中国的图书走向世界十分缓慢。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版权贸易数据,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中国版权贸易平均比例10.17∶1,引进远远大于输出。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缩小到2∶1。这缘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力推的经典翻译工程和出版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的合作。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引进版的管理类图书和文学类图书曾连续多年占据国内图书排行榜。如美国作家丹·布朗创作的长篇小说《达·芬奇密码》,2004年在中国上市,连续三年高踞全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让中国当代作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经典,必须重视对外翻译工作。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则得益于他的作品很多被译介到国外。他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爆炸》1992年就在美国出版,之后几乎年年都有作品在世界上翻译或获得各种奖项。其实中国作家获诺贝尔奖比较少的原因,有汉学家认为,是评委懂得中文的太少,中国作品翻译到西方的太少。西方学者评价陈忠实时曾说,“从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15]。因此,出版单位要积极主动将本单位最为优秀的作品译介到国外,这样才能引起重视。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出版的长篇小说《狼图腾》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发行,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由中法合拍,这与责任编辑安波舜不懈地向外国出版商推介《狼图腾》是分不开的。2005年,小说在中国图书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后,他就用英语做成《狼图腾》推广文案,主动选择国外的主流媒体发表书评,如德国的《南德意志报》、意大利的《意大利邮报》、英国的《泰晤士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并且放弃国内的版权代理机构而直接与外国出版商联系,实现了《狼图腾》一书价值的最大化。
通过评奖来确认经典价值。评奖是一次价值判断,也是一次去粗取精的过程。虽然,无论任何奖项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左右,但如果是确有价值的作品,往往通过评奖这种筛选过程而被人发现。目前国家级的出版奖有“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韬奋出版奖”。同时还有一些省部级的奖项,如中国作家协会设立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尽管入选作品因为种种因素并不都能称之为经典,但具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遗漏。如被人认为是新时期最重要收获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虽然因为作品中关于国共两党“翻鏊子”的一番话曾引起争议,但评委们想方没法,以“修订本”的名义让其入选。其实陈忠实虽然也打算修改这部作品,但当时并没有动手。这部以“修订本”名义入选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开创茅盾文学奖评选先河。虽然有专家和刊物认为此举并不公平,但大多数评委们认为,如果《白鹿原》这部作品不能入选茅盾文学奖,会让这个奖项的含金量受损,评委们也都会终生遗憾。当然,评奖并不是评判作品是否经典的唯一标准,如二月河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评论家丁临一认为“《雍正皇帝》可以说是自《红楼梦》以来,最具思想与艺术光彩、最具可读性,同时也最为耐读的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称之为五十年不遇甚至百年不遇的佳作并不夸张”[16]。该书两次参评茅盾文学奖,但最终以一票之差而落选。不过,此书《亚洲周刊》将其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足见经典是不会被埋没的。
除了政府机构设立的奖项外,出版单位自己通过设立奖项,来推动作品的“经典化”,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上述香港《亚洲周刊》组织专家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即为一例。评选时,编辑部先提供500种图以及书的书目,聘请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北美的知名专家组成评委会。经过多轮淘汰,最终评出在世界华文圈产生了广泛影响的100部作品。由于参评专家权威,评奖过程无权力干预,评奖结果得到各界认可。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设立了“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春天文学奖”“年度翻译文学奖”。长江文艺出版社设立了“九头鸟长篇小说奖”。这些由出版社自己设立的奖项表明了出版社寻找经典的努力,也确实让人们发现了一些好作品。如作家张一弓虽然写了很多作品,但专家认为新闻烙印太重,而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第一届“九头鸟长篇小说奖”的《远去的驿站》,从历史的角度写出了时代与人性的复杂,代表了作家创作的新高度。这部长篇小说后来入围“茅盾文学奖”终评,并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姜戎的《狼图腾》也曾入选第二届“九头鸟长篇小说奖”,后此书获得“亚洲曼氏文学奖”。同时,不同的协会及学会还设立了各种体裁的年度排行榜。如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每年评选小说排行榜、散文排行榜,通过排行来确认作品的经典意义。endprint
加大发行力度,让更广大的读者,包括专家学者了解作品。当然,作品是否具有经典价值,要接受读者包括专家学者的检验。因此,出版单位要尽可能地扩大发行,只有充分地占有市场,读者才有可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容。如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199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因为印数很少,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很少有影响。作品虽由张艺谋改编成电影,但由于电影在国内没有放映,对图书也没有产生推动作用。后来此书的法文版、意大利文版、日文版、荷兰文版、英文版相继在国外出版,并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台湾《中国时报》十本好书奖(1994年),香港“博益”15本好书奖(1990年),《活着》在国内才逐渐产生影响并大量印刷发行。该书作者因此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作品入选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入选中国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
也许有人会说,图书的销量并不能代表图书是否经典,有些十分畅销的大众普及读物与经典无关。畅销书是不能与经典划等号的,但如果具有经典价值的图书能够畅销,则增加了读者和专家的关注,而使“经典化”成为可能。在中外出版史上,畅销书成为经典传世的不乏其书。如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巴尔扎克的《悲惨世界》、安徒生的童话、中国的市井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出版后都曾一度洛阳纸贵,家喻户晓。图书的畅销并不代表其媚俗,反是彰显其价值的最好机会。如当初曾被道学家斥为“淫书”的《红楼梦》,几度被禁,近代研究该书还成了一门显学。
要加大作品的宣传推广力度。中国目前一年有几十万种新书上市,一部再有价值的作品,如果不进行宣传和推广,都可能会被淹没在书海中。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泛滥,图书众多,一本书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如果不能很好地挖掘,读者则无从知晓,专家也不会引起注意。图书宣传的方式本文不再详述,但如果彰显作品的经典意义,一般性的广告、出版消息,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采取大众狂欢的方式来推广作品,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相反还会降低作品本来的经典价值,而被沦为一种大众普及读物。突出作品的经典意义,只有召开专家座谈会,或者请专家撰写有分量的文章,对作品的内涵进行深入解读,然后通过文字的形式,在报刊上发表,或者进入大学的课堂,这对作品“经典化”才会产生催化作用。
专家研讨会上正面的评价是必须的,但如果讨论缺乏真诚的批评,而是一味地赞扬,不仅不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不利于作家的成长。写一篇称赞的文章几千元酬劳的“红包评论”,“实质是市场规则对艺术原则的侵蚀和扭曲”[17],对于作品的经典化也毫无意义。如果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或者撰文反对,相信作品的价值会越辩越明。如张一弓在新时期之初发表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巴金主编的《收获》冒着风险刊发后,也曾引起巨大争议,但作品直面现实,敢于反映历史创伤的无畏精神最终得到认可,小说获得了首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张贤亮的《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出版后,也有批评家认为性的描写太多,但作家反思历史、面对伤痕的真实描写赢得了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再如熊召政获“茅盾文学奖”的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出版后,也有专家撰文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有些情节与史实不符,出版社出版研究论文集时,特意将这篇持不同观点的文章收入其中,那位专家知道后,十分赞许出版社和作者的“胸怀”。
近年来由于大众媒体的兴起,传统纸介质媒体对读者的吸引力在下降,如果通过延伸产业链,将作品改编成不同的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剧,扩大受众范围,则会加快作品经典化的步伐。虽然电影、电视剧属于大众传媒,但电影的放大效应会促使读者进一步阅读纸介质出版物。当然,如果电影电视剧拍摄得十分低劣,对于纸介质出版物也可能还会带来负面效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电视剧放映前图书销售还不错,但电视剧放映后,销售反而下降。当然,如果作品是经典,第一次改编不理想,后面还会有多轮的改编。如《巴马修道院》《悲惨世界》《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外名著,都经过了多轮的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
4 结 语
关于经典的界定,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被称为“经典”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最后发现其并不具有经典意义,而另外一些不被人重视的作品却浮出水面,显示出作品的内在价值。考察中外经典诞生的过程,这是一种符合事物认识规律的客观现象。专家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都要经历过反反复复的‘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拉锯式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所谓文学的‘经典化从来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的、接受各种力量考验的保值、增值或者减值的动态过程。”[18]王国维也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9]如“文革”中十分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图书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还有些作品,因为某些政治原因,或者阅读趣味的变迁,当时并不为人看好的作品,又重新发现其价值。如沈从文的边地小说,张爱玲的女性小说,周作人、林语堂等的散文,时隔几十年,再度进入大陆读者和研究者视野。有人统计过,如果一个作家去世后20年后还有人阅读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该作品能够属于经典之列。
同时,经典也是在不断丰富完善的。如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在战国时与墨家、法家等作为一家之言而对待,汉代经董仲舒等人提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定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著作才被称为“五经”而对待,但后来发展到唐代,将《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文宗开成年间,除了“九经”之外,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成了“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收录,就成了如今的“十三经”。再如《史记》,按当时正统观念看来,《史记》是离经叛道之书。司马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20]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非贬孝武,令人切齿。”[21]除此之外,史学在汉代还没有独立的地位,这种文化背景也影響到《史记》作为经典的建构过程。直到东汉中期以后,《史记》才渐渐受到重视。《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死后,其书稍出。宣帝后,迁外孙平通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魏晋之后 ,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在学术领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记》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才得到人们的认识。再如《圣经·新约全书》,成书之际曾受到罗马统治者的贬抑排斥,只是作为非法抄本在下层人民中秘密流传。endprint
总之,出版社要有历史意识与经典意识。一部作品是否能成为经典,虽然并不是出版者单方面一厢情愿的结果,如前所述,作品的经典化有诸多要素。但是,作为出版单位,在市场经济和新技术带来的双重挤压下,要承担出版人传承文明的神圣职责,则一定要坚守本位,不能做金钱的奴隶,商品的附庸,我们要赢得尊敬,就要多出好书,就要让好书成为经典传之后世。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需要全体出版工作者为之努力。
注 释
[1][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8
[2]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3)
[3]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2
[4] [意] 卡尔唯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譯.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6
[5][加]斯蒂文·托托西著;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4
[6]洪子诚.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0
[7]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64-168
[8][美]A ·司各特·伯格著;彭伦译.天才的编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24
[9]童庆炳.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5
[10]莫言.我与《小说选刊》[2004-01-0 2]. http://vip.book.sina.com.cll
[11]雷达.中国文学作品年度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
[12]陈骏涛,陈墨.陈骏涛口述历史:主编跨世纪文丛及其他[J].名作欣赏,2015(10):67-68
[13]张抗抗.越海之舟[N].中国图书商报,1998-02-06
[14]贾平凹.关于我的小说评点本[N].中华读书报,2003-03-01
[15]寿鹏寰.西方学者评《白鹿原》:不比获诺贝尔奖小说逊色[N].法制晚报,2016-05-03
[16] 丁临一.二月河横空出世[N].北京青年报,1996-02-01
[17]杨晓华.岂能因红包而评论[N].中国文化报,2014-11-07
[18] http: // blog.sina.com.cn/s/blog_5fc7be640102ww1u.html
[19]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自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20]范晔.后汉书·蔡邕传[M].武汉:崇文书局,2017:1471
[21]陈寿.三国志·魏志·王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418
(收稿日期:2017-09-0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