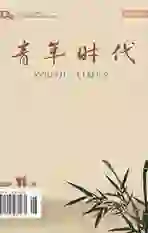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2017-12-07陈美真
陈美真
摘 要:以塞亚·伯林对自由概念的划分成为定义自由的经典,本文将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著名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进行剖析,并着重分析伯林对积极自由的构建和批评,最后分析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背后的所持的价值多元论观点,指出伯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并不能绝对的割裂。
关键词: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理性
一、两种自由概念
首先,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上指出,他所讨论的自由,是政治领域的自由,而不是精神意志上的自由,并且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是源自对“服从与强制”这一政治核心问题的不同的回答。随后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所谓的“消极自由”回答的是,“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而积极自由回答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消极自由
伯林认为,自由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并且特意指出,只有他人蓄意地对人们的行动予以干涉和妨碍的时候才算是自由的缺乏,而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叫作缺少自由。
此外他还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消极自由理论。对人性持乐观见解并相信人的利益有和谐共处的可能性的哲学家认为,人们活动的目的可以自动地相互协调。而另一些哲学家认为人们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并不相协调,必须构建防范措施使其各安其所。但两者都同意保留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而最低限度的自由是什么,伯林指出,“一个人不经殊死搏斗便不能放弃的,是他的人性的本质。”这样对自由的最低限度的问题还要诉诸人性的本质的讨论,因此伯林也没有解决这个界限问题,因为这不是伯林要讨论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自由都是“免于……的自由”,即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
(二)积极自由
伯林对积极自由的论述主要是从批判的角度展开的。
所谓积极自由就是“去做……的自由”,即某一主体能够有权去做他想做的事,或成为他想成为的角色。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決于随便那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的活动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我希望是个人物,而不希望什么也不是;希望是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是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我导向的,而不是如一个事物、一个动物、一个无力起到人的作用的奴隶那样只受外在自然或他人的作用,也就是说,我是能够领会我自己的目标与策略且能够实现它们的人。”因此积极自由简言之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但是伯林指出,这种自由会导向极权主义。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这种理性主义的自由观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一方面,伯林从自我追寻自由方面对理性主义的自由观进行了批判。首先伯林对斯多葛主义的自由观进行了批评,他称之为“退居内在城堡”。对于康德“理性的自律”的自由观,柏林的态度复杂得多。康德指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自由不是他律的,而是自律的,即自由源于自我对欲望的合理控制。伯林对此是赞同的,但他也看到,当人类发现太多的行动道路被堵塞时,从追求“合理的自律”退回到人“内在的城堡”,从“对欲望的控制”转化为“对欲望的消除”有着不可抵抗的诱惑。以放弃外在的行动为代价,片面追求内在的精神自主的积极自由观,是维持极权统治所必需的,或者说,它正好构成了极权暴政的另一面。其次,伯林批判对地位的追求来获取自由的观点。他指出,这种对地位的追求是某种与自由近似但本身并非自由的东西,对地位的寻求并非强调“不受任意干涉”的消极自由,也不完全等同于积极自由。获得地位与承认,虽然会增加整个整体的某种自由,却并不必然增加群体中每个成员的行动自由。
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积极自由观必然导致真实的自由外化为某种规律、某种集体意志或国家意志,以某种共同目标扼杀个人自由。首先他否定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信条,认为这种自由观将人类对必然性知识的探索与掌握看成是自由经验本身,这就构成了事实与价值的混淆,必然会导致“目的证明手段合理”的逻辑谬误,并且它造成了自我实现的自由观的内在悖论:自由即服从,是人类社会完全整齐划一。其次,他对理性主义自由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个人的“真实的”自我被某种社会整体所代替,这个“整体”以真正的自我自居,将其意志强加于其成员,即个人,并且声称是为了把这些个人提升到更高的自由水平,以至以某一目标的名义而强制人们是可能的,甚至是合理的。这必然忽视人们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以人们自己的名义而欺辱、压迫和拷问人们,以自由的名义而剥夺人们的自由。伯林也否认法律等共同规范对人的限制是为了人的自由,平等的自由不等于自由的增加,自由是自由,平等是平等,不能相互混淆,因此他也提出自由与民主的关联并不大,消极自由所关注的“不是谁行使着这个权威,而是不管在谁手中,权威到底应该有多大。”而什么东西能使一个社会成为真正自由的社会?一个原则是,只有权利,而非权力,才能被视为绝对的,从而使得所有人,不管什么样的权力统治着他们,都有绝对的权利拒绝非人性的举动。第二个原则是,存在着并非认为划定的疆界,在其中人必须是不可侵犯的;这些疆界之划定,依据的是这样一些规则:它们被如此长久与广泛地接受,以致对它们的遵守,已经进入所谓正常人的概念之中,因此也进入什么样的行动是非人性与不健全的概念之中。
二、伯林自由观的评析
伯林对积极自由的批判和对消极自由的支持是建立在价值多元论基础上的,他反对极端的理性主义的一元论,提出了以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的多样性与诸价值间存在不可通约的基本冲突为核心内容的多元论主张。其基本内容是:首先,在任何善或行为准则的范围内,终极价值或人类目标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冲突;其次,任何善或价值本质上都是复杂的和内在多元的,其中一些要素之间不可通约,甚至互相冲突;最后,不同的文化形式产生出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这些文化尽管包含着一些重叠交叉的特征,但其中也有许多不可通约的优点、美德和善的观念。这种根源不同文化或社会结构的善的观念也是相互冲突的。endprint
伯林之所以要极力倡导价值多元论,就是为了最终不受制于由理性一元论所导致的极权主义,从而保障人们享有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首先,因为一元论的信条总是倾向于在现实中以高悬起来的唯一目标的形式与现实中的人的自由相冲突,从而缩小以至剥夺了每个个人选择的自由。而价值多元论为每个个人敞开了自由选择的大门,它承认人类的目标的多样性,这些目标不能用同一尺度来衡量,而且还不断地处在彼此竞争冲突之中。其次,伯林认为一元论寻求所谓的“单一答案”。并且一元论认为只有这种“单一答案”才是正确的,而且无论采取的方法是否相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结果上都是追求唯一的,这种观点是机械决定论的结论。最后,伯林认为,一元论主张寻求全部答案,并且认为一旦做到这一点,一切問题的终极解决之道也就找到了。
在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关系上,伯林的主要批判对象主要是马克思,但他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贬低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他的目标本身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如同人首先是社会的人一样,自由首先是社会的自由,没有社会自由就没有个人自由。社会自由是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和基础。个人自由不能脱离社会自由,脱离社会自由的个人自由不成其为自由,其结果将走向自由的反面,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
在表面看来,伯林主张的是多元论,但透过面纱,我们却能看到所隐含的一元论成分。在伯林的心目中,“自由”(实为个人自由)终究是真正的终极性价值。他的所谓的多元化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化而已。
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所关注的是决定某个行为的来源或主体是谁,其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然而,在伯林所认定的消极自由中,同样存在着这种主体对自身的决定作用,而且只要是在主体免受外界干涉的范围内,这种决定作用就是不容干涉或剥夺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并没有从逻辑上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区别开来。并且如果没有一个如伯林所反对的某种强制性干预的法制社会,这种“免于……”的消极自由是不会生效的,所谓“免于……”的自由同时就是能够通过某种手段(如法律)而在某种范围内有效制止其他人干预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任何强制,而在于这种强制是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不受限制而自愿接受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区分哪一种自由,而在于如何把自由和不自由区别开来。真自由既是积极地,也是消极的,而不自由也既可以伪装成积极自由也可以伪装成消极自由。因此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不是自由的两种对立的形式,它们是同一种自由的两个方面。
三、结语
伯林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形式,在价值多元论的基础上,对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认为积极自由可能发展成为极权主义,消极自由才是自由的合理的形式。但是,伯林在逻辑论证上有着不能自圆其说的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无法实现这两种区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只能是同一自由的两个方面,不能相互对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划时代的作用,为我们对自由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英]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英]约翰·格雷:《伯林》,马俊峰、杨彩霞、路日丽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
[3]邓春梅:《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伯林法价值理论及其发展研究》,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
[4]刘明贤:《以赛亚·伯林自由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