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往事(二)
2017-12-06夏栀
夏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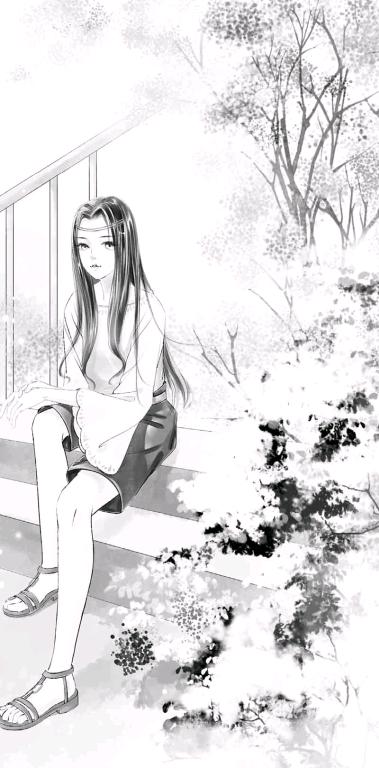
夜里十一点,陆江川悄悄出了家门。
镇上的小路旁是没有路灯的,野草长得有半人来高,不时传来虫鸟鸣叫,风过树丛的摇曳声。
为了不让家人发现,江川摸黑走了很远。背后遥遥似有脚步声传来,他也没敢回头。
这个古镇有着太多太多光怪陆离的传说,即使是年轻气盛的陆江川,也熬不住走夜路时背脊发寒。
脚步声一时间更重了,好像在跟着他。江川打开手电筒跑了几步,身后的“东西”竟然也迅速跟了上来。
“谁?!”
他照向身后,恍惚中看到一张白脸闪过。他正准备抓起路边的一块碎石扔过去,就听到“白脸”焦急地喊道。
“别扔,是我!”
“煜泽?”
江川放下手里的碎石,无奈地松了一口气:“你怎么来了也不出声?”
傅煜泽似乎比他还要无奈,龇牙咧嘴地指着赤着的一只脚说:“你先把手电筒给我,找找鞋!”
傅煜泽是尾随陆江川出来的,他知道他们家十点左右就会关灯睡觉,以江川谨小慎微的性格,一定会再稳一个小时再出来。
他一直蹲在陆家的院墙后面,本来是想吓唬他的。奈何今晚没有月亮,虫草树影又晃荡个没完,他也怕了。偏生江川还越走越快,傅煜泽一路跟下来,没吓唬到江川,自己就先慌了个“魂飞魄散”。
大老爷们儿怕黑,还跑丢了鞋。这话说出来必然是不体面的,所以傅煜泽也没打算说,沿着小路从水沟里捞出拖鞋,义正词严地告诉江川。
“我当然是因为担心你,一个人去哪有两个人去安全,不得有一个放哨的?”
江川说的那户有白马的人家,是镇东头紧挨桃树林的。林子挺大,遥遥一束白光打过去,根本看不见尽头。
白马就拴在桃树林边的一处窝棚里,棚边有一间小屋,灯灭了,住的人想是也歇下了。
两人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边上,没敢妄动,先蹲了一会儿。
“我觉得这匹马长得非常之不友善,你看它,听到我们靠近就在踢踏蹄子。”
煜泽话多,紧张的时候更是止不住话匣子。他就这么蹲在江川身边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江川拎着剪子要过去,又被他一把拉了回来。
“你有没有尝试过马语?要不要先跟它沟通一下?”
江川看他的眼神好像在看一个傻子。
“我这是打心里担心你,你能不能不要用看郭儒雅的眼神看我?”
其实你的智商真的不比郭儒雅强多少。
“哎!等一下,别着急!”
傅煜泽看江川去意已决,再次拦在了他跟前。
“我跟它说说。记得啊,二胡做好了得在陆瑶妹妹面前提一下我。”
江川拧不过他,只能依言站定,把手电筒的光打到窝棚里。傅煜泽就缓慢地,以一种老驴拉磨的姿势绕马而行,脚尖着地,脚跟半悬着,像在进行某种古老的祭拜仪式。
“大白,你我初相见就为了取你的尾巴毛,确实有那么点说不过去。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啊,为什么我们不去剪别的马,偏要来剪你的呢?哈哈,告诉你吧,那是因为你帅气!百里挑一的帅气!”
他当真跟它攀谈了起来。
白马打了个响鼻,不耐烦地挪动了几步。
江川就顺着这几步,向它的背后挪动。
“剪尾巴毛就相当于剪头发,人的头发长了,要剪,马的尾巴毛长了,自然也要剪。我们这边唯一一个不能剪头的日子就在正月,会死舅。但现在的人也没那么在乎这些了,除了舅舅。”
白马像是突然好奇这份唠叨,逐渐安静下来。煜泽暗暗对江川比了个手势,江川就掏出了剪刀。
“你一定没有舅舅吧?就算有,咱们也不是正月剪的。在此祝愿你舅舅身体安康,长命百岁……”
多亏这个时候没人,要是有人,陆江川和傅煜泽能被笑话一年。
两个人也都算是在学校有头有脸的校草级人物,一个对着马念叨着舅舅论,一个一脸凝重地握着把剪刀半蹲在马屁股后面。
知道的是要剪毛,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扒马皮呢。
“其实这些都不可信,我正月里就剪过头发,我舅舅还活得……”
说时迟那时快,江川左手迅速捞起一缕马尾巴毛,右手下剪。眼看着就要齐根剪断,剪子却在这时钝了一下。
也正是那一下,让回过神来的白马长啸一声,后足一个发力,将对它“意有所图”的少年踢出去很远。
“谁在外面?!”
窩棚边的小屋亮起了灯。
“江川!”
吓得手足无措的傅煜泽几步跑到被马踢飞数米之遥的陆江川身边,手电筒掉落在地,光线在黑夜中画出一个灰白的圆弧,像一把扇面纯净的扇子。如果不是有阵阵剧痛来袭,陆江川真想在扇面上画一幅画。
很快有大人从屋里追出来,在强烈的手电筒的白光照耀下,两个孩子根本没有逃走的余地。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大半夜的不睡觉跑过来,想干什么?!”
守夜人本来还有几分担心,以为遭了贼。这时看到是两个孩子,心稳了,火气也一股脑地升到了头顶。眼看着他们不说话,他抬手就打了其中一个人的脑袋。
“问你们话呢,刚才胆子不是挺大的吗,这会儿知道装闷声王八崽子了?到底是哪家的,快说!”
江川的唇几乎抿成一条直线。
刚才被马踢中的时候,他明显感觉手臂发出一声脆响,紧接着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现在连挪动一下都不行了。
傅煜泽是个心里没主意的,挨了一巴掌也只顾着看江川。他发现江川疼得浑身都在冒冷汗,唇色也是惨白一片。屋里冲出来的人又一味地凶神恶煞,两两相交戳着他的神经,急得他心中慌乱,手足无措。
“完了,这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说别来嘛,我家有钱,能买,你就是不听我的。你说这可怎么办?你要是死了,我惦记陆瑶的事还能成吗?我成了杀死大舅哥的混账了。别说你爸你妈,光是陆瑶就能恨死我了。”
煜泽是少爷,从小养尊处优惯了,没遇上过什么大事。这回遇见了,急得好一通语无伦次。守夜人看他像个傻子,正准备再使点劲把他拍醒,他好像又明白过来,瞪大眼睛去扯守夜人的衣服。
“叔叔,赶紧送他上医院吧!”
大人一看这光景,再责难下去也没什么用,但是他不能就此送江川去医院。
首先一点就是,医药费谁出?他们偷跑到自家后院伤了胳膊,贸然送过去,他还得掏钱给孩子看病?万一被讹上了呢?
其二,他看他们都穿着家常裤子和拖鞋,无疑就是这个镇上的,找到他家就不会远。而且这种事情必须得通知孩子的家长,不然可是要落埋怨的。
于是张大叔一连细问了好几遍,才在傅煜泽的嘴里问到了陆家的地址。
两人连托带扶地把江川夹回去,到了家门口,他的两条腿就像生了根一样,不走了。
“叔叔,咱们不要动静太大了。”
这是江川被马踢了以后,说的第一句话。
张大叔以为他是担心父母知道了要挨揍,咧了咧嘴,不仅没有一丝认同,甚至还有点想笑。
“这会儿知道害怕了,下次看你还敢不敢碰那马。”
话虽然这么说,敲门的动静也称得上温和了。
“哪位?”
不多时,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张大叔一听是个中年男音,不由得看了陆江川一眼。似乎在说:小子,这我就帮不了你了,赶巧就是你爸听到的。
张大叔没有发现,陆江川反而悄悄松了一口气,心中微微有点疑惑,他什么时候回来了?
陆东离家已有大半年,这次无声无息地回家却是一副酒醉未醒的样子。大门敞开的时候,他还打了一个响亮的酒嗝。凌乱的头发如杂草一般扎根在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头上,也可能是长久不修剪,已快披肩,纠纠缠缠邋里邋遢。
不修边幅的男人很多,可陆东却更像是一种自暴自弃。他的头微垂着,肩膀微塌,像一具没有生气的行尸,又像是很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脖子,压断了脊骨的走肉。
他眯着眼睛先看了门口的男人,又错开男人看了看他身后的江川和傅煜泽,愣了一下。
“这是怎么了?”
他说话也口齿不清,张大叔甚至不知道这人究竟是清醒的还是糊涂的。
为了不耽误孩子,他决定先挑重要的说。
“你儿子的手臂骨折了,得马上去医院。”
“骨折了?”
陆东这时才似醒了几分,他大概还想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摇晃着走了两步,发现没有办法站稳,只能又停下。
“对,骨折了。你准备一下钱,估计得花不少。”
钱?
陆东低头翻找了一下裤口袋、上衣口袋,再是鞋底。几张毛票子攥在手心,配着他因为翻扯而完全暴露在衣裤外的口袋,有几分滑稽,几分惨淡,几分凄凉。
他将手里的票子攥得很紧,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也许是在估算这笔巨额开销的“重量”,也许是在深思家里要承担的这种无端的负荷,也许,还有其他的。
陆东混沌的目光在张大叔、傅煜泽和江川身上打了个来回,最终定格在儿子苍白如纸的脸上。
“您等等,我去里屋拿些钱,就走。”
他把毛票子揣回口袋,几步踏回小院。院子里的洋井水泵很快响起了古老而悠长的嘎吱声。
陆东用井水踏踏实实醒了一下神,又闷头向屋里走。
跟陆江川一样,陆东也是个寡言的人,寡言到跟自己的妻子和儿女都没有话聊的地步。同时,他也是从男孩叛逆躁动的年纪过来的,有时也不是不想斥责江川,但他从养这对孩子开始,就没有看管过任何事,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也就更加不知该如何责难了。
“陆东,是你在外面吗?”
江川妈妈屋里的灯亮了。
陆江川未受伤的那条手臂,还有手指紧跟着一抖。陆江川爸妈的感情并不好,从江川记事起,两个人就是分房睡的。
江川听到了鞋底趿拉地面的声音,心一阵紧缩。声音越来越近,江川就越是不安。
“江川!你怎么了?”
终究还是瞒不住的。
赵曼如在看到半开的院门外站着的孩子时,三步并两步冲了出来。
“江川,你怎么了?”
“妈,我没事。”
江川强忍着手臂撕裂的疼痛,艰难地抓住赵曼如的手。
江川还想说,您先进去吧别吵醒了陆瑶,就听到赵曼如更加激动的说:“你裤子上怎么全是泥?你的手怎么了?骨折了?”
一连串的追问如连珠炮一般響起,邻居家的大黄狗也因着这串突兀的惊叫,凑热闹一般吠了起来。
“哪儿疼,快告诉妈妈,胳膊还能动吗?”
陆东虽然喝多了,大抵也能明白儿子的意思。他怕妹妹听到了会担心,因此很快拉开赵曼如。
“你先进去吧,孩子现在的情况需要马上去医院。”
赵曼如这才稍稍冷静了一点,她知道不能耽误了正事,听了陆东的话以后,转身就打算回屋里换鞋,却被陆东再次叫住。
“我带他去就可以了,你去睡吧。”
他说完就要走。
“那怎么行,现在孩子这种情况,我当然得跟着去了。”
“别添乱了,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
陆东执意不肯,江川轻声说道:“你在家陪妹妹吧,我怕她晚上突然醒来,没人在家,她会害怕。”
傅煜泽没来陆家做过客,因此并不知道陆家是怎样一个光景。按理说父母同时陪同孩子去医院也是正常的,他为什么要阻止?
阿泽正疑惑着,想说要不就一起去吧,却在看到赵曼如的神色后逐渐变了。
那种神色的变化微妙而诡异,仿佛就在瞬息之间,仿佛又像在经年累月里。女人披着略微松散的长发一步步后退,退到门槛处,脚跟磕了一下。她贴着门框,看着众人,幽幽地问:“为什么我不可以去?为什么在这个家里你们总是视我如无物?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我活得就像一个摆设,一个不起眼的铜锅破盆!”
她莫名的怒火化为歇斯底里。
傅煜泽吓坏了,每一对父母之间都或多或少会发生争吵,他的父母也会吵架,却从来没有像江川妈妈一样,“激动”成这样。
傅煜泽再看回江川父子,他们似乎也被吓了一跳。但这种惊吓跟他的截然不同,更像是对某种即将爆发的灾难,发自内心地恐惧和担忧。
“妈妈。”
江川试图用声音唤醒赵曼如。
赵曼如却已经进入到一种近乎癫狂的情绪中,反复说:“当我是铜锅破盆,当我是铜锅破盆。儿子是不是我生的?儿子……江川!”
赵曼如突然无助地叫了江川一声。
“妈。”
江川趕紧回应。
赵曼如哭了,从啜泣到号啕:“你是我生的对不对?你是我生的,对吧?”
江川说:“是的,妈妈,你冷静一下,我们不要吵醒其他人好吗?”
但已无济于事。
赵曼如神志不清地摇着头。
“为什么大雁知道南归,倦鸟知道归巢,春天的花和秋天的叶知道落地归根,你爸爸却总是不肯回这个家。他不肯回来,那我留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没有倦鸟的巢,没有大雁归来的南方,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有吗?”
赵曼如的声音太大了,有被吵醒的邻居纷纷披衣出来,远远地观望。
站在一旁的张大叔隐隐听到几句“唉,又发作了”,不由得皱眉看向陆东。他一直蹲在地上,十根手指深深地插进头发里,收紧了又松开。
江川极力想要控制住母亲,却在准备再次开口时,彻底僵在了原地。
陆瑶站在了门口。
或者说,她艰难地扶着门。因为脚足内翻,她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到这里。
她还没来得及穿鞋,没来得及披衣,灰尘和泥土粘在她内翻的脚背上,一双眼里挂着将掉未掉的眼泪。
她那么急切地看着江川,那么心疼地看着江川。
“哥哥,你受伤了吗?”
江川快要疼死了。
不是手臂,是心。
“我没事。”
他多想这样安慰她,赵曼如却在此时发起了狂。
赵曼如有轻度智障,是幼时突发高烧引发脑膜炎所致的。后来逐渐好转,可以说清楚完整的句子,有时条理还十分清晰。
只是近些年她越来越难控制情绪,甚至有些向精神病方向发展的趋势。
赵曼如和陆东的结合无关风月,赵曼如的父母真正论起来,该是陆东的堂姨夫和姨母。
陆东是个孤儿,从小被赵氏夫妇抚养长大。陆东本来在镇上有一个心仪的姑娘,却最终为了报答姨夫姨母的养育之恩,不得不娶了赵曼如。
“曼如是个好姑娘,可别人家容不下她,她会被欺负的,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他无法拒绝一个老人在临终之际那充满渴望的殷切的目光,老人握着他的手那么虚弱却又那么有力,那么坚定却又那么颤抖。
“我答应你,我……娶她。”陆东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脑海里浮现着那个姑娘的影子。她在哭泣、咒骂,在奔跑着,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只是那对含着泪水的眼睛,一直在晃呀晃,泪水滚动却顽强得不肯坠落。那双眼睛在以后的时光中,就像利刃一样戳着他的心,在无数个黑夜里鲜血淋漓。
“孩子,委屈你了,谢谢你。”这是老人这辈子唯一说过的一句“谢谢”。
没有人愿意娶一个智障,尽管赵曼如很漂亮。但即使发病的时候,她也依然很美。上天如此不公,将如此残忍的命运降临在她身上;上天又是如此公平,给了她无与伦比的美貌,却没给她健康的身体。古人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不知内情的人以为他们俩是近亲结婚,赵曼如生下“残缺 ”的陆瑶以后,就更加印证了众人的猜测。
他们不知道的是,陆东和赵曼如根本没有同过房。江川和陆瑶都是陆东在雪夜里捡回来的孩子。
这件事情是陆家的另一个秘密,江川知道,赵曼如知道,唯有陆瑶,毫不知情。
陆东不爱赵曼如,失去爱情的他变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游魂,终日除了喝酒就是漫无目的地闲逛。赵曼如得到了一场形同虚设的婚姻,一个目中无她的丈夫。
一场婚姻,两代哀伤,诸多难忍,百样杂陈。
傅煜泽不知道陆家还有这么多故事,只在江川爸爸和张大叔的交谈中,听到了些许江川妈妈重病多年的事。
他的眼睛有些疼,望向江川的目光里满是酸涩。
疯癫的母亲,颓丧的父亲,天生残缺的妹妹,以及一贫如洗的家境。傅煜泽终于明白,为什么高一那年,语文老师让他们写《家》,江川执意不交了。
“陆江川同学,你的作文呢?”
“没写。”
“为什么不写?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题材,想想父亲的肩膀、母亲的……”
“老师,你说够了没有?够了就上课吧。”
那是傅煜泽第一次看见江川公然顶撞老师,这也是煜泽第一次在这个安静灵魂的背后,看到他长眠在骨子里的叛逆与不屑。
他不屑这个题材,不屑这份温暖,也可能是无法得到,所以只能强装不屑。
煜泽想,如果自己是江川,亦然不知道如何在这间破败的小院里,描写出一个美满的“家”。
陆江川后来被送进了镇上的诊所,赵曼如被强制吃了镇静剂,药劲上来以后就睡下了。
张大叔没有为难两个孩子,将人送到医院以后叮嘱了几句就走了。
而江川对于被马踢伤的原因,只字不提。
煜泽几次三番想要开口,也都被他打断了。
“哥哥,你究竟为什么大半夜的去马圈?”
“因为,哥哥想去探险。”
江川总是这样回答陆瑶,无论问多少次,都是这个答案。
阿泽知道,他是想将这个秘密深埋下去。剥开骨头撕开皮肉地埋,直至,他有能力亲手为她做一把二胡的时候。
一个月后。
篮球赛正式开赛,傅煜泽作为主力前锋上场,江川却因为没有完全恢复,留在了医院。
今天也是他拆石膏的日子,陆瑶陪着他一起坐在诊所的处置室内。
她坚持要陪他过来,用那双无法正常行走的腿。她说她要做这条手臂安然无恙的第一个见证人。
石膏拆掉了,江川还有些发怔。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嘱咐他两个月内不能做任何剧烈运动,他答应了。充斥着消毒水味的处置室里干净又静谧,江川在应了声“好”后,却恍惚像是听到了从篮球场传来的哨声。
与此同时,阿泽艰难地投了一个三分球,球没有进,现场一阵唏嘘声。没有江川一起的傅煜泽状态非常差,频频在接球、投球上失利。
今天跟他打配合的前锋虽然在训练时跟他配合过很多次,却仍旧无法达到江川跟他的那种默契——江川甚至会在传球时为他找到最佳的角度。
“哥哥,我知道今天有篮球比赛,但我只跟老师请了半天假。你替我去看看傅哥哥吧,好吗?”
一直安静的陆瑶抓住了陆江川的手,江川知道,陆瑶不是想让自己去看阿泽,而是知道自己渴望去赛场。她是想用这种方式,替自己说出心底的渴望。
“去看看吧,就算不能参加,做一个看客也好。”
良久,陆瑶听到江川轻轻说了句:“好。”
陆江川来到比赛现场时,比分已经是35∶46,古镇中学大比分落后。阿泽一个篮板球被抢断,队友补防,遭到对方两名防守队员夹击。
江川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局势,瞅准一个空当对代替自己上场的另一个前锋吴越遥遥做了一个手势。
卡位,右边。
吴越连忙调整步伐,防守队员接下传球,阿泽再次起跳,灌篮,球进了!
“好!”
场外的啦啦队再次兴奋了起来,其实从看到江川走进来的那一刻,她们就有一种莫名的心安。江川跟阿泽打配合,曾拿下过“最佳篮球少年”称号。跟凤阳中学的对赛,也曾爆出过125∶80的惊人比分。
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定格在45∶52,古镇中学依然落后。
阿泽擦着汗跑下来,显得有些丧气。他抻着胳膊给看台上的江川递了瓶脉动,又反复盯了一会儿他的手臂,然后摇了摇头。
“你不跟我打配合,我就一塌糊涂了,还能用吗?”
他指着江川的胳膊问。
江川抿紧了唇,没有说话。阿泽明白了,有些焦躁地踱了两步。末了他猛地一抹额头:“别担心,我跟他们拼了。”
他想替江川赢。
阿泽懂江川的遗憾,就像江川懂阿泽的焦躁一样。
“不要着急,二号位和三号位的防守是他们的弱项,抓住这两个突破口。”
教练听到他们俩的对话,有些惋惜地拍了拍江川的肩膀。
面前的这两个,都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如果江川的手臂没有受伤,这一场一定不会呈现出这样的比分。
下半场的哨声开始了。
阿泽好像打了鸡血一般,全场飞奔,奋力反攻。抢断,远投,三分!
“阿泽!你是最帅的!”
“阿泽,抢他,抢他!进球!”
担任啦啦队长的郭儒雅不止像打了鸡血,更像是活吃了上百只鸡,气势恢宏到无人能及。
凤阳中学的啦啦队也不是好惹的,看到有这么一个大嗓门在,也跟着一通怪叫。她们的队伍里很多女生都是大嗓门,以至于郭儒雅率领的啦啦队很快败下阵来。
郭儒雅能受得了这个气?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扩音器,刚打开开关,就传出了震慑全场的:来看看啦,全场两块,统统两块。两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你买不了上当,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全场爆笑。
儒雅他们家是开两元店的,就这还是背着她爸爸“拿”出来的。
“你消停一会儿。”
阿泽调整了一下头带,嫌弃地瞥了郭儒雅一眼。
这一眼,却像是给了她莫大的精神支柱。
“阿泽!男神!我永远支持你!”
对方教练喊了暂停。
跟阿泽同为前锋的凤阳中学的肖凛撞了一下他的肩膀,轻蔑地说:“球技上技不如人,改用这种办法找场子了?”
阿泽冷笑:“再不如人,也没被人一场断球过三十几次。”
去年的篮球比赛,肖凛被陆江川一连斩断过三十六次球,吃了七次火锅,原本白皙的脸活生生变成了猪肝色。
“那也不是你,他残了,你就是个废物!”
“你再说一遍!”
傅煜泽单手抓住肖凛的衣领,肖凛摊开双手,贱兮兮地将头伸过去:“你敢打吗?”
在场那么多老师和评委,阿泽这一拳挥过去,后面的比赛就不用参加了。
“煜泽,过来。”
许多人都在喊他,煜泽也本想就此作罢去找江川的。未及肖凛的最后一句话更加过分,没人知道他在煜泽耳边说了什么,只看到激动的煜泽在他话落后,挥起拳头狠狠地打在了肖凛的颧骨上。
“你再说一遍!”
“煜泽!”
教练和双方队员纷纷跑过去,煜泽就是不管不顾地向前冲。
“傅煜泽!再不松手就记你大过一次!”
班主任陈老师气得不轻,眼见他拽着肖凛不放,只能使出撒手锏。
“我马上给你妈妈打电话你信不信?”
那自然是信的。
给你妈打电话,给你爸打电话,给你全家打电话,是所有尚在校园里的孩子最惧怕的魔咒。
傅煜泽被众人拉到替补席上,前来观赛的校领导都要气疯了。比赛期间打架斗殴,严重影响了校风和“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传统精神。即便最终赢得了比赛,滩头古镇中学也不光彩。
“把傅煜泽换下來!”
教导主任一声令下,教练只能把一名替补队员替下傅煜泽。
哨响,比赛再次继续,一连失去两大主力的滩头中学队陷入了更大的危机。比分随着时间逐渐被拉大,89∶100……89∶106……89∶109。
冷静以后的傅煜泽将脸深深地埋进手掌,他真的不该冲动的。
学校的荣誉,班集体的荣誉,以及他想为江川赢回来的比分。
89∶115。
“教练,让我上吧。”
不知何时换上了队服的江川站到了教练跟前。
“江川!”
阿泽叫他,难掩激动。
“是陆江川吗?”
坐在观众席上的滩头中学的校友们重拾起了希望。
江川和煜泽一直是他们心目中最强的篮球少年,如果江川可以上场,也许他们还有翻盘的机会!
“胡闹!你的胳膊才刚拆掉石膏,这个时候上场,你不想要这条手臂了吗?”
江川没有说话。他一直不善言辞,不知道怎么去跟教练解释自己此时的愧疚。
阿泽被罚下场,这场比赛要是输了,更多的埋怨就会落到阿泽的身上。他不想让阿泽背负这些,或者说,替阿泽背负这些。
“教练,让陆江川去吧,我们相信他!”
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余下的附和声也此起彼伏地响起。
“让他去吧!”
“我们相信陆江川!”
“教练,让我去吧。我会尽量不用到受伤的手臂,求你了。”
這大概是陆江川第一次说“求”字,少年眼中的果敢、坚定,以及倔强,深深刺痛了教练的心。
“你应该知道,现在这种情形,即便你上场了,也不见得能赢。”
“可是教练……”江川紧张地攥紧了拳头。
“注意不要用全力。”
张教练最后那句话的声音并不大,在场的人却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陆江川上场以后并没有急功近利地进攻,反而跟队友配合打起了迂回战。江川传球、卡位、过人是把好手,于是他就利用身体的灵活性,单手带球过人。
他虚晃一下偏开防守队员,起跳,后仰,一道美妙的弧线,球进了!
江川上场以后尽最大的努力,很快就将比分追成了115∶117。
最后一节的比赛只剩下三分钟了,如果这个时候江川投进一个三分球,滩头中学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
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紧张而安静地看着那个少年艰难地过人,刘成、吴越等防守队员迅速卡位,再传给江川,江川接球,起跳!
大家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这时哨声响起,比赛结束。
滩头古镇中学输了,凤阳中学赢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凤阳中学的教练亲自过来拍了拍江川的肩膀。
“你已经尽力了。”
最后那一个三分球,江川无法单手完成,只能奋力举起受伤的胳膊。可他的手臂才刚恢复,力度掌控不住,球撞到篮框,偏了。
“是啊,已经尽力了。”
江川的教练也走了过来,紧跟着,阿泽、吴越、刘成,所有滩头中学的同学。
“江川,你已经尽力了,比赛很精彩。”
“是啊江川,你还是我们最强的篮球少年。”
江川沉默着,未受伤的手臂不经意地抚过眼眶,看上去只是一个擦汗的动作。
“谢谢大家。”
他沉声点了点头,站起身,在众人的簇拥下,跟阿泽一起坐上了回去的校车。
窗外清风浮动,绿柳成荫,心事重重的两个少年望着车外迅速退去的景致,仿佛叶落,仿佛花凋,仿佛有什么东西褪去了颜色,深深地镶嵌在了心中一本名叫遗憾的相册里。
“他妹妹是个瘸子,他就折了手臂来陪她,一对残废,多兄妹情深,多感人啊。别是德国骨科吧?”
“傅煜泽,有些事儿你惦记也没用,就像这场篮球赛,没有他,你能赢吗?”
肖凛今天说的话,煜泽并没有打算告诉江川。无论输赢,他都不后悔自己打到对方脸上的拳头。
“江川,再等一年,下一年的篮球比赛,我们一定赢回来!”
煜泽紧紧握住江川的手,江川没有说话,回握的力量是同等的。
等明年,一定赢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