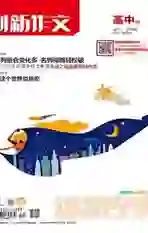初夏的第一声蝉鸣
2017-12-05陈桐
陈桐
夏夜,当窗外传来“嘒嘒”的声音时,我正独自坐在书桌前。
先是一愣,继而莞尔:原来是蝉鸣。
忽又一阵喜悦,继而微微有些惆怅:立夏已过去两个月,我才听到第一声蝉鸣。
记得《诗经·豳风·七月》中有言:“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可我冥思苦想半天,却全然记不起何年我曾在五月时听过蝉鸣。想来古时,那蝉应该更活泼些吧。
我閉上眼,静静听那蝉鸣。小小软腹,竟藏得一把乐器。其声悠扬,音律简单,并没有许多复杂的变化,可就是令人心静。而那些流行音乐,虽然技巧丰富,特效精美,可听来总是让人厌烦。唯有那蝉,才是我最喜爱的音乐家,它们扯着嗓子叫喊,愈来愈响,不知疲倦。也唯有这最本真的音乐,才最能触动人心,使人获得片刻的宁静。
细细想来,我喜爱这蝉鸣,多半也是因其能触动我的情思。一声声“嘒嘒”,仿佛让我回到了童年在老家过的那些夏夜,循着声音去捉那树上的蝉。彼时虽没有杨万里笔下“儿童急走追黄蝶”的烂漫,但较之现在只有独坐书桌前,透着阴森的防盗窗望向窗外的寂寥,却又不知生动了多少。从这点上讲,张平子倒是与我颇有同感: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也许,虫鸣于他而言,寄托的不是童年的回忆,而是片片相思吧。
可如今,蝉鸣离我们已越来越远。我时常会想,是蝉鸣少了,还是我们离自然远了?其实应该是两者兼有吧。也许这正是现代化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我并不是反对发展,甚至,我认为一厢情愿地呼唤追求古时躬耕陇亩的生活是不道德的。可我们能不能做点什么呢?譬如,在自家阳台上种些花草,闲时多去乡村走一走,多注意些节气和时令的变化……这些很难吗?也许对于那些沉溺于新潮与流行的人而言,这可能是难了些。
我读那些写自然的文章时,总会有一个怪异的想法——那些写自然的作家,就像是自然博物馆的导游。他们不是那博物馆的一部分,而是向读者介绍自然的人。他们带着一种陌生而又忧伤的笔调纪念着曾经,纪念着消逝的自然。也由此,我总是不忍读这类文章,生怕眼泪会抑制不住地流下。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一方面文学家们用文字声嘶力竭地呼唤着人们亲近自然,另一方面人们在短暂的感动之后却依旧制造出各种噪音,以致听不见任何从自然传来的声音。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有多久没有好好地听一听蝉鸣了?我想,也许我们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诗经》。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我觉得,《诗经》于现代人而言,最迫切的作用便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改变了多少自然,忘记了多少自然,遗失了多少自然……
若是我们真正想做到亲近自然,那么,就从亲近身边的第一声蝉鸣开始吧。
点评
写自然的名家很多,如德富芦花,如汪曾祺,如王开岭。他们或赞美自然,或感伤古典之殇。而本文作者则结合当下生活中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能仅仅只把自然当作缅怀的对象或一时感动的对象,而是要真正亲近自然、尊重自然、融入自然。作者以一颗柔软敏锐的心,用小中见大的手法,将深深的忧患意识寄托在身边的第一声蝉鸣中。作者在文中号召大家发现自然、亲近自然,这体现出了一个少年对文学与生活的热爱,更体现出了一种责任感。此文此情,不禁让人感叹:后生可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