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源流寻征(六)
2017-11-30刘佑
刘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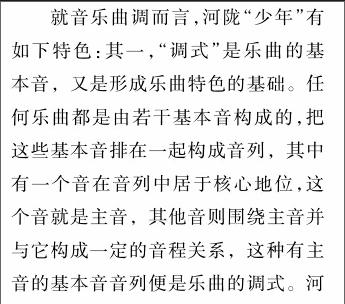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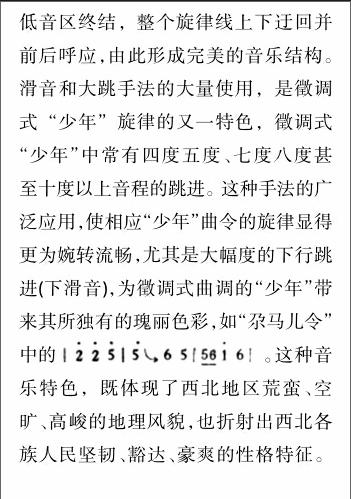
词曲·小令·“少年”
词的最初全称是“曲子词”,原是配合隋唐以来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后来乐谱失传,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题材、手法、格律、风格等方面都独具特色的新诗体。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词就是“被之管弦”的“曲”之词,或者说是“曲子词”。词产生于民间,在敦煌写本中发现了叫《云谣集杂曲子》的唐代敦煌民间词,学界将其定名为《敦煌曲子词》,它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唐代民间词,因而保存了原始词的本来面貌。敦煌曲子词抒写的内容非常广泛,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而以闺情与花柳为题材的作品尤其显得醒目:“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望江南》)“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塠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向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菩萨蛮》)“曲”的本义是乐曲,其作用是与歌词相配,使歌词按照一定的节拍、声情传唱出去。汉乐府就是配樂歌唱的诗体,宋词也是用来配乐歌唱的,因而人们又将其称为“近体乐府”或“曲子词”。到了金元时代,自民间到文坛相继产生了一种新的乐曲曲词,它就是与唐诗宋词并立的元曲。按地域划分,元曲有“北曲”“南曲”之分,北曲“劲切雄丽”,南曲“清丽柔远”(王世贞《曲藻》)。属北曲的小令,以声音美听、可以单独歌唱为要;而南曲中的小令,则以声腔细婉、节板繁密为佳。北曲是元曲的代表,故“元曲”所指其实就是北曲。清人梁廷枬概括了从乐府到元曲的演化承续过程:“乐府兴而古乐废,唐绝兴而乐府废,宋人歌词兴而唐之歌诗又废,元人曲调兴而宋人歌词之法又积渐于变。”(《曲话》卷四)宋朝大词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说,“委曲尽情曰曲”;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通其微者为曲”;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曲之名义大抵即曲折之意”。上述概括突出了曲的艺术风格,那就是通过错落有致的文句来委婉曲折地表情达意。河陇“少年”与元曲几近于相同,由此显见“少年”与元曲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有意思的是,《敦煌曲子词》中的《天仙子》和《柳青娘》,其体式都与俗称“折断腰”的河陇“少年”非常接近:“燕语啼时三月半,烟蘸柳条金线乱。五陵原上有仙娥,携歌扇,香烂漫,留住九华云一片。犀玉满头花满面,负妾一双偷泪眼。泪珠若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天仙子》)“青丝髻绾脸边芳,淡红衫子掩酥胸。出门斜捻同心弄。意徊惶,故使横波认玉郎。叵耐不知何处去,交人几度挂罗裳。待得归来须共语,情转伤,断却妆楼伴小娘。”(《柳青娘》)此外,《敦煌曲子词》中还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诸多无名氏的作品中每有“少年”一词,如:“恨征人久镇边夷。酒醒后多风醋,少年夫婿。”(《洞仙歌》)又如:“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抛逑乐》)再如:“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罗衫香袖薄,佯醉抛鞭落。何用更回头,谩添春夜愁。”(《菩萨蛮》)此种情态,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少年”流行地区年轻人“浪山”时的情境。《敦煌曲子词》中还有一首《菩萨蛮》,写女子对爱情的坚贞,不论其情感基调还是表达形式,与同类题材的“少年”十分相似:“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塠浮,直待黄河彻底枯。向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传统“少年”中也有相似的篇什:“青油灯盏亮照下,羊油的白蜡放下;黑头发陪成白头发,死了时一块儿葬下。”“青石头根里的药水泉,桦木的勺勺儿舀干;若要叫我俩的婚姻散,冰滩上要开一朵牡丹。”两相对比,何其相似乃耳!
“曲”是元代的新诗体,它是“词”的替身,无论从音乐的基础或是形式的构造上,都是从词演化出来的。词本是起于民间的通俗文学,原本流传于歌女伶工之口。五代两宋时,填词已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其体裁日益严格,音律修辞亦日益讲求,由此脱离了与民间的血肉关系,从而其生命也就衰落了下去。但是,都市中的歌女伶工仍须卖唱谋生,他们便在原有旧曲和新起小调中翻新求变,曲子也便慢慢产生了,接着有乐师来正谱,有文人来修辞,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兴的文学品种。宋末元初,外族音乐大量输入中原内地,原有的词调难以与新来的音乐合奏,改造旧有歌词以适应流行的音乐就成为大势所趋,这是“曲”这种新的文学样式产生的外部原因。(参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元曲又称为散曲,是小令、带过曲、套数这三种形式的总称,小令又被称为“叶儿”,本是一种流行于民间的小调,因其鲜活的生机而最先成为构成散曲的单支曲调。明人王骥德在《曲律》中说,“所谓小令,盖市井所唱小曲也”;元人燕南芝庵在《唱论》中说,“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这些记述无不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小令是在北方地区“俗谣俚曲”的基础上演化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歌风格,其鲜明特点是体式短小、语言精炼、音调高亢、形式活泼。明人王世贞在《曲藻》中说,“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山豪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等辈,咸富才情,兼喜音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妄也。”上引“凉山豪嘈”中的“豪嘈”,是说“曲”的音调高峻峭拔,而“凉山”其实是“凉州”之误。如果追溯“小令”原初产地,恐怕要与凉州挂起钩来,而凉州恰恰是河陇“少年”的重要发源地,因而元曲与“少年”免不了也会有血缘关系。早在唐代,诗人元稹的《琵琶歌》中就有“凉州大遍最豪嘈”的句子;近代曲学大师姚华在《曲海一勺·明诗》中说,“惟是街陌讴谣之辞,或染《凉州》豪嘈之习。”这些见解无疑说明,曾被称为“伊凉之调”的古曲《凉州》,实在是元曲小令的源头。如前所述,“伊凉之调”中本就包括河陇“少年”。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无论是小令效法了“少年”,还是“少年”效法了小令,但就体式而言,元曲中的不少小令的确与“折断腰”式“少年”极为相似,尤其与五句式“少年”如出一辙。元曲小令:“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关汉卿《仙吕·一半儿》)“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白朴《中吕·阳春曲》)“昨宵中酒懒扶头,今日看花惟袖手,害酒愁花人问羞。病根由,一半儿因花一半儿酒。”(徐再思《仙吕·一半儿》)“路逢饿殍须亲问,道遇流民必细询,满城都道好客人。还自哂,只落的白发满头新。”(张养浩《中吕·喜春来》)以上小令,看起来虽为五句,其实应被视为四句式,如去掉楔入三五句之间的短句,并不影响整首诗的思想内容,但那个短句不仅起点明题义的作用,而且使诗意的表达陡然间情态毕现。“折断腰”式“少年”:“枣骝公鸡上不去架,叫一声,转槽的根儿里卧下;高墙园里的藏金花,折不上,没精打采地坐下。”“清水的河里磨一盘,三道山,牛羊儿往下者赶哩;陪住尕妹者坐一天,六月天,日子还嫌者短哩。”以上“少年”系四句式“少年”的变体,六句中的一三四六句为正句,二五两个短句不过是加进去的衬句,却产生了补充语气和增添意趣的作用。五句式“少年”:“十八马站三座店,哪一座店里站哩。十个指头掐着算,十二个日,哪一个月里见哩!”“塔尔寺的金瓦兰州的塔,清风儿刮,西海里起波浪哩。千带书的万带话,带到时心安下哩。”五句式“少年”也是四句式的变体,结构方式又分两种,其一是五句中的第四句为衬句,其二是五句中的第二句为衬句,无论哪种体式,如去掉其中的衬句,也就成了四句式。六句式和五句式“少年”,其与小令体式的相似性及衬句功能的相同性,恐怕不仅仅是巧合,而是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endprint
七言歌谣与“少年”
最早的“少年”在哪里?应当循着民歌发展的轨迹“溯洄从之”,即从中国古代民歌中去寻找;民间歌谣与文人诗歌之间又产生交互作用,因而从文人诗歌的体式变迁亦可窥见其对民歌的影响。七言四句是“少年”的基本体式,最早的七言句式来源于中国古代民间歌谣,文人的七言诗其实是对七言歌谣的模仿,因而通过七言歌谣可以窥见“少年”歌词的原初形态。著名的乐府专家余冠英先生认为,诗歌中的七言句式可以上溯到《诗经》,其中不乏近于七言的句子,如果从“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中去掉托声字“思”字,从“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中去掉托声字“兮”,就可组合为七言句了;如果从“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唐风·杕杜》)中去掉末尾的虚字“焉”,从“既夷既怿,如相酬矣”(《小雅·节南山》)中去掉末尾的虚字“矣”,也就变成七言句了。不仅如此,《诗经》中还有不少现成的七言句,见于《周颂》的如“学有绩熙于光明”(《敬之》),见于《大雅》的如“维今之疚不如兹”(《召旻》),见于《小雅》的如“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见于《国风》的如“交交黄鸟止于桑”(《秦风·黄鸟》)。先秦歌谣以四言为主,间或有以七言为主的。如《礼记·檀弓下》所载《成人歌》:“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兄则死而子皋为之哀。”战国末荀卿的《成相辞》采用民歌体式,结构以七言句为主,其第一章为:“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全诗共56章1344字,其通篇体式结构极为严整统一,每章5句24字,头两句均为3字,第四句为4字,三、五句均为7字;各章屡以“请成相”三字起头,是采用民歌的体式和腔调,意为“请奏此曲”;据郑玄注,“成相”之“相”是“送杵声”。人们在集体劳动时,往往通过重复哼唱同一曲调的歌曲,以求动作的协调从而形成合力,如在打夯时必有“吭唷”之声,这种曲调在古代就称为“相”。七言歌谣的产生,还可追溯到更早的年代,《礼记·乐记》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歌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显而易见,这是一首以七言为主体句的歌谣,二、四两句末尾的“兮”字,不过是为吟唱顺口而添加的语气词,并不关乎整首歌词的意义表达。当然,帝舜制琴以歌《南风》之說,或许是小说家笔法;不过,《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这从司马迁的记述可见一斑:“《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
汉武帝时七言歌谣已广为流行,汉乐府中就出现了不少七言句,如铙歌《艾如张》中的“山出黄雀亦有罗,雀以高飞奈雀何?”又如《战城南》中的“野死不葬乌可食”,“腐肉安能去子逃”,“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焉可得?”再如《有所思》中的“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从文人创作来看,七言诗在当时也已蔚为大观,如张衡的《四愁诗》虽仍留楚辞余韵,但更多文句为标准的七言,如“美人赠我差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蔡琰的《胡笳十八拍》甚至出现对仗工整的七言句,如“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寒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在隋唐五代之时,文人创作七言古诗非常盛行,尤以“歌行体”格外耀眼。歌行体以七言为主,间以三言、四言、五言,乃至九言、十言,即兴挥洒,酣畅淋漓。如鲍照的《拟行路难》五、七言杂用,李白的《将进酒》三、五、七、十言杂用;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六、三、七言错落杂用,使整首诗抑扬顿挫,跌宕起伏;高适的《燕歌行》一口气二十六句七言,将要结尾时插入一句八言,使急促的节奏顿时为之舒缓。而所谓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的一种新体诗,也就是讲究平仄、对仗,对格律有严格要求的律诗,如五律、七律。东汉时五言乐府已经盛行,也是五言诗开始萌芽的时代;然而在民间歌谣中是七言多于五言,说明七言歌谣在东汉时已经普遍流行。入乐歌谣更因音乐的力量而流布广远,从而与文人有更多接触的机会,由此形成大量仿作自属理所当然,五言“古诗”便是这样产生的。余冠英先生认为,五言歌谣之所以更多进入东汉乐府,是由于当时流行的音乐最宜于五言歌辞;五言体由于乐府的推广而得以迅速普及,到魏晋时已升格为诗歌的正体了。七言歌谣的流行之所以早于五言,是因为七言句之于歌咏有着天然的适应性;七言诗的产生不过是当时少数人猎奇式的尝试,更多的人并不承认七言是诗的一个类别,因而认为七言诗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看重五言而轻视七言,这种偏见从两汉魏晋延续到了南北朝。钟嵘在《诗品·总论》中直言:“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所推重的是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骈文,而并不把七言诗看在眼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普遍应用的诗体莫不出于乐府,莫不皆借助于音乐的力量而得以流传。尽管也有人早已把七言用之于诗,但七言诗并未因此而广泛流行起来。究其原因,一是两汉的七言中佳作太少,因而不曾引起多数人的仿作;二是七言歌谣在汉代时不曾被采入乐府,由于没有获得音乐的推动,自然也就难以传播和普及了。
文人制作七言乐府歌辞始于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其第一首为:“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七言歌谣直到晋代才开始采入乐府,如《并州歌》《豫州歌》等。《并州歌》为晋代并州(今太原)百姓揭露恶人汲桑暴行的诗,此人曾在成都王司马颍手下干事,颍死后自称大将军,聚众抢掠,极其残忍;他在大暑天穿皮裘,却叫别人为他扇凉,又嫌扇得不称心而当场杀死扇凉的人。有个叫田兰的人为民除害杀了汲桑,当地百姓便作歌并“奔走道路而歌之”。歌曰:“士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裀被豹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豫州歌》是豫州(今河南项城东北)人民对祖逖的歌颂,他做豫州刺史时勤俭爱民,并亲自督率农桑;他还曾置酒与乡亲共饮,耆老在宴会上流着眼泪说:“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慨!”于是用歌声来赞颂祖逖,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明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南北朝以来七言歌谣仍主要流行在民间,七言体在南朝士大夫眼中仍然是“俗”体而非“雅”体。学者葛晓音在《八代诗史》中指出,南北朝乐府民歌对同时期诗歌语言风格的变革产生了关键的作用,为同时代乃至唐代的诗歌发展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南北朝乐府民歌创造了抒情小诗的新体裁成为五七言绝句的源头,北朝民歌刚健清新的气质对隋唐边塞诗具有直接的影响;南北朝民歌所运用的比兴、双关、排句等艺术表现手法,“更是使后世诗人沾溉无穷”。鲍照是南朝刘宋时代的大诗人,他从当时开始流行的五七言杂言体中找出规律,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自由换韵,创造出全新的七言体组诗《拟行路难》十八首。《行路难》本是汉代牧羊童所唱的北方民歌,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在主流文化看来却显得“辞颇疏质”。鲍照的这组诗以七言为主,间有杂言和骚体句,用华丽的辞藻和豪放的气度表现困顿失意中的忧愤,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从而成为其后常见于唐诗中的一种独特风格。庾信是身经南梁、西魏、北周三朝的著名诗人,其所作《乌夜啼》被认为是七律之滥觞:“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乌恒夜啼!”endprint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分为南歌和北歌,南歌以江南荆楚一带的吴声和西曲为代表,北歌则是当时北方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南歌基本上是五言四句体式,也有四言四句体式,以及三言或四言与五言或七言错杂的体式。如“吴中细布,阔幅长度,我有一端,与郎作裤。”(《安东平》)“夜相思,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华山畿》)“白门前,乌帽白帽来。白帽郎,是侬良,不知乌帽郎是谁?”(《读曲歌》)。北歌虽然也以五言四句为常见体式,但也有四言四句体式,还有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尤其有不少相对成熟的七言诗,如:“兄为俘虏受困辱,骨露力疲食不足。弟为官吏马食粟,何惜钱刀来我赎。”(《隔谷歌》)“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系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粟谷难舂付石臼,弊衣难护付巧妇。男儿千凶饱人口,老女不嫁只生口。”(《捉搦歌》)北歌的相当一部分原初是用当时的民族语言传唱的,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接受并提倡汉族先进文化,加速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因而现存的北朝民歌大都是用汉语表达的,其中有些是用汉语翻译的,有些则本就是用汉语创作的。河陇“少年”与“北歌”有着更为直接的内在关联,抑或早期的“北歌”本就包含了河陇“少年”。不过,尽管至今所见到的“少年”大都为七言四句式,但也不能认为“少年”从来都是清一色的七言句式,很可能有过长短句相间或五七言错杂的情况,甚至有过纯粹的五言四句体式。这是因为五言也是北方民歌的基本句式,如前引十六国时期产生于河湟地区的《朔马谣》,就是一首具有汉魏乐府风格的五言歌谣,我们有理由将之视为当年的“少年”。况且民歌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可能固守原初的状态而一成不变。魏晋南北朝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未曾中断。随着历代中原汉族文人陆续进入河陇地区,他们把客居地的民歌转换成自己原本熟悉的诗歌形式,使之更适合于自己的文化心理和欣赏品位,并由此引起本土民歌形式发生一定变化,这样的推理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可以肯定的是,凡见之于文献资料的民间歌谣,必然是经文人加工整理的,单纯以口头相传的民间艺术,是很难长久保留下来的;而文人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加工和改造,必定会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审美需要。由此可以作这样的判断: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民间艺术形式,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民间样式了;就其歌词和章法而言,今天我們所见到的“传统少年”,并不一定是“少年”原初的面貌。
“少年”的艺术特色
任何品类的艺术,它的完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成熟起来。就“少年”来说,诗经是它的远祖,汉乐府是它的近亲,而横吹曲中的“伊凉调”和杂曲中的“少年行”则是它的直系血亲,所有这些共同塑造了“少年”的形式和性格。“少年”是用汉语演唱的,因而其歌词的体式必然受汉族诗歌的影响。就汉族诗歌的发展而言,每一种新的诗体总是出自于民间歌谣,然后经过文人的加工提高方才进入主流文学的殿堂。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主体部分“风”就采自15个地方的民间歌谣,而其中的秦风和豳风,大都是秦陇地区即陕甘一带的民歌,其间应当有河陇地区的古代歌谣。就“少年”的章法体式而言,它承续了“诗经”和“古诗”的比兴赋手法和五七言绝句的简短体式。“少年”具有短小、单纯的艺术个性,开头两句一般都与正文并无直接的意义关联,而只是为正文的出场起牵线、铺垫的作用,随着主题的点明,一首歌也就戛然而止了;“少年”一般只有四句,“折断腰”体式虽然有六句,但其中的第二、第五两个短句不过是为适应调式而添加的部分,它们的存留或去除并不会改变整首歌词的主要内容;“少年”也就是最单纯的一种诗歌形式,这种单纯却赋予文人作品难以企及的通俗美和真实美,也为大众对其表现技巧的掌握和应用创造了便利条件。比、兴、赋的大量应用,是“少年”在表现手法上的鲜明特点。所谓比,就是通过比喻、比拟手法表达意思。比喻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其功能是用某一事物或情境来比另一种事物或情境;比拟分为拟人和拟物两种,其功能是把物当人来写或把人当物来写,以及把甲事物当作乙事物来写。“少年”中的“比”有多种方式,有的是以比拟句起头,有的是主题句中亦用比喻或比拟手法,还有的通篇就是比拟或比喻。所谓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出要说的事情,即俗语所说的“由头”,也就是置于开头以引起下文的话题。“兴”是“少年”中惯用的手法,传统“少年”中开头两句几乎都与主题不甚相关,而只起引出下文的作用,第三句才转入正题,第四句也就是结尾句;一首“少年”所要表达的内容往往也就体现在三、四句中,因而这后面两句又可称为主题句或表义句。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展开叙述。“赋”这种手法在“少年”中的应用比比皆是,但作为韵文体的诗歌,“少年”并不像大白话那样去说、去唱,却是“叙物以言情”,也就是言物必及情,是以饱含感情的词句来打动人心的。概而言之,“少年”承袭了五七言绝句的特点,篇幅短小是它的体式特点;“少年”前两句以比拟句起兴,后两句直言所要表达的内容,结构单纯是它的又一特点;“少年”语言运用的通俗晓畅和情感表达的爽快直率,又赋予它质朴、真实的美学特色。凡民歌类艺术,都有单纯、质朴、通俗的特点。乡下的农夫终年所见无非是草木鱼虫,因而说一件事、抒一点情,自然联想起这些东西,即所谓“托物言志”,因为他最熟悉不过的就是这些东西;他用这些东西“喻”其心志,对方也容易理解。知识分子写诗往往用典,往往借用他人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与乡下人借草木鱼虫托物言志的手法殊途同归,或者说就是学了民间的写作手法;知识分子对书本很熟悉,为了委婉地表达曲折的意思,就习惯于借用典故,如此而已。
“少年”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与我国古代音乐有内在关联,比如以“令”为曲调定名,同一曲调下的节奏改变和旋律变奏,“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技巧的运用,等等。隋唐之际,在凉州地区出现名为《凉州大曲》的组曲,它是《西凉乐》的一个乐种。一部“大曲”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称为“散序”“中序”和“破”,每一部分又包含若干个乐段。在一部大曲中有若干冠以不同词牌名称的音乐片段,以“令”为词牌的音乐片段应用于“破”的部分,狭义上是指所用的节奏较快的曲调,而广义上是泛指一部大曲中所有较短的曲调。河陇“少年”以“令”为调名,由此可以窥见它与《凉州大曲》的内在关联。其二,中国古代音乐实践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根据同一曲调的大体轮廓进行节奏的改变和旋律的变奏处理,使之符合不同内容和不同情感表达的要求。大凡流传久远的曲调,都是经岁月淘洗而保留下来的优秀之作;歌词的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而具有生命力的曲调会长久流传下去并定型为曲牌,成为后人不断为之填写新词的固定格式,“少年”的曲令沿袭和发展亦属如此。沿用同一词牌表达不同的情调,可通过艺术形式上的一些变化来实现,如“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这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实践中常用的手法。“减字”是减少歌句的字数,在音乐上是以多音配一字,将某些字的节拍拖长;“偷声”是增加歌句的字数,在音乐上是分割少数的音以配合多数的字,使每字的音相应缩短;“摊破”是在歌句间插进歌句,在音乐上是增加新的乐句或扩展原有乐句;“犯调”是把分属于几个不同曲牌中的一些乐句联结起来,然后给它换上一个新的曲牌名称,或从一种调转为另一种调、从一种调式转为另一种调式。这些表现手法在河陇“少年”曲令中都有所表现,这与古人通过灵活应用词牌来表情达意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endprint
就其歌词而言,“少年”属民间歌谣类口头文学。但凡民间口头歌谣,其语言表达都有各自的套语。所谓“套语”,“就是在相同的韵律条件下被用来表达某一给定的基本意念的一组文字”(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套语”也就是民歌惯用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或者说是民歌语言表达中的固定套路。民歌是由曲调和歌词两部分组成的,在依声填词的条件下,歌词的语句结构要服从曲调的音乐结构。“少年”的歌词体式是由其曲调的旋律节拍决定的,因而“少年”曲词中的套语也是为适应曲令的旋律节拍而产生的。“少年”歌词中每有这种情况出现:把同一首歌词放在不同的曲令中,该歌词的语句结构会有一定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套语上,即在此曲令中并无套语,而在彼曲令中却添加了套语。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不同曲令的旋律节拍决定的,要把适应于此曲令的歌词移置于彼曲令,如不加必要的套语便难以适应彼曲令的旋律、节拍和节奏。“少年”中的一些曲令是因套语而定名的,如“绕三绕令”“呛啷啷令”“梁梁儿上浪来令”,等等,要与这种种曲令配套,其歌词中就要添加相应的套语,这种意义上的套语也叫“衬句”;“少年”中的一些兴起句也是套语,用以引出所要表达的主题句,如“尕马儿令”中的“尕马儿骑上枪背上”、“河州令”中的“上去高山望平川”,等等。不仅如此,“少年”歌词的押韵,并非是依据韵书的规定来进行操作,而只是为适应乐曲的音乐节奏自然而然地形成的。现在人们根据“少年”歌词概括出诸如通韵、交韵、间韵,或一字韵、两字韵、三字韵、四字韵,等等,都不过是套用一般的格律规则而得出的并不完全周延的概括。其实,人们在即兴吟唱“少年”时并不去考虑押韵与否的问题,他们只不过是依声造辞,力求声辞协调的效果,从而使吟唱自然顺畅罢了。“少年”的押韵与押韵规则无关,却与不同地区的方言口语有直接关系;“少年”的文词只有与曲令乐句恰切协调,才会产生易读易唱易记的效果;这就是说为了唱得顺口,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押韵。
就体式结构而言,“少年”与汉魏以来的乐府有许多相似之处。乐府的押韵非常灵活,有句句押韵,有隔句押韵,“少年”亦然;乐府的章节叫“解”,也就是配合音乐旋律而划分的歌辞段落,七言体乐府一般以两句为一解;“少年”歌词也是两句为一个段落,前一段落的作用是起兴,后一段落的作用是表义。乐府中有“和”即和声,一人唱多人和,一般置于每句歌辞之后,如曹丕《上留田行》:“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梁,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在这首乐府诗中,“上留田”三字既是和声又表曲名,亦可看作是歌辞中的衬句,它与歌辞内容并无直接联系。这种现象在“少年”中非常普遍,如“尕馬儿令”:“尕马儿骑上者枪背上(哎,好花呀开呀哟),照林棵打给了两枪(呗吔,尕马儿回拉着来吔,哎哟,拉回了缓来,肉儿);枪子儿落在个牡丹上(哎,好花呀开呀哟),下马者哭给了两场(呗吔,尕马儿回拉着来吔,哎哟,拉回了缓来,肉儿)。”又如“绕三绕令”:“白牡丹白着是(沙雁儿绕哎)耀人哩呀(沙雁儿绕哎),红牡丹红着个(绕三绕来吧)破哩;尕妹的跟前是(沙雁儿绕哎)有人哩呀(沙雁儿绕哎),没人时我陪着(绕三绕来吧)坐哩。”再如“尕阿姐令”:“大河的沿儿上(尕阿姐)牛吃水(哎),鼻桊儿跌在个水里(呀,尕阿姐看我来);端起个饭碗儿(尕阿姐)想起了你(哎),面叶儿捞不到嘴里(呀,尕阿姐看我来)。”上述“尕马儿回拉着来吔”“拉回了缓来”“沙雁儿绕哎”“绕三绕来吧”“尕阿姐看我来”等,在“少年”的演唱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作为衬句,有依曲调节拍补足歌词音节的作用;作为与歌词意义并不直接相关的添加句,却起了规定曲名的作用;作为乐曲行进中的组成部分,是用于众人唱和的词句。
无论是一首交响乐还是一支简单的歌,都会有一个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一定是重复的,而且这种重复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为了配合特定乐段的重复,曲辞中相关的语句就得同时重复。这种重复方式就是套路,这种重复语句就是套语。这种乐段和语句并行重复的表现手法又叫复迭,这又成为民歌的一种表现模式,其作用是有助于乐曲及曲辞的记忆、诵读和流传。在一首“少年”中,套语的形成与音乐曲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套语作为歌体组成部分,演唱中要与一定数量的音节相恰切;套语的使用能够把歌词比较容易地纳入相应的曲调,从而形成一定的体式规范。乐府诗由于受到音乐曲调的制约,所以诗歌的结构依附音乐的结构;“少年”的歌词是从属于音乐的,特定曲令的音乐曲调往往决定着歌词的语言形式。就乐曲而言,由两个乐句构成一个乐段,是“少年”的主要曲式结构,把这个乐段再重复一遍,也就完成了一首“少年”的演唱。就歌词而言,“少年”也由结构大致相同的两个段落构成,前段为起兴,后段为点题。在一首“少年”中,前段不仅为后段预定了句型框架,而且设定了意义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讲,用于起兴的前段亦可称为套句。作为即兴的口头演唱艺术形式,“少年”歌词的创作有着程式化的特点,这就是套语的运用。在一首乐歌中,套语往往无关正文的文意也并不具有表现歌词具体内容的功能,却具有确定这首歌的体式结构并赋予其情感基调的作用;套语与曲调节拍却有着内在的恰切性,因而套语的运用能够自然地满足音节推进的需要,从而为歌者提供了即兴编创歌词的工具。在“唱少年”这种即兴演唱中运用套语,特定曲令的乐调所固有的节奏为文本创作提供了韵律框架,由于有经验的歌手对乐调的旋律和节奏早已烂熟于心,因而对与曲调所匹配诗句的节奏和语调亦成竹在胸,所以能够很熟练地通过套语的使用布局谋篇和遣词造句。在即兴创作的短暂时间里,结构相同的句型有利于形成某种记忆机制,因而有了套语的示范,歌者就很容易编创出表达主题的词句来。这样的“少年”表演是一种临场的即兴发挥,是一种瞬间的临场创作,套语为表演者提供了常备的“语言构件”,有了这种“构件”,一个不会书写的人也能驾轻就熟地调遣词语,顺利地完成他的即兴演唱。
“少年”这种艺术的重要标志是它的形式,也就是由其曲令所限定的歌词的格式、句顿、叶韵、节奏等,如果改变乃至抛弃了这些有着内在联系的外在形式,那就不是“少年”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对“少年”的曲令,张亚雄先生有中肯的见解,他认为“令”就是“帮腔”,也就是惯语所说的“过门儿”;一个区域有一个区域的令,如“河州令”“尕马儿令”等,而“阿哥的肉呀”“尕马儿拉回者来吔”,则分别是上述两种“令儿”中的“帮腔”或“过门儿”。虽然,作为一种固化了的词句,“帮腔”和“过门儿”对歌词的意义表达并不起关键作用,在歌词的书面形式中甚至可有可无;但是,曲令是唱“少年”的根本依据,“帮腔”或“过门儿”则是特定曲令的标志,用哪种固化词句作一首“少年”的“帮腔”即“过门儿”,便决定了这首“少年”要采用哪种曲令;就其体式而言,“少年”的歌词是大同小异的,大都是七言四句,同一歌词可以用不同的曲令去唱,而其前提是“帮腔”即“过门儿”的选择,这也就是说由于曲令在先,因而要依“令”而歌。就“少年”歌词而言,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作的,判断其艺术水平的高低,兴起句与主体句的搭配协调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凡一首“少年”歌词,一般都由兴起句和主体句这两部分组成,兴起句只是为主体句的句式和押韵起引导和示范作用,其内容则与主体句所要表达的旨趣并无关系;但一首比较好的“少年”歌词,兴起句与主体句之间不仅有表现形式上的关联,而且兴起句对整首歌词的主题有暗喻、烘托、呼应、反衬、强化等作用。下面是几首艺术性较高的“少年”歌词:“大燕麦出穗是索落落吊,歇地里种胡麻哩;一对儿大眼睛水活活笑,笑眼里说实话哩。”“一对儿白马进西海,西海里为王者哩;尕妹妹好像白云彩,给阿哥哈遮凉者哩。”“天上的云彩黑下了,你看是晴哩么下哩;我想尕妹者哭下了,你看是成哩么罢哩?”“日头儿上来胭脂红,月亮嘛上来时水清;白天想你时肝花疼,晚夕里想你嘛心疼。”“天上的星宿星对星,大星把小星哈压了;生下的机溜长下的俊,你把个万人哈压了。”“大雨下给了整三天,毛毛雨下了九天;哭下的眼泪拿桶担,整整儿担给了九担。”“绿悠悠儿的长流水,当啷啷儿地响了;热乎乎儿地离开了你,泪涟涟儿地想了。”“雨点儿落在石头上,雪花儿飘在水上;相思病得在心肺上,血痂儿坐在嘴上。”“长把梨结到树尖上,我当了绿叶的杏儿;尕妹坐到路边上,我当了照人的镜儿。”“铁青马儿绿辔头,马尾上绾了个绣球;走了是丢不下心上的肉,把你是捎在个后头。”这些歌词的兴起句与主体句,不仅在构词方式上互为对仗,而且在意义表达上相互呼应,对作品主题的表达产生了或烘托或强化的作用;这样,兴起句与主体句共同构成了作品的有机整体,使整首歌词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浑然一体,从而产生了水乳交融、珠联璧合的艺术效果。endpr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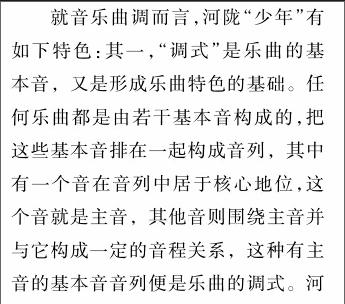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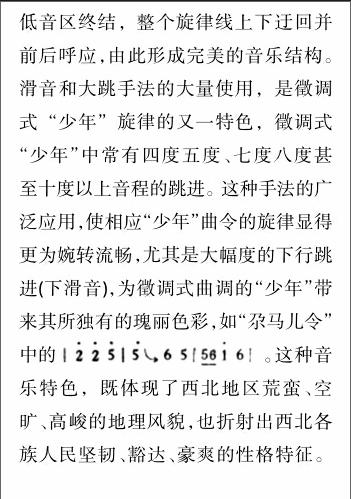
“花儿”?“少年”?
张亚雄先生在其《花儿集》中提到,西北俗谚中有“西安的‘乱弹,河州的‘少年”一说,认为“乱弹即秦腔正宗,‘少年就是‘花儿的别名”。张氏的推断显然有逻辑上的毛病,既然西北地区的人们把河州的山歌称为“少年”,那就说明“少年”是“正名”而“花儿”才是“别名”。在河湟民间,人们一直把当地的山歌称为“少年”,把咏唱这种山歌叫做“漫少年”。其实,把河陇地区的山歌称为“花儿”,其根据似乎并不很充分;而把它称为“少年”,倒是有更充分的根据。“少年”一词早在西汉时就已成为日常用词,这从《史记》对“少年”一词的频繁应用便可证明:“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秦始皇本纪》)“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高祖本纪》)“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陈丞相世家》)“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张耳陈馀列传》)“居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魏豹彭越列传》)“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淮阴侯列传》)“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大宛列传》)“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汉书·昭帝纪》)就其一般意义上讲,秦汉时所谓的“少年”是指未成婚的青年男子;而从社会角色的意义上讲,秦汉时的“少年”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群体。他们轻生死、重然诺、有血性,为底层社会树立了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们讲义气、淡功名、肯担当,为弱势群体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身处城市社会下层,或游手好闲或从事卑贱职业;他们为伸张正义而不惜屡犯法禁,因而受到专制政府的打击与遏制;他们背离正统观念而标新立异,其行为方式成为游侠社会的基础;他们行侠仗义而又狂放不羁,由此受到下层社会的赞赏和推崇。当政局动荡或王朝没落时,这个群体率先举起反抗的义旗,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激进力量。正是由于秦汉时的“少年”具有藐视王朝专制的精神,因而这个群体的成员被统治者视为“恶少年”而备受打击,他们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充军,而西北边地恰好又是他们流放充军的落脚地;也正是“少年”具有侠义风骨和担当勇气,因而成为两汉以降民歌乃至文人诗歌中不断咏唱的主题。秦汉以来,历代中央王朝不断向西北地区用兵,总是把内地的“恶少年”流放到那里去戍边屯守,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了以这些“少年”命运为题材的边塞诗篇。由此有理由作这样的推断:至今传唱于河陇地区的“少年”,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确定了其名。
汉魏以降的乐府诗中每有以“少年”为歌咏对象的诗句,“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是曹植《结客篇》中的句子,“结客”就是结交朋友,“少年场”也就是年轻男子游乐聚汇的场所。以“少年”指代年轻男子,这种修辞手法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人们广泛应用,“少年”由此被确定为曲名而载入乐府《杂曲歌辞》类目之中。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乐府脱胎于诗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府主管部门的专职人员下乡采集的“俚曲讴谣”,亦即民间说唱文学作品。官府设立专门机构收集整理民间歌谣有两个目的,一是供礼仪和宴乐两种场合的演奏,二是统治者借以观风俗从而了解民情。乐府原本是曲与词的结合,曲有固定的调式,词的句式必须适合曲调的旋律和节奏方能演唱。乐府歌词一般为五言、七言句,这是由曲谱的音节和旋律决定了的。汉乐府中有一种称为“倚歌”的表演形式,据《古今乐录》说,“凡倚歌,悉用铃鼓,无弦有吹”。《乐府诗集·清商曲辞》所载“西曲”中有这样两首“倚歌”:“人生欢爱时,少年新得意。一旦不相见,辄作烦冤思。”“人言扬州乐,扬州信自乐。总角诸少年,歌舞自相逐。”“西曲”长于抒情,是南北朝时期湖北一带的民歌,大都表现男女之间勇敢炽热的感情。河陇山歌大都也是情歌,其歌唱主体大多又是年轻人,人们便以“少年”来指称这种民歌,这种理解不仅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有先例可证的。流传于河陇地区的传统山歌,本身也证明了它的名称是“少年”,如下面几首:“大红的桌子上献轮柏,桌子是谁油下的?你唱的少年我明白,少年是谁留下的?”“西天取经的是唐僧,白龙马驮经着哩;留下少年的孙悟空,阳世上宽心着哩。”“大路上过来的光棍汉,手拿了五尺的鞭竿。我给你当人擦一把汗,你把我送上个少年。”“河里的鱼娃儿团河转,为什么不下给钓竿?拔草的阿姐们满塄坎,为什么不盘个少年?”“樱桃好吃树难栽,树根里渗出个水来。心里有你着口难开,少年里拔一句话来。”“大路上来的穿青的,我当是兰州的快班(即捕快,也就是刑警)。你这个阿哥年轻的,为什么不唱一个少年?”“牛毛的褐褂蓝大茶,二郎担扇的纽子。认不得人儿者难拉话,少年上拔你的口气。”(“大茶”系长袍之类的衣服,“二郎担扇”是褐褂上的密门纽扣。缀以“二郎担扇”钮扣的褐褂再配以“大茶”这种袍子,则显得既体面又潇洒,就算得上是“英雄”的装束了)
“少年”被看作“野曲儿”,相对应的该是“文曲儿”。在湟水流域,这个“文曲儿”就是民间的弹唱曲艺平弦,人们称其为“家曲儿”,它有三个讲究:唱词的文学水平、器乐的演奏水平、演唱的艺术水平。这种“文曲儿”是一门具有专业性的综合艺术,其表演的难度和艺术效果都与“野曲儿”有明显区别,它具有艺术欣赏、道德教化和文化承传等多方面的作用,因而较之于“少年”的“俗”和“野”,就显得“高雅”和“文明”了。“少年”被视为“野曲儿”,它的本质特征在一个“野”字上,它的主题是表达人们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追求———情爱。直率地吐露人们对情爱的渴求,是“少年”永恒的主题,男女之间的那些私密的事情,在伦理森严的场合下是难以启齿的,因而“庄子里少年唱不得,老汉们听见时骂哩”;但爱情是人们难以压抑的本能需求,因而到山野去表达、去倾诉,那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这样,“文曲兒”和“俗曲儿”、“家曲儿”和“野曲儿”,便各有表现自己的天地。这种场所和属地的划分得到风俗的确认,在山野唱“少年”就被视为正当行为,因而是不会被责难的。这也说明在数千年的封建礼教社会,对男女之情还是网开一面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其自由表达的。endprint
把河陇山歌称为“花儿”,似乎已成为业界内的主流看法,但所依恃的根据仍然有值得推敲的余地。比如明代被贬谪河陇的高洪写了一首《古鄯行吟》:“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因诗中有“漫闻花儿断续长”一句,人们便断定这种山歌就称为“花儿”。然而,这种推断有可能并不确切———或许诗人因听到唱词中有“花儿”这个词,便顺手借用它来替代这种山歌的名称了呢?河陇山歌多借用歌词中的衬词为其曲令,如衬词为“白牡丹”“水红花”者,则将其定名为“白牡丹令”“水红花令”“尕马儿令”“绕三绕令”等亦属于这种情况。用“花儿”借代男方心仪的女子,这显然是可以肯定的,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河陇山歌就叫“花儿”。其实,张亚雄先生也认为“花儿”一名“复不知始于何时”,这就意味着用“花儿”来定名河陇山歌,其确切性到底如何,仍然是值得深究的。张氏在《花儿集》中谈到,有友人给他寄来河州山歌一百余首,来信中说“敝邑(指河州)野曲,多为男女合唱,随时随地皆可为唱歌的场所”。此人只是说他所寄来的山歌是“野曲”,而并没有说这些野曲名叫“花儿”;这也就是说即便是河州人,也并不知道有把本地的山歌称为“花儿”这么一说。张氏《花儿集》中搜录627首甘青一带山歌,其中直接称这种山歌为“花儿”的仅有两处:“你漫花儿我答话,寻上个大路走了吧”“尕妹好比个海盆里的花,折不下!漫一个花儿了走吧!”而更多的是用“花儿”指代女方,如“我维的花儿你没有见,花儿里挑下的牡丹”“维下的花儿丢不下,丢下是说淡话哩”之类的句子。相反,明确地称河陇山歌为“少年”的句子倒是比比皆是,如“我你哈当人着擦一把汗,你我哈送上个少年”“认不得人儿着难搭话,少年上拔你的口气”“锄草的阿姐们满塄坎,为什么不盘个少年”“尕妹好比个海里的花,折不上它,唱上个少年了走吧!”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少年”之说在河陇地区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如果作进一步研究,我们会发现把河陇山野民歌叫作“花儿”,这可能是一种误会抑或是张冠李戴。以甘肃临洮为中心,流行一种称为“花儿”的山野民歌。这种“花儿”又分北路和南路两支,北路“花儿”流行于临洮、临潭、康乐渭源一带,其代表性曲调是“莲花山令”,基本上是同一乐句的往复循环;南路“花儿”流行于岷县、卓尼等地,其代表性曲调是“扎刀令”,也只是两乐句的反复演唱。从旋律较单一、直言述说的成分较多这一点来看,洮岷“花儿”似乎是介于山歌与谣曲之间的一种体裁。兰州大学郗慧民教授认为,洮岷型“花儿”的艺术特点是“直说性”,即直接诉说心意是这种类型“花儿”的主要表现方式;洮岷型“花儿”的“旋律较为单调,带有某种原始色彩”,它的“节奏自由,曲调缺少较强的稳定性”。与洮岷型“花儿”相对比,河陇民歌的曲调极为丰富,其骨干曲令就有30多种;流行地域极为广阔,青甘宁新等省区都在传唱;群众基础更为厚实,凡西北地区的汉、回、土、撒拉、东乡等民族都喜爱这种山歌。这些差异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河陇地区的山歌与洮岷地区的“花儿”并非同一类型的民歌。在农村、在乡间,人们都把以河陇地区为中心流行的山野民歌叫“少年”,人老几辈子都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其实,把河陇山歌称为“花儿”的只是一些文人,他们之所以如此称名,或许恰恰是以讹传讹罢了;把“花儿”这个仅流行于小范围的民歌名称,戴在广泛流行于西北各地的河陇民歌头上,这其实是张冠李戴。固然,“少年”中多有“花儿”这个词,并且显然是指代男性歌唱者心仪的女子,但不能由此认为河陇山歌就叫做“花儿”;“少年”中更多具体的花名,如“白牡丹”“水红花”等,它们或在唱词中出现,或作为特定的曲令名称,但都不具有河陇山歌总称的意义。涉入“花儿”研究较早且较深入的人,要数乾隆年间的吴镇和现当代的张亚雄,凑巧的是他们均为甘肃人,前者是临洮人,后者是榆中人;临洮和榆中相邻,临洮一带的山歌就叫“花儿”,莲花山则因“花儿”会闻名遐迩,它就在临洮的近邻康乐境内。显而易见,吴、张二位老先生尽管相隔百年,但他们最先接触且接触最多的恐怕都是临洮“花儿”,那是故乡的山歌,与他们有着本能的亲近感,爱屋及乌,由此及彼,他们就把河陇地区的“少年”也当作“花儿”了。吴镇的《忆临洮十首》第九首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句子,这显然也是描述当地群众唱“花儿”的情景,并且概括了“花儿”的两个特点,一是富于比兴,二是风流放浪。的确,吴镇是把当地的山歌称名为“花儿”;然而,那里的“番女”所唱的并非一定就是“花儿”,也可能是称名为“拉伊”的藏族民歌。一些研究者用以证明河陇“少年”也叫作“花儿”的又一根据,是明朝诗人高洪所作《古鄯州行》一诗:“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从北魏到北宋,鄯州即今乐都一带,高洪在任职河州期间曾游历湟水流域,这首诗便是对古鄯州风物生动形象的记述。不过,此处的“花儿”所指并非必定是当地“农夫村女”所唱山歌的名称,也可以理解为古鄯州山歌唱词中的具体花名,因为河湟一带“少年”中多有以花儿之名作衬词来反复吟唱的现象,且不少曲令本来就是以某种花儿的名字来定称的,如“白牡丹令”“水红花令”“山丹花令”“好花儿令”,等等;或许正是由于发现这种现象在古鄯州一带的山歌中普遍存在,高洪遂以“花儿”借代这种山歌也便顺理成章了,但不能由此说古鄯州一带的山歌就叫作“花儿”。近代人慕寿祺的诗作中有“一路唱花儿”“听人隔院唱花儿”的句子;近代人高一涵的《河洮纪行》中有“野田处处唱花儿”的描述,所有这些说法,或是不明就里地受了前人的影响。有必要认真对待的倒是以下情况:清人叶礼所作《甘肃竹枝词》中,有“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的句子,他把河陇山歌既称“花儿”又称“少年”,看来还是非常谨慎的。张亚雄在《松花道人赏识花儿》一文中也曾说,“‘花儿一名,复不知始于何时”,这也就是说,即便是临洮的山歌,是否就叫作“花儿”,那还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他还说河陇一带的山歌既叫作“花儿”又叫作“少年”,理由是“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是男人的自谓,“花事为少年倜傥之行径,故‘花儿又名‘少年”。张亚雄为河陇山歌定称,态度自然是十分谨慎的,但难以自圆之处仍然存在:“花儿”不过是采用了借代这一修辞手法,而“少年”却是一种直白的陈述,因而“花儿”与“少年”并不互为对应;再说不仅仅是青年男子,女子也唱山歌,怎能仅从男方的角度为河陇山歌定名呢?从上述学者们的论述和推断中倒是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河陇一带的山歌大致说来是年轻人的情歌,有人称这种山歌为“花儿”,这是发生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的事情,其中又以甘肃籍的学者居多。自然,名称之争在今日已属多此一举;抑或,它只是河陇民歌研究中的一个枝节问题。
就“少年”的演变,我的观点概括如下:①任何特定的文化,都是由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相应的历史条件共同孕育而成的,单纯从某一方面去追寻“少年”的源流是难以找到合理答案的。②人类自有了语言就有了歌,语言和歌都是为了情志的表达;歌也是一种语言,其表达情志的形式更为迫切和细腻。③羌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缔造者,羌人的祖源则始于河湟羌人;青海不仅是江河的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因而“少年”是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形式。④文化是一条生生不息地流淌的河,在“少年”这条“河”的漫长流程中,曾不断注入与它相遇的“活水”,因而“少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⑤人类群族在不断融合,文化也在不断交流,“少年”正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中变化和发展,它的生命不可能停留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⑥文化是以不改變基因为前提而发生变异的,正如人类种族的后代身上总能找到先祖的遗传基因一样,文化的变异恰恰是以原生形态为根据的。⑦古羌人经历了漫长而沉重的民族蜕变苦难,他们为“少年”赋予了苍凉幽怨的音乐基调;生息在河陇地区的人民是一个不断追求的族群,因而“少年”中充满对现实的期待和对未来的向往。(全文完)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