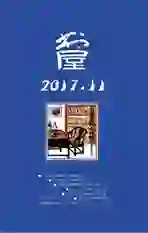读书漫谈
2017-11-27鸣弓
鸣弓
一、为什么读书
纵观历史,读书的原动力,应该是“学而优则仕”。“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应试及第,跻身仕途,得享富贵荣华。如若科考受挫,靠笔墨维生,授徒卖文,以笔代耕,大抵是近乎“十丐”的穷困潦倒生涯。“砚田无恶岁”之说似乎是“理想国”的说辞——除非先做官赚足了银两,而后砚田笔耕,方保悠游无虞。
满腹诗书,只有“货与帝王家”,才能变现为物质利益。北魏四门小学博士董征,好古嗜学,宣武帝征教授四王,后特除员外散骑侍郎。董征还乡,置酒高会,大享邑老,荣耀之极,乃现身说法,告诫子弟曰:“此之富贵,匪自天降,乃勤学所致耳。”
仅有知识不行,还必须“听话”。否则,任你学富五车、读书种子也仕途危殆,甚至性命不保。朱棣进军南京前,智囊道衍和尚(姚广孝)跪求曰:攻取南京后千万别杀方孝孺,杀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方孝孺乃当世大儒,聘为世子师。朱允炆继位,值文渊阁,帝读书有疑,即召讲解。“读书种子”书生气十足,反对朱棣暴力夺取大位,其结果是“秀才遇上兵”,自己被咔嚓了,且殃及“十族”!
元宵夜,宰相宋郊在书房研读《周易》,其弟大学士宋祁却吃喝玩乐,通宵达旦。翌日,宋郊责备弟:你现在如此穷奢极欲,难道忘了那年元宵节,我们在州学吃腌菜的情景?宋祁反问:我们当年吃腌菜煮饭,是为了什么?兄长提醒弟弟,不要贪图享受,忘记读书人本色。宋祁认为当初吃苦,正是为了今天的“好日子”。宋氏兄弟争论的焦点正是吃苦读书为了什么。作为高级公务员,依据制度享受优渥待遇,无可非议,但如果挡不住诱惑,醉心享乐,钻钱眼,纵大欲,那就背离初心,势必自毁。
宋刑部员外郎刘式,酷好读书,藏书丰富。刘式逝后,夫人陈氏召集诸子说:“你们的父亲为官清廉,没有留下什么田庄产业,只有遗书数千卷,可称之为墨庄,希望你们在墨庄里辛勤耕耘,好好继承这份珍贵的祖业。”刘式之子立本、立之、立礼、立德遵从母训,刻苦攻读,学有所成,成了名人。刘氏后裔嗜学成风,绵延不息。“家藏万卷书,文风冠当代”的刘氏墨庄,二百七十年间出了二十一个进士,号称“进士之家”。
北魏博士李先回答皇帝拓跋珪问“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时,非常肯定地说出“莫若书籍”!李博士从纯书生的角度指出读书以文化人的功能。
注重以文化人,就会淡化博取功名,而近乎后世所谓“为读书而读书”。晋皇甫谧不仕,耽玩典籍,忘寝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秏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明代沈锦好读秦汉文,不求闻达。或戏之曰:既不试,学将何用?锦正色曰:下士晚闻道,将以自修,岂专为青紫哉?学益力。认为读书旨在修养悟道,而不是冲着朝服官帽,别是一种境界。
宋代邹极,累官度支员外郎。请补外,除江西提刑。亲丧服除,曰:读书丐禄,以娱亲耳。今亲丧,可复仕乎?力请致仕。邹极读书做官,只是“为了母亲的微笑”,而无关“大地的丰收”;老亲辞世,他即请求退职,想必是厌倦透了官场生活。
许衡,七岁入学,问其师曰:“读书何为?”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七岁童对读书“取科第”提出质疑,令老师大为惊奇,认为这名学生“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稍长,嗜学如饥渴,博览群书并立志学以致用;成年后,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貨、水利之类无所不读。逃难中,得到一部王弼注释的《易经》,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他不食道旁无主之梨,留下了“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的名言。许衡最终成为元初著名学者,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
底下,再列举几位苦读有成的儒生:
后汉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猪。过学舍,忘其猪而听经。猪主求索,见而欲笞之。门下生共禁,乃止,因留宫门下。樵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遂通经成大儒。
后汉高凤,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
前燕王欢,安贫乐道,常丐食诵《诗》,其妻患之,焚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
有“杜武库”之称的杜预,几乎没有什么武艺,但他善用兵,灭吴立殊勋。杜预好学,最喜读左氏《春秋传》,自谓有“左传癖”。其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左传》注解流传至今最早者,收入《十三经注疏》。
王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
明代孙交在南京任部长高官,僚友以事简多暇,相率谈谐饮弈为乐,交默处一室,读书不辍。或以为言,交曰:“对圣贤语,不愈于宾客、妻妾乎!”笃志好学,老而不倦,年八十犹篝灯达旦,诸生劝少息,曰:“汝辈读书日长,我则读书日短矣,何遑息乎?”
屠本畯以荫入仕,自称憨先生,好读书,老犹勤学不辍。人曰:“老矣,奚自苦?”本畯曰:“吾于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欠身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苦也!”
杜、王、孙、屠人在官场功名已就,仍嗜书如故,用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学习型干部。
康熙间,朱彝尊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他常携带一名抄书手出入史馆,随时抄录各地进献的图书。此事遭人告发,朱彝尊被免职,人称“美贬”;他自己也不后悔,说:“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丢了乌纱帽没关系,凭知识底蕴,可以著书立说,乐在其中。
文场与战场,何者博取功名快捷,因时而异。前汉青年才俊傅介子浩叹:“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当驰骋疆场,立功绝域,怎么能长久地沉溺在笔砚之间呢”傅介子重武轻文,并非无据。若逢乱世,枪杆子比笔杆子好使,武人立功比文人成功要来得快。东汉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北齐高昂不喜读书,常说:“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上述说辞,主旨都是以武立身,博取功名富贵。出名求利要趁早嘛!endprint
投笔从戎是一种选择,身在行伍而嗜书,也是一种选择。
宋攻伐后蜀,诸将多取子女玉帛,曹彬行装中只有图书、衣服而已。宋太祖认为曹彬清介廉谨,授任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
金伐宋,攻破汴京,众人争着取府库财物,完颜宗宪独自载图书以归。参加伐宋的山西路都转运副使沈璋也是独无所取,惟载书数千卷而还。
有的人因受刺激而读书。
北魏傅永字修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马鞍,倒立驰骋。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去请教洪仲,洪仲着实嘲讽一番,却不帮他回信。受此刺激,傅永发愤读书,涉猎经史。由此文武双全,受到皇帝褒奖:“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
苏秦出游求官,铩羽而归,嫂不为炊。嫂嫂居然不给做饭,使苏秦大受刺激!乃发愤苦读,终佩六国相印。
唐代湛贲为州吏。其连襟彭伉中进士,亲族集贺,来者皆名士,独湛是小吏,被安排在后阁就餐。妻因责他不自振励,致蒙受此困辱。湛贲因感愤力学,一举登进士第。
明钱士馨,韶年放荡不羁,与靑楼妓昵,欲挟之归。妓曰:“观君谈论,恨读书少。请俟异日。”士馨乃假东湖僧舍以居,夜读《昭明文选》,为沙弥所讥。士馨遂发愤硏究经史,多所撰述。钱士馨学有所成,与妓女、和尚的讽讥很有些关系。
清咸丰间武官张曜,以战功擢河南布政使。他没有文化,御史刘毓楠劾其“目不识丁”,改任总兵。张曜从此立志苦读,几年之后,学问大进,淹通图史,诗文皆有古法。其妻有文化,他就拜妻为师。他还特请人刻了一方“目不识丁”的印章,经常佩在身上自警。
因科场受挫而读书。
宋乐清人万规励义气,敦行谊,人皆尊信之。科场受挫,谢举子业,闭户读书。于家设书塾,教授乡里。万规居地江阔水深,渡者多遭覆溺。万规乃捐资建桥,历经七年,费钱三百万,乡人取名“万桥”。王十朋称其“以弦诵先吾乡,以节行高一时”。
接受领导劝谕读书。
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后鲁肃与蒙论议,惊叹其“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因书香濡染而读书。
《世说新语》故事:郑玄家里的奴婢都读书。一次郑玄曾使唤一婢女,事情干得不称心,郑玄要揍她。她急于分辩,郑玄更生气,就把她罚站到泥淖里。另一婢女过此处,见状,遂问:“胡为乎泥中?”(引《诗经·邶风·式微》,意为:为什么会在泥水中。)她回答说:“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引《诗经·邶风·柏舟》,意为:我急急忙忙去诉说,反而惹得他发火。)瞧瞧郑老师家那个文化氛围,看看郑家仆人的文化品位,普普通通两个奴婢,一说话便是子曰诗云,且引用得恰到好处。
二、读什么
女皇武则天新著《臣轨》隆重推出,定为应举必读,取代传统经典《老子》,全社会争读武著遂成政治风尚;宋真宗好读“天书”,人造“天书”乃应需而出;明太祖对《孟子》中的民主言论大光其火,于是就删经典,出“洁本”。
紧跟官家读书,是聪明人邀宠升官的终南捷径,关键是要探听到皇帝读书的信息。清高士奇直南書房时,尝携金豆满荷囊,如上阅某书,近侍以告,则酬以一金豆,即抽某书涉猎之。偶天语垂问,无不能对大意者,以是益蒙嘉赏,以廷臣中博雅可与道古,莫士奇若也。高士奇由此贵盛一时。
有一种历史文本“起居注”,是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实录,“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这种警戒皇帝的史书却“不令人主见之”,于是就有“天子不观史”的说法。一代明君唐太宗对此亦颇困惑,曾向宰相、监修国史房玄龄求解。房解释说:“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原来是为了保护史官,怕皇帝一见负面记录必定发怒——天子一发怒,后果很严重!唐太宗以自己用心“异于前世”为由,非要观史不可。房玄龄等急忙突击删改高祖、今上实录,而后敬呈御览。上见书六月四日事(即玄武门之变),语多微隐,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这段“天子观史”故事很耐人寻思。皇权威慑,帝王干预,史官战战惶惶,“实录”谈何容易!
唐太宗不但观史,也写书,作《帝范》以赐太子,凡十二篇: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修身治国,备在其中”。唐太宗苦心孤诣为儿子留下一部《帝范》,希望成为其履职的准则。更难得的是,太宗皇帝还现身说法,勇于检讨自己的“不善”,让儿子读懂他这部“活书”。
“天子不观史”,是专就“实录”而言;从汲取历史经验角度讲,天子最应该读的是史书。“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司马光专为皇帝精编的历史读本,经赵官家审查认可赐名《资治通鉴》,缘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学者胡三省特别强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
《资治通鉴》应该是皇帝不离左右的读本,明智的大臣亦持此见。何如宠,累官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退休还家,犹不忘敬告崇祯皇帝时观《通鉴》,察古今理乱忠佞。语甚切。
臣民读什么书,多出于爱好,从中亦可见个人志向。隋朝李密“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一手翻卷书读之”。越国公杨素见此大为惊异,喟叹书生好学。知其所读为《项羽传》,愈大为爱重。李密“牛角挂书”,当时抓住高官杨素眼球,效果奇佳;日后更是干出了类若项羽的事业,朝廷为之震惊,社会为之震荡。
刘恕,少颖悟,过目成诵。笃好史学,正史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钜微之事,如了指掌。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恕为学,自历数、地理、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尝偕司马光游,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终,归验旧史,信然。endprint
新任宰相寇准,在陕遇张咏平定蜀乱归,热情款待,亲送至郊,问“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张咏借古人之言批评寇准“不学无术”;寇准笑而悦读,果有宰相胸怀。
三、怎样读
读书,一要时间,二要吃苦。珍惜分阴,刻苦攻读,自是读书有成的不二法门。头悬梁锥刺股便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苦读典型。据实而论,此种苦读,疲劳战,磨时间,精神可嘉,方法实蠢,并不可取。
下面例说几位苦读典型。
凿壁偷光的匡衡,为了遍读主人家的藏书,宁愿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者。
卢植,东汉末年经学家、将领。少与郑玄俱从马融学,好研精。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如此不受声色干扰,委实难得。
刘峻好学,家贫,寄人篱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自谓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时人谓之“书淫”。这位“书淫”正是为《世说新语》作注的刘孝标。
唐代杜佑,虽位极將相,却手不释卷,白天忙于公务,入夜则挑灯苦读,笔耕不辍,著成《通典》,开创了新的通史类体例,后世纷纷仿效,遂有“三通”、“九通”之说。
前文提及的渊博史学家刘恕,特绕道去宋次道家借阅。次道日具馔为主人礼,恕曰:“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吃喝耗费时间,免了吧。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王冕,七八岁时,父命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并默记之。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王冕离家,寄住寺庙。入夜就坐在佛像膝上,拿着书借佛像前的灯光诵读,书声琅琅直到天亮。佛像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王冕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
《十七史商榷》作者王鸣盛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居苏州三十年,闭户读书,不与当事交接。精校勘考订,详于舆地职官。
李绂,自幼聪颖,有神童之称。进士出身,雍正三年出任直隶总督。赴京途中,得知雍正的宠臣田文镜任河南总督时的苛政,直斥田文镜“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乃为田所恨,屡遭诬告,革职受审。李绂身系囹圄,日读书饱啖熟睡,人称“真铁汉也”。
读书不如抄书,方法虽笨,效果却佳。
宋代周启明,科考第一,仕途蹭蹬,归故里教弟子百余人,里人称为处士。周启明笃学,藏书数千卷,多手自传写,而能口诵之。周启明读书成颂,盖得益于亲自抄书。
苏学士东坡也于抄书后发过一番宏论。他抄两《汉书》,既成,夸以为贫儿暴富。言称:唯手写校勘,经几番注意,自然融贯记忆,无鲁莽之失。今人买印成书,连屋充栋,多亦不读,读亦不精,书日多而学问日虚疏,子弟日愚,可叹也!苏学士嘲讽的拿精装书当摆设、装门面的现象,今时尤甚!
宋代杜鼎昇,雅有古人风,鬻书自给。尝手写孙思邈《千金方》鬻之,凡借本校勘,有缝折蠧损之处,必粘背而归之;或彼此有错误之处,则书札改正而归之。据说他从《千金方》中得养生之道,行之二十年,筋体强壮,耳目聪鉴。抄书敬业,一丝不苟;躬行养生,益寿延年。
四、读书轶闻
诵经获释 诸生包咸,回乡里途中,被赤眉军拘执。十多天,包咸晨昏诵经自如,拘者怪之,遣其归。
读檄治病 官渡之战,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文》,痛骂曹操。时曹操头风病发卧床,读陈琳檄文,惊出一身冷汗,头风顿愈。袁绍战败,陈琳归附曹操。曹操深爱其才,军国书檄多出其手。重用骂过自己的人,阿瞒肚量可见一斑。
献书得罪 隋大业十二年,恰逢五月五日,朝臣纷纷向皇上敬献珍玩,纳言苏威独献《尚书》。有人借此诋毁苏威:“《尚书》中有《五子之歌》,苏威用心恶毒啊!”这一来炀帝更加生气。苏威答炀帝问不合帝意,奸佞唆使人诬告苏威。苏威被判死刑。后改释放,其子孙三代都除名为民。
书中相见 唐代雍陶出刺简州,时名益重,拜见一面很难。秀才冯道明,下第,请谒,言称“与太守有故”。陶倒屣,及见,呵责曰:“与足下素昧平生,何故之有?”冯曰:“诵公诗文,诗集中日相见,何隔平生!”因吟陶诗数联,如“闭门客到常如病,满院花开未是贫”等句。陶延之上坐,待如旧交,厚赠遣归。
藏书腑笥 杨玠娶崔季让女。崔家富藏图书,杨玠常游其书斋。既而告人曰:“崔氏书被人盗尽,曾不知觉。”崔遽令检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经笥矣。”与之类似的是明代周玄,曾挟书千卷,在长乐高棅家读之,十年后以尽记所读,弃书离去说:“在吾胸中矣。”周玄对自己记忆力似嫌太过自信。
爱妾易书 明代朱承爵,嗜藏书,特钟爱宋刻,传说他用爱妾交换一宋刻本《汉书》,堪称藏书奇闻。
剪发易书 元代陈祐少好学,家贫,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
焚香盥手 邓韨,明代学者、书画家。弃举业,以读书自娱,好宋儒书,旦必肃衣冠焚香盥手而读之。敬书虔诚若宗教徒,委实难得。
温公惜书 《梁溪漫志》载司马光读书故事:“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暴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板,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撚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图、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汝当志之。”温公敬书如神,惜书如命,令人叹服。
归罪于书 554年,西魏攻入江陵,梁元帝命人将他收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堆在院子里全部焚毁。人问他为何烧书,梁元帝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之败,所以要烧了它。书有何错?错在人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