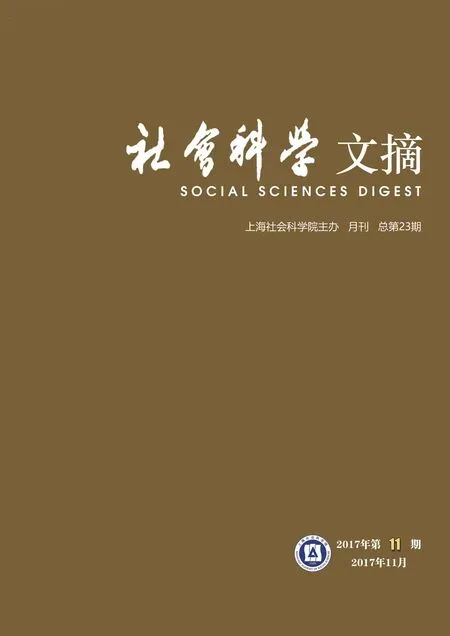哈罗德·布鲁姆与“第四种批评”
2017-11-23曾洪伟
文/曾洪伟
何谓“第四种批评”?
“第四种批评”,亦即媒体批评、学者批评、作家批评之外的作家学者批评,其主体的身份是学者。他们往往身处大学体制之内,以文学教学、研究为其职业,同时也从事业余的文学创作。这种综合性的批评新形态首先要求批评主体具有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双重经历,具有作家、学者的双重身份,然后在文学批评中能将两种资源(文艺创作经验与技能、学术研究的经验与理论知识储备)巧妙地、熟练地、有机地糅合到其批评文本之中。
总体而言,“第四种批评”的核心特点包括:在批评理念上,主张“审美至上”“艺术至上”的观点;在批评实践中,往往聚焦、挖掘文本的艺术性,尤其是其艺术手法、写作技巧的运用;在文字的表述上,注重手法、风格的多元性,但文字、意义表达的审美化、艺术化是其核心。与此同时,它也一定程度地保留了学院学术批评的理论性、系统性、严谨性的特点。
另外,受作家维度的文学创作、表达方式与语言惯习和审美价值追求的深刻影响,作家学者的批评还呈现出丰富的情感性和鲜明的主观立场、倾向与态度,这与学院批评一贯的、常规的有意克制与压抑批评主体自我情感、追求零度情感叙述和客观中性立场的做派迥然不同。
通过仔细考察和深入分析哈罗德·布鲁姆职业生涯与批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布氏后期职业身份和批评著作的“双栖性”、双重性与其前期相比甚为明显和突出。这种双栖型批评实际上就是一种典型的作家学者批评。
布鲁姆文学批评:从学者型批评到作家学者型批评
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生涯大体上经历了前后两个形态、特征各异的时期(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前期主要是学院/者批评家,后期则主要是作家学者批评家(有时他也以学者批评家、媒体批评家的身份出现)。由此,他的众多批评著作中既有纯粹的学术批评文体文本,又有作家学者型批评风格作品;而就一部批评著作而言,它可能既包含学者批评话语、形态、特征,又包含作家批评话语、形态、特征(如《西方正典》),呈现出学者批评与作家批评混合、杂糅、交融的多维面相与特点。以下重点探讨布鲁姆后期作家学者型批评(即“第四种批评”)的整体风貌与特征。
哈罗德·布鲁姆是“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是“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这其中,“最有天赋”是就布氏批评的个人才情而言,“最有原创性”是就其批评的学术/理创新性而言,“最具煽动性”是就其批评的艺术审美性而言。因此,可以说布鲁姆是一个作为“才人”(才性)、“学人”(理性)、“诗人”(诗性)都极为突出和成就卓著的批评家。三种才能及禀赋集其一身,使得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多维性,而他的批评身份也由之具有多重性,即非单一的学者型批评家所能简单概括。事实上,在其后期,除了学院批评(如《智慧何处寻》《千禧之兆》《影响的解剖》等)、媒体批评(如他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上猛烈抨击当红的J.K.罗琳的《哈利·波特》、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等通俗畅销作品)之外,布鲁姆还主要从事作家学者批评。其批评身份在学者、作家之间滑动,总体呈现出“学者作家化”的趋势。
布鲁姆是坚持“审美至上”原则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审美是他文学批评的唯一衡量标准,而伦理道德、政治意识形态、市场、文化等其他因素则被一概拒斥。例如,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布鲁姆对以“憎恨学派”为代表的反审美倾向的文化批评、政治批评风潮极为憎恶和反感,并予以批判与声讨。另外,布鲁姆对从事去审美化文学研究的文学学者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嘲笑,指斥他们的文学研究的非专业性以及对于文学文本审美(分析)的悖离与逃避。因此,对20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学院派“批评的理论化/文化化/意识形态化”趋向与热潮,布鲁姆是极力反对与抵制的,甚至不惜提出“以艺术反对理论”(art against theory)的极端化口号,即提倡以艺术的感性抵抗理论的理性和以审美对抗非审美/去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维护和捍卫审美、感性的绝对权威与中心地位。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文本分析中,布鲁姆从文本细读开始,注重从审美感性(直觉)体验进入(而不是像学院派的文本批评那样从理论开始,以理论先入为主去切割、阐释文本),从语言细节(如词汇的运用)、修辞手法(如反讽)切入,重视分析文本的叙事结构、节奏、声音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刻画等,这些都表明他是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批评文本的。
在文体风格上,布鲁姆后期的批评著作无论与其前期还是与其他学者的批评著作相比,其个性化色彩、表达的艺术性、可读性都非常明显和浓郁。布鲁姆有意识地冲破、挣脱学院派批评的禁锢与束缚,一扫传统主流学者批评理论先行、专业术语充斥、艰深晦涩、行文严肃呆板、理性张扬、感性压抑、零度情感、主体隐匿、客观中立等千人一面的书写模式与范式,大胆建构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首先,在其批评作品中,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到其丰富的情感样态以及强大的情感张力,他时而幽默嘲讽,时而忧伤悲愤,时而温情脉脉,时而激情勃发;在其他批评家作品中难得一见的“我”“我们”等第一人称主体频繁出场,成为作者频频表达、抒发自己多样情愫的喷发口。它们不仅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而且极易引发、触动作者/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对话、交流与共鸣。总之,布鲁姆毫不掩饰自己内心丰富的情感生成,并任由其在字里行间自由流淌、舒展、奔涌、恣肆、抒发,其个性化的风格(包含个人性格、个人情感、个人观点)和爱憎分明的立场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一个个性张扬、情感丰沛、生动立体、轮廓清晰、有血有肉的批评主体形象。
与此同时,布鲁姆还非常重视文学批评表达的艺术性,即诗性/诗化特征。首先,他去除学院批评统一的格式规范和程式化的批评范式的束缚和限制,不拘一格,自由表达。其次,他驱除理论的重霾,卸下理论的重负。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批评主要是依靠审美感悟和直觉的介入,从感性出发,把书中的隐含之意清晰地表达出来,而所谓理论(尤其是20世纪以来生成的各种学院派批评理论)都是赘余之物,毫无用处。这体现出布鲁姆鲜明的实用主义批评观和唯美主义美学观。这样,少了规则的束缚与羁绊,卸掉理论的重负,剥除理论的矫情和刻意装点,在涌动不已、激昂澎湃的内在情感的驱遣下,在感性和直觉的牵引下,布鲁姆轻装前行,其作为作家的才情和多年的文学素养与积淀被激活与唤醒,其行文运思走笔自由生动活泼、诗意流淌、文笔酣畅,其色彩斑斓、轻松活泼的文体风格与其他学者批评灰色、沉郁的基调形成鲜明对照。这充分体现出布氏后期文学批评崇艺、尚美的一面。因此,从阅读效果来看,读者在其文本的字里行间不仅能感受到其率真、奔放的情感喷涌与激荡,而且还能欣赏到其情感、意义的诗意/诗艺化表达。
布鲁姆的批评还有其学者批评的一面,即注意批评的理性、理论性、学理性、逻辑化、历史化、系统化一面。在其作家学者批评著作(如《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我们除了感受、体验到其艺术感性、审美直觉的主导之外(作者往往是从感性、审美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解读/阐释文本),也不难窥见理论、理性、学术性的介入与参与。例如,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在意大利学者维柯历史循环三阶段理论(即神权、贵族、民主三个阶段)以及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对西方文学史的四分法文学循环论(即传奇的、喜剧的、悲剧的、讽刺的四个时期循环)基础上,提出西方文学史的循环四分法,即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混乱时代,并以此为基本的历史演进脉络与批评框架,将26位西方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纳入批评视野之中,然后逐个分析、挨个探察其经典性。这一过程就包含了分类、历史化(亦即“将具体的文学作品纳入文学史框架中去衡量,建立它与其他作品的影响谱系和时空联系”)、整理等活动与行为,而这正是学院/者批评的典型特征(注重和强调系统化、条理化、逻辑化、严密性)。另外,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还使用了比较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从影响诗学/误读理论的角度探究作家之间、文本之间的影响、误读、创新关系(即探究其互文性);从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康德“审美无功利性”和佩特唯美主义、“陌生性”观点对他的理论影响与构建。他对西方文学史本质所作的关于“陌生化/性”的高度理论化、学术性概括,他对当代“憎恨学派”以及其他学院派批评理论所作的剖析与批判等,都彰显出其批评的学院派一面。
总体来看,布鲁姆后期的作家学者批评主要是面向学院外的文化大众和(各种年龄、各类文化层次的)“普通读者”,是一种大众指向的、写给大众的大众化审美批评。它在后现代的反经典、去审美的社会中,在文学终结、经典式微、审美衰颓的时代,承担着经典/审美启蒙、教育和救赎责任,其主要目的是吸引、引导大众读者阅读各个时代的世界文学经典,从而打破经典阅读、审美欣赏的精英化、学院化(垄断),推促经典审美的大众化传播,最终实现以经典文学、崇高/距离美学对抗、遏制后现代社会文学终结、审美衰微的现实趋势。由于读者对象、接受群体发生改变(从专业读者变换为普通读者),布鲁姆也随之改变其批评策略,转变其批评范式(从学者批评转变为作家学者批评),以更加为文化大众欢迎、更易为普通读者接受的方式去批评和写作。而他从小即阅读古今世界文学名著所积累的文学知识与素养、视野与眼光,审美直觉与感悟力,文学才情与天赋,其作为作家的创作经历与体验,和前期作为学院学者的理论储备与知识积累等,都使得他转变身份成为作家学者并开展卓越、成功的作家学者批评成为可能。
对当代中国学院批评的启示
首先,学院体制内应该并且可以有多种批评形态共存。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生产主体是大学文学学者,而他们的产品形态又主要是格式规范统一的学院批评作品,少有其他批评(如媒体批评、作家批评、作家学者批评等)作品存在,而具体到某一个批评主体/个体而言,其批评往往也缺少批评身份、批评类型的变化或多样性。因此,无论从共时还是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学院文学批评的形态、种类、格局都非常单一,总体上缺乏生气与活力。而哈罗德·布鲁姆作为大学体制内的学者,其批评身份从职业批评家到作家学者批评家、媒体批评家的嬗变,以及集多元批评身份于一身,说明学院批评的转型与多元化共生是可能的。同时,布鲁姆的例子也说明,学者与作家身份、学者批评与作家批评形态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互不排斥、完美结合,这有力地驳斥、证伪了国内外知识界长期盛行的“学者与作家不能兼任”“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不能兼事”的固有成见与谬论。当然,除了作家学者身份或批评形态之外,学院体制内还可以有其他批评形态——如媒体学者批评等新形态——存在。因此,当代中国学院批评的多元化是可行的,其单一、沉闷、僵化的批评格局完全可以得到改观。而由此,中国文学批评的生机、活力、张力、生命力也可以得到持续激活与增强。
其次,布鲁姆的作家学者批评转向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接续、恢复、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第四种批评”传统具有重要的启发、示范意义。其实,“第四种批评”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且曾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态(“诗化批评”,即批评的诗化,文本兼具理性抽象的内容与艺术化的表达形式,以及独特的审美关注点,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钟嵘的《诗品序》,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毛宗岗父子评点《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等文本,以及大量的“论诗诗”作品,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绝句》等)而存在,并取得了丰硕瞩目的成果,而且积淀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和珍贵遗产。在中国文化转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一传统仍被继续传承、延续,只不过是以现代形态的“第四种批评”面相而出现和存在(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诗论》、梁实秋的《文艺批评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但在进入当代之后,经过一波又一波文化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冲击,在人为的强力干预之下,现代与传统断裂,西方单一化、模式化的文学批评范式被全面引进学院之中,并被奉为金科玉律和圭臬典范。与此同时,学者与作家、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也被完全不同的两个体制(学院、作协)以及僵化错谬的观念(即所谓“学者与作家身份相互排斥”)强行拆散,两者的统一与融合难以实现。这样,当代中国学院文学批评最终呈现出与西方文学批评同质化的单一态势。作为世界著名、权威批评家的布鲁姆,其作家学者批评转向对于唤醒、激活中国学院学者的批评传统、转换其批评形态意识,使之向“第四种批评”迈进无疑提供了认知可能,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这也构成了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里主要是指文体风格),恢复、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内容。
再次,布鲁姆的作家学者批评对于社会文化公众的美育责任与社会担当值得我们学习。布氏的作家学者批评向中国学者证实了,文学经典批评的成果走出象牙塔、走近大众不仅是可能/可行的,而且作为作家学者还可以以自身的特殊身份与才识优势(知识权威、文化精英)更有力地推动文化成果的社会转化,使之走得更广、更深、更远;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发生或停留于学术界、知识层、学者圈、学院内的知识生产、累积、存储、“搬运”、迁移、更新或传承(的事件与过程),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内循环,而且能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产生社会效益,对普通社会大众发挥美育作用与功效(这也正好迎合了文化大众的内在心灵诉求),最终促使后工业/后现代消费社会中已被高度异/物化、处于心灵危机(物欲横流、精神枯竭)中的人类个体能够通过经典审美以高雅对抗平庸,以精神对抗物化,以审美感性对抗工具理性,以经典对抗庸常,从而修复、还原、整合、建构、重塑一个具有丰富、独立、自由、强大、完整、本真、纯粹、富有生命力的自我。而就宏观的社会与民族发展而言,随着文化大众审美能力、认知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人性的完善,人格的健全,心灵的美化,整个国家的文明素质与水平以及软实力也会相应提升,这对最终建成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美好、强盛的民族与社会将不无裨益,且功莫大焉。以此而言,布鲁姆式的作家学者批评的社会美育功能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