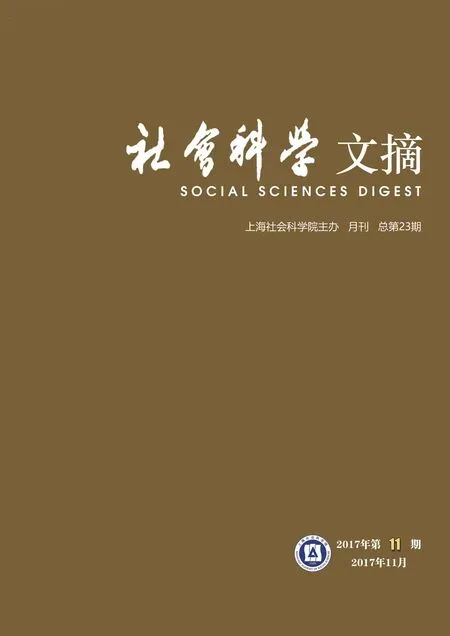政治权力绑架下的西汉天人感应灾异说
2017-11-23蔡亮
文/蔡亮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于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说都颇为熟悉。一般认为,儒生官员能利用灾异来指陈时弊、规劝天子、进计献策,因而可以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从理论上看,这种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从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操作上来看,灾异说其实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使命。本文侧重于研究灾异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并试图揭示西汉官员对灾异解说的热衷,与其说是为限制皇权,不如说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
一方面,儒生用五经取代了卜、史等所掌握的对灾异、星象的专门知识,并将控制灾异的神灵转化成一个作为道德载体的上天。通过这种方式,儒生成了西汉中后期各种灾害、异常现象的主要解说者。另一方面,儒生在成功取代专职的卜、史的同时,却并未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社会隔离层来保证其对灾异解说话语的垄断权。
正如诸多历史案例所显示的,无论是引用五经,还是诉诸解说者自身的道德素养,其实都不能增加其对灾异解说的信服力。儒生官员未能对灾异解说知识实现垄断,也未成功地系统化灾异解释的规则,更没有在官僚机构中建立专职的灾异解说位置,这意味着灾异说无法具有独立自主性,无力履行对无道政治的谴责功能,反而仅仅沦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研究回顾:道德化的宇宙论与限制皇权
众所周知,被誉为灾异政治之父的董仲舒认为,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人格化、道德意化的“上天”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反应。如《春秋繁露》中常常被引用的一段话说:“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影响深远的天人感应传统的源头可以回溯到《尚书》和《诗经》,在《左传》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颇为完整的表述,如大夫文士伯就曾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而灾异说从汉代开始蔚为大观,汉儒对其理论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他们认为,君主是连接宇宙与人类社会的桥梁,其行为和政策都会受到上天的监督,上天会以某种灾害之事或怪异之象来对统治者的错误发出警告。根据儒家传统,《诗》《书》等五经中对灾异的记载和解释保存了圣人对上天旨意的解读,熟读五经的儒生由此成为灾异最合法的解释人。后代的研究者认为,这样通过将灾异联系于当前的政治,汉儒就得以批评朝政乃至皇帝本人。天人感应下的灾异说不仅使皇权在一定的道德约束下运行,而且同时为儒生参政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正如王爱和所论,“汉代的灾异说体现了作为对宇宙社会之间秩序负责的君主和对这种秩序进行规定的儒生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灾异说似乎显示了君主的政治权力和儒生官员所拥有的道德权威之间的一种优雅的平衡。不过,这种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的前提上:第一,认为成百上千的官僚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政治理念,他们与君主构成两个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第二,认为灾异说作为一种话语具有自主的力量,它使儒生官员得以与皇权抗争,以其理想为坐标来改变现实。本文则试图显示,这种理解有简化历史的嫌疑。当我们走出汉儒对灾异的理论探讨,回到各种灾异政治事件的历史语境时,我们就会发现,不仅官僚之间斗争不断,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而且灾异说本身并不构成一种改变现实政治的自主力量,其实际操作往往与其理论宗旨背道而驰。很多时候,它不过只是政治权力的仆人。
灾异与政治斗争:案例分析
汉元帝(前49~前33)继位后,光禄勋萧望之、少傅周堪、宗正刘向密谋罢退外戚许、史两家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结果计划泄漏,对手先发制人,周堪、刘向被投入监狱,萧望之被免官。但是,元帝似乎对萧望之等人怀有恻悯之心。当年春季发生地震,夏季有客星出现在昴、卷舌之间,元帝以此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征刘向、周堪为中郎。同年冬天,又发生地震。当消息传到京城,许、史、弘恭、石显一派认为是有罪复用的萧望之等人引起了地震。恐慌之际,刘向指使其外亲上书,将地震的原因指向弘恭。石显、弘恭很快查出刘向是这封上书的背后操纵者,刘向因此再次入狱,而萧望之也因让其子上书申辩罢免一事而遭弹劾,随后自杀。这场政治纷争并未到此结束。萧望之的死似乎让元帝颇受触动,他随后陆续提拔萧集团的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刘向以为自己重新被重用的机会到了,于是上书言事。在这封长篇累牍的奏议中,刘向旁征博引,以五经中所记灾异为根据来讨论当时的各种灾害异常,指出灾异的出现是因为元帝轻信小人,排斥贤者君子。刘向的上书没能打动元帝,反而进一步惹怒了石显和弘恭。这年夏天阴冷,日青无光,石显、弘恭之流怪罪于周堪等人,认为这都是其处理朝政不当而引起的。在询问了其他两位官员的意见之后,元帝左迁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三年后,宣帝庙门遭火灾,后又有日食。元帝认为这些灾异意味着先前错怪了周堪等人,又召回周堪。
在萧望之集团与石显集团历时五年的斗争中,灾异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导致了中央朝政的人事变动,不同集团的利益消长。但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灾异说从未指向过皇帝,也与限制皇权毫不相干。与此相反,元帝始终扮演着灾异说执行者的角色,并成为两种大相径庭的灾异解读的裁判者。元帝两次利用灾异——一次地震,一次日食——作为依据来提携萧望之集团。当敌对的利益集团互相指责是对方引起灾害时,元帝不得不选择到底采纳谁的解释更好。其实,元帝本身也并不拥有对灾异解说的绝对裁判权,即便身为君主,他有时也“迫于俗”,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
有趣的是,虽然学者认为灾异说有效地让儒生官员来规劝皇帝,但实际上汉儒认为三公等高层官僚更应该对灾异负责。例如,成帝的大司马王凤在一封奏议中说:“《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蚀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灾异往往成为了君主责备、左迁官员的理想借口。如《韩诗外传》中说:“故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则责之司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在《尚书大传》中也有相同的论述。认定是上层官员的失职而导致了灾害或日食,元帝迫使于定国辞去丞相一职,成帝因此将三位丞相——王商、薛宣、翟方进——依次免职,哀帝也将御史大夫师丹、丞相孔光赶出了权力中心。在这些官员中,就有四位是享有盛誉的儒生。灾异出现时免去高层官员职位,这种做法有时是因为君主需要一个对灾异负责的替罪羊,有时仅仅是因为皇帝对某些官员早有微辞,而灾异的出现恰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上层官员需对灾异负责在汉代已然形成一个传统,所以《汉仪注》明确写着,灾异发生时,丞相应主动辞职。
灾异政治的理论漏洞
一个工具往往在使用时会暴露出其设计缺陷,同样,灾异说在其运用时暴露了其根本的漏洞。从天人感应的道德宇宙论出发,汉代官员以灾异论说政治时,往往诉诸于两组概念。首先,假定“上天”为一个道德主体,他们认为各种灾害和异常现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是对君主不正当的行为和不合理的政策的警告。上天旨意曾经是神秘不可预测,但在这种解说下变成了一个公然不容置疑的道德预警。这意味着对上天的领会不再需要依靠专职于占卜祭祀的神职人员。卜、史等所掌握的关于神灵上天的神秘知识和用于与神灵上天交流的各种礼仪都变得多余。既然灾异是上天对世俗社会的警示,那么只要研究是何种世俗政治引起上天遣送灾异,官员便可以正确地理解“天”的旨意,而对世俗政治的探讨几乎是每个官员都擅长的。由此,灾异曾经被理解为由神秘而超自然的力量所引起,而汉儒将灾异与道德化的上天旨意相等同,并将其和世俗政治相联系,灾异的解说就从对神秘力量的猜测转化为对现实政治的检讨。
在将“天”道德化而解说灾异的同时,汉儒也用阴阳说来论述灾异。其论述遵循相同的逻辑:人世间的活动影响到宇宙中阴阳力量的协调,因而引起灾害或者怪异现象的出现。应对灾异在于找出导致阴阳失调的人或事并对其进行纠正。在这种灾异理论指导下,对灾异的探究也完全着眼于对世俗政治的检讨。
这些简单的灾异理论让官员在解说灾异时,拥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几乎可以随意地将各种灾异联系于其敌对的团体以及不赞成的政策。这直接引发了对同一灾异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
由于灾异说仅仅要求一个简单的应对关系,敌对的利益集团互相指责对方引起灾异时,并不用考虑如何提供严格的理论论述。灾异说的这种灵活性在让官员可以自由批评其对手的同时,也让他们丧失了对灾异解释的权威,从而引起对灾异解说无休止的论争。
为了增加其解释灾异的权威性,一些儒生官员会引用《春秋》等经书。他们希望《春秋》中记载的事件能为当代的灾异解说提供历史依据。但是对《春秋》等经典,汉儒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解释传统。
一些汉儒应该意识到当时灾异说所面临的尴尬情况,于是他们开始对灾异解说的理论基石进行修补,希望能以此统一对儒家经典中所记载的灾异的解释,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传统。例如,借用《尚书·洪范》中的各种分类概念,汉儒逐渐建立起一个系统来归纳各种灾异所应对的政治事件。《汉书·五行志》就总结了这一努力。在这篇文章中,《尚书·洪范》首先被誉为由圣人所创立再由商周时期的帝王所传承的治理天下的蓝图。《洪范》中的三组概念——五行、五事、皇极——被用来整理归类各种灾害、怪异现象以及造成这些灾异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个系统显示了各种灾异征兆与各种失败的政治活动的一一对应关系。这种严格的对应试图消除解释灾异的任意性,但是也限制了解释者用灾异表达政治立场的自由度。而且,《五行志》所提供的灾异解释系统仅仅是局限于将灾异列举归类,但并未提供任何理性的依据。这意味着很少有人严格遵循这一系统来解释灾异。
在建立一个系统的灾异解说的同时,一些汉儒也努力为灾异说建立一个更加复杂精致的理论基础。京房将《易经》融入灾异解说中;翼奉则提出了“六情占”,将六种情绪与日期相联系。虽然京房和翼奉引起了元帝的关注,但是他们的关于灾异的理论在当时未得到广泛的承认,影响力非常有限。
灾异说理论上的缺陷实际反映了汉儒所面临的一个困境。通过取代卜和史等专职的灾异解释人员,儒生们推动了灾异解说的非职业化进程,不过当儒生取得对灾异解说的话语权时,他们同时丧失了由职业化所带来的解释权威。在儒生取代卜、史成为灾异的主要解说者时,我们看到两个变化:第一,儒生成为灾异解释的理想人选,他们所熟习的五经取代了卜、史等占卜人员口授相传的关于各种祭祀占卜的神秘知识;第二,儒生直接进行占卜,观测星象,并把这些官方化制度化的仪式变为了他们个人的兴趣追求。
卜和史以学徒的方式通过口授相传获取其特殊的与神灵交流的知识。他们的权威来源于他们对其专业知识的垄断和在朝廷中世袭的职位。但是,随着经书所记载的关于灾异、神灵等知识的广泛传播,人们不再需要求助于这些专业的占卜人士。人们会认为熟读并传承五经的儒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灾异最具权威的解释者。但事实远比这种假设复杂。不同于卜、史注重垄断其专业知识,儒生追求广泛地传播、教授经学。比如,孔子以诲人不倦、教授学徒三千而闻名。西汉的名儒也广收学徒,据说吴章、龚胜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后生。随着经学的传播和学徒数量的增加,儒生开始强调统一对经书的各种解释,比如创立“师法”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在没有任何机构制度来定义和捍卫一个严格的解释规则的情况下,即使同一学派的学徒对经书也有不同的解释。
汉儒从来没有创立一个公认的标准来判断谁对经书或灾异的解读更具权威。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可以垄断经书及其解释。这意味着对于经书和灾异没有唯一的最具权威的解释,而任何人的解读都可能存在争议。班固认为谷永、杜钦和杜邺的经学知识浅薄,远不能跟刘向、刘歆和扬雄等人相提并论。但是因为谷永等人与权贵的紧密关系,他们对灾异的解读远比刘向等人在当时更有影响力。这一观点也在前述的萧望之集团和石显集团的斗争中有充分表现。刘向是享有盛誉的名儒,他对灾异的解读在东汉时已被当成经典。但是在与石显等人的斗争中,刘向对灾异的解释——即使他旁征博引各种经书——并没有任何信服力,反而让他陷于牢狱之灾。成帝没有采用刘向关于灾异的任何建议,而刘向的对手石显虽然是宦官出身,却成功地利用灾异打击了萧望之、刘向,使他们在元帝一朝彻底失去了势力。
在灾异解说的斗争中,个人的智慧和道德修养,如同熟读经书,并不能增加其对灾异解释的信服力。《左传》宣扬道德水准高的人能够更好地解读各种征兆,但这个观点只是一个不具备任何现实操作性的梦想。实际上,宣称自己的道德水准高于自己的政治对手是一个愚蠢的做法,因为君主并不想被告知他所提拔的亲近是奸佞小人。正如刘向激烈地攻击石显,称其为卑微奸臣,元帝却从来不认为刘向比石显更为贤能。
总结
本文通过将思想史和政治史相结合,论述了汉帝国时期灾异政治的两个悖论。汉儒完善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说,从理论上来看,这种学说能够让官员利用灾异来限制王权。但从灾异说现实的运用上看,我们发现其完全背离汉儒的理论设计,沦落为政治权力的附庸。
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导致灾异说理论和实际运用的巨大偏差时,我们发现了第二个有趣的悖论。儒生成功地取代了卜、史等专职官员成为灾异的主要解读者,但他们成功的原因也直接导致他们丧失了对灾异解说的话语权的控制。儒生利用五经和天人感应学说击败了卜、史等人所掌握的关于与神灵交流的神秘知识,迫使后者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儒生没有建立起对五经知识的垄断,也未能在官僚系统中获得特定的职位来保证灾异说的自主权。这导致天人感应下的灾异解读不仅陷于无休止的论争中,而且成为一个仅仅服务于当权者的政治斗争工具。
汉儒其实也意识到了灾异说所面临的尴尬境地。有趣的是,一方面他们看到灾异征兆的解释经常被人操纵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仍孜孜不倦地提倡一个道德化的宇宙上天以及相关的灾异说。若要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应进一步追溯天人感应下的灾异说兴起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