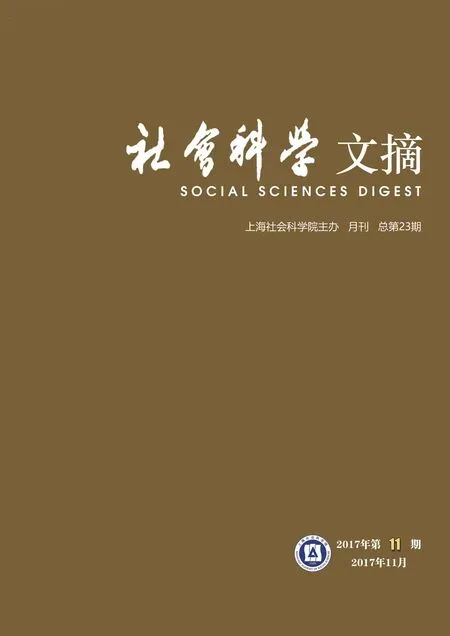中庸之道与意象哲学:中国哲学的重构与诠释
2017-11-23李煌明
文/李煌明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哲学是以西方某一哲学流派(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为理论基础建构起来的。然作为学科之中国哲学与实际之中国哲学,二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和背离。这充分说明中国哲学学科理论重建之必要。对于建构与诠释之关系,一方面,有理论建构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诠释,另一方面,新理论并不是凭空建构而是通过对实际哲学史的诠释来实现,故建构与诠释二者相即不离。因而,对于中国哲学学科之理论重建,关键有两点:一是不能复古,这与中国哲学学科现代化进程南辕北辙;二是不能西化,重建应立足于中国哲学传统自有之哲学观,依其固有之思维方式和问题意识展开,彰显其内在之结构与本来之面目,从而真正揭示中国哲学之特质,展现中华民族之精神。综合二者,便是中国哲学之学科普遍性、现代性与民族性、特质性的同一,书写哲学与实际哲学的相契,此方为本文重构与诠释之主张与思路。
哲学观念与哲学形态
在哲学中总有许多观念,但在诸多观念中有个最核心、最根本的观念——关于哲学自身的观念即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观念,这便是哲学观念亦即通常所说的“哲学观”。任何一种哲学都必定有自己的哲学观,若没有哲学观自然也就称不上是哲学。而且,更进一步地,哲学观如何也决定了这一哲学之特质如何,而对特质之理解与把握又决定了哲学之重构与诠释的好坏。当然,哲学形态亦是哲学特质之一,哲学观亦决定了哲学形态。但无论如何,哲学观与哲学形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如果哲学观是体,那么哲学形态便是用;如果哲学观是微,那么哲学形态便是显。综上,中国哲学的重构与诠释首先要解决中国哲学之哲学观问题,进而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之特质,真正揭示中华民族之精神。
中国哲学之哲学观为何呢?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认为,“哲学即悟道”便是中国哲学之哲学观。但这并非全是孤见独发,如金岳霖之《论道》、唐君毅之《原道》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所谓“哲学即悟道”,就是说“道”不是哲学,只有“悟道”才是哲学。所谓“道”者,简言之,摄贯一切。摄者,一切摄尽;贯者,一以贯之。既然道摄贯一切,故其悟亦摄贯一切。由此,悟道者须一天人,贯古今;彻上下,通内外;合知行,同有无;统本末,摄体用。总而观之,以上所谓道者,莫非叩两端而通其一者。两端者天人、古今、上下、内外、知行、有无、本末、体用;通其一者,中道也,莫非大本与达用也,未发之中与中节之和也。《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故摄贯一切者,中庸之道也。悟道者,悟此大本与达道也,悟中庸之道也。正由此,程朱皆云:“《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具体地说,此“圣人心法”便是十六字决,即《尚书》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心法”者便是存心之要、悟道之法,故亦可视为心道为一之要法也。此要法便是以中和为核心的中庸之道。
在中国哲学中,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名教与自然、有为与无为、圣佛与生众、理性与信仰等等,皆似相反而实相成,是双是双非的圆融一体。《易传·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以意象观之,形而上者,本体之意也,无者也,未发者也;形而下者,形色之象也,有者也,发用者也。意者大本也,象者达用也,故意象亦摄贯一切者,就其质而言亦不外乎中庸之道。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正是对中国哲学精神——中庸之道的写照。由此,中庸之道方是中国哲学之真精神,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价值观,也是中国传统最具特质的哲学观。这一以中道为核心的价值观,在思维上自然体现为“似二而一,似一而二”的圆融特征;在理论结构上便体现为上下、本末、体用的一体性;而在表现形态上又体现为意与象的相即不离。“哲学即悟道”,而中国哲学之“道”正有以上四个特征,故中国哲学之哲学观亦有此四特征:价值的中道性、思维的圆融性、结构的整体性和形态的意象性。由于哲学观与哲学形态的一致性,故以形态观之,其意象性便同时含摄了其余三者,故称中国哲学为“意象哲学”。
本体三性与流行三态
华严五祖圭峰禅师宗密云,水是名而湿是体,心是名而知是体。“愚者认名,便谓已识;智者更问何者为水,何者为心。故闻心为浅,闻性谓深。直须悟得水是名不是湿,湿是体不是名,即清浊、水波、凝流,无义不通。认得体已(矣),方于体上照察义用,故无不通矣。”哲学与本体亦如是,哲学如水心之名,本体似湿知之体。故我们不仅要问“哲学是什么”,更当问本体如何,此谓知其名更识其体。
本体之道究竟是什么?概而言之,超言绝象、离言离相、无形无象。然则此超言绝象、无形无象者究竟为何?对此,只能用《老子》的话答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者,无名而已,谓之“道”已是“强名”。虽然,哲学家们终是要追问,而且终极的追问与致诘,导致具体而不同的回答,这便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如气本论、性本论、心本论,又如普遍规律说、存在意义说、文化样式说等等。同样,我们也有我们的回答:本体之道即本然之意,换言之,本然之意便是超言绝象、离言离相、无形无象者,故可称为“意本论”。
或者换个提问方式,本体之道究竟如何?或称一阴一阳之谓道,或谓无碍即道,或曰彻上彻下、自始至终、一以贯之者方为道。这些回答似皆有所不明:此所问非和合之道,亦非事物之道,而是本体之道,是本然之意,是离相之体。于此,圭峰禅师宗密的真心本体说极富价值与启示,其《承袭图》云:
但云空寂知,一切摄尽。空者,空却诸相,犹是遮遣之言,唯寂是实性不变动义,不同空无也。知是当体表显义,不同分别也,唯此方为真心本体。故始自发心,乃至成佛,唯寂唯知,不变不断,但随地位,名义稍殊。谓约了悟时,名为理智。约发心修行时,名为止观。约任运成行,多为定慧。约烦恼都尽,功行圆满,成佛之时,名为菩提涅槃。
概括地说,本体之道具有三性:空、寂、知。空是空却诸相,是离象之意、言外之意,是本体之道的超越性、形上性;寂是实性不变动义,是至善之意,完满之意,是本体之道的绝对性、理想性;知是灵明不昧,自由自在,是灵动之意,自由之意,是本体之道的灵动性与根源性。就其思想渊源而论,宗密本体三性说与“易”之“一名三义”密不可分,而且“本体三性”与“一易三义”具有内在对应关系。空者,简易也,超越性与形上性;寂者,不易也,绝对性与理想性;知者,变易也,灵动性与根源性。由上,超越性、理想性与灵根性便是本体三性,亦即本然之意或意之本体或本意之内在规定性。此虽为有限之三,然万事由此出,万变自此化,万物源此根,悉在此中,无出其外,无所不包,故曰“一切摄尽”。
此空-寂-知三性便是“三点”,是道体之性能,是本意的三个本质规定性。那么,其内在结构如何呢?在此,我们不妨借用佛家用语,将其内在之结构功能与思维方式称之为“圆伊三点”,也即举一含三而即三即一。所谓“举一含三”便是三者相参相摄,相通相倚,互为体用。举空者,寂知同在;言寂者,空知俱存;论知者,空寂共摄。以任一为体则其余皆为其用,此即所谓“自性本用”,所谓“叩两取中”。“两端”者,虚实也,寂感也,方圆也;通而为一,故曰“中道圆融”。由圆通故,虚则实之,实而不固;实则虚之,虚而不空。动则寂之,寂而能感;寂则动之,动而有则。圆则方之,方而不滞;方则圆之,圆而不流。
由前所论,本体之道与本然之意,具有空寂知三性即超越性与形上性、绝对性与理想性、灵动性与根源性。正因本体之道与本然之意具有灵根性,自由自在,自然灵明,故生生不息乃其固有之用,由是而为万物之宗,万化之根。由是阴阳交感,天地絪蕴,大道流行;由是本然之意,变化贯通,真妄生焉,善恶形焉,吉凶定焉。
尽管对大道流行变化之过程,在不同哲学中或有具体之差异,但总体而言,其共通之结构似无外乎《周易》之意—象—言。如孟子之天—性—心,张载之虚—气—物,朱熹之理—气—物,阳明之心—意—物。由此,意—象—言,便是道体大化流行之结构。无论这个过程如何、阶段如何、变化如何,无非都是此道一以贯之。流行变化只是本体之道、本然之意随时位差异所表现出的不同相状,由此意、象、言便是道之三相、意之三态。意者,道之本;象者,道之显;言者,道之彰。大道流行,气以显之,形以彰之,缘本达用,自幽而明,由微而著,渐形渐固。简之,莫非体用显微、未发已发,两端而已;合之,则一以贯之,一源无间。故统天括地,只此中庸之道,只此本然之意。
大道流行,生意盎然,气象显之,形色彰之,万物散殊,五彩缤纷。以相观之,道有三相:超越相、和合相与形色相。以形分之,超越者与和合者,道之形而上;形色者,道之形而下。以有无观之,超越者,道之无;形色者,道之有;和合者,有无之间。意即道也,与之相应故,意亦有三态:本然、或然与定然。本然者,无动无静、非阴非阳、无善无恶、非吉非凶;或然者,亦动亦静、亦阴亦阳、能善能恶、可吉可凶;定然者,动而无静、静而无动、定善定恶、成吉成凶。
大道之开显与历史之演变
道不自鸣,假人而鸣。道不是哲学,只有悟道、鸣道才是哲学。若不悟不鸣,则道自道而人自人,此谓日用而不知者。故所谓“大道之开显”不仅是指大道之流行发用,更是指通过悟与鸣而得以展示和显现。其道虽一,其鸣不同。古今上下,其道一也,其所异者,则悟也,鸣也,各人所悟所鸣不尽相同。道何以得而鸣?由言行而鸣也。悟道者,得于心而成于行也。故鸣道亦即悟道。故悟道之殊便是哲学之异,于是便有了中国历史上诸多各具特色之哲学。这些各具特色、各不相同的哲学依历史的发展而自然排列,便构成了实际的中国哲学史,此即实际的“历史之演变”。
理不自喻,藉言而喻。作为一门学科,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却有个复杂的问题——如何叙述,具体而言有两方面:一是讲什么,二是如何讲。但是,这二个方面又回到了叙述者的哲学观上:叙述者认为“什么是哲学”,以此为依据决定讲什么和如何讲。换言之,叙述者总是根据自己所解、所悟来叙述中国哲学史。故叙述既是诠释,更是重构。好比自然之道只是一个,但各人所悟之道却不尽相同。同理,实际的中国哲学史只是一个,但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则只能是各人所悟者,故而各不相同。故曰,道虽为一,其理不同;理虽可一,其言固异。
由上,叙述者的哲学观,便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他所叙述之哲学史的内容与结构。正由此,我们说叙述便是重构与诠释。回顾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最重要的莫过于冯友兰以他所理解和接受的哲学即他的哲学观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虽也论及中国哲学特别之精神与表达之方式,但仍然不出西方哲学之总体结构即本体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其晚年则换了一种哲学观,以马克思主义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写成了《新编中国哲学史》。此两种中国哲学史之叙述,观点多有不同,可见哲学观对于叙述之影响。因此,后人在重新编写中国哲学史时,应该先反思一下:自己的哲学观是什么。
本文提出,哲学即悟道是中国哲学之哲学观,而意象哲学便体现了笔者之哲学观。由此出发,中国哲学史又该如何叙述呢?
其一,叙述原则。简言之,叙述原则有三:民族性、时代性与学科性。民族性就是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必须遵循和体现中国哲学之特质;时代性就是中国哲学史各部分之叙述必须遵循和展现时代的脉动;学科性是指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而言,其叙述还必须有学科之标准与专业之共识,这种标准与共识至少包括了理论化与系统化,做到有论有据,结构严谨,思路清晰,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等。
其二,叙述之任务。叙述的展开也就是道体在历史中的开显,这种开显是通过叙述而展现的。由前论,道体依时位之不同而展现出各异之相状,而这也就是书写哲学之“历史演变”体现出哲学的时代精神。由此,叙述之任务有二:首先,遵循和体现哲学即悟道这一哲学观,紧紧围绕“悟道”这一核心与宗旨;其次,在阐明先贤所悟之道的前提下,还应注意时代的特殊性与演变的内在逻辑性。
依以上原则与任务,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似可作如此展开:天人之道—王霸之道—政治之道—玄同之道—圆融之道—圣人之道—常变之道。此处自然不能一一展开,只能蜻蜓点水。天人之道如西周天人合德;东周王霸之道,诸子百家皆是,然有显隐之分,如孔孟仁礼中和,老子玄同有无、庄子有用无用之间;秦汉政治之道,如荀子、韩非皆应属此,汉则以儒为主而兼容道法,以易之一名三义为最;魏晋南北朝玄同之道,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彷徨,寻找得以安身立命之由,以《起信论》一心二门为高;隋唐圆融之道,此圆融不仅是佛家各宗派之圆融,亦是儒释道三家之圆融,表现出盛唐雍容之气象,以宗密思想为代表;宋明圣人之道,其旨皆在“立人极”,何者为圣、何以成圣是整个社会之主流,以阳明思想为极;自清后期直至当下,皆属常变之道,虽变革是社会的主流,但如何以中庸之道正确地处理好常与变的关系就成为关键所在,特别是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开放性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工作,在完成之前难免因循和猜想。
此外,我们还必须明了的是,就书写的中国哲学史而言,所阐明的是古圣先贤所悟之道而不是论述叙述者自己所悟之道,故而哲学史是“无我”的。然而这仅就内容之表面看。但是能真正理解、诠释并叙述诸多古圣先贤所悟之道者,至少说明叙述者已悟古圣先贤之所悟,故而叙述者亦是悟道之人。由此,一个能真正理解哲学史的人是一个有哲学观的人,而他对哲学史的诠释、叙述与重构能且只能依据他所具有的哲学观。故而一本合格的哲学史背后与深处不仅“有我”而且此“我”才是其真正的灵魂,是“真我”。至于叙述者所具有之哲学观是他人所创还是其自己独创,都不影响哲学史叙述背后的“真我”。
于此,可以宗密之语作一总结:或以有我为妄,无我为真;或以有我为真,无我为妄。至道非边,了义不偏,不应单取,故哲学史既是无我,也是有我。至道归一,精义无二,不应两存,故哲学史是无我法中有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