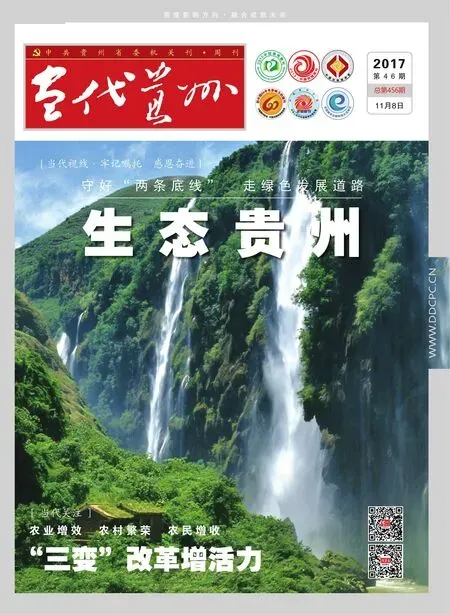宴会、戏台与影堂:墓葬中的生死
2017-11-22李飞
宴会、戏台与影堂:墓葬中的生死

李飞
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海龙屯考古工作站站长。长期致力于中国西南考古,研究成果曾多次获贵州社科成果奖,2016年5月获中国考古学“金爵奖”。
赵王坟石刻表现的,是后龛中的墓主正在接受乐舞、美食酬献的情景。反映了宋元明时期,包括播州土司在内的社会上层宴饮作乐的社会风尚。生死之间,既相互隔离,也彼此相通。
1957年春,贵州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遵义皇坟嘴发掘了播州杨氏第13世杨粲夫妇的合葬墓。与此同时,在隔河相望的赵家坝也清理了一座古墓,当地人称“赵王坟”,这是一座夫妻合葬的双室石墓。由于发掘内容至今没有完整公布,其年代一直存在宋、元、明三说。近有证据表明,这是明初去世的杨氏某代土司夫妇的合葬墓。
两个墓室均呈长方形,左、右、后三壁带壁龛,内饰浅浮雕的场景性画面,以减地壸门作为画面外框。女室后龛石刻未见存于贵州省博物馆,不知所终。男室后龛中央置空椅一把,其左右两侧各立三男子,均戴笠子,着长袍;其中近椅处二人,居左者捧印盒,居右者持笏囊;其余均袖手而立。这是一组反映墓主人及其侍者的图像,推测已佚的女墓后龛石刻应与之相同,空椅暗示了墓主的在场。男女墓室左右两龛的题材一致,左雕乐舞,右为奉食。区别在于男墓刻男子,女墓为女子。人物皆处在形如戏台的回廊下(或为勾阑),作面向后龛的墓主人像徐徐行进状。男墓左龛男子九人,所奏乐器可辨者有琵琶、拍板、笛和胡琴(状如琵琶而略小,但隐然有弓,应为拉弦乐器)等。女墓八人,奏琵琶、笛和笙等;前导一人手持曲首杖,上有羽状装饰,应即《宋史·乐志》所谓“执麾人”。奉食者皆十人,所持之物,可辨者有壶、盒、盏等,反映奉食、供酒与茶的场景。
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引用了女墓左右龛石刻拓片,总称其为“遵义宋墓宴乐歌舞浮雕”,分别是“宴会婢仆”与“女乐”。
墓主人像、乐舞图和奉食图,是宋金元时期墓葬中的常见图式,宴会时佐以歌舞、杂剧,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多见。宿白先生在其名著《白沙宋墓》中引此记载,将白沙1号宋墓中夫妇对坐图和与之对应的散乐表演视作一个整体,释为“开芳宴”。这被此后的研究者广泛沿用,释其系流露出墓葬营建者模拟现实宴饮空间的强烈意愿,因此是墓主生前娱乐的写照或供其死后享用。但也有意见认为这是民间葬礼中“乐丧”的延续,是将一次性的葬仪凝固为静态的、永恒的存在。
赵王坟石刻,刻画出与宋人周密《齐东野语》所记时人张镃举行牡丹会时“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类似的情景。它与宋金时期流行于中原北方地区的“开芳宴”有一些相似处,但墓主夫妇并非对坐,而分置于各自墓室的后龛中。后龛人物,处在三开间的厅堂中,是整组墓葬画面的中心。左右两龛,按理应为厢房,却呈现带有连廊的戏台样式,亦即宋元时代戏曲表演的场所——勾阑。这并不是常见的戏台应处的位置。论者因此对“开芳宴”的解读提出质疑,这样的空间配置,显然不是为了观看戏台中的演出,而是戏台中的演员正准备上演酬神的剧目,墓主夫妇则在献殿恭迎神灵的到来。如果赵王坟左右壁龛的建筑确为戏台,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是其所处的位置并不便于后龛的墓主观看,二是乐舞表演在戏台内进行尚可理解,奉食的场景在戏台出现当作何解?因此,这组画面反映的也许并非墓主夫妇在宴饮、赏戏的情景,而与侯马董氏墓一样,是酬神场景,或丧葬场景的模拟与再现。
墓葬营造出的似是一个祭祀性的礼仪空间,是一个地下的影堂。影堂即是存有祖先画像的祠堂。遵义宋墓中,有铭文将墓室称为堂者的并不在少数。赵王坟石刻表现的,是后龛中的墓主正在接受乐舞、美食酬献的情景。而这一切,是在戏台这一礼仪性的空间展开的,宛若地面影堂中生者对逝者的祭献,应非一场生时宴会的再现。但它也反映了宋元明时期,包括播州土司在内的社会上层宴饮作乐的社会风尚。生死之间,既相互隔离,也彼此相通。
(责任编辑 / 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