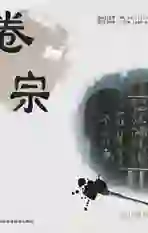唐剧戏曲表演的意境美思考
2017-11-20赵璐
赵璐
摘 要: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关于它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现在一般认为,它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具有虚实相生、意与境谐、深邃幽远的审美特征,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情感上受到感染”。
关键词:戏曲;表演
1 以虚带实、以形传神的写意化
盛唐诗人王昌龄在《诗格》明确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其中对“意境”的解释是“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晚唐诗评家司空图在《诗品》中,谈论到雄浑类诗歌的意境时候,也明确指出“(意境)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概括起来,意境的形成是诸种艺术因素虚实相生的结果,是特定的艺术形象(实)和它所表现的艺术情趣、艺术气氛以及可能触发的丰富的艺术联想及幻想形象(虚)的总和。[1]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古代文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所以中国古代的诗论和画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上面所述,诗的虚境和实境,可以从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上获得更形象的理解。
一方小舞台,一出小戏,如何才能展现万千世界、古今中外呢?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西方戏剧结构理论提出“三一律”法则,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上保持一致性,正如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所说的“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中国传统戏曲却不受“三一律”的局限,舞台的时空可以自由地变换。首先,在时间上,既可以是白天,也可以是黑夜;既可以是把十年八载压缩为几分钟,也可以把几秒钟的思想冲突拓展到一场戏。例如,《水浒记》的《坐楼杀惜》一折中,宋江在黄昏时候,遇见阎婆,进入乌龙院会见阎惜姣。由于被阎婆反锁房门,由深夜到五更天,宋江与阎惜姣都是一直各怀心事,互不理睬地闷坐、闷睡。直到黎明天亮了,宋江才开门下楼。阎惜姣藏起宋江留下的招文袋,宋江转身折回索要招文袋,阎惜姣坚决不肯,宋江唯有翻脸杀惜了。这一折戏囊括了杀惜前日的黄昏、深夜,到杀惜当日的黎明时,由此可见,戏曲的舞台是非常自由灵活的,横跨度可以非常大。其次,在空间上,既可以是千军万马的战场,也可以是花红柳绿的后花园;既可以是守卫森严的皇宫官邸,也可以是淳朴寻常的百姓人家。
2 表演的写意化
焦菊隐先生曾明确指出,西方戏剧是“从布景里面出表演”,而我们传统戏曲则是“从表演里面出布景”。从上可知,无论是时空的写意化,还是道具的写意化,归根到底都离不开表演的写意化。例如,昆曲《玉簪记》中“秋江”一折、《渔家乐》中的“藏舟”一折等,都需要演员“以桨代船”的演出。扮演艄公的演员需要充分利用手中的一支船桨,虚拟划船的动作,让观众感觉到舞台是在河中,正有一叶小舟独行江中。手上没有任何道具代表舟楫的其他演员更是需要通过表演,把“无形”、“虚化”的河水和船只表现出来。譬如跳上船,演员要及时地做出船身摇晃的动作;途中或是风平浪静,或是乘风破浪,演员都需要用动作一一虚拟出来,让台下的观众看到“河面”的情况。
在更多情况下,演员手上是没有任何道具的,纯粹靠着已经程序式、舞蹈化的身段来展示写意化的表演。例如,豫剧的《抬花轿》靠的就是演员扎实的脚底功夫,把人在花轿中,途经上坡、下坡、跳沟、过滩、急转弯等情景给逐一展现出来了。。类似的虚拟表演,还有“上马下马”、“开门关门”、“上楼下楼”、“穿针引线”等。戏曲演员进行虚拟性表演的时候,首先必须要准确。正所谓“艺术来自生活”,虚拟性的表演完全脱离了生活的原型,观众也会看不懂,更不会产生共鸣。要求准确,并不是照搬生活,一成不变,艺术更需要“高于生活”,将戏曲表演艺术美化、写意化一点,也就是戏曲口诀中所说的“藏拙露秀”。例如,悲伤的哭,不需要涕泪满面、声嘶力竭,只要用水袖虚掩一下脸面即可;生病了,不需要蓬头垢面、连声呻吟,只要头巾包扎一下头即可;睡觉了,不需要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只要手托腮帮假寐即可;喝醉了,不需要丑态百出、真的呕吐,只要将醉态展示出来即可。譬如,“卧鱼闻花”,已经把杨贵妃醉酒的神态舞蹈化、美化了;又例如,拥抱、接吻等动作,在戏曲舞台上是不必要直接模拟的,只需要相互搭肩便表现了。
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情节,中国传统戏曲总结了许多程式性的表演技巧,如甩发(又称“甩梢子”)、耍髯口(又称“口条”)、耍帽翅、耍水袖等。例如,“耍水袖”可以用“勾、挑、撑、冲、拔、扬、挥、甩、打、抖”这十个字归纳起来,使用的力度不同,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用以不同情节中的不同人物性格。
3 情景交融、言盡而意无穷的诗意化
作为“剧诗”,中国传统唐剧戏曲的意境论,自然是来自诗歌的意境论,因而戏曲的意境构成和诗歌一样,也是由情与景两个方面所共同构成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总不出‘情、‘景二字,景书所睹,情发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3]。一加一等于二,但是意境美的产生,并不是“情”与“景”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内在的“情”与外在的“景”进行高度的完美融合,达到李贽所说的“化工”境界。
我们知道诗词和绘画都仅仅是一种平面的静态欣赏。与诗词、绘画相比,中国传统戏曲的意境美还具有立体的动感,因为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除了有剧作家的文本创作外,还有演员的舞台表演。由此可知,戏曲的意境不仅有剧作家的一度创作,还有表演艺术家的二度创作和真切演绎,让观众有一种亲临其境之感,眼前的意境美是直接的、立体的,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正如潘之恒在《鸾啸小品》中谈到“余十年前曾见此记”(《牡丹亭》),虽然被剧中之情所触动,但是直到看到丹阳“太乙生家童子”的演出,始为“赏而为解”。
正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中国传统戏曲对演员的基本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概括起来就是“四功五法”,“四功”即是“唱、做、念、打”,“五法”即是“手、眼、身、法、步”。其中特别是“唱”功在中国传统戏曲的抒情方面则显得尤为重要。“戏无情不感人,戏无技不惊人”,作为剧诗的戏曲的意境之美,基本上体现在演员真情演绎的唱词上。面对莺歌燕语、“烟波画船”的春色,杜丽娘不是悠然地陶醉其中,而是触景生情,独怜孤影,感慨万千———“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无限春景,只会加倍地刺伤杜丽娘的“伤春”之痛。唱词中的景和情,已经难以各自分离,景中带情,情中有景,并引导着观众思考更深邃的人生哲理,达到一种“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令人回味的诗化境界。
除了上述唐剧戏曲的局部唱词之外,戏曲的整体,特别是结尾的地方,同样也可以给人们一种言尽而意无穷的诗意化。综上所述,脱胎于中国古典诗歌国度的传统戏曲,无论是在语言、表演,还是在题意的表述上,都洋溢着诗的精神,与生俱来就带有一股意境美的“诗气”。中国传统戏曲的意境美,不仅体现在诗一般的案头剧本上,而且展露在诗一般的舞台表演中。每一次传统戏曲的上演,都给人一种古典诗词的意境美,这种美是无穷无尽的,也是缤纷多彩的。
中国传统唐剧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一直在中华大地的舞台上展露这份独具意境美的魅力。在戏剧的大家庭中,戏曲有着独立的地位与审美价值。对于中国传统戏曲表演艺术的意境美这一个论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大家进一步探讨,限于笔者水平有限,搁笔于此,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