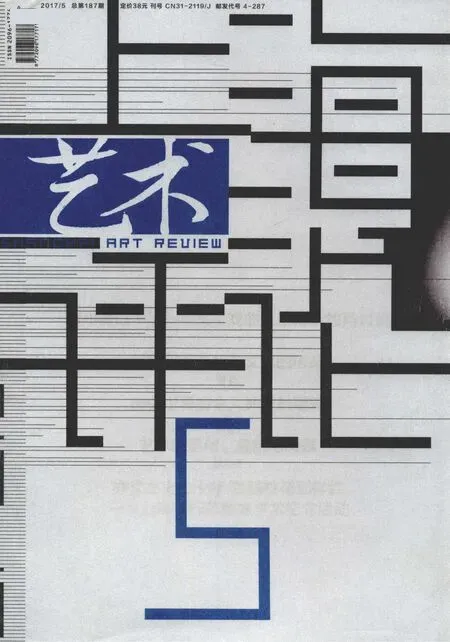《村戏》:沉静而质朴的历史表达与人性拷问
2017-11-20龚金平
龚金平
《村戏》:沉静而质朴的历史表达与人性拷问
龚金平
《村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让这种离散性的力量无限蔓延和不加节制地滋长,而是用一个历史变革的巨大隐喻完成了几条情节线索和意义主题之间的有限缝合。在今天浮躁而功利的商业化潮流中,郑大圣这部质朴得有些“寒酸”的影片不仅是一股清流,更是一部回归初心之作,它回归了电影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对于人心人性的沉静思考,它回归了电影创作者最真诚的自我思考、自我感动、自我表达。
《村戏》(2017,导演郑大圣)的情节框架一度让我想起魏德圣的《海角七号》(2008),即聚焦于一群普通人排练艺术节目所发生的种种冲突、调和,以及众人在排练完成之后所发生的改变。但是,从影片选用黑白色调、原生态演员和粗粝荒凉的环境来看,导演显然想追求一种冷静犀利的历史穿透力。从情节内容来看,《村戏》又与管虎的《杀生》(2012)有惊人的相似,讲述一群人如何放逐一个“不合规矩”之人,折射一个族群的群体意识和潜藏的人性心思及人性的复杂面目,但《村戏》分明还有其他几条情节线索。此外,《村戏》一开始就交代80年代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语境,又让我想起《高考·1977》(2009),也是表现历史变革前夜的躁动与焦灼,以及这场变革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命运深刻的影响。但《村戏》中的这场变革对于个体境遇改变最大的是疯子王奎生,对其他人的影响尚未呈现。
《村戏》至少糅合了四条情节线索,彰显四个意义走向:疯子王奎生因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和利益,被全村人或阴暗或公开地放逐(人性的自私、阴暗、冷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时代性的巨变,将产生农村新的经济、政治结构和生态,将对村民的生活与命运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个体在历史风云中的命运轨迹);为了在大年初二完成《打金枝》的戏曲演出,鹤叔趁机要挟村支书,不仅要保证个人利益最大化,还要强行拆散女儿小芬与树满的恋情(人性的贪婪与残忍);王奎生当年误杀了女儿彩云之后,被村里包装成保护集体财产先进分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历时十余年,他沉浸在自责与忏悔中,无力自拔(特定历史境遇对于正常人性人情的扭曲)。
《村戏》的情节内容和主题表达极为饱满而丰富,构建了多个维度的阐释空间,但是,影片也面临巨大的表达风险,即由于几条线索之间意义缠绕且相互间关联不大,可能导致每一条线索和每一个主题的完成度都受到牵制和削弱。例如,影片从开头就铺垫那场《打金枝》的演出,中间鹤叔也一直率人准备,但最后不了了之,这从情节安排和满足观众的观影期待来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从情节篇幅来看,“放逐王奎生”占了主要比重,导演郑大圣在试映会的现场交流中也强调,他的初衷是要表现一个族群与个体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但其余几条线索毕竟也十分出彩,难免对观众产生强烈的暗示与潜移默化的引导,导致影片的情感力量和思考深度有涣散之感。
但是,《村戏》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让这种离散性的力量无限蔓延和不加节制地滋长,而是用一个历史变革的巨大隐喻完成了几条情节线索和意义主题之间的有限缝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看起来只是一次土地改革,但其背后折射了一种巨大的时代变迁和乡村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一个集体主义的时代(有限地)步入个体主义的时代。更具体地说,那种高度整一化的社会结构板块正在松动、破裂,并分裂成一个个更小的碎片(家庭)。在这种社会性的变化中,人的价值立场、思考方式、生存方式都会发生重大改变。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意识到《村戏》几条情节线索之间内在的联系性:当空洞的“集体利益”和“集体意识”被消解之后,许多以前不以为然或者无足轻重的利益突然变得具体而尖锐。反之,许多以前认为重于泰山的价值瞬间觉得轻于鸿毛。在集体经济时代,九亩半良田可以任由疯子占着,集体可以“无怨无悔”地养着疯子,鹤叔也可以任由小芬与树满有限接触,但在“个体经济”时代,人性的自私就会暴露出来,并产生强大的破坏或建设性力量。如鹤叔,他一直对小芬与树满“郎情妾意”心存不满(树满的父亲就是王奎生),但从集体荣誉出发(小芬和树满可以代表全村去参加文艺汇演),且集体经济可以保障树满一家的生活,他未加干涉。知道即将土地改革之后,鹤叔马上对这场婚姻有了更加实际的利益考量(树满不会做农活,母亲身体不好,父亲还是个拖累;反之,志刚身体强健,干活是把好手),于是,鹤叔“以权谋私”,棒打鸳鸯。而王奎生当年为了集体的利益(领到救济粮),违心地压制失女之痛和强烈的自责,加重了他的精神创伤并终至疯癫,这在以前看起来是一种义举,但在“个体经济”时代就显得荒唐而可悲,不再被村民赞赏或理解。

电影《村戏》
因此,导演郑大圣将《村戏》的主题概括为“族群与个体之间的对抗关系”略有偏颇,是对影片丰富内涵的自我阉割。准确地说,影片是表现历史变革对于个体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命运的深刻影响。只不过这种“深刻影响”更多地不是从外在可见的命运转折或生命毁灭的角度来呈现的,而是从更为隐晦却更加根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来凸显的。应该说,影片对于历史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而敏锐的切入角度,同时也在看似幽默、荒诞的氛围中为今天的观众提供了观照历史、反思人性的契机与通道。如果影片能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更为准确全面的解释(从集体经济走向个体经济),能对几条线索之间的关联作更为自然的勾连,能对几条线索的篇幅、比重有更为合理的安排(可以将叙事重心放在全村人对于王奎生的态度变化上,并大幅度删节王奎生的回忆部分),影片的思想穿透力和主题表达的自然性将有明显的提升。
从影片的影像风格来看,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灰扑扑”的氛围。这种氛围的营造一方面来自于黑白影像所带来的那种冷峻而质朴的低调内敛,也来自于那些富有生活质感的细节、话语、空间造型,更来自于人物那些源自身份、性格所自然生发的言说、行为方式。尤其影片刻意选择北方农村冬天的场景,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没有任何生机,有着死寂般的荒凉。但是,当人物出场时,那种泥土般的生命热情依然扑面而来,尤其王奎生出场时,伴随着晃动摄影,快速剪辑,撑满画面的音效,以及必然带来的暴力和追逐、奔跑场面,显得动感十足。这实际上也完成了对影片内涵的另一种曲折表达:这个一成不变,看起来死气沉沉的空间,将会由某种搅动性的力量产生动荡不安的变化。
从我的私心出发,我希望影片能全程保持这种粗粝得近乎蛮荒的摄影风格,因为这样才能制造形式与内容的强烈反差:单调乏味的空间与激荡起伏的人情百态的和谐共存。因此,我对影片在王奎生的回忆部分刻意强调高度饱和的绿色与红色十分不解。在这些回忆场景里,只要不是红色和绿色的部分仍然是黑白色调,这显得十分怪诞。或许,这种怪诞符合王奎生作为一个疯子的心理感觉和主观感受,但这实际上破坏了影片所打造的一种“气韵”,一种对生活近乎原生态还原和自然主义表现的自我克制。
在试映会现场,郑大圣导演对突出红色与绿色的解释是,他对那个时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两个颜色,他似乎想用这两个颜色来指称那个刻板单调的时代。这个解释其实十分牵强,但却意外地在导演的感性选择与人物的情感逻辑之间产生了一种巧合性的重合。因为,王奎生对于那个伤痛时刻记忆最深的就是碧绿的花生地以及女儿彩云身上的红色褂子。这两个颜色伴随一种灼痛感成为王奎生回忆往事时的强势符号,并使他此后的人生了无生趣。即便如此,从影片的整体风格和艺术表达的克制来说(《辛德勒的名单》就在黑白色调中只对那个红衣小姑娘有惊鸿一瞥的表现),这些过度饱和甚至泛滥的红绿色对于影片的色调语言仍然是一种突兀甚至破坏性的存在。
不得不承认,在今天浮躁而功利的商业化潮流中,郑大圣这部质朴得有些“寒酸”的影片不仅是一股清流,更是一部回归初心之作,它回归了电影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对于人心人性的沉静思考,它回归了电影创作者最真诚的自我思考、自我感动、自我表达。仅此一点,《村戏》就值得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作者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