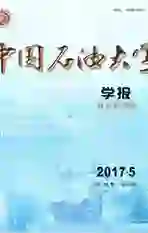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农民告状故事
2017-11-16卢军
摘要:新锐作家张继的长篇小说《去城里受苦吧!》通过讲述村民牛贵祥因征地纠纷被迫状告村长李木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下鲁南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权大于法”的观念仍在根深蒂固地左右着许多农民的思想;个体权利意识淡薄的农民习惯于服从行政指令;农民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直接影响了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因此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小说还表现了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深刻变化的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张继;《去城里受苦吧!》;农民;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5007205
新世纪以来,山东新锐作家张继先后创作了《村长的耳朵》《人样》《去城里受苦吧!》等乡土小说。作者擅长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乡土社会,小说叙事重心多为鲁南乡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事和平凡琐碎的生活场景。在他的笔下,乡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联系着乡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从而具有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联系着人性的细微变化从而具有文化意义”[1],真实地揭示了当下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其中,200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去城里受苦吧!》是在其中篇小说《告状》的基础上扩写的,通过讲述村民牛贵祥因征地纠纷被迫状告村长李木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并探究了农民进城谋生后的身份问题,是一部富有当下意义的力作。
一、“权大于法”观念在乡村的根深蒂固
中国自1986年开展全民普法活动以来,近三十年的普法教育使大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广大农民法律意识仍相对薄弱,“当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突出表现为轻法意识、畏法意识、无讼意识、伦理意识、清官意识等”[2]89。几千年封建文化和专制强权统治使“权大于法”的思想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左右着许多农民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法律的权威根本无法和政府的权力相提并论,对法律不信任的心理态度使他们很少采取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运用法律武器诉讼维权相比,农民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心目中的包公、海瑞式的“清官”身上。
长篇小说《去城里受苦吧!》中村民牛贵祥的二亩好地被村长李木卖给开饭店的商人还村里的外债了,而且事先连个招呼都没给他打,这关系到日后生计和脸面的双重问题,忿忿不平的贵祥在妻子和乡邻怂恿下,放出口风要告状。贵祥起先压根没打算真告,这是“避讼”思想作祟。在封闭、保守的乡土社会秩序中,亲情、乡情在农民潜意识里占据重要位置,农民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宁可委曲求全,选择私了和忍让。打官司、法律诉讼对多数百姓来说是件极不情愿也是万不得已时才采取的解决办法。所谓“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这句俗语即是这一国民心态的反映。贵祥放出风去要告村长时已打算好,如果李木给他道歉并补偿他一块质量令他满意的地的话,他就不告了。贵祥想:“毕竟在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去告谁都不是一件好事情,况且,也是主要的一点,李木还是村长。”
但村长压根没把老实懦弱的贵祥放在眼里。为维护自己的面子,贵祥被迫假戏真唱,踏上了告状之路。牛贵祥先到乡政府告状,他在路上打定主意:“他一不能去派出所告,二不能去法庭告,派出所和法庭都跟李木有一手,他才不去上那个当呢,他要去政府告。”在镇长李向圆处碰壁后,贵祥又进城找市长伸冤告状。他在市政府大院门口向站岗的武警打听市长在何处办公。武警得知贵祥是来告状的,让他离开市政府去法院。贵祥一脸不解地说:“我是来找市长的,干吗去法院?再说我这事太大,法院也办不了,离了市长怕也是不行,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贵祥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市长身上,渴盼市长就是能为他主持公道的“青天大老爷”,“市长他是在电视里见过的,胖胖的,很和蔼的样子,他觉得只要能见到他事情就好说了”,想法真是简单至极。“事实上,历代对明君贤臣的歌颂,归根到底,都是对制度的否定;历来老百姓对‘清官的期盼,实际上都透着浓浓的对法律不信任的情绪。”[2]90正是受“清官情结”的影响,贵祥把一个本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土地补偿问题,变成了上访问题。
当下基层农村执法活动仍存在着少数执法人员执法不公、官官相护滥用执法权等不良行为,也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造成农民对法律的不信任。如贵祥想用告状吓唬村长老婆王学花,王学花听后忍不住笑了,问他“打谱到哪里去告?”,贵祥说“到派出所,到法庭”。王学花告诉贵祥,村长今天一大早就被派出所的李所长和法庭的杨庭长用车接走喝酒去了,“李木也早就知道你要告他的事,他一点不害怕,他不光不怕,说这事的时候还笑呢,他说派出所和法庭的一大帮人,整天都被他喂饱了,一直没有人告他,还没有发挥过作用呢,他正想借你这事试一试,看看他们的关系到底灵不灵,你想想你能赢吗?”贵祥听后尽管嘴上不承认,但是心里对告状的信心几乎一点都没有了,从村长家往外走时“两只脚有些发飘,他一点也不想飘,可是不由自主”。当不久后村长问贵祥是不是还想告他,贵祥说“不告了,告什么告”。李木說:“你也别客气,该告就去告。我今天跟李所长和杨庭长在一起吃饭,说起你的事,他们都说真打起官司来,说不定你会赢呢。”贵祥赶忙摆手说:“我怎么会赢,我要赢了我就是村长了。”法律威力和官员权力在贵祥心中的地位孰高孰低显而易见。
二、农民个体权利意识的淡薄
小说《去城里受苦吧!》中村民牛贵祥告村长是一起民告官事件,本应理直气壮的贵祥却在告状过程中畏首畏尾,皆因官贵民贱思想、服从意识仍在他脑中占据上风。在当下农村社会生活中,一些基层官员习惯于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管理农民,民主意识、个体权利意识淡薄的农民也习惯于接受这种管理。长期养成了服从权力的心理习惯,权利意识淡薄,习惯于服从行政指令。
在诸多新时期乡土小说中,村长们作为乡村政权的代言人,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村民对其只有俯首称臣。一旦有人试图反抗,他们都会给予沉重打击。与强势的村长相对应的是软弱无助的村民。在相对封闭的乡村世界里,他们首先懦弱地臣服于村长的权威,逆来顺受,丧失了个体的尊严。面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正的事件,从无反抗的勇气。其次他们又都是权力秩序的自觉维护者,任何反抗者都被视为异端,面临集体舆论的围剿。endprint
《去城里受苦吧!》前半部分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村长李木在村里的权威和牛贵祥等村民对他的惧怕。如秋天收玉米时,贵祥有一块地在公路边,当时玉米还未熟,镇上为了赶进度,非要贵祥把玉米提前收了,贵祥坚持不收,与镇上一班人闹僵了。有人就把村长李木叫来了,李木老远就骂:狗日的贵祥,反了你了,镇长的话你都不听,你还想活吧。“贵祥的腿就有点软了,他不太怕镇长,却怕李木,镇长只是偶尔见了一次,村长却是每天都长在他头上,就把玉米收了”。李木在村里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由此可见一斑。
贵祥状告村长李木完全是无奈之举,大有被逼上梁山的意味。贵祥放出告状的口风后看村长毫不理会,按捺不住到村长家试探,李木一见他就训斥:“贵祥,你的胆子不小啊,我听说,你要告我。”贵祥慌乱地否认。李木说:“你那边说完,我这边就知道了,你想想,在这村里还有我李木不知道的话?你就是在床头说的话,我都能知道,瞒不了我。”贵祥又连忙承认,并说只是说说而已,“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告你,我只是想弄清楚那點地”。继而讨好地解释说:“村长,你看你说的,这村里的地都是你的,你说卖就卖,你说不卖就不卖,我能有什么意见。再说,我有意见也没有用,是不是村长?”李木追问既然没意见为啥还到处说要告他?贵祥赶紧陪着笑说:“别的意见倒没有,只是那么好的地,卖了怪可惜的。” 在强势的村长面前,贵祥话语谦恭、处处讨好巴结,使人感到悲哀和无奈。为了生存,他根本无暇顾及什么人格和尊严。
李木提出在村西再划给贵祥二亩三分地。但村西的地没有水,土层也薄,一遇上旱天就完蛋了,二亩三也赶不上村东的一亩,贵祥觉得不合适,提出要是村西的地就补给三亩。李木听后大为光火,说“二亩三也不给你了,我要你吃亏吃到底,只给你二亩,这地种呢,你就种,不种就散”,还说,“大不了你去镇里告我”。为了感动李木,让村长改口多补给些地,软弱的贵祥开始不停地为李木家干活,殷勤地给李木擦拭自行车、打气,还主动招认告状是受他人蛊惑,“村长,我刚开始就给你说了,我其实不想告你,都是他们……他们鼓动我,他们……真的,我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李木对“他们”很感兴趣,坚持让贵祥说出是谁。贵祥看着面目有些狰狞的李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悔说错话,当时鼓动贵祥去告状的人很多,可是他谁也不能说,“说出来了李木非治他们的事不可,说不定会治死他们的,这种事情他贵祥无论如何也不能干,他想,干了会丧尽天良的”。贵祥把所有鼓动他去告状的人都想了一遍,为了不得罪人,只有拿老婆搪塞过去。
贵祥还帮着村长老婆王学花拉了一晚上白菜,自家的白菜一夜之间却被偷得一棵不剩,本以为能博得李木的同情,但李木不为所动,坚持只能补给二亩,一分也不多给。贵祥本希望王学花替他说好话,但王学花说“可是他说他是村长,说过的话就不能改,要改就不叫村长了”。满肚怨气的贵祥到乡政府找到镇长告状,镇长李向圆在电话中责令李木尽快解决给贵祥补地的事,贵祥兴冲冲地回村,在村口看到李木手拿皮尺等着他,当着很多看热闹的村民对贵祥夫妻说:“就是告到天边我也是给你们二亩,一分一厘也不会多给你们。”贵祥说这是欺负他,李木的回答是:“我就是欺负你,你怎么着?”说完还用很轻蔑的眼光看着贵祥。“村长李木的这种轻蔑,出于对自身权力的自信。在权力等级秩序中,这种轻蔑往往会把判断昭然的事理搞混淆、弄颠倒。在作家笔下,乡村权力的极端发展让贵祥们尊严全无。”[3]贵祥对李木的不满和愤恨只有通过诸如背后用脏话骂他老婆、偷走村长家的门锁丢到井里之类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得以发泄。
村民对贵祥告状多是持看热闹的观望态度,放羊的学贵提醒他“李木的脾气可不好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有理的事多了,到头来还不都是那样,你有理也不好弄,小心一点吧”;“这么多年了,这村里还没有一户告村长的呢,我琢磨着可能是不好告,如果好告的话,还能轮到你赶上这个第一”。学贵的话深深刺痛了贵祥。贵祥虽然口口声声要去镇上告李木,但他一再找借口推迟,总说时机不合适,老婆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贵祥的心思:“贵祥,你说句心里话,是不是怕李木,不敢去告?”
可见,在已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农民的精神面貌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沉积千年的畏惧盲从权威、奴性与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依然根深蒂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改造国民性的艰巨复杂性。在由专权的村长与惧权媚权的村民组合而成的乡村政治图景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时有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张继犀利的笔锋直指当下中国乡村秩序。
三、农民法律意识的匮乏
农民文化素质相对偏低,直接影响了法律知识的接受水平。如在贵祥村里大家公认的有文化的人小胡只是一个刚毕业的中专生。法律知识的严重欠缺使不少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应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
贵祥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几近于无,更谈不上运用了。纵观贵祥的告状经历,可以用可怜、可笑、可叹来概括。贵祥进城告状很不顺利,去了三天了,连市政府的大门都没有进去,“来的时候他太乐观了,按照他的计划,第一天到,第二天见市长告状,第三天他差不多就能回来了”。市政府门口执勤武警不让贵祥进门,让他去法院告状,贵祥不死心,硬闯几次也没能成功。反思原因后,他认为是自己穿的旧西服出了问题,“他想弄一身好衣服穿上以后,市政府的大门就会不攻自破”。贵祥去批发市场咬牙花150块钱买了一身新西服,但仍被武警拒之门外。贵祥满脑子都是如何进市政府的事情,好像一个将军要去攻城一样,他有很多想法,“一条是依靠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他,就是一夜之间市政府的全部院墙忽然莫名其妙地倒塌了,四通八达,谁想进谁进,甚至有时候你不想进,走着走着一不小心也很可能就进去了;一条是神秘的力量帮助了他,就是忽然间,他具备了一种特异功能,能够把自己隐藏起来,这样他就可在市政府自由出入,谁也看不见;再一条就是他在市政府门前,忽然遇上了市长,几个站岗的不让他进,而市长却向他招了招手,他就把状告李木的事,给他说了”。这几条没有一条是正常途径,所以贵祥自己也对行动悲观起来。老婆出主意让他晚上爬墙进,躲到天亮再出来找市长,依计行事的贵祥不慎暴露后险些被送到派出所。endprint
贵祥又尝试用古代戏文中常见的到衙门喊冤的方式。包工头王建设给贵祥支招,让他找一块牌子写上“冤枉”两个字,往市政府门口一跪,“准有人过来管你的事,比找市长还灵验”。同住的农民工老刘认为贵祥穿崭新的西服去喊冤不行,“你一个喊冤告状的人穿着它太不合适,它太新了,你现在不是要好看,要场面,你得想法让人可怜你,你一被人家可怜,案子就好办了”。连贵祥进城穿的旧衣服也被老刘否定,认为“旧得还不厉害,你是去大街上喊冤告状,穿得越旧越破越好,你穿得像个客似的,就没有人可怜你的”。热心的老刘把自己的一件缝补过数次的“旧得不能再旧的中山装”借给贵祥,贵祥不忍拂了老刘的好意,上身一试大小合适,就是“太难看了,有一种回到万恶的旧社会的感觉”,老刘则一个劲地夸好,说:“正合适,也有效果,一看就像个穷人,你明天就穿着它去吧,保证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第二天由于顾虑面子问题,贵祥没好意思下跪,“他只是举着一张纸在市政府门口站着,他这种做法很像乞讨学费的小学生,根本引不起人们的关注”。垂头丧气的贵祥碰到了王建設,王建设认为问题出在贵祥没有下跪和手里拿的白纸上,说要用纸板才行,能用绳子系在脖子上,还有字也不能用墨汁写,要咬破手指用血写。贵祥嫌丢人,尤其是怕对自己颇有好感的女老板李春看到丢人,王建设一针见血地说:“什么丢人不丢人的,这城市里有谁认识你?贵祥,别拿自己当一回事了,你要真的像回事,是个人物,还会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告状?”贵祥感觉这话说到根上去了,“他贵祥真他妈的不是个人物”。贵祥进城告状已不是一种理直气壮的维权斗争,而是屈辱的、毫无个体尊严的乞求怜悯的行径。
四、转型期乡村价值观念的变化
小说以贵祥放弃告状收尾。原因很简单,他和老婆在城里找到了新的谋生手段,且收入可观。从土地被卖—被逼告状索地—进退两难留城—放弃告状,贵祥的告状史可谓一波三折。
进城告状的贵祥曾数次想打退堂鼓回乡,但老婆不许,因为面子问题:“贵祥啊,你千万别回来,现在这街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知道你到市里告状去了,这么灰溜溜地回来,不是自找难看吗!”羞于回乡的贵祥只好留在城里打工,慢慢地融入了城市生活。首先是开阔了眼界,城里的高楼大厦、宽广的马路、多彩的生活都吸引了他。在城里结识的王建设、李春等人的引导下,贵祥的观念逐渐起了变化。包工头王建设劝他:“这年头你告什么状,有告状的时间,不如想法挣点钱了。” 在王建设看来,牛贵祥告不告状无所谓,“你就是告赢了,也就二亩三分地的事,二亩三分地又能卖几个钱?你紧跟着我打工,保证比你种那二亩三分地挣得多,我一个月开你六百。”贵祥还意外地得到了开小旅馆的女老板李春的青睐,主动委身于他。李春多次劝说贵祥留在城里,贵祥先是在李春的批发部里干活,老婆找上门来,本想把贵祥带回去,但发现城市里更容易挣钱,改变了主意,也要留在城里打工。贵祥给老婆在城里租了个地方练摊,“老婆做服装生意真的有一套,没用多久摊子就摆大了”。李春看出贵祥虽对她好,但好不到与老婆离婚的地步,决定分手,并给他一万块钱,让他拿去租一个门市做生意。做起了生意的贵祥夫妻在城里有了立足之地,经济状况大有改进。
忙着挣钱开始新生活的贵祥已把告状的事抛在脑后。原先认为天大的事现在已不算是个事。小说安排了两个情节表现贵祥思想的变化:一是去给批发部进货路过市政府门口的时候,偶遇一帮进城告状的农民,信访局主任接待了他们。贵祥也动了上访的念头,因快到下班时间,值勤武警让他在市政府门口等主任。贵祥没等多久,突然想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他如果赢了的话怎么办?”他发自内心地问自己:“李木如果把地补给了我,那么,我还要回家去种地吗?他连忙爬上三轮车走了。”另外一次是拉三轮车的老刘拉到市长的一个表叔,跟他提起了贵祥的事,市长表叔答应给市长说说,并把市长家的电话都留给老刘。老刘兴奋地连忙把这个意外之喜告诉了贵祥。但“贵祥看着号码,想起了告状的事,他竟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如果不是老刘提醒,他就把这事忘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现在看这件事,怎么这样小呢?”老婆则说:“生意都忙不过来,还告什么状?再说,那地就是给了咱,咱也没法种了,也是个累赘,算了,不告了。”贵祥竟然发自内心地从侧面想到:“如果不是村长李木,咱们也不会到城里,更不会干成这个事”,大有塞翁失马蔫知非福之感,对村长竟然心存感激起来。
腊月二十八,挣了不少钱的贵祥买了大包小包年货回村过年。他和老婆徐钦娥的城里人的衣着打扮、举止做派,使他们在村里的地位发生了巨变。“从城里回来,贵祥不再是贵祥,因而村长李木也不再是原来的李木了。”他提了酒去村长李木家,举动自然随意,此时的贵祥与村长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潜意识里是高村长一等的。在村长面前,贵祥一扫先前的拘谨敬畏感,变得能说会道起来,还吹起了牛,说挣的钱一年存几万块钱没有问题。引得村长羡慕,说贵祥一年挣的,赶得上十几个村长一年挣的。村长请他吃饭,喊老婆“快弄菜,我要跟贵祥老弟喝一杯”,“贵祥给了他面子”。他还胆敢在村长家里撒尿,而且村长老婆王学花看见了也没有说他。提起当初到李木家要地时村长的凶样,李木不好意思,“别提那事了,那事我做得有点不对,后来我越想越不对,想找你说说呢,可是你又进城了”。喝着酒再次提起贵祥那二亩地的事,说:“贵祥,我给你补三亩。”李木给贵祥补地亩数的反复变化说明他的行政管理方式完全是“一言堂”的封建家长制,毫无民主可言。在村长眼里,贵祥已是城里的生意人,是其农民身份的变化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村长与贵祥原本的臣民关系被彻底颠覆,封闭的乡村权力堡垒动摇坍塌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到村长真要补给贵祥早先梦寐以求的三亩地时,贵祥并没欢天喜地地接受,反而说要回家跟老婆商量商量要不要呢,这使村长大跌眼镜。“通过到城里转了这么一圈,贵祥与以前已经不一样了。”老婆的回答更干脆:“他就是给我们补三十亩,我们也不想要了”,并感叹“你没看出来,咱在城里呆了这几天,连村长都高看我们几眼,别说其他人了。我给你说,在城里做一只老鼠都比在村里做人强”。当贵祥回城时,村长求他把女儿带到城里学做生意,他没有答应。正因如此,尽管贵祥不时有“没有了地我心里怎么有点不踏实呢?”的感叹,但乡村他是不想回了。小说结尾处贵祥夫妇带着邻居小胡一起重返城市,预示着城市化进程的势不可挡。贵祥的命运转变显然带有作者理想化的成分,但诚如沈从文给小说下的定义,是“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4]。这种表现形式是张继一贯坚持的。endprint
《去城里受苦吧!》表現了作者对当今社会转型期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的关注和思考。小说虽讲述了一个告状的故事,但读来并无多少悲凉沉重之感,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形象,充满生活气息、轻松诙谐的鲁南农村日常生活语言,使小说的整体基调轻松风趣。有论者把张继的小说称为“喜剧小说”,认为“他的小说并没有回避当前农村的各种矛盾、问题,但他同时表现了农村的变化和希望,折射出一个真诚作家的乐观情怀”[5]。小说通过村民贵祥告状的经历反映了当下鲁南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让读者清醒地认识到: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首先要更新观念,努力培养他们具有现代法律所必备的平等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逐步引导他们矫正崇权轻法的认识偏差,树立起法律权威观念;还要加大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力度,使广大农民了解和掌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和法律常识。唯有如此,才能逐步培育广大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加快中国法治化进程,真正让法律成为一种信仰。
参考文献:
[1] 刘永春.乡村之魅·女性之痛·成长之惑——近年山东青年小说家的叙事景观[J].小说评论,2009(1):72.
[2] 张学亮.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探讨[J].求实,2004(2).
[3] 孙书文.回不去的乡村——张继《去城里受苦吧》的寓意分析[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24.
[4] 卢军.从书信管窥沈从文撰写张鼎和传记始末[J].文学评论,2011(6):95.
[5] 段崇轩.历史转型期的乡村喜剧——评张继的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1997(3):40.
责任编辑:夏畅兰
A Farmers Tragicomic Complaining Story: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angjis Novel To Suffer in Town
LU 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New author Zhangjis novel, To Suffer in Town, vividly reflects the status of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 in Southern Shandong by telling the story in which farmer Niu Guixiang was forced to sue the village chief Limu for requisition of land disputes. The thoughts that power is bigger than the law are still deeply influencing many farmers. The farmers who lack individual rights consciousness are used to obeying the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 The relatively low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farmers directly influences their acceptance of legal knowledge. The novel reveals that improving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the farmers is still a big and difficult task. It also shows the authors thinking about the rural values and the profound change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Key words: Zhangji; To Suffer in Town; farmers; legal consciousness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