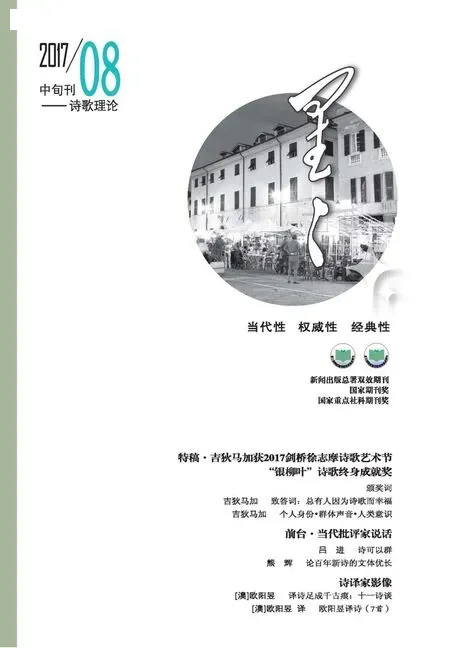穿越历史的启蒙书写
——凸凹新世纪诗歌论
2017-11-16刘波
刘 波
穿越历史的启蒙书写
——凸凹新世纪诗歌论
刘 波
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他总是离不开在语言经营、想象力探寻与历史意识的挖掘上成就一番创造,这样的诗人不需要外在地写一些空洞的诗歌宣言,也不需要画蛇添足地制造故弄玄虚的诗歌理论,他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是靠诗歌本身说话。
以作品本身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在语言的创造上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优势,在对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抒写上建构自己的诗歌王国,在对现实生活的切入与言说中突显自己的艺术个性,这正是巴蜀诗人凸凹在新世纪以来所进行的努力,他正自信地开辟着自己多年来规划与预设的精神文化领地,并逐渐迈进那种充满舒展氛围的诗歌境界。
一、语言与想象的修辞术
如果说凸凹的诗歌有什么过人之处,读之让人耳目一新的话,那首先就是他对汉语言自如的创造性运用。在历史与现实之内,语言与想象的奇妙融合,成为诗人表达经验与展现智慧的重要契机。丰富的词汇、充沛的情感、对天地自然的感悟,那种大气磅礴、浩荡如云的诗风,将诗人记忆与想象中的历史塑造成了“凸凹体”的传奇。
粗犷、奔放的情感,与紧凑的语言结合,定会获得纯粹的诗性光芒,凸凹正是这一创新的典范。他在诗歌语言上的探索,不是那种金刚怒目式的咄咄逼人,也不是那种陈词滥调式的纸上谈兵,而是在语言的表达形式上讲求一种有血有肉的言为心声,这正是诗人不断努力的所在。时而在传统的抒情里不动声色地体验生命对语言的创造,时而又在想象中完成对语言呈现出的可能性的追溯,总之,凸凹的抒写离不开对语言各种潜能的挖掘。
当凸凹在诗歌中开始梳理与排列那些闪耀着历史理性的词汇时,他所面对的,恰恰是打破汉语言长时期以来僵化的陈规,并重新建立起自己的话语谱系:跳跃的想象,真实的经验、清晰的诗性,以及明快的节奏。
“所有的太阳/降为温情的高度/满天的月华/升自国家的杯盏/幻入紫黑之夜的/是一朵思想的夏天/厚厚张开”(《牡丹谱》)。像这样的语言之旅,正是诗人在奔放的想象与透明的词语之间,所见证的艺术显现过程。祛格言化,祛警句化,是诗人在流畅而纯粹的抒写中所坚守的原则,他希望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能最大限度地包容进自己所要表达的诗歌自由精神。
“……最难的,是在爱情、亲情、友情中/把握桃花和水的刻度。而凸与凹,战争与和平/常常令平衡木无处逢源,左右为难:/‘承受挤压和误解,拒绝磨损和争夺’/是的主,是的撒旦,它必须回避祖国,接住/暗夜的流泪,用身体的盐/消解我们的错,乾坤的动荡/并再一次回到森林、内心和平衡木的平衡”。这首《平衡木》的语言,简洁自然,优雅深邃,且极富想象力。诗人豪放的性格,似乎决定了其诗歌的语言气质也属非凡:准确而不乏尖锐,松弛却又不乏力量,这就是凸凹在语言上锋芒毕露却又不失生动的缘由。
在凸凹新世纪以来的绝大部分诗歌中,其语言都是在一种敞开的氛围中得以形成的,更多的是祛除了那种过于阴郁的格调。“桃书”系列诗,是在颠覆性的想象中抒写的生命之诗,是诗人从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中走出后,所完成的对传统文化的一次解构式创新。以此看来,凸凹的这类诗歌,恰恰证实了这样一句话,诗歌是一种鬼魅的语言事业,它完全符合诗人对待词语的摸索心态。
如果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曾经说过的那句经典名言——回忆就是想象力——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得以成立的话,那么它此时被应用于凸凹的诗歌,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在发现汉语言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的渊源时,已经通过回忆和想象,深入到了诗歌话语内部新生的美学意义中,从而打开尘封的记忆之门,向心灵深处的丰富内蕴拓展。“如今/看小人书,做不了少年,只想做君子/基于对人生的认识,亦为了/把生命拉长、再拉长,我的书橱/几易其位,均端正着对小人书的态度——/记忆在应有的位置下着雪”(《小人书,或成长事》);“手电筒时态下,它依然有着白天的笨拙、/惊惶和反光。那在天空基脚处创造的/最矮的高度,最优美的曲线、/那么疾速、无声!散步、思考途中,/一个固体的猛扎/就把天空诱进逼仄的地巷”(《蚂蚁,或俯仰之角》);“白夜的主人,/一个空词,一轴宣纸,面对络绎不绝的造访者,/像一条花溪带走一个时代,带走/天南海北时间之色对/大唐的向往。八月五日,玉林往北,/日与月整体降临窄巷子。对于/逃荒的外省,避难的/动词,巷子深,酒更香,诗比蜀道难”(《致翟永明,或新白夜酒吧开张志庆》)。这些随手拈来的短句子,平实而有力,自由而富个性,其中并没有故作深沉的低调,也没有高深莫测的玄奥,诗人只是在语言上服从自己的独立想象,不论是纵横驰骋的情感撞击,还是左右逢源的内心言说,都是诗人在挑战语言规范时的艺术期待。
其中i=1,2,…n,表示矩阵的行,n表示将每天划分的时间段,j=1,2,…,m,为矩阵的列,m为一周上课的天数。Xi,j是一个整数向量,表示排课基因。
“我是悲伤的。上山,石经寺一支香烛:想象/而且幸福——愿意平地起风,请年轻的香/溯风而上,异地把风换取,或者索性/成为病风中肺部的乌云、黑夜/被闪电击溃,下一场淫雪、甘霖。再次的风/这一切,只与风的胎脉有关,只与/火车、咯血、强打精神的另一场夜风的肋骨/有关。”这首《穴书,或再次的风》是诗人“闻身患绝症的父亲咯血”而作的,即便是如此的带有悲悯意味的抒写,诗人仍然没有忘记对语言进行创新,他在这里通过词语的非常规组合,所唤醒的正是被我们遗忘的那些与生命相关的人性思索。
凸凹所进行的语言实验,与那些热衷于纯粹口语或书面语写作的诗人不同,他不是靠走极端或赶潮流获取惊喜的喝彩,也不是通过铤而走险玩虚招赢得青睐的目光,而是自觉地深入到历史、文化与现实情感的内部,将语言创造与艺术想象、自由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具匠心的“凸凹体”诗歌风格。
二、打开“历史”的理解空间
当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开始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打量中国的传统时,其实这种书写的风气早在诗歌书写中就被传播,而抒写历史与传统文化,又自然地成为凸凹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的主导。凸凹的此类诗歌抒写,在其极富想象力的语言中,完成了大气的精神流转,尤其是那些把握俗常生命的意念、对现实与虚无之存在性的探寻、消解历史背后呈现的内心变幻等,都无不体现出诗人驾驭历史的能力。
在面对历史遗留的文化古迹时,凸凹恪守着一种探寻真相的信念,他在诗歌中所渗透的智性,是历史理性与生活感性的有效结合。他凭借着这种信念,将历史抒写的空间慢慢扩展,从而激活了那一片埋藏心底的精神气场。
历史的瞬间,在凸凹的笔下拥有了阔大的思想内涵,因为他是用那些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建构起了他心目中的文化中国。适量的考据、丰满的细节和文学的记忆,共同构成了一部历史诗歌的传奇。尤其是诗人将对历史想象的空间留给我们去检验时,他那不加掩饰的优雅的话语风度,恰恰给我们带来的是乐观而亲切的文化期待。
诗歌中的历史,不仅仅呈现出的是那些富有趣味的细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的深度,它们所具有的永恒性,应该是能持久的,而不是那种沉迷于时尚、转瞬即逝的史料碎片。在此方面,诗人有着足够的自信,他要用历史与传统文化建构起一种足以融合现实的力量。
与死去的灵魂对话,总不免含有几分感伤与悲悯,这是绝大多数诗人与历史写作者所常遇的精神处境,所以,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是绝大多数涉足历史题材的诗人所面临的困境,对于此,他们需要突围。同样,凸凹也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死的历史,活的理解,诗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从僵死的区域与制度中走出,用自己的灵性与智慧,以改变那些似是而非的历史陈迹,以获得一种新鲜的个人眼光。
凸凹对待历史的方式是动态的与现场感的,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历史与传统文化在诗歌的意义上获得一种诗性的力量,他采取的是抒写现场加想象和回忆的思路。“南方在茶来马去中获得粮食、鸟语和丝绸/而站在路边的观音院,让喘息声/急遽跳动的梦,变得平顺、不远/和石头一样安宁——没有谁/能赛过石头的奔跑、歌声和绵绵的穿透/没有!今儿是冬至吧,你看那些古道上的胡夷/一下子全无:他们正在石头内心——那辽阔的草场/架火、啃羊、拚酒,把冬天吼开”(《临邛怀古,或南方丝绸之路咏》)。诗人对历史的这种动感的、文学化的抒写,是建立在他对历史的一份体悟和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之上的,遥远的过去已成为记忆,历史的真相已变得模糊,它们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或柔情、或粗犷、或光怪陆离、或和风细雨的文化命题,诗人的追思与怀古,都是在貌似随意的松弛中赋予古人与史迹一份生动和韵味。
当一些诗人带着苦难的面孔对历史进行凭吊时,他们的抒写大多会含有悲怆的意味,而与此相反的是,凸凹的历史抒写,却带着几分激进和闲情。他不是被动地为历史所裹挟,而是主动地成为把握历史的智者。他用行走与观赏的方式,将历史古迹、传统文化与野史趣味充分地融合了,以让自己的抒写获得一种浪漫气质与历史深度。
凸凹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兴趣,是敞开的,是回旋的,他有自己理解历史的态度,也有自己把握历史的性情。古人的孤独与寂寞、史实的玄妙与吊诡、细节的生动与迷人,都在他汪洋恣肆的语言才情中跃然纸上。那种信马由僵的笔触,始终环绕在对历史风云变幻的洞察里,让人愉悦,也让人感慨,让人恍然大悟,也让人心悦诚服,总之,他对历史的描摹是带着开阔的、整体性观照之感悟的。“在邛崃,五代十国的记忆/只能是一个村庄的记忆:是火井镇银台村/一截唐碑,一棵井壁草的记忆。村姑黄崇嘏/更适合把蜀国相府当村庄,更适合让/牧羊的声音,把草坡变为宣纸,把/《全唐诗》变为牧场。但她是含羞的、保守的:/不像文君姑娘,只为一个人,就做出了/令天下名士欢呼的举动;只为一个人,就把/邛崃变为一座空城——留给乡人黄崇嘏的/惟有贞节这份遗产。”(《灯下读史,或遥想崇嘏山一位女诗人》)。诗人在此将邛崃才女黄崇嘏与卓文君进行了对比,这种历史人物的对比法,恰恰彰显出诗人对于历史的一份理性的态度。他在找寻与复原古人精神轨迹的过程中,以一种和历史记忆对话的方式,言说了历史本身的吊诡与玄妙之处,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史识气韵。
“大观镇志”、“丁亥秋记,或手艺坊”、“中原八记”、“桃书”等系列组诗,以及《登滕王阁,或文化履》《登黄鹤楼,或中年议》等怀古诗,都是凸凹与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精神对话的结果,它们让诗人从历史的边缘回到了敏感的内心,回到了对生命本真的思考与倡扬的热情里。
三、现实话语的创造性转换
如果说凸凹对历史与传统的抒写得以形成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并进而建构起他涉笔成趣的“凸凹体”的话,那么这应该得益于诗人以行遍华夏的方式所获得的丰富经历。
而除了历史与传统文化的题材,凸凹对现实的书写,让常人读来更觉得有力度。诗人对于现实的抒写,大都是以行走和寻找的方式完成的,他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诗与现实的距离,并大胆地作出了自己的回应。行走、历史与现实,是诗人在心灵经验之外,所能参与的人生体验的全部涵义。
凸凹的性情适合于这种行走,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既仁且智者,山水皆爱。而对于人,诗人则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笔力,不论古人,还是今人,不论是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与己无关的前人与来者,他都从不隐藏自己宽容的情怀。
从历史走向现实,从静态走向动态,是诗人针对当下现实所作出的最为自觉的视野转换,那些山、水等自然景观,以及人、史等人文精髓,都成为诗人关注的对象。像《后桃花,或去昭君墓的途中》《内蒙纵马,或草原旅游记》《从石经寺到塔尔寺,或宗喀巴大师》《去腾格里沙漠,或玩沙》《厦门,或初入闽地》等,都是诗人在旅行或观光的途中所生发出来的心灵感悟。它们是诗人用行走的方式完成的叙事,是他对历史、文化与现世生活的一种个人感怀。
这种感怀是自由的,是启蒙的,是创造的,并不拘泥于什么既定的规则与范式,像“临邛八记”系列组诗,就是诗人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突破性描绘。《车出平乐,或车顶上的柳叶》《芦沟,或竹巅上的古镇》《谒茶,或骑龙记》《无题,或夜宿天台山》《平安夜上游,或放灯书》等诗,都是诗人在临邛这一历史古城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凸凹以他个性化的潇洒姿态,将遥远的历史记忆与自身所处的当下现实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或切入现实,或旁征博引,以期描绘出大气而开阔、且意境深远的话语经验,这种经验让人品咂,让人回味,让我们有足够想象与表现的回应空间。
当我们看到诗人在行走中对每一片风景作出迷人的演绎时,诗歌本身的价值才显得弥足珍贵:“从微醺的昌明河畔,折进/雨后的李白馆。黑黬黬的夜空酝酿着/中秋翩临,罗裙突然下滑/露出唐时的白。间密的疏竹丛没有明月的清影/,只有明月的声音。睡在/明月村右厢房,想起一九八九年/在此写下《大师出没的地方》”(《中秋前夕,或夜宿明月村》)。这是诗人在中秋前夕一个雨夜进入李白纪念馆时的情形再现,此时没有潮流和时尚,有的只是诗人对当下与李白所处时代的交叉怀想,这首诗所流露出的,就是诗人从现代进入古代、又从古代回到现代的一种回环复杂的心绪,这是古人与今人之间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对话,富含历史的沧桑与对现实的认知。
用现世与历史的交织来抵抗精神的贫乏,以激活隐藏于内心里那些潜伏的诗歌能量,这是凸凹在体验历史与现实这双重经历时,所能完成的人生诗化的超越。除此之外,他则是在对现实事相的描述与追踪里,自觉地承担起了重建生活可能性的责任,而这需要诗人倾注全部的心力。创作于2007年的“父亲死亡书”与创作于2008年的“历震札记”系列组诗,是诗人对亲情、死亡与灾难等现实最淋漓尽致的抒写,它们带着诗人真挚的情感和悲剧性的体验。此时的诗人从历史与文化中走出,进入了生活最为真实的状态,他没有文化论争的高姿态,没有“历史言说”的质疑,有的只是一种平易的诉说,一片关乎生活本身的心声。
“两个多月奔走的,不是两公里山坡,/而是你七十八岁的距离。/现在,我,还在奔走的路上,离你/此生桑榆,尚有三十二年风雨。/走在乡间农历,/每一次上坟,都是一次还乡记:/我还乡着我的肉身,你还乡着你的生气。/我们在阴阳两界奔走,一个上山,一个/下山,不说话,忍着讳忌。/有一次,医生说,我热伤风了。于是/决定把上坟时间,挪到翌日——/哪知,当晚我就去了坟山:梦中/全是冷汗、稀泥!此刻,想着/一篇小说与另一篇小说的互文关系,/虚构和美,竟成为惟一败笔”(《上坟记,或去岁11月26日以来》)。这是父亲去逝后,诗人去给父亲上坟时所回忆的情形,他与父亲在阴阳两界的对话,真正突显了诗人此时悲戚而又矛盾的心境,这其实正是现实为诗人带来的审视和反省生活的资源,他在现实与回忆的叠加中,让父子亲情获得了一种永恒的延伸。
当然,最令诗人在现实遭遇中感慨万千的,当属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因为诗人是四川人,灾难发生时,他正身处险境。所以,对于地震发生及其后来的一切,诗人是亲历者,也是旁观者,这双重的身份,让他在这种悲愤与凄惨交织的氛围里,不断地发出自己独特的呼声:“今年的五·一二,护士们/我要你们关注我的成都、我的汶川/我要你们把地球搬上手术台/为它刮毒、割瘤,排放邪恶和隐灾/我要你们在下午两点二十八分以前完成这一切/护土们,我要你们让时空倒转,要你们/谅解一个诗人的梦呓、荒诞和盐浸的诘难/我要你们必须,也只能这样过节!”(《荒诞书:护士们》)这只是呼声中的一个细节,这相对于地震的残酷现实来说,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诗人的呼声却是凝聚了他那时所有的力量与情感。尤其是在那种特殊的灾难时刻,诗人所说的一切,都是含血带泪的,没有做作与虚假的成分,它们是诗人贴着良心写出的文字,可谓明心见性之作。
如果说诗人对去逝的父亲和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有着痛彻骨髓的怀念的话,那么他对自己健在的母亲的那种感情,则有一种超越现实的亲情之力。凌晨五点,诗人到火车站去接母亲,这引起他创造性的联想:“理想的浪漫,就算抵不了现实的残酷/我也要被你掀起的速度,与火车的速度/两两相冲,让你能安静地睡会儿——最多/在梦中,想想离世的丈夫,和三个健在的/儿子,正如我在龙泉驿的梦中,想到你——/想到你在旺盛之龄,完成的生命/分解:我是一个你,二弟是一个你/三弟是一个你。你把自己三等分/让每一等分自由奔走,顾此失彼。”(《去火车站,或凌晨接母》)。这是诗人对于当下幸福生活的回应,因为母亲的健康,她的行走留给儿子的,必定是一种难得的情感慰藉,而这正是诗人在敞开的生活背后,像对待自然与古人那样,所写出的颇见性情的文字。
凸凹在行走与感悟中寻找到了自己对于现实的理解。他那自由的精神革命与深邃而又不乏锐利的思想批判,让他的诗歌在介入现实的层面上力透纸背。这样的创造性转换,则是凸凹在历史与传统文化表达之外,所能获得的另一种更富潜力的抒写路径。

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